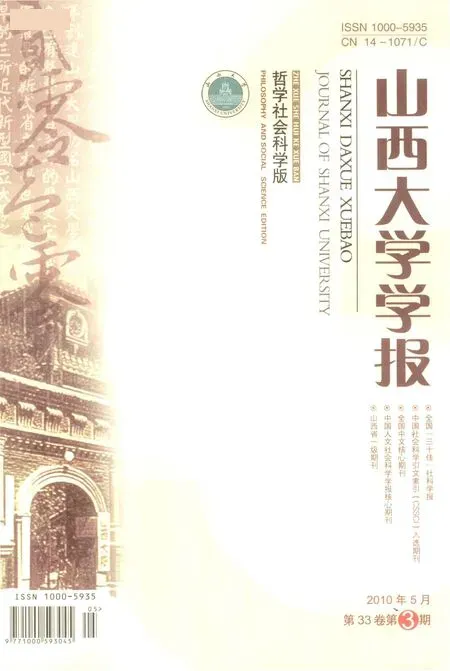误读鲁迅 :赞者的缺失
——鲁迅《青年必读书》阅读札记杨华丽1,2
(1.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2.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误读鲁迅 :赞者的缺失
——鲁迅《青年必读书》阅读札记杨华丽1,2
(1.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2.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在鲁迅解读史上,《青年必读书》事实上成了所有试图全面解读鲁迅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结”。相较于反对《青年必读书》、反对鲁迅的观点而言,我们尤其应该警惕的是那种表面上对其表示赞同,实质上却滑向了反对者的泥潭的观点。这些赞同的理由由于对材料的隔膜、理解的偏差,等等,同样是对鲁迅及其《青年必读书》的误读。将《青年必读书》置于 1925年的时代语境及鲁迅这一时期思想、文化观点的系统之中来进行读解,文章认为,鲁迅在文中所说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是一种策略化言辞,而是他生命中痛苦的文化体验的外化。
鲁迅;《青年必读书》;理解
在鲁迅解读史上,《青年必读书》事实上成了所有试图全面解读鲁迅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结”。当我们仔细去考究那些赞同与反对的意见时,却发现一个现象:有些反对的理由并没有越出鲁迅当年批驳过的范畴,而有些赞同的理由却因为对史料的忽视、理解的偏差,等等,而成为对鲁迅的另一种误读。这种并不入木三分的“骂”,和这种多少有点隔靴搔痒的“赞”,都是对鲁迅及该文的误解,并未能将我们对其的认识引向深入。
相较于反对《青年必读书》、反对鲁迅的观点而言,我们尤其应该警惕的是那种表面上对其表示赞同,实质上却滑向了反对者的泥潭的观点。曾有学者发出如是感慨:“关于这次论争中鲁迅的观点,至今少有正面的肯定或赞同。时至今日,中国更流行的仍然是鲁迅的论敌们所持的观点。”[1]仔细阅读关于这次论争的研究文字后我们会认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关于《青年必读书》,关于此前此后的鲁迅,赞同者们在无意间做了太多误读与曲解。这种“无意”,一方面反映出我们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的偏差,以及对研究史料的相对忽视,另一方面,从客观效果上来说,这种“赞”者,事实上倒成了曲解或诋毁鲁迅的“骂”者的帮忙或帮闲。所以,笔者以为,对赞同的诸观点进行详细分析,是实现理解鲁迅及其《青年必读书》这一目的的、更应该加以重视的一个任务。
一 误读原因之一:对史料的忽视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充满了对史料的轻视。我们常常不尽量去充分阅读原始文献,就想当然地发言,并自以为真理在握。在《青年必读书》阅读史上,有好些赞者的误读就因了其对史料的隔膜。
比如,有论者说“在参加开列书目的选者中,对鲁迅表示明确赞同的有徐炳昶、罗德辉和赵雪阳等人”[2]。说徐、赵两位赞同鲁迅是对的,但罗德辉则不然。因为,罗德辉的信件中涉及鲁迅的文字如下:“鲁迅先生最能观察深刻,他还肯说良心话:‘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同时又明知道交白卷不好,忙在题外讲了几句看书的方法。老实说‘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说法,万万使不得,别要去上当!”[3]这哪里是对鲁迅表示赞同呢?!
又如,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说过“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于是有人认为“在鲁迅看来,青年读中国书的作用和目的就在于学会‘作文’”[2]。这一说法,和《庄子》与《文选》之争中的施蛰存,将其当成鲁迅“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的证据,并引申说鲁迅“承认了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是多么相似!当年,对于施蛰存的随意引申,鲁迅就做了如下解释:“这是施先生忽略了时候和环境。他 (指鲁迅——引者)说一条 (即前所引‘少看中国……’)的那几句的时候,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犹言即使恰如他们所说,也不过不能作文,而去读古书,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4]可见,鲁迅并不认为青年读中国书的作用和目的就在于学会“作文”,而且在当时,他对这个可能的效果深恶痛绝。如果我们关注到这则史料,兴许就不会在这点上误解鲁迅了。
此外,我们知道,1925年的周作人和鲁迅已经失和,此时他们的思想观点也已经有了不小的差异,但并不意味着在“青年必读书”事件中二人的观点会绝对悖逆。可是有人涉及周作人时并没有仔细阅读相关材料,就想当然地阐述道:“在鲁迅之前,周作人也于 1925年 2月 14日在《京报副刊》上开了一个书目,……隔了几个月,他又撰写一篇《古书可读否的问题》,有可能是针对鲁迅而发:‘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5]312查《京报副刊》可知,《古书可读否的问题》署名易金,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①该文后被收入《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收入该文集的文章与《京报副刊》所刊载文字略有不同,但作者本人的思想完全一致。。但在该文中,周作人并未说过论者所引的话,此其一;其二,通观全文,周作人的观点和引者所想表达的观点不是相合,而是恰恰相悖。因为,《古书可读否的问题》开头两段的文字是:
我以为古书并非绝对的不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会读。②《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所收《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一文的开头两段文字是:“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可见,和当初发表在《京报副刊》上时的差异之处有二,即“绝对的可读”和“并非绝对的不可读”之间,“强迫的令读”和“强迫的会读”之间。笔者倾向于认为,第一处差异是周作人在编辑文集时做出的修订,第二处差异则可能是《京报副刊》当年在刊载时出现的失误。
也就是说,在周作人眼里,回答古书可读否的问题需要知道两个前提:读的人是否“通”以及读的人是否是被迫的。接下来,周作人在分述第一个问题之后说“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也就是说,读的人无法达到“通”的程度——第一种假设的前提不成立,因此其结论就是“绝对的不可读”。紧接着,周作人引述了某君公表的通信里涉及的《群强报》中强迫学生读四书五经的一节新闻,最后说“那么,大家奉宪谕读古书的时候将到来了。”也就是说,被强迫读古书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说,“然而,在这时候,我主张,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全文想要表达的意思,恰好是古书绝对的不可读,而非引者所谓“古书绝对的可读”,而这一观点,恰恰与鲁迅《青年必读书》中的观点相呼应而非相背离!
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在这时候”以及“我主张”这两处表达。前者体现了周作人对时限的敏感,后者体现了他对这一主张的个人性的强调。也就是说,在周作人眼里,“古书绝对的不可读”这一结论并不是放之任何时候,任何人那里而皆准的真理,他更无强迫他人服从他的主观意图。而这,与鲁迅答卷中对“现在”的强调,以及“我以为”的表述方式,恰好相通,而其附注中所有被人目为“偏激”的文字,都仅仅是他在“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全无训导、教训的主观意图。也就是说,从观点、姿态到发言方式,周作人正和鲁迅交相辉映,而非其他。
二 误读原因之二:理解的偏差
此外,对鲁迅及其《青年必读书》,我们尚存在不少理解上的偏差。下面择其代表观点进行分析。
(一)潜在读者问题
进行否定式阅读的人,大多忽略了鲁迅答卷存在潜在的倾听对象这一事实,而直接将鲁迅“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判断,进行批驳。而历来的赞同式解读中,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其潜在读者是一般青年,一种认为是某种或某些特定的青年,其中,后一种占据上风,而艾斐、张永泉是其代表。
艾斐的论述充满激情,但《青年必读书》真的是针对“胡适等人”、“类似《青春之歌》中余永泽那样的青年老夫子”、“置民族命运于不顾、一心只啃故纸堆的纯学究派”、“已经读了许多中国书、而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新潮抱冷漠态度的青年”[6]而写的吗?恐怕不是的。且不说鲁迅此时是否关注到了“余永泽那样的青年老夫子”,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新潮抱冷漠态度的青年”,即便鲁迅回答“青年必读书”的问卷时想到了胡适等人,其潜在读者也应该是那些受其“整理国故”思想影响而不与“实人生”接触的青年,而不是他们本身。
那么,什么青年呢?张永泉认为是“那些有志于社会改造的青年。”[7]而其依据,则来自鲁迅所说的“那时的聊说几句话,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或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8]。曹振华则认为将“或一种改革者”当成鲁迅读书主张的特定实行者是错误的,在她眼里,他们只是鲁迅心中的“同道,即在青年读书问题上与自己持相同意见者。”这是非常睿智的一个结论。但随后,曹先生以《〈呐喊〉自序》中的启蒙对象为例,判定“《青年必读书》的对象也不该只是青年改革者,而应为一般青年。”[9]
笔者以为,张、曹二位先生的判断均存在偏差。如果我们细读鲁迅所填表格的形式、内容,并联系鲁迅此前此后的思想、文字以及其他学者名流尤其是江绍原、俞平伯的答卷来进行分析,将对鲁迅《青年必读书》的读者有新的认识。
鲁迅所填的表格分为两栏。一栏本为“青年必读书十部”,鲁迅将其“十部”删去,然后填了“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十四个字。删掉“十部”字样,首先是因为鲁迅并不会开列任何一部书名,“十部”实无存在的必要;此外,这个改动事实,意味着鲁迅对该栏题目曾加以特殊注意,对“青年”“必读”“书”这些关键词,有过慎重的思考。而其思考的结果,和江绍原一样,是也“不相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智识’”[10],和俞平伯一样,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样”的鲁迅,也“绝未发见任何书是大家必读的”[11],遑论制定十部书!所以鲁迅所填写的那十四个字,是针对一切青年的,又由于对“所有青年的必读书”这个问题之荒谬性的感知,加上他一贯所有的拒绝给青年瞎指路,当精神导师的思想,鲁迅才写下了那些字,这和江绍原在“青年必读书十部”栏填“wanted”,俞平伯径直将“青年必读书十部”栏去掉用意相当。
但鲁迅毕竟在附注栏里填写了那么多文字。那么,这些文字的潜在读者是否也是一切青年呢?且让我们来读鲁迅在《聊答“……”》中的自我陈述:
我那时的答话,就先不写在“必读书”栏内,还要一则曰“若干”,再则曰“参考”,三则曰“或”,以见我并无指导一切青年之意。我自问还不至于如此之昏,会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样。那时的聊说几句话,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和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8]
这段话共三句。第一句告诉我们,鲁迅真正想答的话不在“必读书”栏内,而在附注栏里,而附注栏所填内容中的“若干”、“参考”、“或”等字样,不是对“一切青年”的“指导”,这一方面说明他在“必读书”栏所填的内容是针对一切青年的,另一方面则说明他附注栏的言说对象是特定的。第二句表达的是他对“青年必读书”之“青年”的理解,并可作为他在“必读书”栏里为何那么填,在附注栏里为何要特意用“若干”、“参考”、“或”的解释。第三句表面上表明了鲁迅言说的潜在读者是“或一种改革者”,其目的则是“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诚如曹振华先生所提醒的,这一表述逻辑和《<呐喊 >自序》中鲁迅声言自己不免呐喊几声,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存在相似性,但和曹先生的解读不同,笔者以为,在《<呐喊 >自序》中,鲁迅与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不是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关系,他们都属于启蒙者阵营,他们共同面对的一般民众,才是他们共同的启蒙对象,而鲁迅创作《呐喊》,首先希望得到的呼应来自于内心有着变革需求的民众。对于《青年必读书》来说,鲁迅在第三句中所表述的他与“或一种改革者”的关系,也不是导师与被指导的青年的关系,而是以文字提倡“行”重于“言”、注重改革者与以实际行动实践着“行”的改革生力军之间的朋友关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至于鲁迅《青年必读书》附注栏的潜在读者,不是那些行动着的改革者,而是与那些改革者以及鲁迅的心神有着相通之处的青年,即附注栏里所谓的“若干读者”。这“若干读者”,来自“一切青年”之中,而非全部。
换言之,鲁迅《青年必读书》的读者是分层的:“必读书”栏的回答针对于一切青年,而“附注栏”的言说针对的是“若干读者”,即可能成为改革者的青年。鲁迅在两栏中的不同回答,综合起来,恰好就是他对“青年必读书”这一问题的全面回答,只关注其中任何一栏里的内容,都会误解鲁迅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
(二)偏激与策略问题
其实,在赞同鲁迅的诸多观点中,最流行的思路是总体肯定鲁迅的主张而又指认其观点属于愤激之辞,并且将这种偏激的姿态解释为一种策略,李国文[12]、徐雁平[5]、房向东[13]、张永泉、冯光廉等都如此。其中,张永泉和冯光廉的观点很具代表性。
张先生认为,鲁迅的偏激是在新文化运动退潮后的特定背景下,为回击文化复古派强大的复辟逆流这个任务,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特定时代背景特定历史任务所要求的特定策略”[7],冯先生则说,“正是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出发,为了充分唤起国民对改革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的体悟,鲁迅确定了自己的策略原则:激烈决绝,鲜明刚劲,以期振聋发聩,促人深思猛醒。”[14]强调鲁迅是“偏激”的且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是二者的共同点,尽管为何要这样,二者论述的重心稍有差异。他们二人都认为,鲁迅五四前后的大量言论,如他把中国传统文艺说成是“瞒和骗的文艺”,将中国文明视为“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等等,正是这种策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并且他们更进一步,推广至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所具有的共性上,一者说“时代要求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不得不牺牲理论的完整性而把倾向的鲜明性放在第一位,要求他们不得不采用近乎绝对化的语言,片面性的表达来申明自己的理论主张,捍卫自己的思想原则”[7],一者引用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关于开窗与拆屋顶的比喻来说明激进的必然性①。张、冯二位先生的论述思路,正和绝大部分论者的相似,即,首先肯定鲁迅是偏激的,其次认为这种偏激是特定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策略,再推而广之,至于鲁迅五四时期的言论,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的言论,认为他们那一批人在那个时期都具有偏激特征而且这种偏激都只是一种策略。这种思路承认了上世纪 70年代末期以来学界对新文化运动具有激进特征的指斥,而为了维护新文化运动的合法性,就运用“策略说”来勉力招架。
笔者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的种种言论是否偏激,以及其是否属于策略性的选择等问题,不在此处展开讨论。只是认为,似乎万金油似的“策略说”未必适合《青年必读书》中的鲁迅。笔者认为,与其说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所说的“经验”是一种策略地说出的“偏见的经验”,不如说那些“经验”来自鲁迅自身的生命体验:一个深中中国古书之毒,却又忧心于中国未来文化之建设的先觉者,在时代与文化的夹缝中清醒地体验到的生命的痛感。
三 《青年必读书》:生命痛感的外化
与《青年必读书》相关,鲁迅体验到的生命的痛感主要是两方面的:(一)中国古书的痼疾;(二)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严峻和“赤子”的稀少。
(一)中国古书的痼疾
鲁迅对于中国古书的痼疾的感知,最鲜明的体现有两处。一是他因赵雪阳《青年必读书》而写就的《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中的文字: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们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二是他在《坟·后记》中所说的:
我觉得在古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多年痛苦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
因喝酒伤了肠胃而劝青年不要喝酒,和因读中国书中毒而劝青年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其思路是一致的,也就是赵雪阳所谓“试过的此路不通行”后的“宣告”,这“宣告”的背后,是鲁迅中毒的代价,一如他劝青年不要喝酒,是以自己肠胃受伤为代价一样,是鲁迅用多年痛苦的生命经验换来的“真话”,而绝非“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亦非策略。
对这种痛苦体验的表述,《鲁迅全集》中有很多。1919年,鲁迅在致好友许寿裳的信中,就如是说:“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 ……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15]; 1925年,鲁迅很集中地谈到了他对中国古书的痼疾的深恶痛绝:“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16]“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17]。在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论述了朱希祖对假名之非难事,并说“此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之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看中国之书者也!”[18]所以,鲁迅认为,解救“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方法,“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意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19]。读外国书,学洋鬼子,就是“另开”的“药方”,即“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16];1926年 1月 25日,鲁迅说“菲薄古书者,唯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20];1927年 2月19日在香港青年会演讲中,鲁迅又进一步把提倡读经称为唱“老调子”,“生在现今的年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了”[21];1929年,鲁迅在其译作《近代美术史潮论》卷首写道:“倘只能在中国而又偏要留心国外艺术的人,我以为必须看看外国印刷的图画,那么,所领会者,必较拘泥于‘国货’的时候为更多。——这些话,虽然还是我被人骂了几年的‘少看中国书’的老调,但我敢说,自己对于这主张,是有十分确信的。”……可见这些年里,鲁迅对“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认识和坚持是一如既往的,而这种观点的获得,来自他几十年生命历程中的阅读体验,而绝非为了造成某种轰动效应,故意发出的“厥词”。
(二)中国社会现实的严峻和“赤子”的稀少
为什么要如此坚持这种观点呢?这和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即开始形成的“立人”思想有关,更和他对 1925年前后的中国是个“活埋庵”的观察与体认有关。他说:“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22],而且更可怕的是,27年过去了,“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其时的赵雪阳认为“这几年以来,各种反动的思想,影响于青年,实在不堪设想;其腐败较在《新青年》杂志上思想革命以前还甚”[23],涤寰则说“中国的社会情形,政治状况,尤其是思想界——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一切的传统的思想,不但没有打倒,且更显蒸蒸日上的现象了”[24],等等。
怎么办?鲁迅认为,中国当时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25],也就是说,必须改革。因为,“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25]不改革,即便“大同的世界”到来之时,“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警惕于被赶出世界,不能生存,鲁迅认为“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18]而这种踏倒所有阻碍前途者,进行改革的任务,天然地落在青年的身上①他说:“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谁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将反抗他,扑灭他!”(《华盖集·北京通讯》,见于《鲁迅全集·第 3卷》)。为此,他呼吁“赤子”的出现,认为人们应该如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而不是如那些保古家一样,弃赤子而抱千金之璧[25],他希望有行动能力的,思图改变沉寂现状的“活人”、“勇猛的闯将”、“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勇士能够出现,从这个整体设计出发,他立足于中国古书毒害了他的体验,希望自己成为历史的中间物,肩住毒害他的黑暗的闸门,而放中国未来的希望——有志改革的青年、赤子——上前去,弃绝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从而与实人生接触,在坚决的“行”中砸烂铁屋子,毁坏做人肉的厨房。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笔者以为,当我们将《青年必读书》置于鲁迅的整个思想、文本系统中去理解,我们就会认识到,鲁迅在该文中的观点,其实是他立足于作为中国古书的中毒者的痛苦体验,心忧于中国文化之未来,而发表的真知灼见。这些思想,和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即已萌生的人学思想密切相关,和他整个生命过程中孜孜矻矻追求的人国理想密切相关,这种源自生命痛感的文字,当然并非他一时的冲动或者愤激之语,也并非为了达致某种轰动效应而刻意采取的一种策略化的言说。
[1]李新宇.鲁迅的选择[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201.
[2]刘 超.读中国书——《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求书目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2004(6):115-120.
[3]罗德辉.青年必读书·罗德辉先生选[M]//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4]鲁 迅.准风月谈·答兼示[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77.
[5]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12.
[6]艾 斐.忌“虚无”而戒“盲从”——对鲁迅“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的认识与阐释 [J].鲁迅研究月刊,1996(7):11 -15.
[7]张永泉.鲁迅文化批判的历史意义[J].鲁迅研究月刊, 1996(3):5-14.
[8]鲁 迅.集外集拾遗·聊答“……”[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8.
[9]曹振华.我们从“青年必读书”读到了什么[J].鲁迅研究月刊,1999(4):15-23.
[10]江绍原.青年必读书·江绍原先生选[M]//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7.
[11]俞平伯.青年必读书·俞平伯先生选[M]//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53.
[12]李国文.从“青年必读书”谈起 [J].语文建设,2001 (10):28-29.
[13]房向东.鲁迅与他“骂”过的人 [M].上海:上海书店, 1996:67.
[14]冯光廉.鲁迅“全面彻底反传统”论质疑——鲁迅与传统之一[J].鲁迅研究月刊,1999(11):12-17.
[15]鲁 迅.致许寿裳 190116[M]//鲁迅全集·第 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9.
[16]鲁 迅.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M]//鲁迅全集·第 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48.
[17]鲁 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M]//鲁迅全集·第 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8]鲁 迅.两地书[M]//鲁迅全集·第 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9]鲁 迅.华盖集·忽然想到 (十一)[M]//鲁迅全集·第 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2.
[20]鲁 迅.古书与白话[M]//鲁迅全集·第 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1]鲁 迅.老调子已经唱完[M]//鲁迅全集·第 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5.
[22]鲁 迅.华盖集·通讯[M]//鲁迅全集·第 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3]赵雪阳.青年必读书[M]//鲁迅全集·第 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76.
[24]涤 寰,平 平.青年必读书的疑问[M]//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15.
[25]鲁 迅.华盖集·忽然想到 (5-6)[M]//鲁迅全集·第 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
M isinterpreting LU Xun:Approver’sM issing——A Reading Notes of LU Xun’sThe Youth M ust Read
YANG Hua-li1,2
(1.College of L 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064,China; 2.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M ianyang N o rm al University,M ianyang621000,China)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LU Xun,The Youth M ust Read,in fact,has become a"knot"for everyone who attempts to gain a full interpretation of LU Xun. In contrast with the disapproving view ofThe Youth M ust Read,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view which appears to be approving but,in essence,has slide into the mire of opponents.These approving views are also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LU Xun because of theirmisunderstanding of the materials,their deviation of understanding,etc.If we placeThe Youth M ust Readin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in 1925,and in the system ofLU Xun’s thinking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during this period,we’ll believe thatLU Xun’s view in the textThe Youth M ust Readis not a tactic of rhetoric,but the pain of his cultural experience in his life.
LU Xun;The Youth M ust Read;understanding
book=39,ebook=253
I210.97
A
1000-5935(2010)03-0039-06
(责任编辑 郭庆华)
2010-03-09
杨华丽 (1976-),女,四川武胜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① 读其原文,那是鲁迅在陈述白话文的风行与文学革新的提倡以及钱玄同废止汉字的提倡的关系时,打的一个比方。我以为,我们不能将钱玄同提倡废止汉字作为一种策略来理解,就他们而言,当年的他们如此提倡,是真诚的,而且在鲁迅、钱玄同等看来,这本就是很普通的变革主张。“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鲁迅的这段话,我以为,更不能作为策略说的证据,因为,鲁迅的这话,其实是他事后对中国人人性的分析,更重要的是,鲁迅、钱玄同、吴稚晖等所说的我们以前目为偏激的言论,其实都是他们的生命体验所致,而绝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种策略。(参见《鲁迅全集·第 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