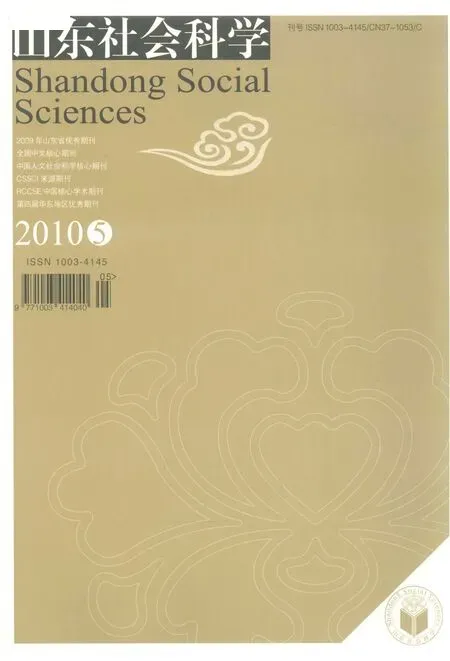“报春的燕子”与“啼唱的夜莺”*
——舒婷、翟永明的诗歌艺术
张晶晶
(山东政法学院新闻传播系,山东济南 250014)
“报春的燕子”与“啼唱的夜莺”*
——舒婷、翟永明的诗歌艺术
张晶晶
(山东政法学院新闻传播系,山东济南 250014)
舒婷与翟永明在上世纪 80年代的女性诗坛上树立了两个高度。但两人的诗歌艺术迥异:在诗歌形式上,舒婷表现为理性雕琢,翟永明表现为感性喷发;在诗歌气质上,舒婷表现为情感的吟唱,翟永明表现为生命的独白;在诗学追求上:舒婷是为人写诗,翟永明是针对自身。两人不同的诗美品格不仅丰富了当代诗坛,被后来的诗人们纷纷仿效,而且对诗歌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女性诗歌的未来也有重要的启示。
诗歌形式;诗歌气质;诗学追求;舒婷;翟永明
舒婷作为“朦胧诗”的中坚,以其诗意的简明、语言的精致、形式的整饬、情感的强烈,在当代诗坛一度独领风骚;而稍后的翟永明以她的鬼魅、神话、她的“黑夜”意象、戏剧性场景与结构,使人怀有不倦的阅读和阐释兴致。两人的诗歌艺术迥异,却又都为读者所喜爱,并在上世纪 80年代的诗坛上树立了两个高度。那么,两人各以怎样的审美品格不仅丰富了当代诗坛,而且分别被后来的诗人们纷纷仿效?她们的诗歌艺术对诗歌尤其是女性诗歌的未来又有什么样的启示?或许都有认真探讨的必要。
一、舒婷与翟永明诗歌的形式:理性雕琢与感性喷发
一首诗的外在形式通常包括诗体、语言、意象等方面,而形式承载着内容,舒婷与翟永明迥异的诗美品格首先在诗歌形式上有所体现。
诗体。显而易见,舒婷擅写短诗,善于对生活中的所见、所感、所思做即时性的抒发。如《致橡树》,就是同一位老诗人散步,听他一席话,感想万千而写下的;《神女峰》,是游览长江时路过神女峰,于途中所写。由于“文革”对人性的戕害,使诗人们一旦有了说话的机会,便迫不及待地要倾诉,于是短诗成为包括舒婷在内的众多诗人的选择。从诗的题目,如《中秋夜》、《在潮湿的小站上》、《双桅船》、《滴水观音》、《赠》等可明显看出,诗人的情思意向往往聚焦于特定的时间、地点,特定的人与物及特定的情景。此时,短诗以其单纯精致、形式完整和传达快捷,被诗人首选。舒婷的短诗不同于冰心的小诗,后者多是瞬间的感悟与升华,寓简单的哲理于其中;而前者则要复杂得多,它是一种主观的思考,是诗人将自我作为主体去感受一切。
翟永明的诗歌多是整体喷发,组诗是其主要的诗体形式。《女人》虽然不是她的第一部作品,她却因为《女人》引起了诗坛的关注,这不光是因为诗中强烈的女性意识与女性形象,气势磅礴的组诗形式也是过去诗坛少见的。不同于舒婷的具体与理性,翟永明是抽象而非理性的,无论是《女人》、《静安庄》、还是《死亡的图案》,都是存在意义上的复杂的集合,诗人以其深刻的洞察力进行了意识流似的观照。对于这种诗体形式上的追求,翟永明曾说,“首先是青春期的泛滥精力,其次是对诗歌的狂热追求,使得我在每一次较为投入的写作中,非组诗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不受羁绊地表达我的冲动的内心。除此之外,我对诗歌的结构和空间感也一直有着不倦的兴趣,在组诗中贯注我对戏剧的形式感的理解,也是对我所喜爱的戏剧的一点痴心”。①翟永明:《正如你所看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48页,第34页。因此,翟永明的组诗虽然阴冷,有时还有点儿令人费解,但那空间感、戏剧形式感、以及天、地、人、神的错综交织,把人带入了一个非理性的、有些失控但近乎完美的世界,使人不但没有产生读长诗经常会有的疲劳感、厌倦感,反而会想到某种神灵的启示。它的变化无端、它的难以言说、它的推进力量,以及它所体现的诗人的结构能力与布局意识,都不断激发着人们的解读热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舒婷的短诗更具音乐性,它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翟永明的组诗更具绘画与建筑性,它冲击人的视觉、撞击人的灵魂。
语言。不可否认,舒婷和翟永明都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滋养,尤其是古典诗词,它的韵律自然地提醒着读者的阅读态度,隐秘地牵动着作者的写作兴趣。就语言事实来说,舒婷的语言雕琢感很强,“找到关于那几个唯一正确的字的唯一正确的安排方式”②舒婷:《你丢失了什么》,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8页。是她不懈的追求。在这种诗语观的指导下,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工对整齐、精致优美、韵味十足的诗句:“风,若有若无,/雨,三点两点。”(《在潮湿的小站上》)“月台空荡荡,灯光水汪汪”。(《在潮湿的小站上》)“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苦一晚”(《神女峰》),这些对偶、对仗、对称的句式加上合适的韵脚,组合成完整的句群,形成独特的空间美感,使舒婷的许多诗都具有了词的声音。“不怕天涯海角 /岂在朝朝夕夕”(《双桅船》),无论情感还是语言,都与南宋秦观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有一脉相承之处。词本来就与音乐密不可分,舒婷的许多诗也都是适合吟唱的,加上她较常使用的排比句式,已然成了当代许多朗诵诗模仿的原型,也使得她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远比翟永明和其他许多诗人大得多。《致橡树》那精致的语言、复沓的节奏、内在与外在整体的律动,已成为当代诗歌史上的经典。对于自己如此“字字珠玑”,舒婷的回答是:“写什么?怎样写?都听从内心不可抗拒的召唤。永不背叛的唯有语言,星星点点分布在经验的土壤里,等待集结,等待惊蛰。也许仅仅是蠕动着,为了‘片刻的羽化,飞行状死去’。”③舒婷:《凹凸手记》,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7年版,第208页。她的“雕琢”带来的不是繁复,而是更加简洁隽永,许多诗就像是直接说出来的,口语化极强。
与之相比,翟永明的诗歌语言像是从内心蹦出来的,极具形式感。她的《女人》虽难免某些雕饰和粗糙的成分,但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浑然天成的。如诗人自己所说:“事实上,面对词语,就像面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我,同时也相信与我一样的那些女诗人们,只是默默地握住那些在我们体内燃烧的、呼之欲出的词语。并按照我们各自的敏感或对美的要求,把它们贯注在我们的诗里。它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④翟永明:《正如你所看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48页,第34页。翟永明的语言是视觉型的,“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 /她秘密的一瞥使我精疲力竭”(《女人·预感》)“站在这里,站着 /与咯血的黄昏结为一体 /并为我取回染成黑色的太阳”(《女人·瞬间》)。透过这种颇具描摹力的语言,我们看到了一个特立独行而又惊恐万分的女人形象。就语感来说,舒婷的“雕琢”并不做作,翟永明的“形式”却有质感,读舒婷与翟永明的诗,仿佛从重理性的北方来到了重感性的南方,不变的是诗歌的灵性。
意象。舒婷诗歌的审美点往往聚焦在词意象上,海、船、水、鸽子、橡树、百合花、鸢尾花等,这些既有传统特色、又有诗人家乡的地域特征的自然景物在其诗歌中占据了独尊的位置。诗人将丰富的情感投射在这些词上,靠词与词之间的呼应、对比和激发推进诗的进展,并以此为中心努力营造优美的意境,使整首诗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一个动人的故事情节,随着词汇意象的跳跃,形成整体的律动。如《会唱歌的鸢尾花》,“我”就是鸢尾花,鸢尾花成为主体的象征,它寄托着诗人全部的情与爱,它引起诗人情绪的流转,情绪的流转又带动了诗思的变化。而翟永明的诗多有跨行,如“深夜,人神一体的祖母仰面于天,星星不断轮 /转,……以死 /亡的气质,在黑暗中也能看到 /蝗虫的眼睛。……我始终在这个枯井村庄,先看见一块 /大石头 /再看见古老的血重新显现,一根桩子在万物欢 /腾时 /寂寞,像一个老人”。(《静安庄·第七月》)一般说来,跨行是为了强调或对比,如“轮 /转”、“死 /亡”“欢 /腾时 /寂寞”等。不断的跨行就使得整首诗变得紧张、急促,读者不得不“一目十行”,跟着句子往下走,于是形成了不同于舒婷诗歌词意象的句群意象:祖母仰面、星星轮转、寻找水源的人灵魂冒气、我口中有裂痕、召集群鸟、看到蝗虫眼睛……强奸、太阳松弛、祈祷、头肿胀、看见光染红屋顶、做梦、掠夺者至、我看见石头、血、桩子寂寞等等,既扩大了人与外界的联结点,又带来了诗歌内部巨大的审美空间,而且,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很难得之,这也正体现了生命及生命与外界之关系的复杂与神秘。
舒婷的诗歌意象是温暖的、柔韧的、唯美的。她曾经跟她的老师蔡其矫先生说过,除了水,她最喜欢植物,如“一朵初夏的蔷薇,/划过波浪的琴弦,/向不可及的水平远航”。(《向北方》)“你比大海多了生命 /今夜,你和大海合作 /创造了歌声”(《海的歌者》)。水是洁净的、有生命力的、包容的,植物是柔美的、沉默的、坚韧的,这些带有明显的诗人的家乡和生活地特征的意象,也是传统文化赋予女性的象征。这种自古代女诗人就有的对自然的挚爱,从更高意义上来说,是作为人、人类存身的最基本也最根本的生命执著与生命精神,它经过历代的传承,已成为生命文化的一部分。相比较而言,翟永明的诗歌意象是阴冷的、荒凉的、唯真的。在她的笔下,除了黑夜,便是血、鸟等相对动态的生命,如“我目睹了世界 /因此,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女人·世界》),“当我十二岁,流出最早的鲜血 /浑身发抖,倒在你冰冷的怀抱”,(《死亡的图案·第七夜》)“故事刚刚开始 /传说这样结束 /——正值乌鸦活动的时候”(《女人·夜境》)。这些与女人本体密切相关、又与生命同属的意象,使翟永明的诗迥然不同于舒婷,舒婷的创作离不开鼓浪屿,翟永明的创作却与成都无关,她即使换个城市生活,创作也不会改变。她的诗歌意象与借鉴西方有关,更与思维方式有关。舒婷诗歌的意象是生命的象征,而她的诗歌意象直接就是生命本身;舒婷带给人的是生命的暖意,而翟永明带给人的是生命的荒凉,二者相互缠绕,构成生命的复杂与真实,这也许正是生命和诗意的永恒所在。
二、舒婷与翟永明诗歌的气质:情感的吟唱与生命的独白
舒婷的诗歌是舒缓的、深情的,她像一位善解人意的大姐,用语词温暖着、慰藉着受伤的心灵,憧憬着美好的生活,表达着个人的情思,“好像世界是一个黑孩子 /已经哭够了 /你哄着他,像大姐姐一样 /抚柔了他打湿的卷发”(顾城《希望的回归——赠舒婷》)。舒婷的诗直接继承了以蔡琰、李清照为代表的女性的细腻情感,不管是吟咏爱情,还是讴歌友谊,都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儿,“我的童话是一张白纸。/你小心地折起它,对我说:/我要还给你一首诗。/从此我常常猜想:/在你温柔的注意中,/有哪些是我忽略过的暗示?”(《小渔村的童话》)。坎坷的经历使舒婷的诗歌情感不同于林子的单纯,她是复杂的,“招之不来,挥之不去,/似近非近,欲罢难罢。/有时像冰山;有时像火海;有时像一支无字的歌,/聆听时不知是真是假,/回味里莫辨是甜是辣”。(《自画像》)忧伤但不颓废,痛苦但不沉沦,矜持中暗含骄傲,阴柔中透露阳刚。她的许多诗歌文本都不是单一的声音传达,“而是彼此纠葛、质询的多重指向与意义声部,体现了‘我’的多样性、经验的复杂性”。①陈超:《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1270页。她为暴政下的人性沦丧而伤感悲恸,为时代压抑下的情感缺失而难过,为传统的男女不平等而呼唤。在她的诗中,人的尊严感与忧伤氛围并存;人的坚韧性与女性的温柔互相渗透、补充,带有强烈的个人使命意识和时代色彩,既是社会情绪的抒发,又是个人情感自然而然的流露。
舒婷是抒情的高手,用白描手法构成优美的意境是她最主要的艺术特色。她善于描绘生动形象的细节,表达细微的情感,如“我匆匆跑下,在你面前停住。/‘你怕吗?’/我默默转动你胸前的纽扣。/是的,我怕。/但我不告诉你为什么。/……/我拽着你的胳膊在堤坡上胡逛,/绕过一棵一棵桂花树。/‘你快乐吗?’/我仰起脸,星星向我蜂拥。/是的,快乐。/但我不告诉你为什么。/……/我满脸通红地收起稿纸,/你又庄重又亲切地向我祝福:/‘你在爱着。’/我悄悄叹口气。/是的,爱着。/但我不告诉你他是谁”。(《无题 1》)在这首诗里,诗人用三个美丽温馨的情节,如同三个动人的电影画面,恋爱中少女的大胆、羞涩与诡秘,深深地嵌入读者的脑海。其中三个转折的句式,使诗情变得曲折起伏,“但”字的反复使用,也发挥了巨大的逻辑力量,使普通的词语变得熠熠生辉。再如《神女峰》,用蒙太奇的手法,将神女的寂寞与游人的欢呼加以对照,白描手法加现代感觉,使舒婷的诗总是回环复沓、韵味无穷。
翟永明的诗歌是焦灼的、尖锐的。舒婷似的强烈的情感表达在她这里已难寻踪影,她善于沉潜情感、上升感觉,致力于探寻同属人的精神世界的另一半,即纯粹的内在精神感觉。“我更热衷于扩张我心灵中那些最朴素、最细微的感觉,亦即我认为的‘女性气质’,某些偏执使我过分关注内心,黑夜作为一种莫测高深的神秘,将我与赤裸的白昼隔离开,以显示它的感官的发动力和思维的秩序感”。②翟永明:《黑夜的意识》,载谢冕,唐晓渡:《磁场与魔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142页。翟永明的诗中没有抒情、激励,只有非议、质疑,她 80年代的诗歌一直被认为是“普拉斯的中国版”,“自白”也成了她的代名词。今天看来,就表达方式而言,确实有借鉴的成分,来看几组句子:“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翟永明),“我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女人”(普拉斯);“海浪拍打我 /好像产婆在拍打我的脊背”(翟永明),“接生婆拍拍你的脚底”(普拉斯);“我十九,一无所知”(翟永明),“我七岁,一无所知”(普拉斯)。无论语感还是句式,甚至本能的裸露,从翟永明的诗作中总能寻到些普拉斯的影子。但翟永明有普拉斯的自我袒露与痛苦、怀疑,却没有她的歇斯底里,翟永明是沉静、内敛的,她以深刻的洞察力和体验的深度,对女性的生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精神关注,以自己的经验推及集体的经验、女性的经验,她不断地展示着个人的、内在的、诞生前就潜伏在她身上的一切,她的尖锐与焦灼略带恐惧与不安,以及急切的追寻。
翟永明的生命独白运用了戏剧独白的形式,使诗歌之“我”始终居于主体地位,“我是……”成为她诗歌的主导句式。如“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女人·独白》),“我是唯一生还者,在此地”(《静安庄·第四月》“我是死亡的同谋犯”(《死亡的图案·第一夜》),这里的“我”或许是诗人自己,或许不是,“当诗人把自己放入自己的作品中时,诗人的自我便立即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 (同时也与诗人的自我密切相连),变成了艺术作品中的一个存在物”。①彭予:《美国自白诗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66页,第65页。舒婷的诗歌也经常将“我”放在首位,但往往是出于抒情的需要,“我”是抒情的主体,而翟永明诗中的“我”通常可看作“女人”。翟永明一直钟情的诗人叶芝认为,“控制和戏剧感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关系,假如我们不能够想象自己与真实的自我不同,以第二个自我的面目出现,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把控制加在我们身上,因此积极可取的态度是有意识的戏剧化,戴上一副面具”。②彭予:《美国自白诗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66页,第65页。翟永明或许深受叶芝面具理论的启发,她不断地向自身内部挖掘,并实施控制,使她的诗歌彰显了结构的意义。《静安庄》“十二个月”的铺排,《死亡的图案》“七天七夜”的叩问,以及《女人》中不断出现的“冬夏”的时间概念,都仿佛有一种造物者似的口吻。春夏秋冬、日月轮回,构成了神话原型的基本框架,而天、地、时间、空间,也在翟永明的诗歌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西方现代主义诗人为了创造较大的结构,使现实的细枝末节在这些结构中具有意义,常常求助于神话,翟永明正是创造了关于“自我”、关于“女人”的神话。传统的神话为诗人和读者共享,而“自我”的神话只能通过诗本身传达给读者,如何完成这一转变就要看诗人的结构能力了。《女人》始于《预感 》,终于《结束 》,其中有“臆想 ”、有“渴望 ”,有“噩梦 ”,有“世界 ”的呼号 ,有“生命 ”的痛感 ,它几乎涵盖了与女人生命相连的全部,它的内在结构、它的巨大激情、它的审美经验,使《女人》奠定了她在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再如《静安庄》,十二个月份的框架设置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划分,而是“通过诗使人内心的节奏和律动、诗的节奏和律动与自然的节奏和律动彼此呼应”,③唐晓渡:《谁是翟永明》,载翟永明:《称之为一切》,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年版,第13页。这样,诗人、我、自然,就具有了本质意义上的内在同构性,以“自然”的形式描摹自然的生命,使《静安庄》获得了一个不断变化而又浑然一体的生命与心理过程。《死亡的图案》之“七”,既与星月运转有关,又直接源于中国传统人死后过“七”的习俗,人之死被纳入了自然的轨道。
舒婷的“重表现”与翟永明的“冷抒情”源于二人思维状态的不同。舒婷善于把外在的客观物象,放在主观的映照下,她诗中的意象不过是一种象征,一种诗人主体思想和精神的承载,在舒婷的诗中,诗人自己往往是不出场的,她努力寻找与感情相对应的自然景物,当胸中的郁积不得不抒发时,便着力组合这些自然景物,以高扬的主体对客观世界进行干预和介入,在她的笔下,一切外在景物都是拟人化的,都是浸透了人的主观情感的,正如杨炼所说:“我的诗是生活在我心中的变形,是我按照思维的秩序、想象的逻辑,重新安排的世界。那里,形象是我的思想在客观世界的对应物,它们的存在、运动和消失完全是由我的主观调动的结果。那里,形象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本身的客观内容,更主要的是我赋予它们的象征内容,把虚幻缥缈的思绪注入现实、生动、具有质感的形象,使之成为可见、可听、可闻、可感的实体。”④杨炼:《我的宣言》,《福建文艺》1981年第1期。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舒婷的诗中出现了各种隐喻、通感、错位、蒙太奇等现代操作手段。而翟永明喜欢用客观、中性、超然的语气刻画人物、分析人的命运和深层次的痛苦。在她的诗中,人与物同在,人不过是自然之一种,各种景物都在它自己的轨道上独立运行,不与人喜、不与人悲,她善于描写场景,而这种场景就是人与物共存的状态,它们是两回事,但又是平行的,诗就是对它们的直接描写。与舒婷的强烈情感不同,翟永明是重感觉的,感觉本身即富有一切。她的诗歌偏好叙事,追求纯净透明。她认为,“看山是山或看山不是山都与山无关”。⑤翟永明:《正如你所看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9页。她试图与诗中的客观物象对话,进入他们的世界,此时,无论是客观景物,还是小动物,都不是诗人精神和思想的具体的承载,它们与诗人共处诗歌世界的奇幻王国。在她的笔下,客观事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运行着,这也就使得诗人更多地使用叙述、反讽等艺术手法。
三、舒婷与翟永明的诗学追求:“为人写诗”与“针对自身”
舒婷曾说到她的美学追求:“关键是动人——感动人。”①舒婷:《你丢失了什么》,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2页。她的创作无论是早年的那种“美丽的忧伤”,还是稍后的沉重的思索,都是“为人写诗”,尽管起初是完全无意识的,或曰“写诗出自本能”(《停电的日子》),但实际上她一直努力地表达着“思想”,她提笔的理由是为记录一代人的思想和情感,表达社会化的个人情绪。其诗意指向外部的社会、历史、时代,是“为人生”的,因此,她的诗往往是因具体的人物或事件有感而发。如《风暴过去之后》是为纪念“渤海 2号”钻井船遇难的同志而作;《白天鹅》是因一只白天鹅被枪杀而写……她的诗旨在唤起人的良知、正义、责任,表现对人的关切,从“人”出发,又回到“人”。通常是先有了一种感触、一种思想,然后寻找一种形象,或一种画面,以此表达一种隐喻,如《墙》:“夜晚,墙活动起来 /伸出柔软的伪足 /挤压我 /勒索我 /要我适应各式各样的形状,”诗人用“墙”的形象象征“压抑人的力量”。她的诗歌有形象、有温度、有意义,缘于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又以此影响现实生活,感染现实生活中的人,以文学的诗意带来文学的暖意。
在诗学追求上,翟永明更关注的是内心的表达,她的诗歌创作“都是首先针对自身,其次才是针对他人”。②翟永明:《正如你所看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47页,第130页。不同于舒婷的外部指向,翟永明意在将诗指向内在生命空间;不同于舒婷的象征,她旨在用诗传达感觉:“身体波澜般起伏/仿佛抵抗整个世界的侵入 /把它交给你/这样富有危机的生命、不肯放松的生命。”(《女人·生命》)她用个体生命的感觉代替了整体的意义,用具体代替了抽象。“我们是黑色房间里的圈套 /亭亭玉立,来回踱步 /胜券在握的模样 /我却有意使坏,内心刻薄 /表面保持当女儿的好脾气 /重蹈每天的失败”(《黑房间》),在这里,“黑房间”是“一幅画、一个空间,一种与生命及青春敌对的感受,或许是一种毁灭的力量”。③尹国钧:《先锋试验》,东方出版社 1998年版,第168页。她首先针对自身的创作,仍然包含了对现实,特别是现实中的女性的关注。舒婷诗中的主体往往是“我们”,而翟永明诗中的主体往往是“我”,对于后者来说,外部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翟永明写诗,是为所谓的“无限的少数人”而作,但她似乎永远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读者,她的诗歌首先是对自己内心的“抚摸”。写诗,对她来说是一桩“快乐的事情”,写作中词语的流动、词语与自己所发生的具体的情感关系,都使诗人获得快感,并把这种快感传达给别人,最终打动读者。因为:“对一个人非常真实的东西,对众人也非常真实。”④[法]罗丹:《罗丹艺术论》,沈琪译,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年版,第4页。舒婷关注的是诗的社会意义,而翟永明关注的是诗歌自身。如《颜色中的颜色》:“黑与白 /黑色的马踏过草地 /为谁奔命?八月的手在钢琴上飞舞 /带来蓝色气味 /内心的破碎怎样消化?/策马路过草地,想起苍白的青年 /黑与白 /我聆听什么样的智慧?”她通过闪烁不定的词语组合,制造了词与词之间的偏离,以此造成了诗歌形象的陌生化效果。对词语的追逐实际上是对触觉、听觉、视觉的表现,其中所涵盖的或许是支离破碎但更加真实的个体体验。所以,舒婷和翟永明的诗学追求迥然不同,其中既有诗歌历史和现实的影响,又有个体艺术倾向的差异,但两人的美学立场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从社会化的个人到存在着的个人,“美”的主体意识不变。
从舒婷到翟永明,诗美品格表现出从抽象到具体、从外抒到内观、从意象象征到生命本身的发展变化。其中既有对诗歌传统的背弃,又有接受,因为,“我们只能身在一个传统之内才能反对该传统”。⑤翟永明:《正如你所看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47页,第130页。应该说,这种变化与区别是复杂的,而且与当时诗歌艺术从“朦胧诗”到“第三代”的整体性嬗变密不可分,又与女性意识的深入互为依托,是诗人个性、艺术追求与文化资源的直接缝合与统一。舒婷与翟永明,以各自独特而又高超的艺术审美体验,为当代女性诗歌、尤其是 80年代女性诗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 90年代诗坛乃至未来诗歌艺术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责任编辑:艳红)
I052
A
1003—4145[2010]05—0150—05
2009-11-01
张晶晶 (1974-),女,山东政法学院新闻传播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