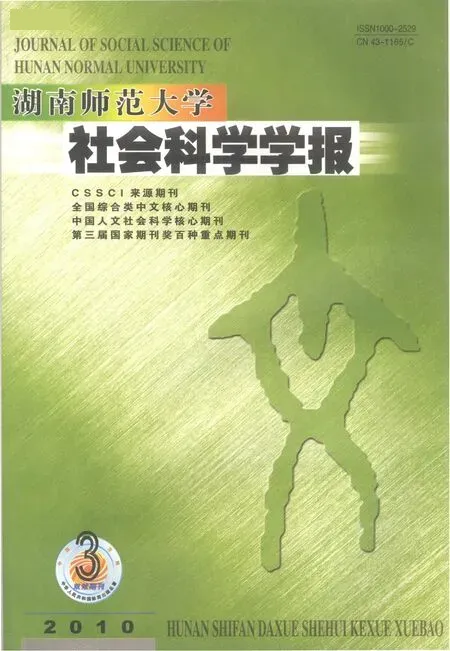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挑战与建构
——以杭州飙车命案为例
雷鑫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政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挑战与建构
——以杭州飙车命案为例
雷鑫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政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刑事和解为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部门探索的解决刑事案件的新途径。刑事和解基于恢复性正义,通过和解性程序达到恢复性结果。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面临适用范围、正当程序、内涵的澄清等方面的挑战。目前我国正在建构中的刑事和解制度,应严格限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程序,厘清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刑事和解;挑战;建构
2009年5月20日,杭州市公安局宣布,杭州“5.7”交通肇事案的侦查已经终结,肇事者胡斌被以涉嫌交通肇事罪移送杭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与此同时,杭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受害者家属与肇事方已经达成协议,受害者父母获赔约113万元。随着杭州飙车命案进入民事赔偿协调阶段,外界担心受害者家属受到赔偿后被封口,事情进一步“大事化小”。对此,受害者父母明确表示,“决不做交易,不能用钱买刑”,赔偿协议中没有交换条件,强调“民事归民事,刑事归刑事”。受害者家属的这一表态,也意味着本案家属拒绝刑事和解[1]。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无刑事和解的明确规定,不过随着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逐渐推进,近年来在不少地方已经有所实践,且无论从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方面,还是从刑事和解的实质来看,社会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但是,刑事和解自实践以来也一直面临着“以钱换刑”、“以钱买命”的质疑。杭州飙车案之所以引起公众和舆论的广泛关注,是因为舆论普遍认为肇事者家属会用金钱来换取法律对肇事者的惩罚。本文拟以杭州飙车命案受害者家属拒绝刑事和解为例,分析我国刑事和解面临的挑战与构建问题。
一、刑事和解的国外实践及其理解
刑事和解起源于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制度,作为一种刑事法理论思潮,它肇始于20世纪中叶,直接起源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两个年轻人所实施的一系列犯罪性事件①。1989年新西兰以立法的方式肯定了对青少年犯罪只能在恢复性司法不能适当处理的时候才可以运用正规的刑事司法程序。20世纪90年代后,刑事和解逐步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推开,成为西方刑事法学上的显学之一。从刑事和解产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刑事和解是西方国家新的刑事法理论思潮和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产物,是西方国家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司法形式,也是刑法谦抑性在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的最好诠释,同时也是以保护被害人和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刑事司法理念的司法形式之一。
目前,有关刑事和解的概念表述繁多。总体而言,这些表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刑事和解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主动直接和解,没有国家专门机关介入。如有人认为,“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对刑事责任问题达成的协议,一般而言,受害人一方不追究加害人一方的刑事责任,而加害人一方则可能为此对受害人一方进行物质性赔偿等。”[2]第二种观点主张刑事和解需要国家专门机关的主导,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被动直接和解。如有人以为,“刑事和解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经由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被害人与犯罪人面对面直接商谈,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目的是恢复被犯罪人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3]第三种观点主张刑事和解需要非国家专门机关的第三方调停,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被动直接和解。如有人认为,“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过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的帮助,使受害方与加害人有机会直接面对面地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之前被加害人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受害方因此而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4]刑事和解又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使加害人与被害人直接商谈、协商、解决刑事纠纷。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目前在西方国家较为通行的刑事和解实践模式有四种:一是社区调停模式,在犯罪发生之后,犯罪者被司法机关逮捕之前,由特定的社区调停组织而非司法机关主持犯罪者与被害者双方之间的调解;二是转处模式,在司法机关已经启动刑事司法程序之后,在程序终结之前将案件交由社会上的纠纷调解中心处理,而不通过刑事司法程序来最后解决犯罪者与被害者之间的纠纷;三是替代模式,该模式在尊重被害人意志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对犯罪者的刑罚处遇而使纠纷得到解决,实现犯罪者与被害者之间的和解。其典型做法是勒令犯罪者对被害者进行刑事赔偿、赔礼道歉或为社区提供服务;四是教会模式,在美国其典型是由门诺教派组织的刑事和解方案。该模式的目的是将犯罪看作是必须治愈的社区所受的创伤,强调的重点是治疗,重建正常的关系,手段是对被害人的补偿而不是报应。无论是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国家,还是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甚至在这些国家内部各司法辖区之间,刑事和解的制度安排并非完全相同,而是根据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及司法制度的不同有所差异。
二、我国刑事和解及其面临的挑战
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在对待刑事和解的态度上,自始就存在两派对立的观点。一部分学者积极倡导刑事和解在中国法典制度化,并认为中国传统法律的和谐思想为其制度化提供支持。“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有着丰富的现实土壤和悠久的文化渊源,也契合了国际现代法治的潮流。适用刑事和解,是刑事司法实践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体现”[5]。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刑事和解对于我国刑事法治而言,并无现实意义[6]。因为我国传统刑事立法与司法上的“苏联模式”在观念上一贯强调国家主义与集体利益。按照学术界的流行观点,“准确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首要任务。
因此,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司法现状仍然处于试点、摸索阶段,在司法制度层面不存在制度化的刑事和解。但是,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中也吸收了很多英美法系的理论,其中包括以被害人利益为中心的刑事和解制度:一方面,我国司法实务部门在刑事和解方面做了很多实践性的推动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和经验。实践证明,刑事和解在保护被害人利益,让犯罪人复归社会,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成本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尝试,其正当性日益受到挑战。其根本原因在于刑事和解制度本身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瑕疵,其直接表现就是社会公众中所谓刑事和解就是“用钱买刑”等说法。从而导致司法实务中不泛滥用刑事和解,放纵犯罪的现象。这一现象可以从人们对杭州飙车命案的高度关注得到印证。目前,我国刑事和解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内涵理解的模糊带来的挑战
从我国一些地方刑事和解试行规定中关于刑事和解内涵看,既有相对明确的内容,也有亟待澄清的问题。首先,在刑事和解的成立上,是否以一个非物质性的、相互沟通协商的过程为必备内容这一问题上,实务界的看法比较一致。即,无论是何种犯罪类型,刑事和解的成立,必须包含一个这样的沟通协商过程,而绝非仅是一种责任的实际履行。应当说,这样的立场具有合理性。因为,一方面,对被害人而言,实际的物质补偿固然重要,但精神层面的沟通、交融则更加不可少。犯罪行为不仅带来了物质的损失,更导致了人格上深深的侮辱和精神上强烈的负担。如果犯罪人在沟通过程中能坦言错误,真诚致歉,对被害人的精神恢复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犯罪人而言,只有通过这样的沟通过程,才能真正理解自己行为的错误性质与恶劣后果,产生来自内心的真诚悔悟,并切实地、具体地承担责任。总之,刑事和解过程中的沟通协商,能有效地增进共识、消除误会、恢复和谐,其可谓构成了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核。
其次,刑事和解的成立,是否必须具备被害人的接纳,以及进一步地,是否必须具备被害人的“内在接纳”问题,还存在广泛的可探讨余地。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立场来看,刑事和解的成立,只要犯罪人有严肃的、尝试性的努力即可,并不需要具备被害人的接纳,亦不需要一个损害再复原的有效结果的达成。从《德国刑法》第46条a的规定的语言表述来看,立法者也明确承认了,此种严肃的尝试性努力本身即可构成有效的刑事和解。由此可知,刑事和解的达成,不完全寄予被害人同意,是立法者与实务界的一种共识。我国一些试点刑事和解的地方性规定中对于刑事和解是否需要被害人的内在接纳是不明确的。譬如,2006年11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中对于和解的成立只是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当事人自愿”等规定,并没有进一步详细规定被害人是否需要“内在接纳”问题。杭州飙车命案中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样也就是和解是不是真正出自受害人的内心意愿。如果该案进入和解的话,法官如何把握和解方案是否真正能够被被害人接纳。这也是刑事和解中最富有争议的一个内容。
应当说,以被害人“内在接纳”来评判刑事和解能否成立,存在相当的问题,至少从操作层面来看,要去清晰地判明被害人接受犯罪人的义务履行的动机,有时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在被害人接受行为的背后,往往隐含着情感的、利益的、名誉的等诸多因素的复杂考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实中的协商调解,几乎没有那种是完全不带丝毫杂质的、纯粹的“内在接纳”。
2.我国刑事和解适用范围问题的挑战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从国外来看,似乎对刑事和解适用的犯罪类型未给予任何限制,似乎无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自然人犯罪还是法人犯罪、既遂犯罪还是未完成犯罪、轻微犯罪还是严重犯罪,都可适用刑事和解。至少从西方一些主要国家法律文本的纸面意义上看,刑事和解是一项普适性的、基础性的刑罚裁量事由。譬如,《德国刑法》第46条a的规定,尽管德国立法者没有在法条中设定明确限制,但是德国实务界却在刑事和解的具体运作范围上,表现出相对谨慎和拘束性的姿态。特别是在其能否适用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类型这一问题上,即使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显现出极为暧昧的立场。
我国试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地方性规定中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弹性较大,需要检察官去把握。譬如,2006年11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第四条确定的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范围主要包括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其适用范围弹性是较大的。可以看出,刑事和解作为减刑或免刑事由是否适用于所有犯罪,司法运作始终远非法条文字那般简单。尤其是,针对严重侵犯个人身体权利、人性尊严的犯罪类型,如故意杀人、身体伤害、暴力强盗抢夺、强奸行为等,是否毫无疑义地适用刑事和解,始终存在巨大分歧。杭州飙车命案被害人家属拒绝刑事和解,在司法实务部门是存在异议的。譬如,2007年11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第四条规定的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就包括交通肇事案。通过我国许多刑事和解案件的总结发现,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问题,始终构成这一制度践行中的主要困惑。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还进一步牵涉到“平等原则”的贯彻,以及这一制度的体系问题。如果严格限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那么刑事和解的运用前景就成问题,如果只有某些案件可适用和解,而另一些案件则不能和解,这一制度自始便透漏出不平等的信息。同时,如果只能适用于部分案件,就会大大降低这一制度的体系地位与运用前景,使其至多成为传统犯罪应对模式的一种补充,丧失普遍意义。
3.我国刑事和解程序正当性问题的挑战
在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上,我国实务界的看法比较一致,即必须具备犯罪人的坦白。与传统刑事诉讼制度不同,刑事和解的纠纷解决方式首先由被告承认罪行、讲出真相,并且将这一点视为是启动和解的必备前提。而传统诉讼模式则支持被告人隐瞒、回避甚至否认自己的罪行,并且具体表现为沉默权的赋予、对抗式的诉讼模式、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可以看出,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是严重违反传统诉讼模式程序规则的,是对传统诉讼程序规则的背弃,或者说两者是根本对立的。
应当看到,我国实务界关于刑事和解制度适用前提的规定,顺应了世界范围内刑事和解运动的一般规律,也符合刑事和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的基本宗旨。犯罪人的坦白可谓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内核,不容舍弃。从国际范围内观察,所有践行这一制度的国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被告人自愿认罪,设定为启动和解程序的首要前提。
当然,如果承认这一适用前提,也会立即产生如下问题:首先,这将与我国刑法无罪推定原则相抵触。在和解程序中,只要被告人承认自己的罪行,接下来的问题就不是证明,而是如何确定被告人的责任承担。这无疑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公然违背。因为,根据该原则,任何一个刑事被告在法院以生效判决确定其有罪之前,都必须被视为是无罪的。其次,与之直接相连的,是违背基本的证据规则。因为,和解程序的进行,通常只需被告人的认罪即可顺利进行并达成协议,根本不需要其他的证明。这显然触犯了被告人自白不能作为认定犯罪之唯一依据的“口供补强规则”。再次,与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背离。因为,一个有罪宣告的成立,必然要求法院对于被告的罪责具有毫无怀疑的确信,只有这样方能推翻无罪的预设。显然,这一“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绝非简单的自愿认罪所能满足。杭州飙车命案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对司法机关来说是个挑战,面临启动的前提以及如何确保加害人与被害人在程序上是公正、公平的,这同样也是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路径探析
基于刑事和解制度在被害恢复和加害恢复上的双重价值,它同时兼顾了公正和效率价值,对此制度应当进行合理的借鉴,构建符合中国现状的刑事和解制度。同时,刑事和解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和其存在的瑕疵,使得在构建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时应当全面的考虑,通过制度设计来减少刑事和解中可能引发的问题,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优越性。杭州飙车命案处理中,之所以在是否能够适用刑事和解问题上引发争议与社会舆论的关注,其原因之一,就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刑事和解规范。如何在中国目前的法制现状中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建议,有学者给出了近期、中期、长期三种方案[7]。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的设计应当考虑到刑事和解的中心任务、基本的价值取向以及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瑕疵、我国法治理念。但作为一项替代性司法模式,其中有些问题仍然应权衡考虑,利弊兼顾,尤其是对适用对象、程序、影响等方面有一个清醒而理性的认识,以便发挥刑事和解制度应有的作用。
1.明确界定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树立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
从立法上明确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譬如,刑事和解制度是否以一个非物质性的、相互沟通协商的过程为必备内容,是否以被害人“内在接纳”来评判刑事和解能否成立,等等。笔者认为,我国建构中的刑事和解需要有一个被害人与加害人进行面对面的充分沟通协商过程,评判刑事和解的成立应以被害人“内在接纳”为标准。被害人与加害人通过充分的沟通协商,有利于化解被害人的怨恨,有利于加害人从内心深处充分认识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最重要的是有利于被害人“内在接纳”加害人的忏悔,从而促成和解协议的达成,化解矛盾。从立法上明确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能有效地克服把刑事和解制度当成无原则的“和稀泥”的观念,同时能避免无原则的一味从宽处理的做法。
对待刑事和解制度要树立正确的司法观念。提倡刑事和解并不是要取代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而是试图构建与现行审判程序并行不悖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惩罚性、预防性的理念是从国家宏观角度去治理犯罪,重在威胁;而和解理念却是着眼微观,从每个具体犯罪人入手,重在修复。它们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共同形成社会治理犯罪的完整系统。在整个系统中惩罚性、矫正性、恢复性的理念应该相互协调,发挥各自的作用。
2.对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定
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各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普遍的适用对象是未成年人犯罪,只允许少部分犯罪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够适用刑事和解来解决。比如说我国刑法规定的自诉案件和一些情节轻微的案件。目前,司法实践中,以和解方式处理的案件,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故意轻伤害案件肇始,现以扩展到侵犯财产的故意毁坏财产案件,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肇事案件,扰乱公共秩序的寻衅滋事案件、妨害公务案件,等等。若对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未严格限定的话,会造成司法机关各行其是,势必造成滥用刑事和解,放纵犯罪的现象发生,不利于保证法律和执法活动的严肃性。
适用刑事和解的前提是能够恢复。它既包括客观上能够恢复,又包括受害人与加害人主观上愿意恢复。客观上能够恢复的案件首先是从案件的性质出发。笔者认为,一般来讲,应该适用涉及个人财产、人身权利受侵害的案件,因为个人权利受到侵害后存在恢复的需求,且这种需求比其他犯罪更强烈。而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管理秩序的案件不适用。另外,基于刑事政策的需要,针对一些特殊案件,如:婚姻家庭的案件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不适用于惯犯、累犯,倾向适用于偶犯、情感犯。还可以从主观罪过来做一个区分,过失犯罪适用的应该比故意犯罪更为广泛些;从量刑来看,大致上来说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轻罪、或者后果较轻的重罪。
3.应当明确刑事和解制度的程序规定
首先,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是被害人与犯罪人自愿,也是刑事和解主观上的适用条件。这是刑事和解本身的协商、自治理念要求的,如果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达成所谓的和解,不仅起不到被害与加害的恢复,而且是对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刑事和解需要各方的积极参与,只有在确保双方自愿同意适用的情况下,和解才成为可能。在制度的构建中要充分注意保证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即便是已经进入了刑事和解程序,当事人仍然有权随时撤回这类同意。其次,刑事和解的提出与审查。刑事和解可以由被害人、加害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审查的范围主要是提出和解的案件是否是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是否是出于当事人真实的意愿才参加刑事和解的,被害人是否真实地原谅加害人,加害人是否真诚的悔过,等等。另外,要禁止司法机构对于当事人决定权的干涉[8]。在刑事和解中,强调当事人的参与性,尽力回避公力的介入。然而多数情况下,警察等司法人员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一个建议往往就会直接促成双方协议的达成,这就给他们的权力发挥带来了很大的空间,而这种权力几乎处于一种不受监督的状态;协商或调解的结果往往又被看成是纯粹的私人处理结果,也没有人去关心这种结果是不是渗透了司法人员的主观意志。这样的状态带来的常常是腐败,司法人员会利用这种优势使被害者获得超出其损失的赔偿或者使犯罪人逃脱必要的处罚。因此,建构刑事和解的公正程序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再次,刑事和解适用的阶段。刑事和解由于是在尊重被害人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调解,最大化的体现当事人的意志,因此,为了更有效的保护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只要双方当事人同意通过刑事和解来解决问题,都应当接受。
注 释:
① 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缓刑机关和宗教组织共同努力,使实施了一系列破坏行为的两个年轻人与22名被害人分别会面,让他们了解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与不便,从而在6个月之后全部交清了他们曾经坚决拒绝的赔偿金的时候,或许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案件,开创性地启动了到20世纪90年代,在很多国家得到发展和应用的恢复性司法之路。
[1] 山 风.杭州飙车命案受害者家属拒绝“刑事和解”[EB/OL].http://qzone.qq.com/blog/17150205-12583841 71,2009-12-29.
[2] 何军衡.“轻轻”刑事政策及其在检察工作中的应用[J].中国检察,2007,(1):59.
[3] 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J].现代法学,2001,(1):152-154.
[4] 马静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J].法律科学,2003,(4):45.
[5] 周世雄.也论刑事和解制度——以湖南省检察机关的刑事和解探索为分析样本[J].法学评论,2008,(3):13.
[6] 朱德宏.恢复性司法及其本土制度化危机[J].法律科学,2008,(2):20-28.
[7] 马静华,向朝阳.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J].法律科学,2004,(2):67.
[8] 邓陕峡.构建我国恢复性司法的意义与设想[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3):69.
China’s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Challenges and Construction——Hangzhou Drag Racing Murder as an Example
LEI Xi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04,China)
In recent years,criminal reconciliation has become a new way which is explored by our judicial departments to solve criminal cases.Criminal reconciliation is based 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and achieve restorative outcomes through reconciliation procedures.By our system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trial,our criminal settlement systems are facing challenges,such a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due process,and clarification of the meaning.At present,the criminal settlement system which is being constructed should strictly limit the scope of the criminal settlement.The due process in the criminal settlement system achieve restorative outcomes,and should be the content of the clarifying criminal settlement system.
criminal settlement;challenge;construction
D911.01
A
1000-2529(2010)03-0073-04
(责任编校:文 泉)
2009-12-12
湖南省重点学科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建设经费支助项目[湘教通(2006)180号]
雷 鑫(1969-),男,湖南洞口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