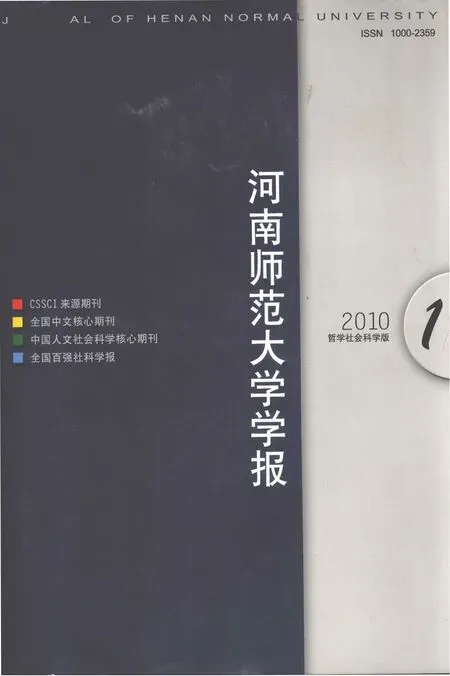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兼听独断”决策机制
樊有平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部,河南南阳473000)
论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兼听独断”决策机制
樊有平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部,河南南阳473000)
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兼听独断”决策,形成了集议制度、审议制度、咨询制度、奏报制度等决策机制,君主决策有一定的法律制度作保障,决策活动有一定的程序性和民主性,既维护了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决策的“独断”权,又“兼听”各方面的意见,较充分地发挥了各级官僚机构和官吏的作用,集思广益,从而减少了专制君主决策的失误。关键词:专制君主;兼听独断;决策机制
“兼听独断”是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决策的基本形式。管子说:“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1](《明法解》)刘向说:“众人之智,可以以测天,兼听独断,唯在一人。”[2](卷一三《权谋》)都是讲君主在决策时要“兼听独断”。所谓“兼听”就是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就是谋,可以扩大视听,防臣下之蒙蔽。所谓“独断”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君主做出最后的决断,可以防止大臣专权,维护君主独裁。谋之在“兼听”,断之在“独断”,“兼听”是“独断”的基础,只有“独断”才能保障“兼听”,“独断”又是“兼听”的结果,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兼听独断”的决策形式,使君主既能够通达政情,集思广益,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又能够“独断”大政,减少专制君主决策的失误。然而对此学术界论之甚少,本文试图系统研究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兼听独断”决策机制。
一、集议制度
集议制度又称为会议制度,就是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凡在遇到军国大政之事,总要亲自或委托宰相主持召开有关官吏会议,进行集体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最后君主做出决定。根据决策的内容、范围,参加人员和决策地位,历史阶段的不同,集议主要有廷议、宰相议、百官议、部议等类型会议。
廷议又称朝议,是专制君主定期或不定期在殿廷召开大臣和有关职事官的御前会议,讨论日常政务或决定重大政治、军事行动,最后做出决断。定期的朝议是君主召见有关大臣商议国家大事的例行会议。汉代君主召见大臣议政的时间比较固定。自宣帝开始,规定五日一听事制度,而光武帝刘秀则每日视朝,日侧乃罢,就是每天都要会见群臣,听取意见。这是听政受事的小朝,还有十月朔和岁旦举行的大朝,接受王侯百官郡国上计、少数民族的献纳与朝贺。唐代以后,朝议分为常参和朔望参,常参就是君主每天在正殿召见五品以上职事官以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等群臣,后改为单日御朝,双日休朝,讨论朝政大事。朔望参,是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日君主在殿廷召见凡在京的九品以上文武职事官,讨论政事。清代,除常参外,君主还要御门听政,了解社情民意。不定期的朝议是君主临时召见有关大臣的会议,讨论军国大政。明朝的廷议制度和程序进一步明确,议题更加集中。朱元璋在太子朱标死后,召开群臣会议讨论立储的问题,提出打算立燕王,征求大臣意见,当时学士刘三吾进言:“皇孙年富,世嫡之子。子殁,孙秉嫡统,礼也。即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朱元璋就决定立其孙为皇位继承人。清代廷议多讨论军国大事,如雍正五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在沙俄支持下发动叛乱。雍正七年二月,雍正帝乃“命廷臣集议”,决定出兵平叛[3](卷三○二《傅尔丹传》)。廷议之权在君主,没有君主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召集大臣廷议,而且廷议的结果也是君主最后做出决定。
宰相会议又称宰辅会议,是宰相集体讨论政事的会议。宰相定员,是国家政治体制中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理国家行政事务,专制君主在决策时,总要先与宰相商量,充分发挥宰相的参与决策的作用,宰相也要举行会议讨论有关行政事务,提出决策议案,上报君主做最后决断。汉代的丞相府有四出门,随时听事,“每国有大事,天子车驾亲幸其殿”,与“太尉与司徒、司空决而论之”[4](《百官志》)。唐宋时期,设政事堂(又称中书门下)作为宰相办公的地方,君主的决策必须经过政事堂集议,秉笔宰相签署,其他宰相副署,否则便不成为诏令,百官可拒绝执行。宋朝宰相也要举行议政会议,“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5](卷二七《官职仪制·宰相上殿命坐赐茶》)。明朝的内阁大学士承旨办事,帝王把所要决策的军政大事交给他们讨论,形成了阁议制度,君主“召阁臣面决,或事关大利害,则下廷臣集议。……圣旨所予夺,亦必下内阁议而后行,继雍蔽矫诈之弊”[6](卷一九六《夏言传》)。清朝,内阁大学士、学士“掌议天下之政”[7](卷二《内阁》)。凡君主的决策必须由内阁阁臣草拟诏旨,“皆由内阁起草进画,以下诸司”[8](卷一○《内阁》)。清朝的君主把不能裁决的军国大政交军机处讨论,提出解决方案,上奏君主做出最后决策,然后由军机大臣据君主旨意撰写谕旨,由君主颁布执行,需要明示天下共知的交内阁明发,事关机密的由军机处密发,称为“廷寄”或“寄信”。
百官会议就是经君主批准,由宰相或者有关大臣召集官吏讨论国家军政大事的会议,与会人员的等级差别在不同朝代又有不同的形式,但百官会议议定的方案,要由宰相或主要官员上奏皇帝,皇帝批准后颁旨有关部门执行,而君主要派亲信监议,参议人员的范围和资格也有明确规定。汉宣帝时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就是宣帝“亲称制临决”[9](卷八《宣帝纪》),并有宣帝派往会议的监议使者,颜师古作注说“(使者)谓当时诏遣监议者也”[9](卷八八《儒林传》)。百官会议也有有关部门长官主持或指定人员主持。如王莽时征聘有官官员讨论水利事宜就是由负责水利的司空下属司空掾桓谭“典其议”[9](《沟洫志》);汉武帝元朔五年讨论的是设博士弟子问题,就是由太常主持的会议讨论决定的[9](卷六《武帝纪》)。唐朝的百官会议规模更大,没有定期,与会人数也不固定,君主凡是遇到军国政务需要处理时,就下令召开,一般由宰相主持,在三省中进行,多数为讨论皇帝提出的疑难问题或大臣奏章中提出的议案,讨论的结果由宰相以中书门下的名义具状上奏君主,经君主批准后才能成为正式决策。宋孝宗初年,曾命令侍从、两省官每天到都堂集议一次,君主据集议提出的决策方案,或者口头指示、或者书面批示给两府长官。两府长官与其他相关长官起草“圣旨”,经君主评审无误后,便通过两府下达执行。明清时期的百官会议又称“廷臣集议”,奉旨举行,参加会议的包括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等,主要讨论军国大事。明朝还有吏部主持的讨论人事任免的廷推会议,还有对重大案件覆审的三法司和六部尚书参加的九卿会议。
二、审议制度
审议制度就是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在决策过程中,有关部门对决策的方案进行审查,匡正错误,纠偏补阙,主要包括谏议和封驳两种制度。
谏议制度就是对君主的决策进行批评,提出正确的决策方案。中国古代君主在中央决策中枢设有专门的谏议机构和专职人员,主要有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司谏、给事中等,其职责就是向君主进谏。王符《潜夫论》第七《考绩》说:“大夫、博士、议郎,以言语为职,谏诤为官。”[10]“大夫”就包括谏议大夫,是以谏诤为职责的。唐代的谏议大夫“掌侍从规谏”[11](卷二一《职官三》)。所谓“规谏”,就是指向君主的决策,涉及由此造成的大政失误和用人不当。唐玄宗在开元十二年曾下令,凡决策中有“除拜不称于职,诏令不便于时,法禁乖宜,刑赏未当,征求无节,冤抑在人”,谏官应该“并极论之,无所回避”[12](卷五五《省号下·谏议大夫》)。宋代左右谏议大夫的职掌为“掌规谏。凡朝政阙失,大臣及百官任非其人,皆得谏正”[13](卷五○《职官四》),就反映了谏官规劝君主的精神。不仅谏官专职规劝君主决策过失,而且百官都可以“据道谏君”,对帝王决策提出意见,廷争面折,知无不言,历代君主也鼓励劝谏,“上封事”“言朕过”,出现了贡禹、严肋、魏征、海瑞等直言进谏、匡正过失的著名谏臣。
封驳制度就是对帝王决策在下达执行之前进行审查,凡不符合政令而有失误的,可以驳正违失,封还执奏。封驳有两种形式,一是中央决策机关设置的谏官对皇帝决策的审议封驳,二是行政执行机关对帝王决策的封驳。秦汉时期,丞相府与尚书台相互制约,二者都有封驳君主决策之权。尚书台是审查政令、收受奏章的封驳机关,还起草君主诏令。宰相三公,对君主的诏书有封驳权,汉哀帝时想增封宠臣董贤,诏书“下丞相、御史”,“(王)嘉封还诏书”[9](卷八六《王嘉传》)。唐代的门下省是政令审查机关,其中的谏官给事中就有封驳之权,“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14](卷四八《郑覃可给事中敕》)。唐朝的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执行机关,与司法监察机关御史台对“所有制敕及官属除不当,宜封章上论”[12](卷五四《省号上》)。具体行使封还诏书权力的是尚书省的左右丞,凡是认为诏书有不当者皆可封还,拒绝执行。宋代以后封驳制度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君主的诏书必须经过给事中的审署,才能颁下执行。如果给事中认为君主决策的诏令对统治不利,就可封还,并写上自己的意见,请君主重新决策。《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载,给事中“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其二是百官所上各类奏章,在上奏君主之前,必须经有关人员审议,方可经君主批发,作为决策而付诸实施。在唐宋时则由给事中“读署奏抄,驳正违失”,“考其稽违而纠治之”[11](卷二一《职官三》)。明清时期,凡奏章都要先呈报君主审阅,实际是内阁代替君主“票拟批答”,经君主批准作为决策在下达执行之前,要经过给事中驳正违失后,方可由给事中下达有关部门执行,《大明会典》卷一二三载:“章奏既下,又经六科,六科可封驳,纠正违失。”[15]就是讲的六科给事中对君主批示实施的章奏进行审议,有违失要“封驳”。
三、咨询制度
咨询制度就是君主在遇到军国大政需要决策时,广泛征求有关专家和学者意见,集思广益,用集体智慧弥补其专断缺失。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在自己的周围设置顾问官员和顾问机构,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随时听候君主的咨询,“论思献纳”,“拾遗补阙”,为帝王的决策服务[16]。秦汉时期在宫廷办事机构中设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光禄大夫等诸大夫,有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等诸常侍,还有议郎、给事中和博士等,主要职能是为君主“顾问应对”。《后汉书·百官志二·光禄勋》说:“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后汉书·百官志三》说侍中“赞导众事,顾问应对”。唐代翰林学士称“内相”,可以“朝夕召对,参议政事”,“本以文学言语备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优宠”[13](卷五四《职官八》)。宋朝翰林学士“ 侍 从 以 备 顾 问, 有 献 纳 则 请对”[17](《职官志二·翰林学士院》),还有馆阁学士,《群书考索后集》卷一○说:“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议论,典校雠。”[18]明代的内阁大学士仍具有翰林学士院中翰林学士待诏的性质,与君主“商机务,备顾问”[19]。清朝的军机处仍基本上具备顾问官的性质,备帝王咨询,《清史稿·职官一》说:“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日常侍直,应对献替。”[3]“顾问应对”“切问迫对”“备顾问”都是讲的君主召见顾问官,咨询治道,访以政术;“拾遗补阙”“应对献替”“参谋议,纳谏诤”“与议论”“代言拟旨”“商机务”都是讲的顾问官的职能,就是为君主出谋划策,匡正决策失误,提供决策议案。
中国古代帝王顾问官吏多是兼职,临时差遣,无定员,无办公衙署,无任期,无印信,只要是宫廷内或宫廷附近某地方待诏或转流值班等待君主的咨询,而且任用不问职务品级,也不问有无官职,唯重才能,职卑权重,出入侍中,专受专对,独立行使为君主谋议的权力,便于发挥其功能。历代君主非常重视顾问官的参议决策的作用,每遇军国大政疑难问题就要召见顾问官,咨询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顾问官也“知无不言”,献谋献策,形成了一种“召对”制度。唐朝君主“朝夕召对”学士,咨询处理政事,文宗时“上每有疑义,即召学士”王起、许康佐、柳公权三人,“入便殿顾问讨论,率以为常”[20](卷一五)。明孝宗对内阁大学士刘健的奏请无所不纳,“诸进退文武大臣,厘饬 屯 田、盐、马 诸 政,(刘)健 珝 赞 为多”[6](卷一八一《刘健传》)。清朝的军机大臣“常日值禁廷,以待召见”,“召见无时,或一次,或数次”,随时就听从君主召见,商讨军国政务,承旨办事。
四、奏报制度
奏报是各级官僚向君主报告行政信息,对国家军政大事发表见解,提出意见、要求以及进行批评、驳议的制度,为帝王决策提供依据。
各级官吏的奏报,是君主了解下情的重要途径,古代君主非常重视,形成了奏报制度。从秦汉起,历代君主都有要求中央与地方官吏“上封事”的规定,“上封事”就是臣下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制度。明清时期,臣工奏事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这就是进呈起奏本章制度,各级官吏汇集各地行政信息,向君主呈题奏本章。康熙时奏折取代了题本,臣工奏报机密要务,使用一种秘密的文书,称为奏折,由具折大臣亲自书写,然后密封直达君主。乾隆时密奏取代了奏折,就是把奏折密封直接上呈君主,一折一事,既速且密。奏报内容按法律规定:一是必须真实可靠,不得弄虚作假浮夸;二是文字简练,禁止繁文缛节,做到“信”“达”“雅”。历代君主都鼓励臣下上奏行政信息,提出对军国大政的意见,其中不少有独到见解的奏报,如流传至今的《谏逐客令》《论积贮疏》《论贵粟疏》《上屯田疏》《徙戎论》《出师表》等,都成为君主决策的主要依据。宋朝君主曾要求臣下有事无事都要上报奏章。明朝内阁也有密奏制度,称为进密揭,就是密封言事。清朝科道官有事无事都有每天上一道密折,报告社情民意。对于各级官吏的奏报,历代君主都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管理。汉代自昭宣帝以后,宫中“通章奏”的尚书权力不断扩大,负责各类文书的上奏和下达,各级官吏上奏文都要经过尚书台上达皇帝,而尚书令有拆发阅读章奏的权力,群臣有所奏请,都由尚书令奏之。唐代奏报各级政务信息的管理,主要是由尚书省负责,尚书省把收到各级官吏的奏报先转交门下省审查,认可后送中书省起草拟批答,呈请君主批示,才能由中书门下颁布执行。明代设立通政使司负责公文的上达,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参议等,专掌“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臣民实封建言,陈情申诉,及军情声息灾异等事”[6](《职官志二》)。凡内外大臣的奏章,必须经通政使司传达给君主,君主批示的旨意,再经过通政使司抄送给有关衙门和官吏执行。明清的内阁是处理各级官吏奏报的机构,大学士的任务“点检起奏,票拟批答”,就是协助君主处理大臣的题本和奏本,提出处理意见,为帝王决策提供依据。到清朝,军机大臣处理百官的奏章和上谕,而例行公文题本仍由内阁处理。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君主“兼听独断”决策机制有两个特点:一是决策有法律制度作保障,使决策有制度可遵、有法律可依,制约了决策权的滥用;二是决策有一定的程序和民主性,凡决策必须经过宰相集议、百官会议、顾问审议、谏官封驳等程序,扩大了参与决策的范围。这就保证了中国古代君主决策中,君主既拥有独断权,又能兼听各方面的意见,从而减少决策失误。
[1]黎翔风.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向宗鲁.说苑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托津,等.大清会典[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8]孙承泽.天府广记[M].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
[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汪继培.潜夫论笺[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2]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3]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5]申时行,等.大明会典[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16]刘太祥.中国古代帝王顾问制度[J].南都学坛,2009(1).
[17]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章若愚.群书考索后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19]黄佐.翰林记[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20]孙逢吉.职官分纪[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责任编辑 孙景峰]
K23
A
1000-2359(2010)01-201482-04
樊有平(1965-),河南新野人,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2009-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