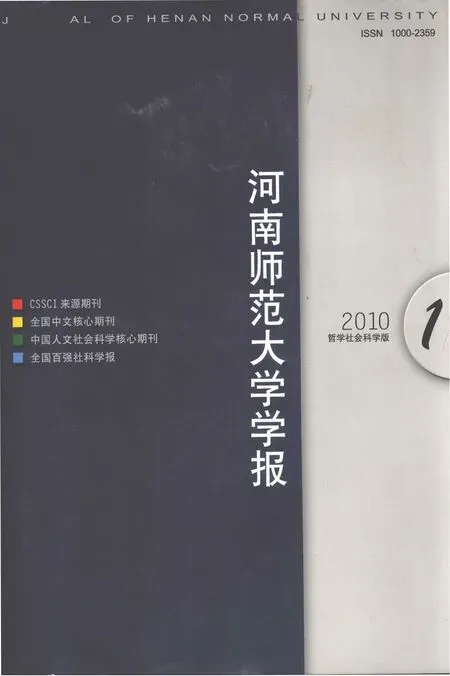从制度文明看现代政治价值
陈 毅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1620)
从制度文明看现代政治价值
陈 毅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1620)
近现代政治基于“政治是一种必要的恶”的认识,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提供免于匮乏和免于支配的政治自由,使人们过上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政治生活,寻求制度化的整合,驯服国家机器这个庞然大物,把政治看做人为构建的产物,通过制度化的设计从而寻求合理公正的制度化安排,这是近现代政治的主旋律。作为近现代政治核心的民主政治,实质上就是如何通过政治博弈的参与过程达成合理公正的制度化安排。从制度文明的三个历程的演进过程看,从人为制度设计到“法律是主权者的意志”而与“道德无涉”,再到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全面理解,这一历程同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再到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变迁相吻合。我们能很好透视现代政治价值确立与转变,加深我们对近现代政治生活的理解,澄清和积累政治文明的价值,通过对制度的全面理解寻求更加合理的制度建设,更好地为现代政治服务。
制度;理性;主体性;政治价值
一、现代政治寻求“政治祛魅”的制度化安排
现代政治文明的积累说到底是制度文明的演进,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政治把“何谓优良的政治生活”的传统道德问题转化为“我们应该怎样过公正的政治生活”这样一个道德实践问题,即把道德是什么的追问融入到怎样才能过上属于道德的生活的问题中。用罗尔斯的话说,“就是从康德式的‘道德建构主义’走向‘政治建构主义’”[1]。这在政治实践层面就体现为如何构建政治制度的问题。
何谓道德的争论构成人类的永恒主题,在伦理政治的人治传统下,人们一次次受到所谓的“精神领袖”或“道德圣贤”的欺骗和愚弄。历史证明,人们想先构建一套完美的政治蓝图,然后再去安排现实的政治生活的做法一次次以政治灾难的形式告终。然而,在过世俗化的利益政治面前,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发生了转变,人们直面利益冲突,政治并不神圣,也不崇高,政治就是平衡利益冲突,就是为了提供最具权威的分配方案。把政治从道德中分离出来反而更有利于认清政治内涵的伦理维度。政治由“天国”还原到“人世间”,融入人们每天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去,政治离我们并不遥远,也并不神秘,这也是为什么说近代政治过程是一个“政治祛魅”的过程。这种道德实践的政治过程正是现代政治所追求的民主政治生活。近现代民主政治过程越来越追求由人治走向法治,法治最具实体化的表现形式是制度。
制度设计考虑问题不再是从至善的道德要求出发,而是只要满足制度伦理要求的“底限共识”就行,即“在现代民主社会合理性多元论的文化条件下,我们把社会规范看作是作为社会公民之理性选择的结果,它应该是也只能是全体(或绝大多数)社会公民基于公共理性与平等对话所共同选择的一种合理的道德秩序的原则性表达。在此意义上,社会规范应该是通过某种公平合理化的选择程序而形成的道德制度体系,与社会的法制系统有着直接的关联”[2]。这就是政治秩序建构所依凭的制度伦理(或底线共识)。
过上制度化的政治生活是人们要求把“虚幻的政治”还原到“人世间的政治”的这种真实体验的需要。政治不再是少数人愚弄民意的工具,人们要求参与政治生活,政治要为保障人的权利实现服务。经由公民亲自参与的制度化政治整合尽管不够完美,但是也真切感受到自由意志得到表达和体现。政治合法性不再是追求道德圣贤或全知全能的上帝的统治,而是为了满足公民过世俗化的政治生活的需要。政治不仅探求为了过上人之为人的生活而寻求政治合法性,还要探求如何过上更好的生活所需要的更加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从制度设计看现代政治合法性的转变
近代以来,国家被比作“利维坦”,这个庞然大物是人为构造的产物。把国家机器作为对象来研究,为“政治祛魅”,人们越来越需求通过制度化来驯服“利维坦”。启蒙运动以来的制度研究,就是为了如何过上民主政治的生活而寻求一整套的制度安排,主要围绕政治权力是如何产生、如何运转和如何监督这一体系化的过程,最主要从个人权利的维护出发来监督政治权力的滥用。所以制度设计就有这样三个预设:
第一,“每个人都是无赖”的人性恶假设。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我们就不需要制度。休谟对于“每个人都是无赖”这一假设的著名论断,“表达了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为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为‘无赖’,那么对他们必须实行制度制约”[3]85。即政治规则设计者们也应当被看做无赖,因为他们可能会操纵制度的制定过程。这种对人性的幽暗认识并不是否定人具备美德的一面,对人为恶的一面认识得越深刻也越有利于人克制自己的局限,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这也一改过去的伦理政治对人性过于乐观的认识。
第二,“政府是必要的恶”的有限政府预设。“政治是一个‘社会中价值的权威分配’的决策领域,从本质上说,需要‘完全理性’的支撑。然而‘理性短缺’正是政治领域最常见的现象”[3]99-100。在神权政治或伦理政治下的全能政府越来越受到民众的质疑,对政府侵权为恶的可能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政府的理性能力和执行能力都是有限的。这也说明,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与制度创制,来预防和弥补人理性的不足。然而,人们也发现无政府也并不好于一个有政府的统治,“对‘利维坦’这种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这样一个理论预设:‘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3]93。不是不要政府而是如何更好地监督以便使政府充分有效地行使其应有的职能。
第三,“原子式个人”的自足性主体预设。制度设计对参与制度制定的主体是充分肯定的,这也受到启蒙思想影响,以往被压迫、被奴役的臣民甚至奴隶终于翻身成为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获得主体性人格的承认。一个经受公民授权和同意的政治才具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这三个预设有助益于政治合法性的现代转变。经过对制度设计的三个预设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它给予我们看待政治现象的全新视角,使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由道德圣贤或异己神灵的统治回归到人自身的选择能力上来,确立起近代以来新的政治观:第一,由伦理政治到道德与政治的二分;第二,由神权政治到世俗政治,即由“君权神授”到“非天使统治”;第三,政治统治最具合法性的证明是追求一种“同意的政治”。
三、制度沦为政治合理性证明的局限
一旦政治统治确立下来以后,政治合法性问题就转变为政治合理性的问题。统治者利用人们对制度的崇拜,在放松“意识形态控制”的同时,又加强“制度控制”,操纵对制度制定的决定权,凌驾于制度作用范围之上。因为真正对制度的存废起决定作用还是统治者,也即一旦选举结束,反映民意的统治就转变为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当制度的合法性证明转变为政治统治提供合理性证明时,制度就失去其价值维度,而沦为统治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法律实证主义者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而与“道德无涉”。即主要把制度看作外生变量,从外在制度控制的角度来看如何维系和巩固政治统治秩序。这也说明,一旦把制度仅仅理解为外在具有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并把它赋予高高在上的超越于制度制定过程之上的主权者时,僵化的制度就又一次沦为统治工具的地位,越完备的制度可能带来的禁锢就越大。这也是人们反对“制度神话”的原因所在,“制度神话”可能与“道德神话”带来同样严重的后果。
作为政治治理最普遍的制度安排形式的官僚科层制,受到新制度主义最大的质疑就是:片面追求制度的可操作性、确定性、可控预期性,而过分夸大了制度制定者对理性能力和科学理性的运用,认为凭借完全理性能力能够设计出一套完美的制度安排,凭借科学理性能够使制度高效和谐地运转。实际上,作为利益平衡机制的制度在产生之时就带有很大的妥协性,制度就是尽可能包容各种利益的“大杂烩”,更多是“满意就行”而很难达到“最优”,也就是说,很难制定一个完满的制度。制定出来的制度往往受制于所适用的范围和时效的限制,而且制度很容易出现滞后性,因而,也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完全理性的空想性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科学理性的片面性经不起价值的评判。而一旦失去价值维度沦为统治工具的制度安排,难以解决“谁来治理治理者”的问题,寻求主体性解放的自我统治就会被外在物化的机构或制度所异化。这也是反思启蒙运动、反思现代性的一大批思想先知者的理论自觉,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是否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它为了体现人的主体性的自我意识而取代传统的宗教信仰,构建合乎理性的精神家园,然而,结果却导致工具理性的增长,忽视人们行为的内在价值,而仅仅寻求程序的可操作性和结果的有效性,从而加深了主体被物化和异化的程度。制度的泛滥和粗制滥造,导致制度的成本越来越高,琐碎的制度和被歪曲滥用的法律很可能给人们带来的不是便捷和公正,而是更容易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对社会的不满。因为旧体制养活了一批靠体制吃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牢牢控制着体制的变迁,不公正的体制化的压迫使人们身心疲惫,难逃其枷锁。
人们寻求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过程也是使政治走上科学化的道路的过程。面对政治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寻求确定性和可控性,使政治学成为政治科学,使政治过程越来越透明,政府越来越容易被监督,人们参与政治也越来越简单易行。这一趋势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要找回被启蒙的主体性,人们越来越反思控制得越来越死的官僚科层制,重新反思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这里就存在一个如何理解制度的问题,如何走出“制度的悖论”呢?从对制度的反思来看,这也是新制度主义兴起的必然原因所在。
四、新制度主义对制度本义的全面诠释
新制度主义放宽了旧制度主义的制度设计的预设。如第一,人不再是原子式的自足个体,人是关系和境遇中的人,人的理性能力有限和存在结构性的理性无知。第二,从制度的内生价值来探讨在何种情况下制度是自我实施的,既没有否认人为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又凸现了制度演进的内在必然性,在传统演进中操练政治技艺,习得政治美德。理想的制度是自我实施的,这样,执行制度的成本就很低。人们在长期的博弈交往中,传承下来的习俗、惯例等具有这种特点,“自然形成的和演进的制度总会带来良好的结果。如同斯密所说:‘自然形成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4]也是制度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三,把利益相关者都纳入制度制定过程中来,尽可能缓解“谁来治理治理者”的难题。从研究治理理论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家对个案研究的制度分析看,在规模可控的共同体内部制定的制度,实施的效果最好。因为在这样的共同体中,规模有限,人员流动较小,利益兼容责任连带,声誉机制实施惩罚的效果明显。我们不要奢望有大而全的制度方案,正是人们从身边的制度化参与中,习得近代民主政治的规则意识,这才是最重要的,人们在点滴的制度化过程中,训练了如何制定、运作和监督制度实施这一全套过程的参与能力,也是个人主体性权利意识最好的培养方式。
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使政治文明的制度根基更具合理性。
第一,制度的“有限理性”预设。从制度的生成过程看,制度是制度设计和制度演进合力的结果,也要认识到人在制度生成过程中有所能有所不能;从信息来源看,人们难以穷尽资料的收集;从知识的增长看,人们存在结构性的无知和理性不及的盲点。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把理性狂妄到极大化,全知全能者不是天使就是魔鬼,因为他总想做人类的代言人。
第二,重申制度的伦理维度,走出“制度悖论”。“制度悖论”学说是从外在制度的角度讲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既说制度是为了控制人们的行为,又说制度是人们选择的结果,那么制度的客观性与选择制度的主观性之间就自相矛盾。之所以出现“制度悖论”,是因为他们忽视了制度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为了发现和实践美德的过程,过于强调制定出来的制度的控制性作用,而忽视了人对制度变迁的能动性作用。制度的伦理维度就是重申人在制度中的主体性地位,选择制度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满足人过更好生活的需要。制度规范区别于道德伦理规范,但首先应该符合道德伦理规范,诺斯对制度的定义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5]3。
第三,从制度的演进看制度的内生价值。人们在对制度的崇拜和追求的过程中,为了走出“制度神话”的困境,越来越看到外在制度的不足。青木昌彦从内在规则的视角把制度理解为博弈规则,即“博弈规则是内在产生的,他们通过包括实施者在内的博弈参与人之间的策略互动,最后成为自我实施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思考制度的最合理的思路是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博弈均衡”[6]。把博弈规则看成包括实施者在内的一种演进的内在规则,有利于把传统的延续和人的主体性的参与有机结合起来,也只有从制度的构想和创设到制度的演进与变迁这一动态的过程中去全面理解制度,对制度文明的认识才是比较全面深入的。
第四,从实践理性看制度的博弈过程。制度的产生不是外在于制度之上的第三方制定的,只有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纳入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来,充分博弈,才能使得任何一方的意见不受忽视和利益得到体现,才有利于解决外在制度的困境——“谁来治理治理者”的难题。即“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他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5]225-226。类似,罗尔斯把基于相互性之上的规则和程序构成的社会关系称为“公平合作系统”。简单说,就是基于合理利益的关系博弈,不需要外在强制性权威,人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学会换位思考,尊重他人的同时就是约束个人的私欲膨胀。这种相互主体性的博弈过程,也有利于达成合作共赢的效果。这样制定出来的制度既有效力,又有效果。基于这些认识,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全面理解既打破了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也是使制度越来越回归其本义中去、越来越符合实际需要的必然选择。
五、制度文明、主体性与现代政治
从制度文明的累积看,制度经历了这样三个明显过程:选择制度化政治整合对现代政治合法性转型的意义、旧制度主义对制度理解的局限、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重新理解。尽管这一进程过于追求外在制度的可控性而易导致人的异化,但它一直朝着制度文明大趋势演进却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全面理解,在重视制度设计的同时,遵循制度变迁和演进的逻辑,既打破了“制度神话”的盲目崇拜,又有效地解决了所谓的“制度悖论”,即由片面追求“与道德无涉”的制度发展为制度与道德走向融合。
人们对制度的反思和认识深化的三个历程与现代政治观念史的变迁是一致的。当我们提起耳熟能详的现代政治价值时,诸如,公民权利神圣不能侵犯、政治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支配、政治反抗具有合法性、政治共同体差异性共存,我们应该明白,这些价值被普遍接受并以制度安排的形式真正得以保障实施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政治观念演进和变革过程的。每一次变迁都是人们认识水平提高的结果。启蒙运动把人与神区别开来,使我们能以人的眼光从人自身来赞美人,张扬人的主体性价值;但是,当“人定胜天”的人为改造自然的灾难一次次冲击人的“完全理性”能力时,人是万物的主宰的观念也受到全面质疑,在谈人与外界之间的关系时,人开始认识到人不过是个高级动物而已,人应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人不仅难以主宰万物,进一步讲,人在主宰自身时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诸如习俗、惯例、传统,还有社会交织形成的关系网和社会结构等,因为个人难以选择传统演进下来的生存境遇,退一步讲,尽管个人可以选择一些个人策略,但是个人决策也受制于他人的策略选择,这也要求人应遵循传统,与他人和谐相处。我们强调这种从宇宙到主体再到主体的内心世界的这种认识深化过程,反映到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正好体现了制度发展的三个历程的要求,对为什么需要过制度化的政治生活的追问有利于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上,这很好地体现了个体的主体性价值。然而,在对制度的诉求过程中,想通过制定一套完美的制度来治理整个人类政治生活,越来越寻求刚性的外在制度导致越来越陷入“制度的悖论”——“谁来治理治理者”,也导致统治者操纵制度的制定过程,使得人们越来越受制于制度的禁锢。寻求主体性价值的个人又被沦为制度、机构的奴隶。对制度的反思使我们对制度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也是“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拓展认识,把对制度的人为设计与制度的传统演进结合起来,既发挥人的理性能力,又保持对人的理性能力一,政治是人为建构的产物,政治并不神秘(为政治“除魅”);第二,制度具有日趋完善的可能性,正是人的理性能力的运用结果,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价值;第三,制度建构针对的是意见世界的纷争,既然每种意见表达都具有合法性,那么制度的建构就不是以先入为主的“自我中心”来设计,而是从相互性的视角来兼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第四,既然制度是人为建构的,那么制度就必须提供修错补正机制,因此,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应为制度变迁预留空间,对于习俗、惯例和传统等非理性因素对制度的演进所起的作用也应该引起足够重视。这种制度设计的理念才与公共领域复兴的当今道德回归政治生活的要求相吻合。
高度警觉的正确态度,保持对制度的参与和监督,在一种相互主体性的制度生成过程中,重申制度的伦理维度,更好地体现人的主体性价值。
这也与现代民主政治就是直面利益博弈的政治过程而寻求一种合理制度化安排的政治这一精神意蕴相适应。近现代政治最主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在过一种世俗化的政治生活中寻求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实现。因而,政治不仅要为探求为了过人的生活而寻求政治合法性,还要探求如何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寻求更加合理的制度安排,这样,政治生活就要探求主体性的个人如何与他人、与社会和与传统制度化共存的问题。
总之,政治制度的建构应内含这样几层价值:第
[1]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571.
[2]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4.
[3]秦德君.政治设计研究:对一种历史现象之解读[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4]盛洪.为什么需要制度[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51.
[5]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6]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2.
The Value of Temporary Politics in View of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CHEN Y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China)
The temporary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is based on a point of view that politics is a necessary devil.To guarantee that the right and obligation of the citizens are sacred and can’t be invaded,to supply the freedom of politics without lack and domination,and to make people regard themselves as“human bodies”and then live a political life principally,the in- stitutional fusion must be sought to dominate the state machine which is very gigantic.In this way,the politics can be thought as people’s composition,and a kind of reasonable,fair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 can be looked after by mean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This is the main rhythm of the temporary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And in fact,the democratic politics is to research how to reach a kind of reasonable,fair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 by the way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political game.The manmade institutional design,the point of view that the law embodies the purpose of sovereignty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doctrine are three phases of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And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change from the separation of the experienced pol- itics from morality to tight stick of them.This paper presents a clear perspective of the formulation and change of the contem- porary political value.By this means,it gives us a deep insight of temporary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life.Based on this,we can clarify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accumulate it.To seek a more reasonable institutional formulation based on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institution can serve for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s.
institution;reason;individual;political value
D521
A
1000-2359(2010)01-200542-05
陈毅(1979—),河南信阳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主要从事集体行动理论和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孙景峰]
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项目“博弈规则与合作秩序”(hzf-07010)
2009-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