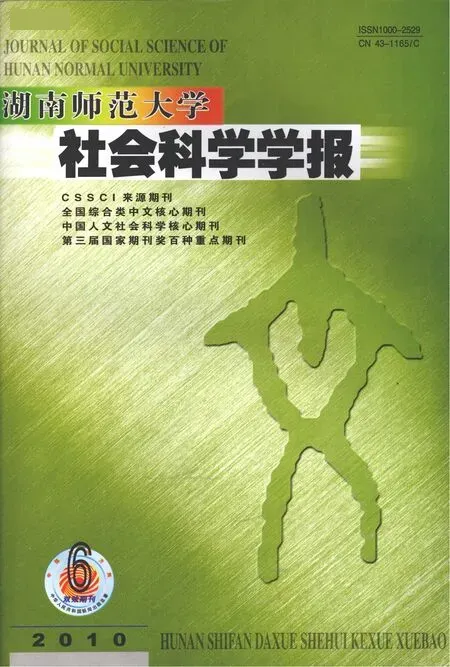疾病的隐喻与疾病道德化
孙雯波,胡 凯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疾病的隐喻与疾病道德化
孙雯波,胡 凯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疾病的隐喻和人类寻找意义的思维模式,使社会形成了对特定疾病或病患的道德评判和道德态度,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生态和道德统治的需要相结合,对疾病的道德偏见转变为行动上的社会歧视、排斥甚至社会压迫和伤害。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使疾病远离那些意义和象征,尊重和关怀患者,回归医学伦理的人道主义终极关怀,对促进健康和维护社会和谐意义重大。
疾病隐喻;道德评判;道德情感;道德态度
当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世界的图画”时,当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时,他们不仅是在以隐喻的方式谈论语言,而且是通过语言的隐喻性显示语言的张力,显示语言的形象性,显示语言对于人的本真意义。隐喻(metaphor)一词来自希腊词metapherein,即meta+pherein,大体可以理解为带到(字面的)后面。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Poetics)中指出:“隐喻是用一个陌生的名词替代,或者以属代种,或者以种代属,或者以种代种,或者通过类推,即比较。”作为修辞手段隐喻是指在本义域内词语间的替代关系,多指一个词(能指)以一种破除老套、非字面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目标物或动作(所指)之上,它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相似(对应)关系。[1](P429)隐喻的运用扩展了语词的空间和意义的场域,给语言增添亮色和美感,丰富语言的表现力和创造力。1936年语言学家理查兹在其著作《修辞哲学》中把隐喻从传统的修辞学意义中解放出来,提出思想隐喻观念先于语言隐喻观念,隐喻是思想的、概念的、经验的、无处不在的,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工具。隐喻不仅给语言带来生命的气息,而且给思想带来审美的自由。1980年美国著名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通过对大量语言事实的考察,提出“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在思维和行动中,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和概念系统从本质上来讲是隐喻的。”[2]他们主张隐喻的本质是一种跨越不同概念领域间的映射关系,这种介于概念实体间的对应,使得我们能够运用源域里的知识结构,来彰显目标域里的知识结构,因而隐喻具有这样的功能:令我们藉由某一类事物来了解另一类事物。学界对于隐喻的认识经历了从修辞学到语义学再到跨心理学、哲学、语用学、符号学等不同学科进行研究的几个阶段。通过他们的研究,揭示隐喻不仅仅是两个事物相似性比较的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一种意义的阐释,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的体现。
一、疾病隐喻与道德评判
在西方的分类医学里:“疾病具有与生俱来、与社会空间无关的形式和时序。疾病有一种“原始”性质,这既是其真实的性质,又是其最规矩的路线;它是孤立存在的,不受任何干扰,也没有经过医学的加工,它显示了自身本质如植物叶脉的有序脉络。但是,它所处的社会空间变得越复杂,它就变得越不自然。在文明出现之前,人们只有最简单、最基本的疾病。农民和老百姓接近于基本的疾病分类表。”[3](P1)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没有人能躲得过疾病的侵袭,但疾病在社会中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越了生理层面的具象意义,总有一些鬼魅般的阴影萦绕在疾病中,被附着上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道德和政治意义。正如苏珊·桑塔格所揭示的疾病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疾病隐喻暧昧表达我们的道德情感和态度,并做道德的评价,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它和人性的异化以及苦难的悲怆联系在一起,都是指向社会的压抑与焦虑的偏执,使对某种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疾病被道德化或政治化,使疾病不再是疾病本身,而是成为了一把衡量人的类别属性的尺子,这尺子因背后的国民性理念而即刻升华成为一种政治、道德的审判。不同疾病所包含的道德意义不同,并非所有的人类疾病都会出现道德评判现象,一般来说在当时社会被认为难以治愈、神秘莫测即人们缺乏了解的疾病,或者是具有强传染性,导致痛苦死亡的极度恐怖,或者跟性有关的疾病道德隐喻的色彩浓厚。
人类对特定疾病的道德渲染,那种寻找意义的思维模式使某一疾病所附加的意义,渐渐超越它的本名,武断地成为这个疾病的本质描写、文化上的意义和道德上的判断。疾病与患者的道德评判是指认为某种疾病及其患者是咎由自取,因为个体有道德缺陷才发生,或者是认为患特定的疾病是耻辱的、罪恶的、堕落的、肮脏的、羞耻的。在“隐喻”俨然面孔之后其实隐藏着诸如“健康=德行”、“洁净=德行”等无数隐蔽公式,而传染病人在被冠以“高危群体”的标签后自动成为“疾病=堕落”公式里的最受欢迎的填充物:他们要么象征着普遍的放纵,要么呈现着道德的松懈乃至政治的衰败。[4](P213)通常对传染性疾病,尤其是瘟疫的隐喻,被给予的“另外一个名字”,通常带有夸大、歧视的意味,使得透过隐喻去理解这个疾病的人,容易对疾病产生偏见、误解、贬抑和恐惧。疾病隐喻化过程实质上是社会个体或群体道德推理的过程,既是个体在推理规律制约下对利益关系不明的道德现有的举善思考,也是其道德信念的原则内容在思维中的具体演绎。疾病的隐喻是一种阐释和再创造,“在文本清晰明了的原意与(后来的)读者的要求之间预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而阐释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而为了解决这种不一致性,“阐释者并没有真的涂掉或重写文本,而是在改动它。”[5](P6-7)于是真相与原意就在各种被阐释的努力中日益模糊,“词”与“物”开始相互背离。患者不仅是生理病痛的受害者,更是疾病隐喻的受害者。在医学的X光透视和人类的想象阐释的双重努力中人身体的神圣性被消解,而患病者因而常被置于完全“物化”的境地,背负沉重的被歧视排斥的心灵压力,在疾病中沉沦。
在大量的流行性传染病中就充斥着丰富的道德隐喻。“流行疾病是社会混乱的一个普遍问题。‘传染’(pestilent)来自瘟疫(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它的象征意思是指‘对宗教、道德或公共和平的中伤’,意思是‘道德毁灭的或有毒害的’。对罪恶的感受被投射为一种疾病。”[6](P54)没有任何其他一类疾病像性传播疾病在病理现象和社会反应之间有着如此紧密复杂的关系。19世纪最经常被当作邪恶之隐喻使用的梅毒是继结核病后又一种声名狼藉的病灾,它不仅被看作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种令人羞耻的、粗俗的疾病。19世纪由于梅毒在欧洲的盛行,它成为了一种时代流行病,再变成了一种政治病。家庭和社会要么讳莫如深,保有危险的神秘,要么有意夸大其后果和威慑,医学再次成为帮凶,将病理学和道德混为一谈。“面对家庭解体和财空的危险,对性病的恐惧心理从此起了预防作用。它变成了精神卫士,代替国王派来看守的弓箭手,制止引起破产的放纵行为。”[7](P39)法国诗人、文学家波德莱尔说过“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都已经被染上了民主思想,就像我们都染上梅毒病体一样。”[8](P1)乐于把梅毒当作一种时代病可以缓解道德压力,不必为此感到羞耻。波德莱尔还把它与共和政治联系起来,暗示梅毒也是一种反叛的政治激情,凭藉某种幻想的政治意义来驱散其当初幻想的道德意义,使其由一个道德问题转变为一个政治问题。
由于艾滋病在起源、感染方式、易感人群及病症等方面的特殊性,社会对艾滋病的反应并不是完全由疾病的生物学特性所决定的,反而更多地受到社会文化对疾病的认知和传统价值观念影响,疾病本身和道德没有关系,然而当它和不道德的行为发生关联的时候,这样的修饰就难以避免。艾滋病特殊的感染途径与人类特定的社会文化行为相联系,包括特定条件下的性行为、吸毒者共用针头、输血、医疗性事故感染、(怀孕妇女)生产,哺乳等。患这种疾病的高危人群是妓女(或者性工作者)、嫖客、吸毒者、同性恋者,而这些人的行为在很多人眼中是不道德的。因而艾滋病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性放纵的结果,是极端个人主义和毫无节制享乐主义的产物,是对当今极度享乐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控诉。因而艾滋病便获得了一种象征,是一种承受严厉的道德评判而被社会高度道德化的疾病。人类性行为本身是为了及时行乐或孕育生命的,这两者差不多是织就生命意义的经纬,揭示了人的内在的道德诉求和本真的情感渴望。医学的进步曾使得人们无须承担性行为导致的后果,但艾滋病的出现却使得天平又摆向了另一侧,而作为生命的象征的血液和体液现在却成了污染的载体,对性的担忧当然使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安全感,对性道德的拷问又一次在艾滋病危机中重现。
二、疾病隐喻与道德情感
社会形成的疾病道德评判,决定了社会对特定疾病和病人的道德和情感。由人的社会性所决定,健康抑或生病不仅是社会个体自身的问题,还涉及和影响到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罹患传染性疾病,它绝对不是私人性的事件,既是个体的不幸,又无形中给社会、他人带来潜在的危害或是具有一份社会的责任。伴随着疾病的进程,涉及医学、伦理、社会文化等多因素相互影响和作用,整个社会呈现出不同的道德认识、评价、情感选择方式,构成了疾病患者与医生、与社会其他人之间的复杂道德关系和张力互动。患者本人或社会他者围绕疾病的发生、发展或痊愈,表现出深刻的情感体验和爱憎、好恶的情绪态度,它是主体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在处理相互道德关系和评价自己或他人行为时所体验到的心理活动。这种道德情感可从患者本人和社会外界两个方面表现出来。认识和掌握病人的道德情感和心理特点,有助于理解和帮助他们健全人格,保持健康的心态来战胜疾病,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共健康和人际和谐。
疾病具有丰富的人性色彩和社会意蕴。英国著名的伦理学家休谟在研究人性问题时曾说过:“凡是我们自身所有的有用的、美丽的或令人惊奇的东西,都是骄傲的对象;与此相反的,则是谦卑的对象。”[9](P9)他又指出:“身体的痛苦和疾患本身就是谦卑的恰当理由……对于传染别人并危害别人或使人不快的那些疾病,我们感到羞耻。我们因癫痫症而感到羞愧,因为它使在场的人都感到恐怖;我们因疥癣而感到羞耻,因为这种病是传染的;我们因瘰疬而感到羞耻,因为这种病通常是遗传的。”[9](P335-338)由于当时医学科学认识和治疗水平有限而无法解释病因或治愈,特别是某些当时无法治愈、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能留下不良预后的传染性疾病,不仅对病患本人身体健康及社会生活产生严重影响,同时又给其亲密接触者或周围的人带来疾病的困扰、痛苦甚至性命之虞,令人恐惧且使病患有失人格尊严。社会外界对疾病的情感态度是基于对特定疾病的道德认识和评判而体现出来。特别对传染性疾病,社会和他人因为感官上的不快和认识上的不了解而产生恐惧、厌恶、防备等道德情感,人人谈之色变或避之不及,纷纷在意识深处和现实生活世界空间中与之“划清界限”。而患者本身的道德情感也十分复杂,特别是传染病患者在治疗或流行病调查中涉及袒露身体和隐私,确诊病情严重的还要隔离治疗。由健康的人到病人,再到传染病人,伴随着身体上痛苦不适和生活世界的转换,患者本身心理上会发生一系列微妙的变化和心灵上的痛苦挣扎。病患会因为患病而产生谦卑、羞耻、不幸等道德心理,会因传染或影响到他人产生羞愧和内疚。1963年社会学家Goffman首先提出病耻感的概念,“羞耻感是个人的自我道德意识的一种表现,表示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动机和道德品质的谴责时的内心体验。”[11](P201)耻辱既可能源自外部的压力和凌辱,也可能源自对族类和个体生存状态的理性审思,而最后,总是要归结为内在精神的紧张和痛苦。
人类多种病症特别是艾滋病的出现,确实都与人类自身缺乏自我约束、过于放纵身体有关。似乎自然本身有一种道德约束,有一种对身体的自我保护,通过疾病告诫人们,以免不可救药。由此可见法规和道德控制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在西方,回归家庭,忠于一夫一妻制,远离异常性行为,杜绝各种恶习(如吸毒等)等保守主义热衷提倡的说教,终于又赢回了它的价值。病耻感的存在不同程度上会制约病者改变或摒弃不良的生活习惯,洁身自好,从某种意义上再一次体现了人类道德图式对生活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疾病所具有的一定正面制约作用。但过度、武断的道德评判,加上社会的渲染夸大,加诸传染病之上的道德意义带给病患的负面意义似乎更大。病耻感的存在使病患在身体病痛之外还须负担道德谴责的社会异样眼光,承受那些加诸疾病之上象征意义的重压,在他们看来,后一种痛苦远比前一种痛苦致命,因为它以道德评判的方式使患者蒙受羞辱。羞辱到严重的程度会挫败个体的归属感,把一个人从人类共同体中革除,使一个人失去了对自己生存的基本把持,从而导致患者失去治疗疾病的信心,失去生存的信心。
三、疾病隐喻与道德态度
由于疾病的隐喻,社会形成对特定疾病和病患的道德评判和道德态度,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道德统治的需要相结合,道德偏见转变为行动上的社会歧视、排斥甚至社会压迫和伤害。“‘歧视’被定义为‘基于种族、肤色、……语言、宗教……民族或社会起源,……出身或其他身份的差别而采取的区分、排除、限制或优惠,其目的和效果是为了消灭或削弱所有人在平等基础上对权利和自由的享有和行使。”[12](P447)按照这一定义,构成歧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存在差别待遇;2.这种差别待遇未经证明有任何客观、合理的根据或者追求的目标与采用的手段之间缺乏相称性。在这里“合理的差别待遇”或者“追求的目标与采用的手段之间的相称性”则成为判断是否构成歧视的关键因素。人类为保护自身健康,在遭受病魔侵害时,常常受宗教或迷信观念的支配,将疾病视为上天的惩罚,或躲避、驱赶,或关押乃至大批残杀和消灭那些被认为患了传染性疾病或瘟疫的个人、家庭、社群部落甚至整个人种,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曾不断发生。数千年来麻风病就像一记魔咒跟人类纠缠不休。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世界上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麻风病,麻木、溃疡和残废是患麻风病后无法避免的结局。由于病因成迷且病状奇特,由怕而无奈,由无奈而生恨,人类唾弃不幸染病的同类,把他们隔绝在人性和理性的围墙外。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的人们均把麻风病患者看成鬼怪,认为是命运、佛祖或上帝对有罪之人的天罚。生理上的“病人”变成了社会中的“罪人”,麻风病患者不仅要承受疾病的折磨,得不到同情和救治,还要受到社会的歧视,甚至还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和强权的迫害。历代统治者或教廷出于对无知的恐惧、丑陋的自私心理往往最终迁怒于染上麻风病的病人,采取非理性方式处置他们,甚至十分残酷地百般迫害,不是用火烧死,就是活埋或淹死。而最人道的处理方式则是把麻风病人放逐隔离在荒郊野外和无人居住的山谷、海岛,让其自生自灭。远离主流社会,物质和精神交流方面被孤立、冷落和抛弃,麻风病人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这种集中关押治疗的方法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和后遗症。如我国20世纪50-60年代建立的“麻风病村”,基本上属于严重污名化的社区。历史上隔离麻风病人的夏威夷群岛中的莫罗开岛,患者们如同饥饿的动物般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必须在岛上待一辈子,直到死亡,在那里没有希望,没有意义,没有时间,是一个为天堂而存在的地狱。尽管人类最终找到治愈麻风病的良方,解开了纠缠数千年的咒语,但一个人一旦被烙上麻风病的印记,送进“麻风村”,即使患者被治愈并恢复健康,但社会歧视仍附加其上仍处社会边缘,患者通常也很难再回到主流社会中去,连他们身体健康的子女也被烙上“麻风后代”的印记,在社会中屈辱地艰难地生存。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在其著作《颠狂与文明》中所说:“在麻疯病院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疑比麻疯病存留得更长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疯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疯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12](P4)
当今社会“乙肝”现象又再一次彰显某些人的科学上的无知和道德上的狭隘。据流行病学调查,目前我国有慢性无症状乙肝病毒携带者约1.2亿,而乙肝患者大约有3千万人。差不多10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乙肝肝炎病毒(HBV)携带者。乙肝病毒主要通过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和性传播,临床上常将HBsAg阳性而无任何症状体征、肝功能检测正常半年以上者(既往从无肝功能异常病史)称之为乙肝病毒无症状携带者。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不一定就是乙肝病人,在机体免疫功能正常的情况下,这些病毒或细菌一般难以发病。乙型肝炎不会通过食物或者平常的接触比如咳嗽、打喷嚏、握手、共同吃饭饮水而传播。权威的医学观点认为,这部分人除不能从事献血、幼托和饮服行业外,可照常工作、学习。乙肝病毒携带者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社交活动中不会对周围的人群构成直接危害。
由于缺乏科学的医学知识和社会舆论不恰当的过分渲染,加上部分人狭隘的道德心态。目前,我国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面临着入学、就业、婚姻等诸多方面的困难,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劳动的权利被剥夺,他们在婚姻方面屡屡受挫。因为得不到正确的有关医疗信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他们还要花巨额费用做无谓的治疗。来自社会的莫名的歧视和非难使他们苦不堪言:在幼小的时候,无法进入幼儿园上学;因为乙肝携带,即使考上大学、研究生、博士,无论成绩有多优秀,许多学校都不会接纳;因为乙肝携带,就业的门槛对他们来说高不可攀;因为乙肝携带,必须面临被单位辞退而加入失业者的行列;因为乙肝携带,在婚姻的路上,一路荆棘等等。绝大多数人害怕自己HBVER身份的完全暴露而给自己引来更多歧视的目光,他们放弃了抗争,默默忍受着贫穷、孤独、屈辱以及求学求职道路上的磨难。在平等权、工作权、受教育权、隐私权等遭到严重践踏的情况下,沉重的生存压力使他们一些人面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一些人陷入绝望的境地,社会和自身造就的压力也改变了他们的性格、人生观和命运,小到失去工作,失去朋友,大到报复杀人和自杀。这种社会歧视的根源不是单纯的某种差异,不同于种族和性别歧视,因而具有更强的穿透力和更复杂的伦理意义。
隐喻是开放的。它既向语词的更新开放,又向人的想象和思想开放,更向变化着的生活本身开放。隐喻活在语义的更新中,活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和诠释学的重要代表保罗·利科(PaulRicoeur)一度致力于对隐喻问题的综合性研究,提出了“隐喻的真理”概念。对他来说,只要人抽象地思想,只要人以形象性的语言去表达非形象性的观念,人就进入了隐喻。隐喻以似乎不太合乎逻辑的方式传达着准逻辑的真理。换言之,隐喻并非与真假完全无关,它也以间接的方式显示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不同的阶层与人群为达到各种意图而将疾病隐喻化,这样的隐喻被人们逐渐接受,成为了生活常态。疾病隐喻看起来如此自然而然、浑然天成,但事实上它是一种与以己论人、以心定仁的思维方式有关的带主观臆断的投射推理,如同能指到所指的表意作用一般,具有任意性,而且它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可视为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反动,危害不小。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和联想所塑造的隐喻一直都在遮蔽疾病原本的真相。在我们的身边以隐喻的方式阐释疾病,使之成为某种社会共同想象的意象的过程仍然在继续。苏珊·桑塔格说:“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8](P5)
“疾病本身是无辜、无罪、无恶的,辜的是我们的心灵,罪的是我们的意识,恶的是我们的思想,或者说辜的是我们的历史,罪的是我们的文化,恶的是我们的现实。”[13]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8](P161)使疾病远离那些意义,那些象征,尊重和关怀患者,虽不一定能直接帮助他们减轻疾苦和苦难,至少可为他们的生存在学术上作见证,为他们的命运作道德哲学的探索,“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8](P161)
[1]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Lakoff,G.and M.Johnson.1980.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黄集伟.你走神不如我走神[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5][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6][美]B·维纳.责任推断:社会行为的理论基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法]皮埃尔·德·格拉西安斯基.性传染病[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
[8][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 巍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9][英]休谟.人性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
[10]曾钊新,李建华.道德心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
[11]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国际人权法教程:第一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2][法]米歇尔·福柯.癫狂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M].北京:三联书店,1995.
[13]毛喻原.疾病的哲学[EB/OL].http://hexun.com/myy5566/default.html.
The Metaphor&Morality of Diseases
SUN Wen-bo,Hu Kai
(Th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13,China)
The thinking mode of the metaphor of disease&the content of human looking for,which is making society forming the moral judge&attitude of definite diseases,combined with the demand of politicical ecosystem&moral control during the definite history period,and more which is changed from the moral prejudice of diseases to the action of social discrimination、exclusion,and even the social oppression&harm.It is significant to promote health&protect social hamony,through to reveal、critcize、canvass to the limit,making the diseases away from the significance&symbol,respect&care patient,recur the humanism ultimate care of medicinal ethics.
disease metaphor;moral judge;moral emotion;moral attitude
D091
A
1000-2529(2010)06-0043-04
2010-05-25
孙雯波(1967-),女,湖南澧县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胡 凯(1952-),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