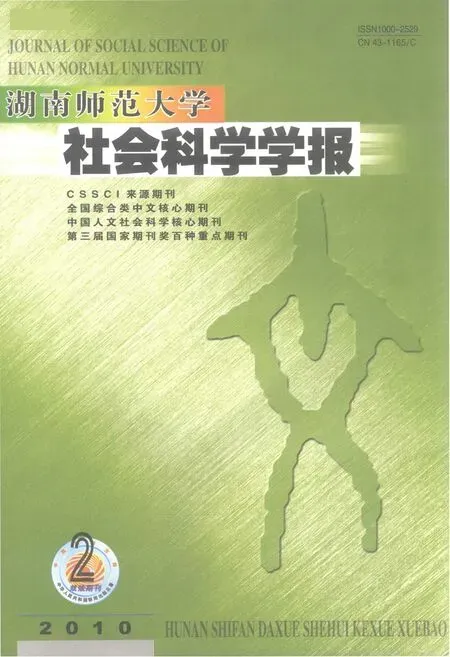神的解体与神性招魂
——论中国现当代作家与巫文化
易瑛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神的解体与神性招魂
——论中国现当代作家与巫文化
易瑛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在文化的边缘地带孤独行走的中国现当代作家,深刻表现了原始神性被消解后的文明之痛和自然生命解体后的人性之忧。他们召唤着自然人性与巫术仪式的回归,让在理性中迷失自我的现代人恢复对自然的信仰与敬畏,重建人与自然谐和的精神乐园,实现重造国家民族文化的目标。
神性;人性;巫术仪式;文化重建
在沈从文、迟子建、阿来、郭雪波、乌热尔图的文学创作中,“神”或“神性”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语,但其内涵非常丰富,使我们很难对“神”或“神性”作一科学的界定。尽管作家对“神”和“神性”的认识并不统一,对“神”和“神性”的概念也缺乏明确的界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所说的“神”并不指涉某一具体的神灵,而是用来描述他们心目中自然的神性和“有神的人性”的一个诗意的表达。
沈从文等现当代作家在作品中,精心营造了一个可以供“神”居住的空间。它们是沈从文《边城》中神性之“边城”,是迟子建《微风入林》里的“罗里奇”,是郭雪波《银狐》中人与银狐相互追逐嬉戏的瑰丽诱人的大漠,是阿来《遥远的温泉》里的梦中温泉……它们都地处偏远,风景优美,保存了原始的淳朴与野性,人性健康、朴素、优美、自然。然而,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作家营造的神性空间开始出现解体,自然之神的地位已经动摇,诗意的世界走向功利化。在“神性”行将远逝的时代里,作家们建构的闪耀民间宗教信仰的神性之光的空间,已经成为了靠文化记忆打捞的碎片,虽美丽却令人忧伤。他们书写的文化的边缘地带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格很难被化约到主流文化之中,反而遭到了20世纪理性文化粗暴的批判和强制性改造。文化的衰落和即将逝去的命运,使他们对生命神性的书写,被涂抹上了一层感伤忧郁的色彩。
一、神性丧失后的文明之痛
“文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现代文明无疑是一种进步和开化,它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文明也造成了人的生命力的萎缩、自然美德的丧失、生命意志的脆弱。对于现代文明造成的人的异化,沈从文等作家都保持着一种警惕,并在作品中对都市文明对边缘文化的渗透和侵蚀进行了批判。
沈从文《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里的北溪村,在外来文明入侵前本是一个人间乐园,但在外来者的暴力冲击下,善良置换为堕落,勤劳置换为懒惰,真诚置换为欺骗,神置换为大王。为了保存家园,逃避“此后族中男子将堕落,女子也将懒惰”的现实,七个男子逃到山洞作了“野人”。最终七个野人遭到了外来者的剿杀。外来者带来了捐税、鸦片烟、乞丐、娼妓、盗贼、谎言等,北溪村文化走向了破碎。
与北溪村的命运一样,迟子建的《采浆果的人》也讲述了金井村这个充满神性的“边城”在外来商业文明的冲击下,其乡村生活的原始神性被消解,原始文明走向溃败的悲剧。“金井”是一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农庄,人们过着与自然合一的宁静而朴素的生活。然而,“一辆天蓝色的卡车”打破了这个小农庄的宁静。在“卖浆果换现钱”的城市商人的鼓动下,正在忙于秋收的村民们竟然扔下手中的农具,奔向森林河谷采摘浆果去了。在人的神性丧失后,金井村处处充满了不祥。果真,一场大雪悄然降临,大地全部冰冻,金井人一年的收获都被掩埋在大雪之下。
除了外来文明对自然生命的侵蚀,民族文化本身也蕴藏着重重危机。沈从文在批判现代文明对于自然人性的压抑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1](P59)。《丈夫》里,婚后不久的妻子到城中做妓女,丈夫留在乡下种田,妻子每月将她的卖身钱送给丈夫;贵生真诚地按古老民俗求婚,却在金钱和权势面前遭到失败(《贵生》);萧萧生命不能自主的悲剧仍在代代轮回(《萧萧》),这些都预示了原始、自由、蒙昧的生命形态已逐渐丧失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环境。在现代文明的入侵和本土文化隐藏着的文化危机之下,生命的神性在走向消失。
与湘西苗族文化的命运相似,迟子建、乌热尔图关注的鄂温克族文化也在渐行消亡。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一个在丛林中生活了近百年的鄂温克族部落在现代文化和工业文明侵入、生态遭受严重破坏下,被迫走出了山林的命运。这个部落最后一个萨满——妮浩萨满的死亡,表明了信仰万物有灵的民族与大自然、人性与神性沟通交流的桥梁被切断,神性的空间不复存在。选择告别城市、回归自然的画家依莲娜也无法重新找回昔日人与自然合一的神性,她在历时两年完成一幅萨满乞雨图后投河自杀。
乌热尔图身为鄂温克人,对于族人对民族传统坚守的悲剧和民族文化衰落带来的痛楚感触尤深。森林在减少,野生动物在消失,依赖森林生存的民族也在改变。成为旅游者观赏对象的达老非萨满在悲愤中出走,他选择栖身于幽暗的熊洞里,从容地葬身于大熊的腹中(《萨满,我们的萨满》);火烧光了山,卡道布老爹死后连风葬的树林都已不复存在,他临死前悲哀地请求“我”:“你让我顺水漂流”(《你让我顺水漂流》)。这些“最后一位萨满”的命运,预示了民族的文化走向了解体,“一个被遗忘的民族,一种正在消解的文化,一种精神信仰,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日渐消亡。”[2](P51)
民族文化消亡的危机,民间信仰失落的现实,使沈从文等作家创作的作品浸润着灵魂的孤独、感伤和悲壮。他们吟唱的是自然的颂歌,是现代性冲击下民族文化无可挽回走向衰落的挽歌,也是无可避免被主流文化同化下努力寻找本民族文化属性的悲歌。
二、自然生命解体后的人性之忧
现代都市文明的渗透和本土文化的危机四伏,使自在的诗化生命逐渐消失。人渐渐远离了大自然,也渐渐失去了与自然相连的本真,金钱、门第、等级等观念开始腐蚀人的灵魂,“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自然生命形态开始解体。沈从文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说:“地方的好习惯是消失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像汉族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是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东西了,……”《丈夫》中的乡下妇女自进城到船上做皮肉生意后,“慢慢地变成为城里人,慢慢地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有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边城》中翠翠的爱情最终以悲剧告终。尽管有命运的偶然性因素,但现代文明的实利和交易原则对“边城”的渗透也是造成悲剧的原因。到沈从文1938年创作《长河》时,他对现实的堕落、人性的变异等表现出一种内心的焦虑。“好看的总不会长久”正是沈从文在体悟到“神在生命中”的常态很难维持,“常”在现代社会里趋于“变”,理想生命本身极其脆弱之后发出的感叹。
迟子建的小说也绝不是只有温情与和谐。在《白银》那里,因利益的争夺,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谊逐渐丧失。《零作坊》中,女老板对那位被车撞成重伤的伙计不闻不问,导致其他伙计对她的寒心,作坊最终分崩离析。《雪坝下的新娘》中充满人性之恶的现实世界更让人感到刻骨的悲凉。
郭雪波则着力表现人在丧失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之情后,开始以自我为中心,疯狂地破坏大自然的植被、肆意掠杀动物的残忍、贪婪。人类也为自己对自然犯下的罪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漠狼孩》的悲剧,是人类对狼的疯狂剿杀使母狼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所致。《沙葬》中出现可怕的热沙暴,源于人类对草原植被肆意破坏和过度索取导致了草原沙化后产生的恶果。
神性解体后人的恶欲膨胀的悲剧,在阿来的很多小说中也得到了表现。阿来《鱼》写藏族的古老文化传统中保留了对自然神的崇拜,吃鱼成为藏族人的一种禁忌。但是,在20世纪的后半叶,藏民都开始吃鱼了。不太爱吃鱼肉的“我”也开始钓鱼。古老的民间信仰褪去了它神秘的色彩,自然所具有的神性走向荒芜。神性的失落使人性走向了变异乃至疯狂。《天火》里,机村人祖祖辈辈信奉自然神,相信色嫫措湖里的那对金野鸭能保佑他们永世的平安。但是,“革命”来了后,“新的世道迎来了新的神”,机村呼唤火神、风神的巫师多吉被捕,神湖被当成妖湖炸掉来灭火。当漫天的大火在无情烧毁森林时,也在烧虐着人心和人性。机村人开始疯狂地偷窃外来救火者的东西,神性解构后人性异化的图景让人触目惊心。
失去了人神合一的民间信仰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鄂温克人的先辈将这种回报的心愿祭献了山神,可山神啥模样,现在连孩子都不信了。”(《丛林幽幽》);达老非萨满为陌生人披上神袍,满足的是异族人猎奇的欲望。他那件象征着超常、神秘的自然力的萨满神服,被同族人偷走廉价卖给了城里的博物馆(《萨满,我们的萨满》)。萨满的被遗忘,预示着自然生命的解体。失去了对自然的热爱和敬畏的人类开始疯狂地掠夺自然,“山上的树全让他们干倒了,横在地上,像一堆死尸”,而保护他们的森林家园的猎人却被暴打致死(《悔恨了的慈母》)。乌热尔图为自己的民族失去了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而悲哀,为现代人人性的堕落而痛心。
“人永远离不开森林,森林也离不开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神性时代何日能重返?作家们在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中揭示了神性解构下人性变异的悲剧,也在对民族古老的巫文化的追溯中,寻找重返人与自然的神性的路径。
三、神性的招魂:自然人性与巫术仪式的回归
神的时代离人渐行渐远,这些身居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深情地呼唤神的归来。他们发现了巫文化“万物有灵”、“人神合一”的观念孕育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的乐园。无论是南方的巫傩文化还是北方的萨满文化,都具有原始拜物教信仰的特点。原始拜物教相信“万物有灵”。“万物有灵”并非对自然的臣服和对自我命运的放弃,它是人类渴望与自然沟通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积极行动,是人类向大自然表达尊重和感谢的心理诉求。它有效地抑制了人的狂妄、贪婪、残忍等,张扬了人要用超自然力量控制外界的自信,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和谐,人释放焦虑和满足自身需求的祈愿。这种原始的思维方式造就了特殊的生命形式,即人性率真自然,达到与自然的神意合一的生命状态。
首先,人们在有神的时代,都能保持一颗单纯的心灵,享受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按自己的本性自在地生活。
自然人性的最高表现是“神性”。沈从文在《边城》中营造了一个自然朴素的“神”的国度。翠翠生活在纯净的大自然中,生命与自然已融为一体,成为爱与美的神的化身。撑渡船的爷爷白发如银、宽厚大度、忠于职守,船总顺顺重义轻财,杨马兵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傩送、天保质朴勤劳、正直自尊,他们都是“自然之子”,与自然融合无间,生命的单纯、庄严,与宇宙之间具有微妙的感应,放射着神性的光辉。
乌热尔图的多篇小说里,充满神秘和庄严感的老萨满选择在大自然中从容走向死亡,这是萨满“为自己安排的富有启示性而别具特色的归宿”。郭雪波的《银狐》结尾描绘了一幅人与兽都融入大漠的神奇图画。人与自然的融合,被涂抹上梦幻般的色彩,它为心灵迷失的现代人指出了一条皈依萨满教义、回归自然怀抱之路。
另外,与自然合一的生命形式显示出蛮强野性的原始生命力。沈从文笔下的虎雏、柏子、贵生,迟子建笔下的土匪胡二、鄂伦春猎人孟和哲、乌热尔图笔下的熊娃等都是具有原始野性的生命强力的人。他们性格外露,粗野蛮悍,坦率重义,充满了原始的蛮力之美。他们摆脱了金钱物质的功利交易,也不受道德规范的束缚,在与自然的契合中,拥有优美、健康、自然、合理的原始情欲和性爱。
沈从文、迟子建、乌热尔图书写的性爱,不受道德法则的束缚,不受金钱物质关系的牵制,它们随着自然的律动而与自然融合,充满着纯净、神圣、庄严。沈从文《夫妇》中,那对夫妇受春光感染,忍不住在野外寻欢;《雨后》中的四狗和“阿姐”、《采蕨》里的阿黑和五明,都是在春雨后暖和的阳光下忘情地做了一点傻事。迟子建《逆行精灵》中的“鹅颈女人”的身体的欲望和大自然的呼唤相互呼应,在与自然相契合的性爱中体验到本真、自在的生命状态。《微风入林》中,能拯救女医生方雪贞的人是自然的象征——鄂伦春男人孟和哲。这种自然的生命力进入了方雪贞的体内,让她“自己也感到像一株植物了”。乌热尔图《丛林幽幽》中的“熊娃”额腾柯在性爱方面表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精力”。
沈从文等作家对于性爱的描写,表达了他们对健康、活泼的生命、合理的人性的思考。礼赞摆脱固有道德的约束、回归自然和本真的人性,潜藏着作家对人性异化、生命力萎缩、情感苍白虚假的现代人具有的种种人性症候的否定和批判。作家们试图用原始野性的生命力来对抗封建文化和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摧残,让文明容纳野性而充满了强健的生命活力。
其次,对神性的召唤,也是对巫术仪式的召唤。人要返归自然,回到有神的时代,仪式是重要的通道之一。重视巫术仪式的描写,成为了行走在文化的边缘地带的作家们的共同特点。
仪式(ritual)又译为仪典或礼仪。当前对仪式的定义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日本宗教学者竹中信常在《宗教学序论》一书中提出:“礼仪应该是使人接近神,形成一条沟通由神到人的道路。”[3](P420)人们通过一定的程序、规则的操演,表明神的存在,即“宗教的各种仪式,入世礼、丰收仪式、图腾仪式、食物尝新的仪式……多意在使人类的生活与行为神圣化、规范化,从而成为一种最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力量”[3](P442)。另一方面,与“人的神化”同时并存的是“神的俗化”。人以象征性的语言和动作表示对神的依赖和敬畏,“神在接受人的礼拜、献祭以后,也对人的祈求表示自己的态度,作出反应和回报。这是神趋向和接近于人的过程,有些宗教学者把这称之为‘神的俗化’”[3](P420)。
仪式是巫术活动的主要形式。巫术仪式包含了“人的神化”和“神的俗化”这两方面的内容。人们在由巫师主持的种种巫术仪式中,感受到仪式的庄重、神圣,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的虔诚和敬畏,实现了人意与神意的合一。
沈从文的《神巫之爱》、《凤子》、《长河》等小说比较完整地描写了巫师请神——迎神——娱神——送神的傩祭仪式。傩属于巫文化的范畴,是源于远古的一种驱邪纳吉、禳灾祈福的祭祀性巫术活动。《凤子》描写的整个傩祭仪式中,“神”已经来到了人间,它和人间的生灵一起受到热情的“款待”,一起“观看”庄严又欢乐、轻快又诙谐的表演,一起“陶醉”于巫师跳傩的歌舞中。群众与神同娱同乐,向神表达感谢,并期待再次得到神的赐福。生命在“神性”烛照的社会中富有生机和活力。沈从文正是从苗族祭神的仪式里,看到了“神之存在,依然如故”,神尚未完全解体。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写到鄂温克族人为猎杀的熊举行风葬的仪式。乌热尔图《丛林幽幽》诗意地描写了鄂温克族风葬的象征意味,“那高耸的风葬架象征着木排,载着告别阳光的灵魂,顺着氏族的河流而下,漂向最终的归宿地。”阿来《随风飘散》里描写了为死去的兔子举行的火葬仪式。《天火》中,巫师多吉烧荒时吟唱颂歌和举行跪拜等仪式,庄严而神圣。郭雪波《沙葬》里云灯喇嘛平静地等待沙葬的降临。在种种仪式中,人向神许愿、还愿、祈祷等,完成了人与神的情感的交流。
仪式是一个部族区别于其他群落的文化标签。仪式的复现,既是对庄严神圣的情感的呼唤,也是对仪式中蕴藏的本民族已经逐渐失落的文化的招魂。对仪式的召唤,成为了少数民族作家标识自身民族身份的重要途径。在外来者的眼里,图腾崇拜、原始宗教、巫术仪式等被归入原始、野蛮、迷信和非理性之中。但是,在沈从文、乌热尔图、阿来、郭雪波等作家看来,它们恰恰是作家对民族文化祭祀和追认的手段。沈从文用大量文字描写了苗族赛龙舟、跳傩、行巫、赶尸、落洞等仪式。他希望把由湘西人朴素的原始宗教情绪升华出来的宗教精神推及到所有的人,推及到整个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内部“人与人关系的重造”[4](P7)。对民族古老文化和历史真实的叩问,使乌热尔图发现了鄂温克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共同的精神资源——萨满文化。阿来则着重书写藏族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撞下出现的失语、变异和衰落。在他看来,原始宗教、巫术仪式等是确认民族身份的途径。郭雪波将萨满教作为蒙古族人精神的集中体现。他在《大漠魂》中,浓墨重彩描写了萨满教的女巫荷叶嫂唱安代歌舞这种古老的驱鬼避邪、祭天拜神的巫术。他们都深入到民族记忆的深处,一次又一次召唤着仪式的复归,一遍又一遍重申着本土民族文化经验。
对神性的召唤,使沈从文等作家对仪式的描写,已不同于20世纪启蒙作家对仪式的叙写。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祝福》、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台静农的《拜堂》、《红灯》等作品对祝福、冥婚、拜堂、放河灯等仪式的叙述,仍服从于启蒙的话语逻辑,指向对乡村民众愚昧、麻木、迷信的批判。作家们从启蒙立场出发,将仪式视为民众丧失主体性、愚昧僵化的劣根性的集中体现。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巫术仪式被视为三仙姑式“装神弄鬼”的封建迷信的代名词。并且,对巫术仪式的书写被置换为对“革命仪式”神圣化、权威化的描写。对科学理性和革命功利性的张扬,使人与神沟通、人向神表达情感的仪式被视为迷信愚昧之举加以强行压制和剿杀,巫术仪式中人对自然之神的敬畏之情被“人定胜天”、人是宇宙的主宰等观念所取而代之。沈从文等作家对仪式的大量描写,显然区别于20世纪崇尚科学和理性为主导的作家所持的启蒙立场。他们对仪式的召唤,让人们重新思考现代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关系,让在理性中迷失自我的现代人返归人性的原始、本真,恢复对自然的信仰与敬畏,重建人与自然谐和的精神乐园,最终实现重造国家民族文化的文化目标。
总之,沈从文等作家对神性的招魂,并非要重返原始、蛮性的社会。他们对非主流的民间巫文化的认同,与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的文化立场相关。现代性推崇和强调理性,去除宗教和神魅。但工具理性的扩张和渗透导致人的异化,祛魅后人的狂妄自负带来种种不幸和灾难。正是从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的立场出发,作家们回到了乡土民间,以边缘来改造中心,以地方传统来改造城市文明。崇尚原始,返归自然,神性复出,更多是作为一个关于人类历史的现代寓言,给在现代社会迷失的人指出一条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
[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 季红真.众神的肖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篇(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4]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Disintegration of Divinity and Evoking Divinity——On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riters and Wizardry Culture
YI Yi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Some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riters who walk alone in the culturally marginal zone represent their agonies for civilization and their sentiments for humanity after the primitive divinity and natural life have been all disintegrated.They try to evoke the return of natural humanity and wizardry rituals,to recall the modern human beings belief and awe to the nature lost in reason,and to reconstruct the spiritual paradise of balance and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or the purpose of remolding the national culture.
divinity;humanity;wizardry rituals;reconstruct the national culture
I206.7
A
1000-2529(2010)02-0107-04
(责任编校:谭容培)
2009-06-12
湖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07K013);湖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民间宗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
易 瑛(1972-),女,湖南岳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