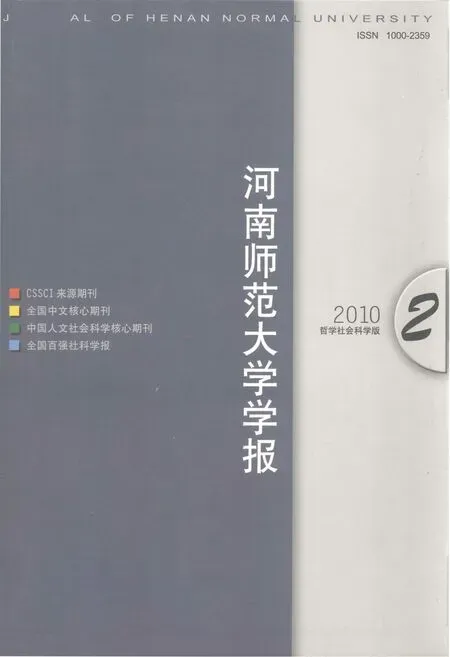通往现代之路
——以惠特曼、威廉斯为研究对象
武新玉
通往现代之路
——以惠特曼、威廉斯为研究对象
武新玉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234)
惠特曼与威廉斯,是近代美国诗坛最重要的两位诗人,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诗学联系。惠特曼具有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超前意识,威廉斯则开创性地运用多种艺术技巧,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现代派诗学,使美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们的出现对于近百年来美国诗歌由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内在诉求;语言艺术倾向;形式创新;多艺术融合
一、诗歌艺术的内在诉求
惠特曼诗学的核心,可以说就是他在《草叶集》出版序言中宣布的“现实与灵魂之间的通道”。他说:“大陆和海洋,植物、鱼类和禽鸟,天空和星体,山岳和河流,这些都不是小题……但人民所期待于诗人的,不只是指出那些无言之物所常常具有的美好尊严而已……他们期待他指出现实与灵魂之间的通道。”[1]147惠特曼认为,“诗歌的目的在于自由地表达激情”,而激情和灵感则要“深入到当前的生活潮流和实际中”去寻找,“观察,亲近,用直觉,用自然所表现的外形和形状,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历史与现实中强烈情感的实际表现……使用这些,并抓住其中的实质……这便是形象创作的才能,可以与物质创造媲美,相匹敌,甚至超乎其上”。这就是惠特曼的诗学核心之“表现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名浪漫主义诗人,他却非常强调客观现实的地位,指出:“歪曲真实形状或虚构超自然的存在物、环境或偶然事件……那真是令人厌烦和作呕的行为。”[1]147在这里,惠特曼实际上已经接近关于艺术来源于现实、反映现实乃至忠于现实的观点,形成了高于一般浪漫主义的创作论。但作为浪漫主义诗人,他同时重视内在的体验,认为“只有狂热的幻想才能从那些已看见的东西中看到尚未出现的东西”。诚然,在诗歌的创作中惠特曼强调所要凭借的是“狂热的幻想,天才的神性魔力”,这与现实主义仍不完全一样,甚至有所矛盾,但这样一种矛盾的存在也正体现了浪漫主义诗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现代主义的一种诉求。从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新型的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是在从实际出发向未来进行着大胆探索。
惠特曼在《草叶集》出版序言中写道:“美国诗人的表达手法将是卓越而新颖的。那将是非叙述和史诗式的……因为在这里,主题富于创造性又具有远景……能在至今还没有实际形状之处看见未来坚实而美丽的形状。”[2]可以说惠特曼自己一生都在向往着这个未来的远景,甚至往往立足于未来看待当前和过去的“现今”,并为此提倡“未来诗歌”[3]。
作为美国诗坛的领军人物,惠特曼对未来诗歌的探索精神影响到很多美国诗人,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威廉斯。虽然后者所处的时代与前者相距甚远,但二者在诗歌创作的思想方面契合很多,称惠特曼为威廉斯一生钟爱的诗人也毫不为过。早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的时候,威廉斯就对惠特曼的《草叶集》爱不释手,并为诗中洋溢着的“粗放力量”所叹服,《草叶集》中惠特曼的那种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态度”也深深地感染和触动着威廉斯并直接影响了他对诗歌创作的基调和主题。在惠特曼的影响下,威廉斯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一首诗”[4]26。这也正是现代主义达达派艺术家杜尚的观点——一个普通的事物也能成为一件艺术品,只要将其加以重新组合和进行陌生化处理。威廉斯试图从一个能细致观察任何事物的理性观察者的角度去揭示那些日常生活中被我们所忽视或者所忽略的事物,比如其代表诗歌中的“一辆红色的手推车”“破碎的玻璃瓶”“救火车上的数字”等。这样的思想最终发展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客体派”理论。
二、诗歌语言的艺术倾向
惠特曼在《草叶集》出版序言中说:“艺术的艺术,表现手法的精彩和文字光辉的闪耀,全在于质朴。没有什么比质朴更好的了。”与质朴相关的是自然,他指出:“在文学中,只有以动物行动时那种端正和漫不经心,以林中树木和路旁花草的情操那样的清白无瑕来发言,才是艺术的上乘。”[5]
惠特曼在艺术表达上,主张质朴自然的另一个提法,是坚持经济和坦白的原则。他要求语言简练,词意率真,在语言的选择和锤炼上下工夫。他在谈到选择词语的标准时说:“我喜欢那些能精确形容其对象的字眼。如果一个丑陋的字能够说明更多的含义,我就宁愿用它而不用美丽的字。”他又说:“言词的长处在于它的敏捷和必要性——击中要害而不迂回累赘。”而且,“在诗歌、讲演、音乐创作活动中,那些没有说的话和那些说了的同样重要,包含着同样丰富的意思”[6]。
总的说来,惠特曼重视从工厂、农场和码头等民间语言中吸收营养,喜欢将俚语、土语和印第安语写入诗中。而且,惠特曼受超验主义语言理论的影响,认为事物原是象征,词语又是象征的象征,要完美地使用词语便得使用事物本身。与此同时,他又企图跨越语言的限制,进入它所能引起的气氛即精神境界中去,如同超乎肉体达到灵魂世界那样。但在实践中,惠特曼的语言实验并没有得到最理想的结果,他的语言一方面有着罗列事物的现象,另一方面又有抽象化的倾向、概念化的倾向,其结果反而与诗人务求词语本身即能嬉笑怒骂的初衷相距甚远,有碍于诗歌艺术力量的发挥。
有批评家指出,威廉斯是在继续由惠特曼开始的诗歌语言革命,他一直在探求的是如何从本土发掘诗歌的主要动力,以深化惠特曼的诗歌语言实验。为此,威廉斯于1925年出版了《美国性情》这部散文集,通过重新挖掘美洲大陆的历史,鼓励美国艺术家在作品的创作中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认同感,建立起以美国方言为主的美国自己的诗歌传统。同时,由于受到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影响,威廉斯又将这样的语言观上升到诗歌创作的高度。威廉斯在论述艺术家与孕育其成长的土地之间的关系时认为:“艺术家不必也不可能试图详尽地描绘整个宇宙,而应专注于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个体之间的简洁、直接的联系,从而去体现普遍性的意义。”[7]174“事实上,除非建立在地方性之上,不可能有普遍性的文化——我多年来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普遍性只寓于地方性之中。”[8]换句话理解,在威廉斯看来,为了表现普遍意义上的美国,艺术家的创作可以而且应该与某处特殊的、为其所熟知的地方相关联。而这“地方”,在威廉斯毕生的创作历程中就特指为他的出身地——鲁瑟福德,一座位于新泽西州的典型的美国小城镇。
三、诗歌形式的创新
在诗歌形式发展史上,惠特曼也是一位著名的探索者和创新者,一位反对陈旧传统的严厉批评家。他的批评是根本的、彻底的,全面否定了以音节、重音和脚韵为基本要素的诗歌格律,而代之以奔放自由的艺术形式,即所谓惠特曼式的自由诗体。
惠特曼诗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诗的特性并不在于韵律或者形式的均匀”,因为它所要写的“不是事物和它的表象,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精神”。何况宇宙万物多种多样,它们不需要机械的、外表的规律和统一。诗歌为了传达自然的创造力及其丰富多样性,必须抛弃传统的模式,创造一种新的能表现其内在和谐的格调。这种格调是民主的和泛神主义的,它带有无限宏伟的宇宙性和原动力特征,能与人类灵魂相适应。惠特曼引用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的观点指出:“一切独创性的艺术都是自动调节的,没有哪一种能从外部加以调节。它具有自己的平衡能力,毋须从别处获得这种力量——它以自己的血液维持生命。”[7]108尤其是诗歌,惠特曼说,“它的法则和领域永远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因此它的节奏也只能从内部产生,在内部调整,而不能以某种形式从外部强加于它。这就是惠特曼的“有机韵律”说。布罗斯据此加以发挥,把传统的韵文形式看作一件“紧胸衣”,说它“对于一个美好的身材没有多少修饰作用,反而一定会妨害它,因为它只能遮掩缺陷而束缚丰满的体态”[9]。
威廉斯赞赏惠特曼的自由诗。正像惠特曼把生活看成一个过程和不间断的运动一样,威廉斯的自由诗首先也具有所有自由诗的一般性原则,如采用开放的、即兴的形式去表现诗歌的主题与意象,尽量避免相邻两行出现同等数目的音节,避免重音分布的趋同,避免无意出现的尾韵等。如在诗歌《幼橡树》中,诗人以“我必须告诉你”为始发点,一气呵成地向人们展示出即便是一棵“只有两个/长满古怪树瘤的/树枝/向前弯曲/长在树顶/如角然”的小幼橡树,也依旧生机勃勃、孕育不息。对于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变化的世界当中的现代派诗人,那种开放的、不完整的诗歌形式无疑更适于情感的延续与表达。
惠特曼自由诗体中的两大创作特色当属对句法和目录诗。所谓对句法(Parallelism)是将一组数目不定的诗行并列相呈,各句中的词类或思想排列顺序原则上都遵守一定的格式。而目录诗(Catalogue Verse)则是诗中一系列的人名、地名、事物或思想结合成组,而每组名称中通常含有一个相同的主题,如英雄气概、美、死亡等[10]。惠特曼认为,诗人若想对宇宙的真谛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最佳的途径莫过于将一连串的事物、思想一一加以列举,而在列举的过程中,宇宙的基本肌理纹路也就自然而然地从字里行间涌现。
与惠特曼这种较长的目录式的自由诗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威廉斯的自由诗多采用短小诗行。他认为,唯有在特殊性中方能表现事物普遍深层的含意,故而每一件小的、不起眼的事物经过诗人独具的匠心提炼之后,都近似于一个大的层面上的浓缩和聚焦,如一株树、一辆手推车、几片碎玻璃、贴在窗玻璃上的女人的面孔等。
简言之,惠特曼“自由诗”的主要特点是一无脚韵二无格律。早在古希腊,一种以音节为基础的格律就出现了,例如荷马史诗便是以扬抑抑格六音步的模式写成的。英语诗歌中,从14世纪的乔叟和15世纪的民谣开始,直到19世纪末,这种格律诗历来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惠特曼在抛弃脚韵的同时也一举摧毁了传统格律的限制,这是诗歌史上一个空前的革命行动,无怪乎《草叶集》当时引起了那么大的震动和毁誉皆有的反响,而且至今余波未了,仍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议题。
四、诗歌表现手法的多艺术融合
惠特曼自称“歌手”。他的诗确实有音乐性,而且不少篇章被音乐家谱了曲子。作曲家瑞特指出,惠特曼的许多作品,“其主题是那么丰饶,那么能引起新的和声与旋律”,以致读到它们时音乐家的手指便会“立即动弹起来”[11]140。有的批评家从“有机韵律”的观点着眼,发现《草叶集》中的词语和短语起着乐曲中音符般的作用,同时重复与变化也是音乐的基本手法之一。
惠特曼自称是在歌剧的启发下开始致力于诗与音乐的结合,以摆脱“民谣”即传统格律的束缚的。用他自己1860年的话来说,“要不是看了那些歌剧,我也许写不出《草叶集》来”[11]152。他晚年同特罗贝尔谈起这个问题时依然记忆犹新,他说:“我年轻时候,生活是那么洋溢着这种音乐给我引起的激情,狂喜,昂奋,以致我后来的作品要不带有它们的色彩,那才怪呢!”[12]345
《草叶集》中不少诗篇采用了意大利歌剧的手法,其中最为显著的要算《从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其次是《当紫丁香最近在庭院中开放的时候》。在这些诗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在交替运用宣叙调和咏叹调作为独特的艺术手法,使情绪和音调协和律动,发展变化,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他的一些较长的诗篇还运用了歌剧中“渐强”—“极强”—“极弱”的音响旋律,以获致高潮涌退的艺术效果。另有若干诗篇,如《暴风雨的壮丽乐曲》《神秘的号手》《红木树之歌》等,虽然没有明显的歌剧特征,但艺术手法丰富多姿,音乐性也较强,被批评家誉为“富有交响乐风味”。
继惠特曼之后的20世纪是“分析的时代”,正如美国哲学家M.怀特在分析20世纪哲学时所说,“‘分析’是本世纪最强有力的趋向”[13]。这种哲学领域的分析“趋向”在艺术中同样鲜明地表现出来——西方现代艺术与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相比,更显出它的精致细微与学科渗透,为耽于习惯审美中的观众打开了阳光灿烂、五彩缤纷的多种艺术融合的世界,这成为20世纪艺术的转折点。
自1910年始,威廉斯沉浸在纽约的先锋派艺术运动中,他积极借鉴现代艺术,探索诗歌革新的途径。正如惠特曼在歌剧的启发下开始致力于诗与音乐的结合,以摆脱传统格律的束缚一样,威廉斯和当时的一批年轻诗人们受现代派绘画的影响,逐渐割断了对英国浪漫派诗歌的依恋,最终引领一批先锋派艺术家走出了20世纪最初十年——美国艺术与诗歌发展的断层期。
威廉斯成功地将绘画的技巧和特质带进诗歌,他常常用一种绘画性的思维来创造性地构思一首诗歌的创作,而我们在阅读威廉斯的诗歌时,仿佛也是在欣赏一幅现代派的绘画作品。正如威廉斯所说,“我试图将诗歌与绘画融合在一起,将二者视为同一种艺术的创作”[4]26。威廉斯创作诗歌就像“在一幅画布上作画”[14]。作为一名用词语作画的诗人,威廉斯独创性地运用简洁的词语在页面上“绘画”,营造出了视觉的张力。他的诗歌会使读者产生一种视觉的空间感,这种由线性的直线阅读到视觉空间多维的产生实际上是一种读者的再创作的过程。由于多艺术的融合,诗人创造了一种形式,在这样的形式中,意蕴是不固定并有一定空缺的,这样的空缺需要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来填补。于是威廉斯的诗歌留下了很多空间让读者进入,读者通过阅读来参与文学作品的再创造,这样的再创造过程同样也是现代诗歌给人所带来的新的启迪和愉悦的过程。
五、结语
惠特曼强调建立民族民主新文学的思想和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逐渐深入和感染了许多美国作家,对近百年来美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由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不少文学史家认为,惠特曼既是美国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又是现实主义乃至现代文学的先驱。正如著名批评家罗·哈·鲍尔斯说的:“一部美国诗史可以写成对惠特曼的继续发现和重新发现,即不断地肯定他对美国诗人使命的至关重要……我们伟大的现代派诗人从艾略特到威廉斯,无疑全都在自己的诗中记录了他们的发现。”[15]另一位评论家在1982年1月的《美国文学》杂志上写道:“如果说对于一位伟大文学家的鉴别在于他是否永远改变了一种文化的轮廓,那么惠特曼就是这种文学家的最高范例之一。”[16]1955年威廉斯在纪念《草叶集》出版100周年的文章中也着重指出:“惠特曼的自由诗是对诗歌本身的堡垒发动的一次进攻;它向所有活着的诗人提出挑战,要他们说明为什么自己不能这样做。这个挑战经受了整整一百年的猛烈打击,但毫未受挫,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他宣布:“我们必须把旧的推开,来为自己取得容身之地,不管我们将招致多大的损失并为此受到威胁。”威廉斯的评论是对惠特曼“未来诗歌”的总括,同时也仿佛是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宣言,鼓舞新的诗人沿着惠特曼所开拓的方向前进。
[1]孟德森,王以铸.惠特曼论[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147.
[2]王佐良.读《草叶集》[J].美国文学丛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2).
[3]李野光.惠特曼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278.
[4]Peter Halter.The Revolution in the Visual Arts and the Poetr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5]李野光.惠特曼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232.
[6]Baym Nina.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M].4th ed.New York:North&Company,1994:994.
[7]William Carlos William.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M].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67.
[8]John C Thirlwelt.The 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Carlos Willlams[M].New York:New Directions,1984:224.
[9]唐根金.20世纪美国诗歌大观[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136.
[10]李达三,谈德义.惠特曼的诗[M].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7:5.
[11]温伯格,埃利奥特.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革新者和局外人[M].马永波,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2]孟德森,王以铸.惠特曼评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3]涂纪亮.美国哲学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76.
[14]Terence Diggory.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nd the Ethics of Painting[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237.
[15]李野光.惠特曼评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467.
[16]彼得·昆斯.美国诗人50家[M].汤潮,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149.
I109.9
A
1000-2359(2010)02-0233-04
武新玉(1977-),女,江苏镇江人,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文学研究。
2009-05-16
[责任编辑 海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