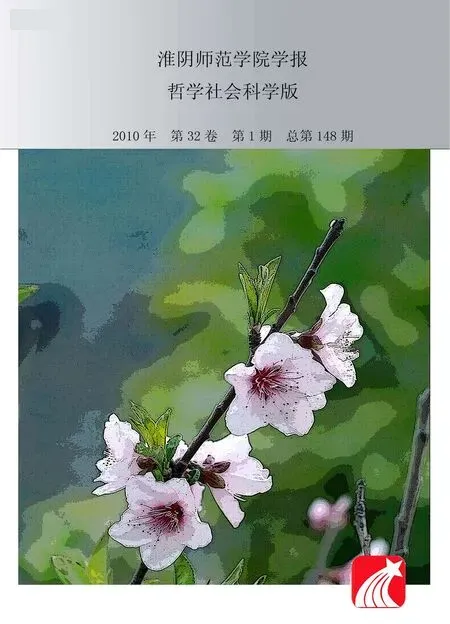战后日本“亲华”保守政治家的对华政策观
——以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众议员为例
翟 新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历史学】
战后日本“亲华”保守政治家的对华政策观
——以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众议员为例
翟 新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松村谦三是中日复交前积极主张发展对华关系、为两国关系正常化身体力行而建功甚巨的日本保守政治家,然构成其对外行为的精神基础的则为中国对于日本国家利益的增进具有重大意义这一认识,也正是这个基于现实政治需要的对外观,从根本上制约了松村对华政策构想的性质和射程。
松村谦三;日本政治家;对华政策观;中日关系
1972年中日两国之所以能一举恢复邦交,从日本方面来说,与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有一批长期致力于发展对华友好关系的保守政治家的努力难以分开。在这些人士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一直受到我国领导人赞誉而长期任国会议员及自民党顾问的松村谦三。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松村团聚一批保守政治家和实业家,根据先贸易后复交的目标,长期以渐进及积累的方式推进对华交流事业,为最终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其贡献和影响可谓巨大。那么,身为保守政治家的松村为何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如此执着于发展对华关系?本文试通过将松村的对华政策观置于国际政治和他的对华活动过程中予以分析,期有助于我们弄清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前提。
一、主要的中国经历和为政生涯
松村1883年生于日本富山县西砺波郡福光町,1903年9月考入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学就读。期间,他因幼时受喜欢汉诗的父亲和祖父的影响选修过中文,并经常参加与东亚地域有关的学生社团活动,大学二年级时还随早稻田大学师生至中国修学旅行。不过,约一个多月的大陆之行,对当时陷于半殖民地深渊的中国的所见所闻,几乎彻底摧毁了松村原先持有的由古代圣人的淳风美德编织而成的理想美妙的中国图景,以致发出诸如“吾人必须祈愿如此堕落之极的国民灭亡”这样极端的中国论,但此行毕竟使他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对于日本所具有的物质上的价值[1]。
松村大学毕业后,被推荐进入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创办的著名大报《报知新闻》当记者,还任过该报社在名古屋和大阪的分社社长。后因父亲去世,他才结束记者生涯,回乡继承家业。1917年,自少年时代就抱有成为政治家愿望的松村参加了福光町议会议员的竞选活动,并一举成功当选。两年后又被选为富山县议会议员,从此从政活动一发不可收拾。至1928年大选,松村以民政党的代表身份参加竞选,并如愿当选众议院议员,自此开始在日本中央政界的政治生涯。
松村任众议员不久,日本田中义一内阁为了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而数度出兵侵犯山东。该事件发生后,当时处于反对党地位的民政党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以牵制执政的政友会,迅即派出由该党六名众议员组成的考察团前往山东,松村即为其中一员。在结束考察绕道中国东北回日本途中,正遇日本关东军施谋炸死张作霖事件,民政党考察团经细密调查,很快得出爆炸事件乃日本军人所为的结论,于是在民政党内有人开始借此对政友会展开攻击[2]71。可是,直接参与调查而深知内情的松村在当时却只对该党领导人作了汇报,但在公开场合则始终对真相保持沉默。显见,虽属反对党议员,松村在事涉国家外交之际,比起所属政党的利益,他更看重并选择的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立场。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新任内阁首相平沼骐一郎为了解决在侵华战争扩大后矛盾日益突出的农业问题,把精通农业问题的松村提拔为农林省政务次官。这个人事变动意味着松村从此成了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内的重要成员。1943年,松村还官至臭名远扬的国家主义团体大政翼赞会第八委员会(国防体制)的委员长,次年出任同样是全国性的国家主义团体翼赞政治会的政务调查会会长。不过,在这一段非常时期,松村也曾因在公开场合主张恢复日本战前的政党政治体制,而遭到亲近军部者的攻击[3]328。但此时松村对日本正在急剧膨胀的军国主义政治和对外侵略,并未正式表示过任何严厉的批判态度。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松村任大日本政治会的干事长。也就是说,直至日本战败,他作为当时最大的国家主义团体中的第二号人物是和这个策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国家机器共命运的。
数日后,由东久迩稔彦组成战后日本首届内阁,松村受邀出任厚生大臣。两个月后,战前以推行对美英协调外交路线著称的币原喜重郎组成新内阁,长于农政的松村应邀出任农林大臣。但三个月后,正当松村倾全力推进国家农地改革之时[4],却因战前在重要的国家主义团体中担任要职的缘故,受到美国占领当局解除公职的处分。自此至1951年解除处分为止,松村离开政坛一直在家闲居。
松村的公职处分被解除后,立即和志同道合者成立政治团体民政旧友会,1952年2月重光葵组成改进党后,他又担任该党中央常任委员会的议长,并在10月举行的大选中当选众议院议员,以此遂其战后重返中央政界的心愿。1953年,松村担任改进党干事长,于是根据其一直坚持的推行清廉的保守政治的理念,不断在公开场合主张应在日本形成两大保守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他的持论是:日本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所以应该避免让社会党人上台;但赞成保守政治不等于对保守政党不加以任何制约,为了牵制当时执政的自由党,目前迫切需要扶植能与其抗衡的新保守政党[2]156-157。可是,日本政治的潮流最终并没有朝松村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即不仅没有形成两大保守党轮流执政的态势,相反出现了保守政治势力大联合的结局。1955年11月,自由、民主两党正式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即自民党,不久松村担任自民党顾问,同时辞去文部大臣一职,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政府内任职。这一年年底,松村和率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日的郭沫若举行会谈,席间郭沫若邀请松村在适当时候访华[5]171-172。这也是战后松村和中方最早的接触。因松村当时尚想在日本中央政界有所作为,故并没有马上接受中方的邀请。
二、领军保守政治阵营的对华交流活动
1956年年底,成功取得对苏联复交和日本加盟联合国两大外交业绩的鸠山一郎首相激流勇退而辞去公职。在继任的石桥湛山首相组阁时,松村放弃出任阁僚的机会,而以首相私人代表的身份,历访了中东、大洋洲和东南亚各国。通过这场外访,松村重新感受到日本在世界尤其是亚洲的地位十分重要,以及亚洲各国对于日本将来的发展也有难以估量的利用价值[6],并在此基础上萌生了日本与各国谋求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新亚洲主义理念及政策观。
但不久石桥首相突然卧床不起,遂由岸信介组成新内阁。岸信介任首相后,赌其政治生命竭力推进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这个对外目标使日本在外交政策的选择上向美国倾斜。另一方面,因1958年发生长崎国旗事件等外交问题,岸信介内阁被中国政府指责为偏袒台湾方面,以致日本和中国大陆之间仅剩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全面中断。在这一背景下,自民党内迅速集结起批判岸信介内阁内政外交政策的反主流派势力。1959年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时,松村被池田派、三木派国会议员推荐为总裁候选人,准备与希图连任总裁的岸信介首相一决雌雄。松村的竞选纲领中鼓吹的两个亮点:一是推行反对金权政治的清廉之政;另一是日本要把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作为民族的使命[7]。但结果,松村却以166票对320票大败于岸信介。这个挫折使松村最终做出转移活动舞台的决定,即完全放弃在政治权力中枢的博弈,而将余生贡献于对华交流事业。
当时中日间经济文化关系中断,日方虽有自民党方面的石桥湛山和社会党方面的浅沼稻次郎等政治家先后访华欲打开局面,然中方坚持“只要不复交,中日就不可能再进行贸易”的立场[2]201,遂使两国即刻恢复经贸关系的前景十分黯淡。这就是1959年松村一改先前犹豫不决的态度而接受中方访华邀请的主要背景。当时松村认为,自己既已决定淡出中央政界,鉴于中国在市场及安全保障方面对日本所具的重要性,为改变战后因两国高层间没有沟通政治意思的管道以致问题迭出的被动局面,有必要于此时甘冒被日本一些势力毁损政治名誉的风险,迅即展开对华接触。这个访华决定也标志着松村正式登上对华交流活动的历史舞台。
1959年松村一行的访华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此间,松村等向中国方面说明了日本的社会制度和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也解释了日本政府关于国际政治的基本政策及立场,力图排除因两国政府间的误解而引致的相互不信任。虽然松村对岸信介首相并无好感,但面对中方的会谈对手,他始终坚持岸信介内阁并不敌视中国的立场,并对中方的岸信介批判不时予以解释[8]15-29。从这里,我们也可清楚见出一个执着于民族主义信念的保守政治家在对外问题上恪守的原则和策略。
松村回国后,通过讲演、报告和为媒体撰稿的机会,将其在访华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对华认识转告于日本国民:中国作为新兴的民族国家,正在依靠自力更生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变革,中国领导人清廉勤政,日本决不能无视这样一个民族意识旺盛、百废待举的偌大邻国[3]214-228。松村指出:“现在人们正在倡导世界和平,但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世界和平是不可能有的。日本虽然站于自由主义国家的立场,但同时也是亚洲的一个国家。中国既是共产主义国家,也是亚洲的民族国家。近在咫尺的两个邻国没有理由不和睦相处。即便为了亚洲的繁荣和世界和平乃至人类的幸福,也必须打开日中关系。”[2]225而松村首次访华的最大功绩,则是和中国领导人达成了以积累及渐进方式发展两国关系以致最终实现复交的共识[9]。以后,这个认识也成了松村等人展开对华交流主要的外交目标。
然而,松村的这个对华观以及随之产生的对外行为,很快被自民党内的鹰派攻击为纵容共产主义的“思想侵略”。而松村则对此毫无惧色地反驳说:“从历史上看,中国一次也没有侵略过外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优秀民族的日本,即使遭受外国的思想侵扰,也不会轻易就被洗脑的。”[2]226松村就是这样既不失原则立场,又极富智慧地与党内外的反对派据理力争。但因他坚持以对华友好理念致力于中日交流,遂不免常被人批评为“容共”主义者,一段时间里甚至还被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扣上了“排他性亚洲主义者”的帽子[3]334。但实际上在松村的对外观念中,中国一直是被视为与苏联那样“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民族主义国家”;并且鉴于中苏之间的复杂利害关系和中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现实,松村始终坚信和美国具有同盟关系的日本如发展对华关系,这将成为日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补充,即中日友好和日美同盟完全可以两立[2]228-229。这也是松村坚信对华交流活动有强盛生命力的理由所在。就是说,松村在就中日关系局面作形势判断时,并非如一些论者所言,只是限于两国间这个较为狭小的框架及视角,而是基本立足于围绕中日两国的国际政治大局进行构想和展望的。在这里,当然首先应该承认,即便是松村这样对中日关系高度关注的政治家,也是把日美关系看作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即在这方面日美关系具有不可取代性,所以松村及其周边的对华友好人士基本上都是日美同盟关系的支持论者。然松村的可贵之处则在于,他把对华关系和日美关系作了平行化的处理,这就和当时日本政府及执政党主流派所持的将对华对美关系完全对立的对外立场有很大不同。
松村在展开对华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的是在池田勇人首相当政期间。池田首相出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市场需要,主张和中国保持更为密切的经贸关系[10]。池田的这个基本对华观也是松村和中国方面经反复交涉终于确立起长期备忘录贸易体制和交换中日两国新闻记者制度的主要政策背景。而事实上这个属于半官方的贸易体制,切实扮演了沟通两国政府及执政党之间的联系管道、以及为实现复交目标培植社会基础的作用。松村也因积极坚持推行这些活动,深受中国方面的尊敬和信赖,被称为日方的对华“总联系人”。松村每次访华,周恩来总理等中国政府领导人都要拨冗与其会谈。但另一方面,随着松村和中国方面的接触增多,他在国内受右翼组织和党内鹰派的威胁及政治性攻击的程度也逐渐升级。这种情况自佐藤荣作内阁成立便愈演愈烈,松村甚至被人斥为“卖国贼”。但在作为谈判对手的中国人面前,松村还是坚持不懈地主张日本方面的见解和理由,在这个基础上探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和方式。就是说,在松村的富有特征性的对华交流姿态当中,既有尊重理解中国主张的一面,也不乏坚持自身及至日本国家的原则立场的另一面。
1965年初,在佐藤首相不断表现出迎合美国的对外姿态的同时,松村谦三分别出任自民党议员组织的亚非问题研究会和外交调查会的顾问,积极参与执政党内对外政策集团的活动[11]。但在一段时间里,松村一面支持佐藤的政敌河野一郎,一面则对现政权的对华政策仍寄予一定的期待。1964年底,松村在早稻田大学发表题为《世界中的日本和中国》的讲演。他在这个讲演中主张日本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也是和中国同文同种的邻国,当务之急不是为了防备中国的原子弹而改变日本的宪法及国防方针、甚至去制造核武器,如果那样做的话,就会重蹈战前军国主义的覆辙,而是应该为使中国尽快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往大陆派送大量技术人员,给予其经济援助。并且,日本作为亚洲的一员,为了亚洲的和平和发展,应该在美中两国之间担任调停的角色,而不能无条件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只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才是日本应采取的对外方针[12]296-298。
1965年2月,松村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做美中的调停者》一文,提出两个观点。第一,靠日本单枪匹马改变对华关系确有相当难度,所以有必要采取先说服美国的战略。就是说,今天的国际社会中承认中国已逐渐成为趋势,日本如在对华政策方面只是满足于跟在美国后面投反对票,就会给日本将来的发展留下很多问题,所以应该找到既能维护美国的面子,又不损害中国面子的妥协之计。这倒未必要像法国那样一步到位和中国复交,对于日本来说,目前最稳妥的做法应是先成为美中之间的架桥者,然后实现日本自身的外交目标。第二,以长远的视点妥善解决一些靠日本自身力量能够奏效的问题。佐藤内阁应该拿出勇气做几件这样有突破性意义的工作,首先是尽力维护并扩大来之不易的对华长期综合贸易体制,其次是从长期考虑妥善解决包括中方高层人士来访在内的两国人员交流问题。松村在该文最后以“佐藤君既处于总理之位,总要设法做一些让人刮目相看的业绩”一语,表明自己仍然没有改变对佐藤的期待[12]299-306。松村如此低调奉劝现内阁班子转换对华政策,与其说是对佐藤的信任,还不如说是出于无奈。因当时自民党内已没有派系力量能与佐藤首相直接抗衡,故改变佐藤的态度才是扭转日本对华政策方向的关键。
三、退出政界后的对华交流活动
可是,佐藤首相出于国内外政治的需要,加上对当时正处于文革的中国国内形势的消极判断,不时显示出强硬的对华姿态,遂使改善两国关系的外交空间越来越狭小。就在中日关系趋于低潮的1969年,已达86岁高龄的松村宣布从政界完全脱身,即不再出马竞选众议院议员。但他在引退声明中还是强调:“自己毕生的心愿就是改善日中两国的关系”,“自己虽然力量有限,但也要把余生贡献于打开日中关系和确立亚洲和平的基础”[2]274。为显示自己一如既往继续对华交流事业的心迹,1970年松村再率访华团抵达北京。在松村一生最后的访华过程中,他一直鼓励日方谈判代表努力克服障碍,和中方代表一起促成两国备忘录贸易协定的续订。此时的松村所以能够坚持这样的姿态,完全是基于以下的对华观。
当时日本的舆论十分关注改善日中关系,而中国也正在发生巨变。所以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日中关系的现状实难令人满意,日本政府和自民党的对华政策及在应对中国问题上的基本姿态,实如“掩耳盗铃”一语所云。中国是日本重要的邻国,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一点是改善两国关系的前提,日本国民应以新的感觉去研究中国及中国问题。当然像社会党和共产党那样,无论什么都说好也无甚意义,是好则说好,是错则说错。中国的做法虽也有不少的矛盾,应该就其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然后考虑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日中之间发展贸易的空间甚大,中国方面也需要日本的技术,但如日本只是跟在美国后头反对中国加盟联合国,就不免有集体自杀之虞,日本应该有自己的对策,但在积累及渐进方式的框架内是没法解决这类问题的。就是说,靠以往的积累及渐进方式来解决日中关系问题,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日中关系必须在广泛的范围之内,并从根本上加以改善[13]。
1971年7月,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松村惊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他一面惊叹美国先于日本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一面则作为应急对策,敦促佐藤首相马上前往北京,和中国方面直接展开外交交涉,以改变日本外交被动的局面。但松村的愿望再一次被政府当局的不作为所辜负。同年8月21日,松村因胆管炎等疾病在医院去世。
周恩来总理在随即发出的唁电中评价松村为日本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深深的尊敬[14]。松村的葬仪原定为家葬,但实际上自民党和各在野党的领导人及日本民众为缅怀这位中日交流活动功臣的业绩,自发组织了由三千余人组成的堪称国民之葬的葬仪[15]。一年后的1972年9月下旬,日本的田中角荣首相赴北京出席中日复交谈判,就是在参拜了位于东京护国寺的松村墓之后启程的。
由以上考察可见,决定了松村对华政策观方向的虽有同为亚洲一员的地域主义观念的影响,但促使其长期执着于解决对华关系问题的主要思想动机还在于中国对于日本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所具的重大价值,也正是这个现实利益的需要,从根本上制约了松村的对华认识及其实践的归趋,而他本人一面力促对华关系的发展,一面却明确拒绝自己是“亲华派”[16]的举动,则也为此作了绝妙的注解。
[1] [日]木村时夫.松村谦三明治三十七;八年中国旅行记:上[J].[日]早稻田人文自然科学研究,1969(35).
[2] [日]远藤和子.松村谦三[M].富山:KHB兴产株式会社出版部,1975:71.
[3] [日]松村正直,等.花好月圆——松村谦三遗文抄[M].东京:青林书院新社,1978.
[4] [日]保谷六郎.战后社会改革和松村谦三[J].[日]圣学院大学论丛,1996,9(1).
[5] [日]川崎秀二.早稻田的政治家们[M].东京:恒文社,1975.
[6] [日]松村谦三.亚洲的黎明[J].[日]早稻田学报,1957(669).
[7] [日]松村谦三.施行不需要金钱的廉洁公正的政治[N].[日]日本经济新闻,1959-01-22(1).
[8] [日]田川诚一.日中交涉秘录田川日记——14年的证言[M].东京:每日新闻社,1973.
[9] [日]松村谦三.如何打开日中关系[J].[日]朝日杂志,1960,2(1).
[10] 首相与记者对答希望扩大对华贸易[N].[日]朝日新闻,1961-06-23(01).
[11] 外交调查会扩充/松村;藤山氏任顾问[N].[日]朝日新闻,1965-02-02(01).
[12] [日]木村时夫,等.松村谦三:资料篇[M].东京:樱田会,1999.
[13] [日]松村谦三.我的意见[N].[日]日本经济新闻,1966-06-06(01).
[14] 松村氏去世/周总理等致遗族唁电[N].[日]朝日新闻(晚报),1971-08-23(01).
[15] 三千人参加已故松村氏的葬礼[N].[日]朝日新闻(晚报),1971-08-26(01).
[16] [日]松村谦三,等.中国问题和日本外交[J].[日]世界,1964(223).
D829.313
A
1007-8444(2010)01-0064-05
2009-09-17
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SS005)。
翟新(1953-),男,上海人,法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东亚国际关系和现代日本政治外交研究。
责任编辑:仇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