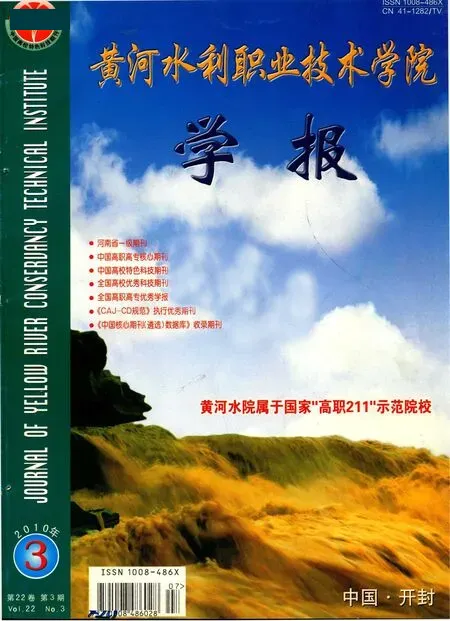托尼·莫里森新作《仁慈》的互文性研究
张聪沛
(河南大学,河南 开封 475001)
0 引言
作为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重要的文本批评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出现于20 世纪60 年代。尽管其发展历史不过半个世纪,但它已成为后现代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的标志性术语,也是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 本文试从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两个方面来解读首位诺贝尔文学奖黑人女性得主托尼·莫里森的新作《仁慈》中的互文性,以此来证明莫里森对历史﹑社会和人心的深刻洞察。
1 互文性及文本之间的联系
1.1 互文性
互文性这一术语是由当代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最先提出的。 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1]这里的“另一文本”,既可指涉历时层面上的前人或后人的文学作品,也可指共时层面上的社会历史文本。 但是互文性绝不能被理解为摘抄﹑粘贴或仿效的编辑过程,因为“从本文之网中抽出的语义成分总是超越此文本而指向其他先前文本,这些文本把现在的话语置于与它自身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更大的社会文本中。”[2]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任何文艺作品都有它存在的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而特殊的历史时期又决定了当时社会的特殊的意识形态。 有别于其他的互文性理论研究者,克里斯蒂娃在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情况下更为深入地剖析了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以及其他文本之间的联系。 她区分了水平互文性和垂直互文性。 前者指一段话语与一连串其他话语之间的具有对话性的互文关系,后者指构成某一语篇较直接或间接的那种语境,即从历史或当代的角度看以各种方式与之相关的那些语篇。因此,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不仅指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吸收和改编”,还包括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关联。 顾名思义,文学文本是指有待于读者阅读并赋予意义的语言产品,而文化文本则是指言语所存在的社会﹑历史环境。 换句话说,互文性既可以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也可以是文本和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语境之间的相互映射。 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处于文化文本之中的,是对社会﹑历史文本的摘取和反映,所有的文学文本背后都蕴涵着意识形态和阶级性等社会因素。
1.2 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联系
克里斯蒂娃相信: 艺术揭示的是一种特定的时间,它被凝结于一种具有极其多种多样表现的生产方式中。 它把陷入众多复杂关系中的主体织入语言(或其他“意指材料”)之中,如“自然和文化关系不可穷源的意识形态传统﹑科学传统与规时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欲望和法则、身体,语言和‘元语言’等之间的关系中”[3]。 对她而言,互文性意味着欲望、历史、文本等语言学或非语言学、文学文本或非文学文本的相互指涉。 它超出了狭窄的文本范围,进入到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中。
此外,互文性还意味着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其他符号系统之间的互换或互补。 作为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将符号(文本)的意指过程分为“前符号态”和“符号象征态”两个层面,而后者与历史和社会以及意识形态这些外部领域相联系。 它意味着主体已经进入社会领域,被各种社会规范所统治。 “因此,文本是具有双重或多重意义的成分所构成的复合结构。 在这种结构中,文本所表达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本本身,成为这一文本与其他文本或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表征所组成的临时的符号系统。 这种符号系统就是在文本阐释所处的历史语境下的所指。 因此,互文性理论的意义在于强调文本结构的非确定性,加强了文本阐释的流动性,为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文本解读方法画上了句号。 文本阐释流动性的动力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其他文本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历史和社会等文化因素。”[4]互文性理论认为,一个文本从一开始就处于其他历史文本的控制与影响之下。 读者在解读文本时受到他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这种环境既包括历史和社会等因素,也包括读者本人及政治环境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因素。 历史、社会、政治等同样是文本性的,是作者和读者通过把自我植入其中而加以重写的产物,语境通过互文性揭示了文本意义的建构方式。
2 《仁慈》中的文化互文性
2.1 《仁慈》主题的超越性
莫里森以往的作品,大多涉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黑人和黑人奴隶,反映他们在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的精神缺失﹑人格扭曲以及在寻找自我和追求完整过程中的艰辛﹑曲折和困惑。 而她的新作《仁慈》超越了以往的主题,把故事的背景置于17 世纪后期(1680 年前后)的北美大陆,比《宠儿》的时间背景(1873 年)又前置了近两个世纪。 那时的北美仍是一派混乱的局面:印第安部落出没于无边际的森林中, 瑞典和荷兰的殖民索赔遭到抵制,而任何一次土地的延伸都可能被一所教堂申请获取﹑被一家公司管理,或者成为皇族成员的私人财产并被当做送给子孙或爱人的礼物。 在《仁慈》这部小说中,莫里森试图超越对奴隶制的表象批评,尝试着追溯到更远的历史语境中,探寻“奴隶制和种族主义联袂之前的年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莫里森在谈及她的小说的创作动机时也指出:“我真的是想要抵达那个蓄奴制尚未与种族画等号的地方。”而那时候,人们“肤色黑白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什么,他们的力量何在。”[5]
《仁慈》 区别于其他奴隶主题作品的特色即在于其超越了对非裔黑人奴隶的关注,而把注意力投向了更远的历史。 在那个时候,种族或肤色并不成为一个人是否受奴役的标志,不只是黑人,各色人等都处在身体和精神的束缚之中, 备受灵与肉的折磨,即使是白人也难逃其困。 “尽管在所谓的‘伊甸园’时代的美洲大陆上,一切的毒素都开始凝结,所有的苦难都在酝酿,但在1680 前后,美洲的蓄奴制还处于无论肤色、大家为奴的‘机会均等’的状态,并非后来演变成的那样严格﹑特别的制度。”[6]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作品形成深刻的互文性,从而揭示了各色人等的异化。 尤其是小说中对白人的刻画和精神剖析,势必会引起在当今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中努力生存的众多白人的共鸣。 不仅仅是 《仁慈》,莫里森的所有作品都带有这种历史的精神力量及其文化特质,从而构成了文本与文化的互文性。
2.2 《仁慈》与现代社会生活中政治生活的互文性
《仁慈》的发表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生活也构成了互文。 2008 年,奥巴马成为轰动一时的美国大选的赢家,也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 他的获胜,表明美国社会已冲破了种族肤色的羁绊。 就在2008 年初,奥巴马和希拉里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莫里森就在《致奥巴马公开信》中表示了对奥巴马的支持,而《仁慈》的出版也正好处于大选结果揭晓后的一周。 评论家将《仁慈》与奥巴马的当选联系在一起,认为在“这一特别时刻,该书获得了更大的隐喻力量。”[6]在2008 年末的年度十佳出版物的评选中,《仁慈》处于小说类五部推荐作品之中,这表明了对少数族裔美国人身份的认同问题以及对美国历史的重新反思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关注。
3 《仁慈》的文本互文性
《仁慈》 不仅与其社会历史背景构成文化互文,还从内容﹑主题等方面与其他文本构成了互文。
3.1 《仁慈》与《宠儿》之间的互文
在《仁慈》出版之后,不少评论家都不约而同地将其同《宠儿》联系在一起,指出“两者都是关于‘母性’的小说,表达了蓄奴制带给人痛苦的‘主题’,《仁慈》是《宠儿》的同主题‘前篇’”[6],等等。 的确,在新作《仁慈》中,莫里森同样讲述了类似于《宠儿》中的不同寻常的母女之情,但是却在内容﹑主题等方面进行了改编。
3.1.1 主题的互文性
《宠儿》 的重心集中在赛丝这个黑人女性身上,为了不让女儿像自己一样遭受白人奴隶主的折磨和羞辱,塞丝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女儿。 小说描述的是杀害爱女后母亲的痛楚。 而在《仁慈》中,中心人物从母亲转向了女儿一方, 作品以女儿的视角剖析了17 世纪的北美大陆。 莫里森在《宠儿》中把笔触伸向奴隶制时期,揭示了不合理的制度和歧视对黑人造成的精神创伤,并探索了黑人奴隶该如何解救自己。而《仁慈》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则比《宠儿》更早了两百年,展现的是蓄奴制初期各肤色奴隶所遭受的肉体或精神的奴役,强调肤色并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受奴役的决定因素。
3.1.2 两位母亲的互文性
同《宠儿》中的赛丝一样,《仁慈》中的母亲因自己历尽了磨难和耻辱,并深谙“在这种地方,身为一个女人就像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愈合的伤口。 哪怕表面已经结疤, 内里也永远是痛的。”[7]163所以她想要“像鹰”[7]一样保护自己的女儿,使她免于重蹈覆辙。于是,她请求前来讨债的雅各布带走女儿,“期许奇迹能够发生”[7]162,因为她看见雅各布像看“一个人类的小孩”[7]一样看她的女儿。 虽然没有《宠儿》中的母亲那样极端,但《仁慈》中母亲的“带走她,带走我的女儿”[7]26的话语同样撞击着读者的心灵, 也给她的女儿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为女儿以后的悲剧道路埋下了伏笔。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同赛丝一样,《仁慈》中的母亲虽然自身被奴役,但有着对自由的渴望,因而她在精神上是自由的。
3.1.3 两位女主人公的互文性
作为书中女主人公的弗洛伦斯,在精神上却远不及她的母亲自由。 当她爱上了自由黑人铁匠的时候,她彻底失去了自我,甘愿成为感情的奴隶,并非常享受这种奴役。 当她在树林中第一次感受到自由时,她却说:“我有点害怕这份轻松。这难道是自由的感觉吗?我不喜欢。 我不想要没有你的自由,因为只有和你在一起时我才是活着的。”[7]166在这里, 弗洛伦斯对铁匠的依赖与《最蓝的眼睛》中佩克拉对白人的蓝眼睛的渴望形成了互文。 不管是为了寻求爱情,还是为了找寻尊严,两个女孩在追求的路上都迷失了自我,成为受害者。 所不同的是,佩克拉最终无法战胜精神的奴役疯掉了,永远成为种族制度的殉难者,而爱情的失败却使弗洛伦斯“自由”了。她在墙上刻下了最后几行字:“我变得狂野, 但是我仍然是弗洛伦斯。 充实。 不被谅解。 也不原谅人。 无情,我的爱人。一无所有。听到我的话了吗?奴隶。 自由了。我终于自由了。”[7]70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反映出是自由还是被奴役,不是由肤色和地位决定的,关键是取决于自己的内心,就如弗洛伦斯所说:“是内在的枯萎才使人沦为奴隶。”[7]161
3.2 《仁慈》的叙事手法与此前黑人叙事小说的互文性
此外,《仁慈》 独特的叙事手法还与此前的黑人叙事小说形成了互文。 黑人叙事是由获释奴隶讲述亲身经历的一种散文形式的美国黑人文学体裁,以线性叙事为主,将记忆以独白的形式机械地再现出来[4]。 莫里森的大多数作品都与黑人叙事作品相关,也深受其影响。 但是,在《仁慈》中,莫里森对传统的黑人叙事进行了改写,通过采用非线性和多视角的叙事策略,为小说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并将其置于了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小说以故事的结尾开篇,逐步追溯到往事,进而打破现在与过去的时界,并且以多人物的声音来讲述故事, 将叙事故意模糊化,使读者不得不积极地去思考, 最终达到对小说的理解。 同巴特一样,莫里森非常重视读者与小说的关系,她说:“如果小说是长命不衰的,愿意看我的书的读者就会明白,那不是我,而是他们实现的。”[8]莫里森希望作家与读者之间能建立一种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能征服文本中出现的异化格调。
4 结语
综上所述,莫里森的新作《仁慈》通过与经典文本或文化文本的互文,凸现出其特有的社会历史属性及意识形态。 作品通过曲折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在一个还没有严格按照种族和肤色进行奴役的美洲大陆上各色人种的生存状态,揭示出人是否被奴役关键不在于肤色,而在于精神,具有唤醒民众的力量。
[1] Kristeva, Juli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J].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86: 245-248.
[2] 王瑾. 互文性[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2.
[3] 罗婷. 论克里斯多娃的互文性理论[J]. 国外文学,2001(4):9-14.
[4] 张燕楠, 张艳清. 托尼·莫里森作品的互文性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分析[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467-470.
[5] Kachka, Boris. Toni Morrison's Historical Lesson [J].New York Guides. Aug 24, 2008: 312-315.
[6] 王守仁,吴新云. 超越种族: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奴役”解析[J]. 当代外国文学,2009(2): 35-44.
[7] Morrison, Tony. A Mercy [M].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8: 163, 162, 166, 166, 26, 70, 161.
[8] McKay, Nellie. An Interview with Toni Morrison[M].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1983: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