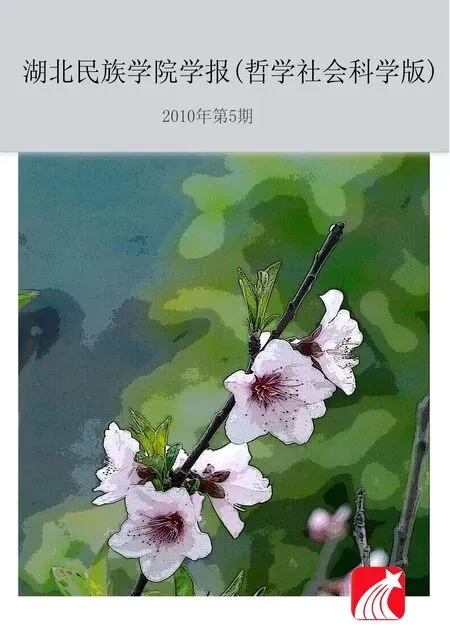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
李技文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
李技文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问题是当下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文章主要运用社会记忆和族群认同的有关理论,结合相关的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从英雄祖先记忆、家族祖先迁徙记忆与苦难记忆等方面对亻革家人的族群认同进行了诠释。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对其族群认同有着深刻的影响,社会记忆体系不仅是强化族群自我认同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区分、标识族群之间和表达其族群认同的特殊“历史叙事”方式和媒介。
亻革家人;族群;社会记忆;族群认同
在人类社会中,记忆不仅属于人的个体官能,而且还存在叫做社会记忆的现象[1]。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自1925年率先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经典概念,并将“记忆”分为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三种类型[2],以及1989年美国著名学者保罗·康纳顿对“社会记忆”研究的巅峰之作《社会如何记忆》出版之后,社会记忆在当代学术界,特别是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如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视野,将族群认同与社会记忆理论相结合,运用文献与田野资料,由人类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以及历史记忆或社会记忆与失忆,探讨了以华夏边缘界定的华夏认同的形成、扩张与变迁[3]6,就是其经典的范本。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重安江两岸的诸多村落中,世居着一个拥有约五万人口的特殊族群——亻革家人。亻革家人是我国目前一个族称待定的少数民族群体,笔者前后多次到亻革家人聚居的枫香寨①枫香寨是目前亻革家人居住的最大的一个自然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境内的重安江畔,辖上枫香和下枫香两个行政村,距县城32公里,隶属于黄平县重兴乡。据统计,全寨共19个村民小组,共750余户,亻革家730余户,总人口约3600人,其中亻革家人约占总人口的97%,且均为同一姓氏——廖姓。2006年7月到2010年2月,笔者曾先后四次到枫香寨进行田野调查,时间累计达三个多月。调查得知,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与民族繁衍中,亻革家人不仅创造了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和艺术特色浓郁的民族文化,同时在传承、强化和维系本族群的族群认同时,还有着以社会历史记忆为内核的特殊的“历史叙事”方式。因此,本文尝试运用社会记忆和族群认同的有关理论,结合相关的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拟从亻革家人的英雄祖先记忆、家族祖先迁徙记忆与苦难记忆等方面对其族群认同进行诠释,藉此探寻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对其族群认同的影响及其规律。
一、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的理论视角
何谓社会记忆?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inzer)结合彼得·伯克(Peter Burke)对之的理解把它定义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4]根据伯克的观点,社会记忆属于回忆社会史的范畴,有“口头流传实践、常规历史文献(如回忆录、日记等)、绘制或摄制图片、集体纪念礼仪仪式以及地理和社会空间”[5]等内容。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将社会记忆界定为“人们将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过程的总称”[6]24。王明珂则认
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对一个族群的认同有着重要影响。族群认同就本意而言指的是本群体独特的、与他群不同的特征,它一方面是指人们对我群体情感的认知和依附,另一方面也指群体自身对外群体的一种感情弱化与“排他性”。族群认同的产生,至少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因为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群,如果不和外界接触就不会自觉地认同。族群(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族群(民族)的认同[9]。在很大程度上,认同是一种主观上的自我群体的认知,是一种“想象的共同群体”,这个“想象的共同群体”并不是人们主观凭空的“想象”,而是由基于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一个群体区别于另一个群体的“特征”所表达出来的。这种诸多特征“符号”有的是一种“根基性”的情感;有的则是人类在资源竞争中为了追求集体利益,而产生的“工具性”情感,它们保留在人们社会历史记忆中,并构成一个群体集体意识的基础,从而凝聚和强化认同。因此,可以说“族群”这样的人类结群是人们为了维护共同资源,以主观的社会记忆彼此联系并排除外人的人群组合[3]46。
可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又如何把握社会记忆去探讨族群认同问题呢?通常在一定的社会群体里,族群认同意识的表达是通过一定的社会记忆媒介去实现的。一般来讲,特殊的“仪式活动、庆典、照片、族谱、口头传说、所经历的苦难与遭遇”等都可以说是强化或维系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的媒介、方法与手段。我们的许多社会活动,都可视为一种强化此记忆的集体回忆活动。如国庆日的庆祝活动与演说,就是为了强化作为“共同起源”的开国记忆,以凝聚国民中此一人群对国家的认同[10]。
二、英雄祖先记忆与族群身份认同
在亻革家人的社会历史里,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与诸多因素的影响,一直以来他们都没有本族群的文字,各种知识技能主要是通过口头叙事与民间传说来记忆和传承。传说是记忆的叙述[11],是一个社会群体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公共记忆[12]。借用作为口头叙事的地方传说来解释村寨聚落的形成、发展,是民间草根表述其历史记忆的惯常方法。尤其在无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村寨社会中,口头叙事更是被村寨成员视为最主要的“信史”而长期流传[13]。口头叙事与民间传说是某一族群在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情境中所建构的一种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与历史表述。它是族群为了强化其认同、增强族群内部凝聚力,进而对本族群历史进行的创造与建构。以口头传说(口耳相传)为记忆媒介的“英雄祖先记忆”是亻革家人对自我族群身份认同的一种表达,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叙事文化,即王明珂先生所说的“历史心性”[14]。亻革家人在其历史心性下的“英雄祖先”是一位“射日英雄”,他们宣称本族群是“射日英雄”的后人。
在黄平县黄飘乡的黄猫村,有这样一则关于亻革家无名英雄祖先射日的口述:远古时期,天上有七个太阳,大地炙热,南方山林里的部族无法生活。部族最高首领会商议事,选出了三个射手去射太阳,并决定谁射得多,将得到最高首领之位和一顶红色帽子的奖励。第二日,射手们身着铠甲去射太阳,一下子就射掉了六个。首领连忙令三人收箭,留下了最后一个。大家前去认箭时,发现有五个太阳都是被亻革家人的红箭所射下的,最后,亻革家的“射手”赢得了红帽并当上了最高首领。很多年过去了,由于部落之间的战争,亻革家人战败,被迫迁徙到更为偏远的山林中。后来,亻革家后代为缅怀祖先射日的功绩,就将红帽子取名太阳帽,并打造银簪子斜插入帽顶佩带在女子头上,世代相传[15]。
颇为巧合的是,在重兴乡枫香寨廖姓亻革家的古歌《摆解轰》中,也有十分类似的英雄祖先射日的口头传说,其大意是:祖先查义查娅①查义查娅,系亻革语,指古代亻革家人的两个创世祖先。开天辟地之后,大地一片漆黑,遂抛撒黑泥和细泥引来了七个太阳和月亮。太阳月亮出来十分炎热,大地岩石被晒裂,田地里的庄稼全被晒死了。家族集会商议,推选技艺超群的卡又卡谷①系亻革语,指古代亻革家先民,善射。去射太阳和月亮。卡又卡谷造好弓箭,爬上杨柳树,在靠近天的地方,瞄准一箭,射下了排头的月亮,其它太阳和月亮见状再也不敢出来了。从此,世间又是一片漆黑。大家又集会商议,决定请公鸡去喊太阳和月亮。公鸡说“月亮太阳是我舅爷和舅妈,我喊他们肯定会出来”,公鸡放开嗓子咯咯叫,一个太阳冉冉升起。公鸡又再咯咯叫,一个月亮也应声出来了。白天有了太阳,黑夜有了月亮,人间从此有了光明和温暖,世上也有了好年岁[16]194-195。还有一则广为流传于亻革家社会中的英雄祖先射日故事是:很久以前,天空出现七个太阳,把大地都晒焦了,人们难以生存。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商量选中武丁去射太阳。武丁搭上巨箭,一连射中了前面六个太阳,第七个太阳慌忙躲回山里去了,再也不愿意出来。没有了白天,人们无法生活。于是叫太阳的舅公——公鸡去请太阳。太阳最后答应每天只要听到鸡叫三遍,它就出来一次,这样亻革家人的生活才恢复了正常[17]。
以上三则口述资料,彼此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就其不同之处而言,第一则资料中的“英雄祖先”是一个无名英雄,后面两则中有具体的姓名,且文中的叙事情节与内容也多有不同。就共同之处来讲:三则口述资料中都描述了天上有七个太阳,酷热烈日都给古时亻革家先民的生活和生存造成了巨大危害;都表述了一个“英雄祖先”射日的故事母题,从整体上展现了亻革家关于“英雄祖先”射日的社会历史记忆的叙事模式。
由此可见,亻革家人普遍宣称自己是“射日英雄”的后裔这一身份,主要是通过传承和记忆英雄祖先故事来表达的。在枫香寨调查时,笔者就此问题曾访谈过几位亻革家老人,他们说:“虽然现在确实无法证实这当中的真实性,但是我们一直都相信自己就是射太阳的英雄的后代,因为在传说中我们祖先就是射太阳的”。他们还向笔者展示了象征和纪念他们祖先的“红缨花帽”以及每家每户都供奉在神龛之上的红弓和白箭。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考证射日英雄后裔之说,其真伪确实无法考辩,可如果从民族学视野中去探寻族群认同的建构,就会很清楚地发现所要找寻的并不是历史的“事实”,而是亻革家人对过去的理解,是今天的他们对自己过去的社会记忆,和对自己是谁的解释[18]。诚如钟年先生在论述《评皇券牒》在瑶族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时所述:“流传于许多瑶族地区的《评皇券牒》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其内容的历史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起到了凝聚瑶族族群认同的作用”[19]。那么,千百年来流传于亻革家社会中的英雄祖先传说的社会记忆,其作用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家族祖先迁徙记忆与族源认同
家族祖先迁徙记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记忆,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人们常常通过追忆家族祖先的迁徙历史来记忆和强化其族群认同。一定程度上讲,家族迁徙传说本身就是对祖先艰难开拓历程的刻意渲染和强调,是对其祖先族源的追溯与记忆,目的就在于通过这种记忆来不断增强族群对族源的认同。“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这是人们在找寻自己的族源、自己祖先时的一个很直白的疑问。对于无文字记述的亻革家人来说,他们对族源的认同往往是通过口传和记忆家族祖先迁徙历史来表达的。在黄平枫香寨的廖姓亻革家口头流传的《迁徙词》中,有着对其家族祖先迁徙的祖居地的明确载述:
祖公颂利,祖公读地;祖太波肯,祖太波弄。②颂利、读地、波肯、波弄,系亻革家语,均为人名。我们祖先廖姓,住地在南京;我们祖先罗姓,住地在北京。……祖公牵着水牛留绳来,抬着祖鼓留种来;祖公下来找大地方种来吃,陆续落业在这个地方。落业龚吴旺解京。……我们的祖公廖姓,来住广东地;我们的祖公罗姓,来住广西地。……我们祖公廖姓,来住拱洋地;我们的祖公罗姓,来住拱江地。……我们的祖公廖姓,去落业拱拢;我们的祖公罗姓,来落业门赛。……我们的祖公廖姓,去住拱弄地;我们的祖先罗姓,去住麻引地。……我们的祖公廖姓,去住斯张地;我们的祖公罗姓,去住嘎哄地。……我们的祖公廖姓,去住梗面地;我们的祖公罗姓,去住架长地。……我们的祖公廖姓,去住地麻哈;我们的祖公罗姓,去住地麻粟。……我们的祖公廖姓,去住麻哈地;我们的祖公罗姓,去住独神地。……我们的祖公廖姓,去住雄蒙地;我们的祖公罗姓,去住寨弄地。……我们的祖公廖姓,去住卡里地;我们的祖公罗姓,去住将故地。……我们的祖公廖姓,去住常大地;我们的祖公罗姓,去住嘎兄地。……我们的祖公廖姓,去住翁伸地;我们的祖公罗姓,去住嘎弓地。……我们的祖公廖姓,去住更我地;我们的祖公罗姓,去住加巴地。……我们的祖公朋蒙住碑铜①朋蒙,即廖朋蒙,指廖姓亻革家搬迁到枫香寨时祖公的名字;碑铜,系亻革家语,地名,指今天的枫香寨。,我们的祖公蓬逢住甲卡②蓬逢,即罗蓬逢,指罗姓亻革家搬迁到甲卡寨时祖公的名字;甲卡,地名,在今天哈龙寨的东南面。亻革家罗姓祖先到黄平时先是居住在甲卡寨,后才搬迁到今天的哈龙寨。。[16]198-208
上述迁徙《迁徙词》中表明了枫香寨的廖姓亻革家和黄飘乡哈龙寨的罗姓亻革家对其祖先迁徙地的社会记忆。相传,枫香寨的廖姓亻革家是同哈龙寨的罗姓亻革家是一道迁徙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婚姻集团。如果将以上迁徙地名作一个简化处理,则廖、罗二姓亻革家的祖先迁徙所居住的地点就可以表述为:
A南京、北京;B龚吴、旺解京;C广东、广西;D拱洋、拱江;E拱拢、门赛;F拱弄、麻引;G斯张、嘎哄;H梗面、架长;I麻哈、麻粟;J麻哈、独神;K雄蒙、寨弄;L卡里、将故;M常大、嘎兄;N翁伸、嘎弓;O更我、加巴;P碑铜、甲卡。
以上迁徙地名,英文字母代表迁徙的先后顺序;每个英文字母处有两个迁徙地名,前一个是廖姓亻革家迁徙地、后一个为罗姓亻革家的迁徙地。根据相关研究显示③参见《贵州亻革家民族研究文集》编委会.贵州亻革家民族研究文集[M].2006:6.39-40.,除 C、D、E、F处的地名未查实外,其他均已考证清楚:A处的“南京”指今河南商丘一带,“北京”指古时的汴梁城(今河南开封);B处的“龚吴”讲的是皇宫,“旺解京”指的是皇宫的大门;G处的“斯张”、“嘎哄”分别在今贵州的都匀市和独山县境内;H处的“梗面”、“架长”指今贵州黔南福泉市的“马场坪、铜鼓、羊老、鸡场”一带;I处和J处的“麻哈”、“麻粟”,“麻哈”、“独神”是今天黔东南州麻江县的“麻哈”、“麻粟”;K处的“雄蒙”、“寨弄”分别是指今贵州凯里市的“舟溪”、“哑口寨”;L处的“卡里”、“将故”即今黔东南的“凯里”和“岩头河”(今凯里市火车站一带);M处的“常大”、“嘎兄”指的是今贵州凯里的“凯棠”和“凯哨”;N处的“翁伸”、“嘎弓”是今黔东南州台江县内的“革东”和“革种”;O处的“更我”、“加巴”是指今黄平县的“牛场”与“加巴”;P处的“碑铜”和“甲卡”分别指的是今黄平县的“枫香寨”与“甲卡寨”。④见注释⑥。
从枫香寨廖姓亻革家的迁徙词中可以得知,尽管不断地迁徙,但是他们对本族群所居住过的祖居地却有着很深的社会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是对本族群“族源”的一种追溯和表达。族源是族群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族源认同既是对自己祖先发祥地和世居地的认同,更是其成员在作为他群体之别时的强烈的寻根意识[20]。王明珂认为,“共同的起源”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社会记忆形式,它以追溯人们的共同血缘起始,来仿真并唤起族群成员们的根基性情感联系[8]179,无论是祖先、起源地或一个源始世界,都能凝聚人群,人群再以共同族源来凝聚认同[3]54。可以说亻革家人从 A 处的“南京”、“北京”到P处的“碑铜”、“甲卡”这一迁徙过程不仅是一部关于祖先迁徙的口述史,更是亻革家人为了强调本族群共同的起源和强化自身的族源认同,而对其历届祖先所世居过的迁徙地的一种社会记忆,这种深刻的社会历史记忆,可以说是他们对本族群族源认同的最深层次的表达。
四、苦难记忆与族群自我认同的强化
苦难记忆是社会记忆的重要内容,在人类社会中“苦难记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这一点在犹太学中尤为明显。二战以后,犹太民族不断遭受外族的迫害,其集体性的苦痛记忆具有错综复杂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对苦难的态度是“不忘记”。之所以不忘记“苦难”,是因为“苦难”对于塑造人类记忆、凝聚族群意识和强化族群自我认同的作用十分强大。亻革家人在历史上的命运也十分坎坷和悲惨,他们的民族史可以说是一部反映共同历史遭遇与坎坷生活经历的苦难史。从一定意义上说,亻革家人对族群的自我认同主要是他们以文本或口述为叙事方式,对其先民“苦难历史”的追述和记忆去强化的。在亻革家人的社会生活中,对本族群的苦难记忆主要表现在历史上所遭受的几次惨绝人寰的屠杀的苦难事件上,其中有的是有文本记载,有的则是口头传说。
明洪武九年(1376年),贵州黄平、瓮安、余庆一带亻革民起义,明军先后三次镇压才将之平息下去。《明史·土司列传》载:“洪武九年,黄平蛮僚都麻堰乱,宣抚司捕之,不克。千户所以兵讨之,亦败。乃命重庆诸卫合击,大败之,平其地。”[21]关于这次起义的实况,有相关学人进行过调查考证。据黄平县民族识别工作组1981年的调查资料显示:余庆县龙溪的小乌江上游有个麻堰洞,麻溪河侧面也有个麻堰洞。所谓“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两麻”、“两洞”加上“邑十为都”,这就构成了“都麻堰”。当地如今还有亻革兜⑤革兜,又称“仡兜”,即亻革家,是汉语对亻革家人的别称。屋基、祭祖坪等老地名,残存有生于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的廖母胡氏太君墓碑。这些材料表明,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亻革兜居住龙溪一带了。“黄平蛮僚都麻堰乱”,应指龙溪亻革兜人的反抗[16]3。根据工作组的调查,我们可大致推测“都麻堰”位于今贵州省余庆县的龙溪镇,“僚”就是指今天的“亻革家人”,“黄平蛮僚都麻堰乱”指的就是当时黄平、瓮安、余庆一带的亻革民起义。当然,这一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考证,但从族群认同的角度来讲,以上的表述可以说是亻革家人为了强化其自我认同的一种寻根意识或社会历史记忆。
清顺治四年(1647年),亻革民兰二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率领数万名亻革民和其他民族起义,捣毁黄平州府,杀死了州牧,其势波及瓮安、余庆等县。《黄平州志》云:“顺治四年四月,土贼兰二大肆猖獗,先破瓮安、余庆两邑,人多从之,至围黄平数日即破,……以里应外合者众也。”[22]后来起义被清政府镇压,兰二被杀于旧州冷水河,亻革家人也因此遭到了清政府的大肆屠杀,这次屠杀使得亻革家人口锐减,生存下来的大多也被迫改族换姓。关于兰二是否为亻革家的问题,也有人做过一些调查。如1982年2月17日廖启科等人调查过黄平县野洞河乡万丰村的亻革家老人王国清。据老人介绍,在历史上他们家族是姓王,后因一位叫兰二的祖先发动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官兵采取“见兰就杀的灭族政策”,为了生存家族被迫改姓,但是今天在写香火牌位时仍要把兰、王二姓都写上去[16]4。此外,罗德华也曾在根据翔实的调查与文献资料所撰写的《关于兰二是亻革兜人的调查》一文中指出:“经过对兰二后代的寻访以及对兰二有亲友关系的后代提供的大量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兰二的民族成分是亻革兜人。”[16]138
另一次遭受屠杀的“苦难事件”大约发生在清朝末年。那时黔东南的苗民起义,亻革家人因此受到牵连,又蒙受了一次很大的灾难。笔者在枫香寨调查时,一位亻革家老人在谈到他们祖先这次苦难事件时说:在清朝,苗族有一次起义使得亻革家遭受很大的牵连。起义军声势浩大,轰动整个黔东南,后来朝廷派大军镇压,军队打到黄平时只要见到苗民和苗军就杀。被打败的苗军往南溃逃进入亻革家人的聚居地,苗军为了求生就对所到之处的亻革家村寨大搞“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挖光”(挖亻革家人的祖坟),同时清反动军队进攻到此又进行第二次杀戮。那次屠杀,使得亻革家人遭到的灾难达到空前,人口被灭了一大半,仅小部分人躲在深山莽林中得以幸存。就因为这次灾难,使亻革家人苦难的阴影至今都还未消除,所以到今天他们都很少和苗族通婚。
以上是三次亻革家人历史上比较重大的灾难事件和苦难的社会记忆。当然,据亻革家老百姓口述,在历史上他们的苦难遭遇远不止这三次,这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罢了。在这三次苦难记忆中,前两次有粗略的文本记载,后一次更多的则是口头叙事。至此,这似乎也就涉及到一个关于亻革家人“苦难事件”的“真实性”问题。其实不然,不论以上苦难事件是否真实,但对其大多数亻革家人来说,他们都已相信这是“真实的历史”了。因为在多次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已发现这样的“苦难事件”在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中已经根深蒂固,关于“苦难”的口头叙事在亻革家村寨中也早已妇孺皆知了。亻革家人之所以竭力考证自己先民和历史文本记载的一致和一再宣称历史上自己的先民曾遭受过若干次的大肆掠杀,是因为在一个民族所经历的许多不幸与灾难中,有些记录灾难的符号能激发一个民族奋发和自强的信心,能激发它从灾难中汲取教训、走向成熟,记载一个民族不幸与灾难的符号应该保留下来,成为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23]104。也就是说,亻革家人的“苦难事件”可以说是他们为了强化其族群的自我认同和族群意识,加强族群的凝聚力和使之不断走向成熟的社会记忆的“符号”。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无论这些“苦难事件”是否真实,亻革家人都持一种“认可”和“相信”的态度的原因了。
五、结论
综上论之,亻革家人的族群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自己族群的社会记忆而去实现的,他们以“对英雄祖先记忆、家族祖先迁徙记忆和族群苦难记忆”等社会记忆方式,去不断强化对本族群的身份认同、祖先迁徙地和族源认同以及族群的自我认同。一定意义上说,族群的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塑造出一种族群认同的意识。正如哈布瓦赫所指出的,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由于一些记忆让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因此许多社会活动都是为了强调群体的某些集体记忆,以延续并巩固该群体的凝聚[24]。
从对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的研究中,我们也应该明白族群认同就本质而言指的是我群体独特且与他群不同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中,如荣耀感、归属感、苦难感和危机感等重要的体验结构大都是在社会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族群的这些情感和特征通过诸多符号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23]107,并通过
社会记忆展现出来使其成为族群认同意识的基础。同时,族群认同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族群主观意识构建的过程,是动态的并由各民族系交流融合而成[25]的过程,是把一个族群的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和把族群建构起来[26]的过程,而这种勾连的桥梁和构建的手段就是——“社会记忆”。有了族群社会记忆的存在,人们所经历的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才成为了可能。应该知道,一个没有记忆的族群是可悲的族群,对过去的遗忘也就意味着对历史的否定。因此,笔者认为,族群或民族独特的社会记忆体系不仅是强化族群自我认同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区分、标识族群之间和表达其族群认同的特殊“历史叙事”方式和媒介。
[1]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
[2] 马成俊.基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生产与族群建构[J].青海民族研究,2008(1):1.
[3]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代序)[M]//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等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
[5] Peter Burke,Geschichte als soziales Ged?chtnis.in:Aleida Assmann und Dietrich Harth〔Hg.〕,Mnemosyne.Formen und Funktionen kultureller Erinnerung,Frankfurt am Main 1991,S.392ff.?
[6] 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7]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138.
[8]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9]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0.
[10] Lewis A.Coser,“Introduction:Maurice Halbwachs ,”in On Collective Memory,ed.&trans.by Lewis A.Cos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Maurice Halbwachs,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emoi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2).
[11] 万建中.民间传说的虚构与真实[J].民族艺术,2005(3):71.
[12]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7.
[13] 肖青.口头叙事与村名之争:一个村寨历史记忆的建构——以云南石林彝族撒尼村寨月湖村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08(1):53.
[14] 张原,曾穷石,覃慧宁,等.反思历史与关怀现实的学者——历史学家王明珂专访[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48.
[15] 刘芝凤.寻找羿的后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1~22.
[16] 贵州亻革家民族研究文集编委会.贵州亻革家民族研究文集[M].2006.
[17] 龙初凡.飒爽英姿“古戎装”、红弓白箭“射太阳”——亻革家服饰文化内涵考[J].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5):28.
[18] 定宜庄、邵丹.历史“事实”与多重性叙事——齐齐哈尔市富裕县三家子村调查报告[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2):33.
[19] 钟年.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从《评皇券牒》看瑶族的族群意识[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4):25.
[20] 李远龙.广西防城市的族群认同[A].徐杰舜.族群文化与族群[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358.
[21]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一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2] 王孚镛.黄平州志:卷三[M].嘉庆本.
[23] 李达梁.符号、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J].读书,2001(5).
[24]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0-94.
[25] 明跃玲.族群认同与互动:兼论苗族瓦乡人的族群意识[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7.
[26] 赵世瑜.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19.
责任编辑:谢娅萍
Social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of Gejia People
LI Ji-we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430074,China)
Social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topic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ethnology, sociology etc.This paper, referring to the theory of social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an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data of field work,analyzes Gejia′s ethnic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memory of heroic ancestor,memory of ancestor′s immigration and past suffering of Gejia people.Gejia′s social memory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its ethnic identity which is not only a key factor in strengthening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but also a special way in telli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expressing their ethnic Identification.
Gejia people;ethnic group;social memory;ethnic Identification
C955
A
1004-941(2010)05-0025-06
2010-09-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计划项目“未识别民族法律地位研究”(项目编号:10XFX0002)。
李技文(1985-),男,侗族,贵州施秉人,硕士,现主要研究方向为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民族文化与文化遗产保护。为,社会记忆是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7],是由人群当代的经验与过去的历史、神话传说构成,借由文献、口述、行为仪式(各种庆典、纪念仪式与讨论会)与形象化物体(如名人画像、塑像,以及与某些记忆相关的地形、地貌等等)为媒介,这些社会记忆在一个社会中保存、流传[3]253。他还将“社会记忆”同“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作了比较[7],认为社会记忆的范围较大,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三者之间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其实,在实际的研究中,三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包含与共融的关系,很难割离和具体区分。因而,在相当多的论著中,学者们也并未将之划分得泾渭分明,如常出现社会历史记忆[8]117、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6]7、集体历史记忆[3]252等概念也正是这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