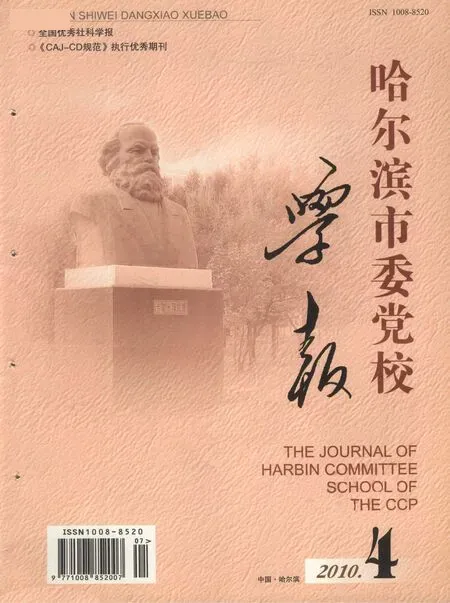中共七大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再探讨
李 亮,马晶钰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中共七大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再探讨
李 亮,马晶钰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中共七大迟迟未能举行不是偶然的,有战争的客观原因,但最主要的是毛泽东认为历史问题研究清楚了才能召开七大,首先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有多方面的原由,但最为主要的是,党和毛泽东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的思想,没有自觉地意识到领袖个人思想与作为集体智慧的党的指导思想之间的严格区别;另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新民主义革命的思想,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思想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
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党的指导思想
目前,关于中共七大许多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在此纪念七大召开 65周年之际,我们拟对以下两个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中共七大缘何迟迟未能举行
在 1931年 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就着手七大的准备工作,此后又多次作出过召开七大的决定。但是,直到 1945年 4月中共六大之后时隔 17年之久,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在延安召开。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次全国性代表大会迟迟未能举行呢?1940年 3月 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分析其中原因时指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困难的环境进行斗争造成的”[1]。任弼时在 1945年 4月 21日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开[2]。以此为据,史学界绝大多数人认为由于战争的原因影响了七大的召开。笔者认为,战争是导致七大延期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七大延期召开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于毛泽东为搞清历史问题而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
1928年 7月中共六大闭幕以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逐渐在党中央占居了统治地位,在中国革命道路上致力于调动红军主力攻打大城市,以配合城市起义,自然没有精力召开七大。1930年 9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瞿秋白、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时停止了冒险计划,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但六届三中全会及以后的中共中央对冒险主义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算。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扩大发展,特别是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行动,震动了国民党反动统治。1930年 11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一结束,就调兵遣将,致力于“剿共”内战。1933年 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同年 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的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 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 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盲目地听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方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失败,随后被迫进行了长征。1937年 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爆发。抗战全面展开后,中共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决定由周恩来率代表团与国民党再度谈判。但因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仍然犹豫不决,不愿答应中共提出的合理要求,因此,直到“八·一三”事变后,才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9月 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两党才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来解释七大的推迟召开。
但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 12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最近时期”召开七大而再被推迟,并且后来一直到 1943年 8月 1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中共中央 6次提出筹备召开七大都未能如愿,这就很难用战争解释了。马文瑞等七大代表在回忆中认为,七大迟迟未能举行主要是由于要进行延安整风。胡乔木印证了马文瑞等人的说法。他说:“最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战争,后来不是战争,主要的原因就是整风,就是要研究历史问题。把历史问题研究清楚了才能开。”[3]76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这个革命大本营。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的小后方,与其他各敌后根据地相比,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和安全。至少从 1940年年初起到 1941年上半年,各地的七大代表也已陆续云集延安。在这样情况下,召开七大不是不具备条件。况且,整风这么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可以在战争环境中进行,并且持续了三年之久,那么,只需要一两个月的代表大会为什么就不能在战争环境中如期举行,而是被一推再推呢?显然,战争并不是影响七大召开的根本原因。七大延期召开的根本原因,唯一的解释是先要进行整风运动。
《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应当对于自党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4]。但是从 1940年底起,政治局势开始恶化。就国内而言,首先是国民党于 1940年底完全停发了给中共的薪饷和物资,并调集几十万兵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年 1月国民党又包围袭击了奉命北移的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 9千余人。国民党惨绝人寰地制造屠杀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出现了尖锐对立的对抗局面。出于对国民党排除异己的卑劣行径的义愤,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毛泽东认定:“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5],一度被迫准备与国民党全面破裂和对蒋对日两面作战。
就国外而言,1941年 1月,日本政府为确保占领区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纲要》,从正面战场不断调集大量兵力用于维护后方治安。到 1942年时,日军在华北华中的 55万军队中有 33.2万人用于占领区,对我敌后根据地进行分割包围,这使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抗战时期,苏联则采取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希望中国抗日能捆住日本人的手脚,以使苏联避免陷入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1940年 12月,斯大林在召见即将出任驻华武官和蒋介石总军事顾问的崔可夫时,明确提出:“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运送给他们的武器,而且还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的信心。”“只有在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避免两线作战,如果德国侵略者进犯我们的话。”[6]为了笼住蒋介石积极抗日,苏联甚至不惜以牺牲中共力量为代价,采取单方面援助蒋介石的做法,这无疑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亲俄反共是蒋介石早有的预谋。1940年 6月,国民党制定的《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第五条原则就规定:“处置共党与对俄外交本为截然二事。中俄唇齿相依,邦交之亲睦,势所必然,况日寇之横暴,尤为两国共同敌人。中国现在艰苦抗战,苏俄亦不愿袒庇共党,致碍抗日。故吾人欲求对俄外交之进步,更非坚定本党对共态度,而有严正之立场不可,若多事瞻顾,使共党气焰日益嚣张,则非仅启英美法之疑虑,影响其对华援助之信念,且于苏俄之国际外交亦增多困难。”[7]而此时“苏联援华之前途已转趋积极”[8],蒋介石认为利用这个时机“关起门来打内战……苏联会不关心”[3]117,于是又一次磨刀霍霍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发生后,莫斯科以低调姿态调停国共两党关系。说服中共不要发生内部冲突,对于国民党的进攻克制和忍让。1941年 1月 15日,驻华大使潘友新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会晤,交换对皖南事变后时局的看法。潘友新认为,中共中央不应对国民党采取坚决反击的对策,中共领导人应同蒋介石会晤。他强调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必须同蒋介石会晤,不要期待蒋介石向中共乞求,要就所有的问题进行会晤和交谈。形势要求这样做,这一会谈只会对中共和中国有利。”[9]1月 25日季米特洛夫来电,要求“中共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以免上亲日派的当”[10];中共通过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要求苏联停止对蒋武器援助而转为援共,以便我夺取兰州一事,亦为苏方所拒绝,并再三叮嘱中共要设法延长国共合作关系。2月 5日,季米特洛夫再次来电提醒中共中央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要集中火力打击亲日派[11]。崔可夫还向周恩来转达了斯大林对国共两党的意见,要求国民党避免国共两军冲突;团结抗战;积极行动,歼灭敌之有生力量。要求中共军队积极行动,发展壮大自己;要继续抗战,起模范作用[12]。莫斯科的态度引起了中共中央的不满,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与联共迁就蒋介石的政策保持一定距离。
到了 1941年,无论国内外还是党内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党内整风成为必须实施的历史任务。1941年陕甘宁边区陷入经济财政的短缺危机,征粮达到空前的 20万担。各敌后根据地受到分割,地盘缩小,人口减少。恶化的形势对中共党内体制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这就要求中共党内迅速实现全党意志的统一,集中领导处于高度分散的各抗日根据地,并实行各根据地的分散决策,实际上即是要采取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同年 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军一度失利,德军兵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其后方又受到日军意图集结北上的威胁。这种自顾不暇的形势,无形中使斯大林放松了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于是,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控制,确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而发动的一场重大政治斗争。就中共党内来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流毒在党内还有很大的影响。1940年 3月,王明再版十年前写的“左”倾冒险主义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他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13]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也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看待党历史上路线是非的问题。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使全党同志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性质和后果认识清楚,就不可能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团结一致,成为坚强的革命指挥部。为此,毛泽东从 1940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看到许多过去在中央苏区没有看到过的材料,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而当时党内许多人包括党的高级干部却对此缺乏认识。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记载:“即使在党的高级干部中,1941年,也还有一些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要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可能的。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认识。”[3]176
1941年 9月 10日至 10月 22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整风决策,一场关于党内历史的大讨论就这样开始了。毛泽东已不打算轻易召开七大了。九月会议以后,七大的召开时间依然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已下了决心,不完成整风目标便不召开七大。这也是七大一拖再拖,直到抗战胜利前夜才召开的根本原因。
二、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原因
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有多方面的原由。多年来,研究者主要从国际国内党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本身的科学性和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中共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主要是由于党和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本身内涵认识所引起的。
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共党内多数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的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这是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主要原因。
1938年 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全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939年 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以比较完备的形式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原则。遵循这一原则,毛泽东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从各个方面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毛泽东的带动下,党内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高潮,并日益深切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为了树起中国革命的理论旗帜,以正确的思想体系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有必要对主要由毛泽东提出和总结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评价。
1941年 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第一个为毛泽东的理论命名。他在《共产党人》杂志第 16期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3年 7月 4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22周年,刘少奇写成《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于 7月 6日《解放日报》第 2版上发表,在文中他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同年 7月 8日,为庆祝党的诞辰,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最早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他指出:“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同志初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人所接受,在党内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并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下定义,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1945年 6月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至此,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正式被确定下来。
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阐述虽已揭示了它的基本特征和内涵,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文化水平的局限,王稼祥和刘少奇以至党内许多领导人,都没有正确认识和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之间的关系,经常把作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视为同一个概念加以使用。在上述王稼祥的文章中,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14]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他个人的思想。1943年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凯丰致信毛泽东,要求为毛泽东祝寿并提出要宣传毛泽东思想。4月 22日,毛泽东回信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 (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做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15]当时有人还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不赞成这一提法,他在与王稼祥的谈话中又指出:“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提主义。”1980年 8月 2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指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16]正是由于毛泽东以及党内绝大部分党员对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结晶缺少充分的认识,因此一旦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就会轻易地将毛泽东的思想替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工作指南。
除了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的思想,没有自觉地意识到领袖个人思想与作为集体智慧的党的指导思想之间的严格区别外,中共党内多数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本人还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新民主义革命的思想,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思想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这是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又一重要原因。
1942年 7月 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文章中写道,我们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同月,陈毅在《伟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中,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动力、前途及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关于革命战争问题,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关于建党问题,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并指出,毛泽东在湘赣闽粤四省进行苏维埃和红军建设期间,“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1943年 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也指出:“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他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1945年 5月 14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概括地说,毛泽东思想,就是“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里刘少奇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实质上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刘少奇的这一认识充分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认识水平,这从毛泽东当时对于七大有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和规定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可以得到佐证。
毛泽东思想不仅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也应该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而当时中共党内多数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只是把毛泽东思想简单理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因此,经革命战争的洗礼和延安整风全党认识达到一致后,中共七大便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了。
[1]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1936—1943): (1921—1943)补编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46.
[2]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436.
[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36—1938):第 10册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400.
[5]皖南事变 (资料选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183-184.
[6][苏 ]瓦·崔可夫.在华使命 [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0:36.
[7]孟广涵.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 [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649.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8:88.
[9]历史和现代·一个外交官的札记 [J].远东问题,1991, (1).
[10]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9.
[11]1941年 2月 5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信[J].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6,(13).
[12]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491-492.
[13]王明言论选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4.
[14]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3-336.
[15]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12.
[16]邓小平文选: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5.
[责任编辑:孙 霁]
D231
A
1008-8520(2010)04-0082-05
2010-04-06
李亮 (1971-),男,山西代县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