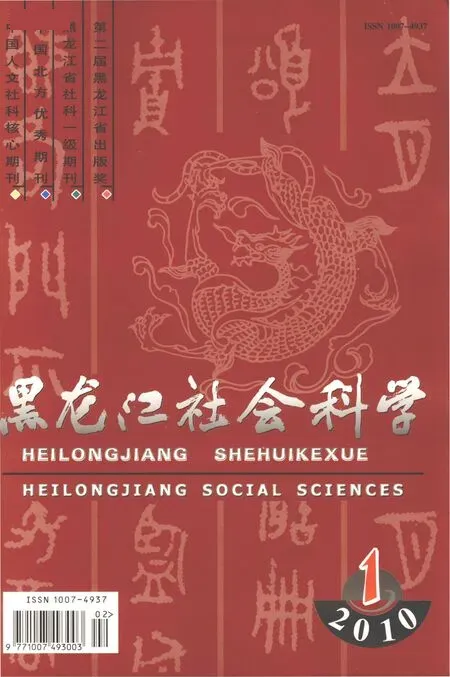从《饿乡纪程》到《赤都心史》——试论瞿秋白思想和心灵的发展轨迹
郭长保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387)
从《饿乡纪程》到《赤都心史》
——试论瞿秋白思想和心灵的发展轨迹
郭长保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387)
瞿秋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经历较为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初激烈变动的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心灵苦闷和矛盾心理;二是典型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和思想追求。这种矛盾和苦闷的心理在其早年的文学作品《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留下了清晰而鲜明的发展轨迹,典型地体现出“后五四启蒙者”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
瞿秋白;“后五四”;《饿乡纪程》;《赤都心史》
一、迷惘:苦闷中的追求
从《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到《赤都心史》清晰而鲜明地留下了瞿秋白从一个中国近代文人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型的深刻烙印,他的思想和心灵的转换历程较典型地折射出了20世纪初一代知识分子从晚清以来的绝望中开始寻求新希望的人生道路。从这一角度来看,那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向往和仰慕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形成这一思想基础和历史条件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家庭,在20世纪初中国的传统家族制度走向衰落的事实已几乎是人所共知,而家庭的变故往往对人的心理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个人的经历和生活可能使其产生厌世的态度,也可以激励其追求新生事物,试图改变现状;二是社会的现实也往往会使人的认识发生大的变化,要么很容易绝望颓废,要么去寻求改造社会的希望。
而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现状是在晚清衰落以后,尽管辛亥革命的暂时胜利曾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和兴奋,但兴奋过后很快就是绝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对文化的改造上,而对文化的改造又必须建立在对民众(国民)的改造上,譬如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就转而把中国的希望建立在“国民”的身上。但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的彻底改造需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主义”基础上,毫无疑问,这一思想的形成以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曙光。而瞿秋白正是在这一新希望的吸引下于1920年8月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启程赴俄罗斯实地采访。《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就是记载瞿秋白赴莫斯科的过程和在莫斯科一年多的感受和感想,“是中国最早的记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初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情况的作品,同时又非常真挚地刻画了作者如何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发展的过程”[1]。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府城内一个败落的士绅之家,由于家庭的败落,经济的拮据,其母金璇于1916年2月自杀。家庭的不幸遭遇对年少时的瞿秋白心灵打击是巨大的,正像他在《饿乡纪程》的绪言里开头所说,“我有生以来,没见一点半点阳光,——我这到如今还不知道阳光是什么样的东西”。在这样的人生旅途中要么很容易绝望颓废,要么去寻求改造人生和社会的希望。瞿秋白正是在人生绝望和苦闷的过程中经历了人生的历练,也正是这坎坷的人生经历促使其试图改变现实。于是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同年11月参与创办了《新社会》旬刊。1920年初,他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和知识分子思想的微妙变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说正迎合了当时许多类似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心理追求。
不过,我们在看到“后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理想追求时,必须注意到它和近代文人追求的联系性,他们试图完成近代文人所未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所不同的是,近代没有十月革命,是在黑暗中摸索和探求中国的未来,“洋务运动”失败了,“维新运动”也失败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即使“辛亥革命”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因此才有了鲁迅,鲁迅是中国近代变革失败背景下的产物,他试图在绝望的近代文化背景下寻求中国的新生和一线希望。这希望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民族和民众的觉醒。而在几千年封建文化奴化文化背景下生存惯了的中国国民的觉醒是何等难的事情。因此鲁迅是“孤独”的,甚至是“绝望”的,这就是鲁迅文章中始终充满批判性和攻击性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天人们难以读懂他的原因。读者常常会把他置于新的文化背景下看,殊不知,其实鲁迅更是一个近代性的作家,形成鲁迅思想体系的背景是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而主要还不是新文化;鲁迅追随新文化,那是因为新文化正符合了鲁迅的追求和理想。他在《呐喊》序言中就说过:“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2]这也说明鲁迅确实是从梁启超到“新青年”派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之间的桥梁式的中间人物。所以,当20世纪20年代末鲁迅一经和瞿秋白接触,便有了共同的语言。这共同语言,一方面是两者的家庭背景多少有些相似,都是败落的士绅之家,另一方面说明瞿秋白对鲁迅有着不同于当时年青一代知识分子的真正理解,因为当时一些甚至是非常进步的知识分子,对鲁迅是不能真正理解的,因此鲁迅对瞿秋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他在赠给瞿秋白的对联上写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在瞿秋白身上看到了五四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希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还没有找到新的光明,始终在黑暗中摸索光明,而瞿秋白似乎点燃了鲁迅内心的光明。确实,从瞿秋白所走的道路来看,五四新文化,特别是十月革命后一部分进步青年似乎看到了中国未来的一线光明,尽管这光明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是那样的模糊,“我眼睛早已花了,晕了,我何尝看得清楚”[3]2。但也正像他自己所说:“一线的光明!一线的光明,血也似的红,就此一线便照遍了大千世界。”[3]4这里所说的一线光明应该是说明作者对苏俄十月革命的向往和期待。这样的向往和感受可以说是几乎贯穿了整个《饿乡纪程》中,因为《饿乡纪程》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写作者去“饿乡”的过程中的经历和感想,还没有真正接触到实际的“饿乡”现实,其中只有后半部分才有了到“饿乡”后的一些具体感受,但并没有上升到理性的思考阶段,不过尽管作者在去苏联的路途中所遇到、所看到的并不都是好的印象,但到苏俄后还是给作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我寻求自己的‘阴影’,只因暗谷中的光影相灭,二十年来盲目求索不知所措,凭空乱舞我的长袖,愈增眩晕。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3]109。由此可知,瞿秋白在刚刚到了俄国以后,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不仅是自己的希望,更是祖国的希望。在此之前,他其实对中国的前途是不抱希望的,甚至是有些“颓废”的,也是无奈的心情,比如在哈尔滨滞留期间,作者就多次对中国国人的麻木精神多有不满,但这只能说是作者的直觉,并没有上升到理性的角度去思考。而《赤都心史》就不同了,在对十月革命的光明向往中,也蕴含着作者对革命后的困难和矛盾的深层次思考,而非是简单的歌颂。
二、追求:探索与追求中的矛盾
作者在《赤都心史》的序中说:“《赤都心史》将记我个人心理上的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3]114这里关键的是“所思”,因为瞿秋白到达莫斯科后,接触了很多俄罗斯共产党的官员,甚至是高级官员包括列宁,也参观了很多地方,包括托尔斯泰的宅邸。如果简单看来,作者确实是记载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且是用了散文和随笔式的手法记录了他的经历,但我们把《赤都心史》中每一篇看似零散的短文联缀在一起时,就不能看成是简单的记录和报道了,它包含了瞿秋白对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更深的理性思索。因为无论从任何角度看,瞿秋白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革命者,正如他在1935年5月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中所说:“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此可知,他更热衷于文学,从《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部作品集中也不难看出,他并不是从一个革命者的角度来报道,而是从一个对革命抱有极大热情和理想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角度去写的。因此,这两部作品的研究更应该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所以文学史中常常把它看成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滥觞。
瞿秋白的写作才能和激情应该说主要是来自于他对新生事物的探索兴趣和对“十月革命”的崇拜。他尽管不是五四新文化的启蒙者,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但他却承担了“后五四”启蒙者的重要角色。如果说第一代中国的启蒙者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文人,其启蒙任务主要是“救亡图存”话语,那么以鲁迅、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承担了20世纪中国“新文化”理念的启蒙者角色,其任务主要是完成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为中国文化的下一个任务奠定了思想和历史的基础。
而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就可看成是中国文人思想理念从“新文化”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转型。瞿秋白就是这一观念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分子。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所以受到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青睐,它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中国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现状决定了的。尽管第一和第二代启蒙者们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从社会实际和经济的角度看,显然还是一种理念、一种理想,还只是停留在文化层面上的变革,因此那只是一种价值观念,并非是一种物质的和制度的东西。“如果要全盘抛弃这种传统,那就要对它的政治结构或经济制度的根源进行抨击”[4]。尽管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也不断呼吁“一个有计划的政府”,但“后五四”启蒙者则不同,他们并不认为沿袭着旧文化的政府能真正意义上挽救中国,他们试图寻求一种能够保证“新文化”和“新理念”的代表着下层民众利益的制度,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五四学生们深信,他们能够从下层通过唤醒同胞们的社会意识的办法挽救中国”[5],再加上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罗斯的成功,毫无疑问地为新一代知识分子们增强了复兴中国的信心。而瞿秋白就是带着这种既不想抛弃自己曾经的文学理想,又怀着对十月革命的向往和崇仰之情去“赤都”的。
那么,带着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情去十月革命的故乡,他就不可能完全从“革命者”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问题。他在莫斯科期间的确看到了许多令他兴奋的事情,比如,1921年7月以中国记者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就被列宁的演讲所折服,正如他在文中写道:“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3]162作者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特别是对列宁个人魅力的崇仰之情,使他对十月革命的未来增强了信心。但也有很多社会现象使作者产生了一些疑虑,特别是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还不是很好,大部分人,甚至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也只能吃到黑面包,“——呵,你们来开‘大会’的,预备回去宣传无产主义吗?我笑着回答他不是的。他还不信呢……奄奄的生气垂尽,一切一切都渐渐在我心神里磨灭……还我的个性,还我为社会服务的经历来!北地风寒积雪的气候,黑面包烂肉的营养,究竟不是一片‘热诚’所支持得住的。唉!心神不定,归梦无聊。病深了,病深么”[3]164-165。从当时瞿秋白的思想情绪看,确实很难说他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思想家,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作为“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进步代表者,他也并不放弃十月革命为全世界“劳工”所带来的希望,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还是选择了无产阶级的事业,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者。“总有一天,所有的‘士’无产阶级化了,那时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总有那一天……”[3]211瞿秋白本人就出生在一个衰落了的“士”的家庭,尽管对此还是悲挽的,但他对无产阶级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比较典型地代表了“后五四”启蒙者一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复杂的心态。
我们说瞿秋白对现代中国的文化贡献是巨大的,那是不仅仅因为他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宣传者,而且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推动者。正是他的热情宣传和翻译俄国无产阶级的文艺著作,为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所以说他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发展功绩是无法抹杀的。
也可以这么说,鲁迅正是与瞿秋白这样的共产党人的接触,才使鲁迅进一步产生了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信念。这使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的第二代启蒙者代表鲁迅与“后五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代表之间的思想契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世纪转折的背景下,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是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痛苦抉择中而走向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
[1]瞿秋白文集(文学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3.
[2]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9.
[3]瞿秋白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48.
[5]许纪林.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239.
J3
A
1007-4937(2010)01-0093-03
2009-11-27
郭长保(1958-),男,山西太原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郑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