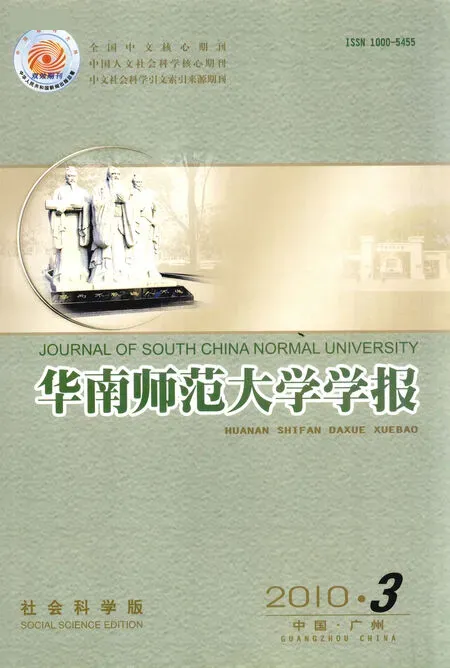帝党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新探
王亚芳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广东广州510076)
帝党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新探
王亚芳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广东广州510076)
对帝党这一不可忽略的作用,以往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深入的研究。百日维新的出现与帝党的努力、采纳维新派新政并重用维新人士有密切关系,帝党与维新派新政建议的相同或相近也是促成百日维新出现的一个关键所在。同时,帝党的政治主张与维新派的政治主张相比也有许多矛盾之处。不弄清楚帝党与维新运动之间的关系,就难以对帝党这一政治集团作出恰当的评价,难以充分了解维新运动的复杂性,也难以深刻阐明维新变法所留下的历史教训。
百日维新;帝党;维新派;变法失败
在戊戌变法时期发挥作用的各种政治力量中,帝党是十分重要的一支,对维新运动的兴衰起着明显的制约作用。从维新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看,没有帝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在守旧势力盈朝、维新派势小力微的情况下,变法运动的迅速兴起乃至百日维新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而戊戌变法之所以昙花一现、迅速失败,也与帝党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关系。
一
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种观点认为帝党虽然主张变法,但只是忠于皇上,只是主张在皇帝的独断下改革某些弊病。他们并不同意康有为的民权平等说,与维新派的许多变法主张也大有差距,只是为了利用维新派,才不得不暂时容忍和合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变法的态度明显地前后不一。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如何正确认识帝党在变法运动中的矛盾表现及其与维新派之间的差异,是研究帝党与维新运动失败原因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甲午战争后,洋务派官僚所办“新政”破产,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战后清政府的经济危机较以前更为严重,人民反抗已不断地、小规模地发生,由地主、商人转化为资本家的资产阶层也不满意清政府的统治而要求政治上有所改革。这样在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就酝酿着改革运动。帝党作为一种要求政府对“内政”进行改革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封建顽固势力盘踞的皇宫和朝廷里,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中国社会深刻变动的结果,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渗透下,出现巨大裂痕的表现。
帝党的这些朝廷命官,与维新派这些士人学者相比,在政治思想上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他们之间,有相互合作的一面,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无论是变法初期还是变法高涨时期,这两方面都交织在一起。那些较年轻的帝党人物,如文廷式,原是强学会的一个重要成员,但在百日维新前,就骂康有为“此伧耳,何能为”①?又如沈曾植,也是竭力鼓励康有为发起强学会、并且赞助他变法的人,但在百日维新前,就不满他的“鲁莽偏激”②。张骞也认为康有为“张甚”,他的变法活动是一种“轻举”,“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③。从他们在变法前及变法过程中的若干活动看,他们对康梁所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是支持和赞助的,他们之所以不赞成康有为等采用“骤变”的手段,主要认为在封建顽固势力掌握统治权的局势下,采用激进的做法是一种冒险,于大局无补。张元济于各省广设学堂及废八股的诏书颁布之后,劝康有为“乘此机会,出京回籍,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上,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④。而康有为未能从其言。张骞的长达二万余字的《变法平议》也表达了这一态度。他在开头的前言中,就批评了戊戌变法,反对康梁的“速度”的做法,认为“意行百里则阻于五十,何如日行二三十里者之不致于阻而犹可达也”⑤。这种想法,在变法者内部也同样存在,康广仁就以康有为倡导的变法“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为虑,认为“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⑥。可以说帝党一些成员所设想的变革方案,与康梁变政想法相比较,显得温和缓进。这固然是由当时的政治局势和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但其中的合理成分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
翁同龢与康有为的关系,是帝党与维新派之间联系最紧密的一个环节。他对康有为的知遇之恩可谓深也。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1898年1月间,翁同龢曾面荐于上,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⑦说“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或过于夸大,但大量的史实已经充分证明,翁同龢不仅曾向光绪皇帝推荐重用康有为,而且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也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翁氏和康有为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康有为变法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不满上。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二日,“看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⑧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七日记:“上命臣: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⑨读《孔子改制考》而知“此人居心叵测”,可见翁氏与康有为在思想认识上是存有分歧的。在帝党内部,对康有为孔子改制理论持反对态度的不只是翁氏一人。陈宝箴、黄遵宪是热心的改革者。湖南维新运动的轰轰烈烈,与他们的倡导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但他们不赞成孔子改制理论。当湖南维新守旧两派激烈冲突时,陈宝箴上了一个《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认为孔子改制之说是“偏宕之辞”“伤理害道”,请“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板本,自行销毁”。黄遵宪则认为康有为宣传改制的原因是“南海见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为泰西富强由于行教,遂欲遵我孔子以敌之”⑩。他在南学会的讲演中说:“今日但当采西人之政以弥缝我国政学之弊,不必复张吾教与人争是非短长也。”直到1902年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还反对康有为以孔子为教主的宣传。
这里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帝傅孙家鼐。他在变法中虽然是拥护变法的,但对孔子改制理论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康有为才华甚富,学术不端。梁启超奉命办理译书局事务时,孙家鼐怕他借机宣传孔子改制,特上了一个《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侯钦定颁发并严禁悖书疏》,认为孔子改制理论如果宣传开去,会“蛊惑民志”、“导致天下于乱”,要求把“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宣明降谕旨,亟令删除”。结果在变法蓬勃兴起之时,孔子改制考又一次遭到了被封禁的命运。孙家鼐是戊戌变法时期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他一生自道光七年至宣统元年,几乎经历了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目睹了几十年来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长期的官宦生涯使其不可能产生与康梁相同的维新思想,因此出现分歧是难免的。这一点对其他帝党官僚也同样适用。除此而外,孔子改制考理论在学术上的武断及牵强附会,也使人们难以倾心相从。康有为宣传孔子改制理论,是想论证变法维新合乎圣人之道,以避免和减弱守旧顽固派对变法的攻击;但他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结果引来众多的反对,连梁启超都认为“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时时病共师之武断,后遂置之不复道”。维新派尚如此,那么帝党官僚反对孔子改制理论也是无可厚非的。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使君权思想根深蒂固,但对帝党来说,维新派从西方搬来的天赋人权论,提出了开议院兴民权的思想主张。对君民关系产生新的想法的帝党并非全都反对,名列帝党的陈炽和汤寿潜早就在他们的论著《庸书》和《危言》中,论述了开议院的主张,实际也是要求伸民权。翁同龢曾专门把这两本书进呈光绪帝。御史宋伯鲁则详尽地提出了改革封建政体的建议,认为“今日岌岌救危,不能改制立法”,建议皇上“特开立法院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入院办事,皇上每日亲临时,三大臣派为参议,相与商榷,一意维新,草定章程,酌定宪法”。其他人虽然没有提出开议院的主张,但也都有要求公开政治的强烈呼声。徐致靖提出了“省冗官酌置散卿”的主张,骆成骧的“今议院未有豫开,则公半执政之法,不可不为先务也”。这些力矫专制积弊的措施,多少带有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要求。虽然他们所主张的议会制度,还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而是皇帝手下的咨询机构,没有立法权,最高权力仍然操之于皇帝之手;但是他们提出的公开政治的要求,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尤其是由受过几十年传统教育、饱食俸禄的封建官僚口里提出,更是意义重大。
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与标记。新旧交替的时代必然产生新旧杂糅的思想。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要士大夫具有忠君思想。按传统方式通过科举入仕的封建官僚不可能在一夜间抛开这一观念而变为革命者。帝党和维新派在时代的交替中曾一度相互依赖,也有过矛盾,但不能否定这一依赖对历史向前发展的作用。
政治斗争的转折关头,往往最容易鉴别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在生与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帝党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表现不尽相同。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在变法开始前,是最早向皇帝递奏保荐康有为的官员;但政变刚一发生,就迫不及待向慈禧献策,请将康有为、梁启超“务获解京,或即就地正法,以免蔓滋”。早年参加过京师强学会的御史王鹏运,与康有为来往密切,多次代康上书,弹劾“事事阻挠”新政的军机大臣徐用仪;戊戌正月,他又代维新派上书请示朝廷明确表态,宣告变法。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王鹏运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不仅要慈禧对维新派“悉与惩治”,而且要“将该员等分别等差,治以应得之罪”。人们读史至此,莫不对人类历史上这种可悲现象痛心疾首。
对大部分帝党官员来说,他们与维新派的合作关系是始终如一的,表现出对变法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战斗精神。湖南守旧党曾廉上书请杀康梁,深文罗织,谓为叛逆,刘光第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杀康梁则“先请坐罪”,表示把自己的命运和维新派连结在一起。戊戌七月以后,新旧两党矛盾已极度尖锐,守旧势力十分猖獗,京师气氛极为紧张,宋伯鲁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同康有为往来更密切。他曾代康有为递上弹劾“昏老悖谬、阻抑新政”的两广总督钟麟和广东省臬司魁元,主张用李端芬、陈宝箴等倾向维新的大员取而代之。政变前夕,他和杨深秀等人还同往康有为住处慰问。戊戌八月初六日慈禧颁布了训政诏书,宋伯鲁还代维新派递上最后一个奏折,要求光绪帝采取紧急措施,重用康有为。张元济也是如此。八月政变后,张元济在致函汪康年书尤说:“事变之来,且更有不可意想者,向来变法莫不如是,惟望新党勿为所摇夺耳。”帝党正是由于有这种为改革献身的精神,便能够在危难时刻始终与维新派结盟,才使得戊戌变法的光辉得以划破封建统治的夜空,给后人的继续探索前进提供巨大的启示和鼓舞。
从《马关条约》签订到百日维新结束的4年,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4年,也是帝党从思想上与维新派不断趋同的4年。由于帝党成员的参预与支持,使得“布衣改制,事大骇人”的变法活动能够冲破种种障碍而兴起和发展,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究其原因,是帝党一旦投入维新运动中,即以他们较高的政治地位,在变法中运用自身的权威,做出了维新派不能做出的贡献。戊戌变法最终是失败了。它的失败虽取决于诸多因素,但帝党权力的不足是一大关键。它决定着变法的最终命运。总观帝党对维新运动兴衰中所起的作用,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中所蕴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无疑是值得后人认识吸取的。
注 释:
①② 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2页。
③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光绪戊戌年(1925年铅印本)。
④ 张元济:《追述戊戌政变杂咏》,《戊戌变法》(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5页。
⑤ 张骞:《张季子九录·专录》,第七、二卷,中华书局1932年版。
⑥ 《戊戌六君子集·康幼博茂才遗文》,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1-2页。
⑦⑧⑨ 《翁文恭公日记》,《戊戌变法》(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五月初二日、四月初七日,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⑩ 黄遵宪致梁启超的信(1902年),见壬寅四月《新民丛报》。
【责任编辑:赵小华】
K256.5
A
1000-5455(2010)03-0104-03
2010-04-20
王亚芳(1969—),女,吉林农安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