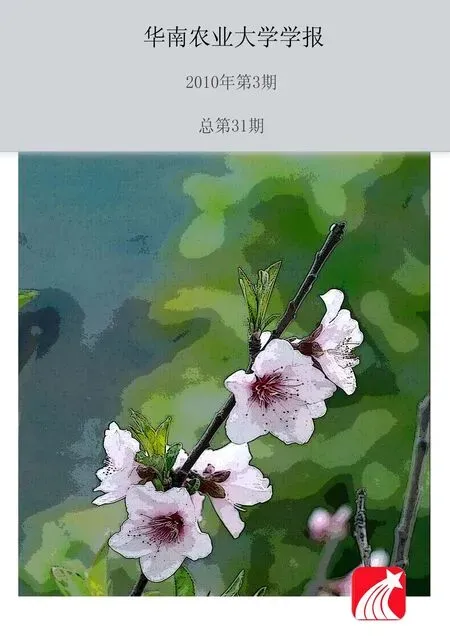民间宗教的语言与城镇化农村治理
——以妈祖信仰为例
朱武雄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农村城镇化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是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城镇化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仅以经济标准来组织城镇化、衡量城镇化,而忽视了如何使作为城镇化主体的农民融入新兴城市,使他们成为城镇化农村治理的主体,使他们转化为市民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民间宗教是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民间宗教内含的符号系统实际上已经在城镇化农村构建了一套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体系。这套体系区别于作为正式制度的村民自治系统,是一种隐性、非正式的治理系统。城镇化农村中的妈祖信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研究这套系统不仅有利于解决民间宗教与城镇化农村治理之间存在的各种复杂矛盾,克服民间宗教自身缺陷,还可以应用它来鼓励农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提高他们的公民意识,从而真正把他们转化为市民,让他们有机会共享农村城镇化带来的成果。
一、语言、神话与民间宗教
(一)语言与神话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可以被视为文化的产品,一个社会所使用的语言是整个文化的反映。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语言也可以说是文化的一部分[1]73。不同范畴的社会现象和语言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相似性,而语言本身即为社会现象之首[1]538。那么什么是神话,神话与语言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作为语言的样态,神话和民间故事是对语言的‘超结构’运用,因为它们可以说形成一套‘元语言’,结构存在于它的所有层次上。”[1]621当然,单纯的“元语言”也不足于形成神话,它必须与语言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神话和民间故事。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拥有一些共同的层次,但是这些层次却又是相对错开的,“神话中的词语虽然依然是话语的词项,但其是作为区别性成分的那一部分从中发挥作用的。”[1]621-622因此,从归类的角度看,可以把“作为区别性成分的那一部分”称为“神话素”,神话素的位置不在词汇层次,而是在音位层次上。神话素具备双重含义:“它们是词语之词语,它们在两个方面同时起作用:在语言方面它们继续各自表达着自身的意义,但是在元语言方面,却是作为带有超意义的成分而发挥作用的,而二者只有结合方能产生超意义。”[1]623因此,神话就是语言行为,但它是一种在极高层面上发挥作用的语言行为[1]225。显然,语言与神话之间不但存在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还是相当密切的。
(二)从神话到民间宗教
在研究从神话到民间宗教的演变过程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民间宗教。美国学者泰勒认为,民间宗教是“在官方宗教之外所发展出来,不为法律所允许,也不为在官方登记并接受管理的佛教或道教僧侣接受的各种结构松散的信仰崇拜”[2]。台湾学者郑明志认为,民间宗教依附在民间信仰的生态环境上,它依存于社会,却偏向于儒释道的宗教形式,有其自成体系的固定教义,以及具有发展动力的教团组织,是潜伏于基层的宗教势力,是一种新兴宗教,存在成为“正统”宗教的机会[3]。马西沙认为,民间宗教,是指流行于社会中下层、未经当局认可的多种宗教的统称[4]。显然,民间宗教属宗教范畴,它以对神灵的信仰和崇拜为核心。它满足的对象通常是中下层民众,并且往往未获得统治当局认可(当然这也并非绝对,妈祖信仰就是例外,她自宋代到清代共获统治当局敕封达36次之多),因此民间宗教往往具有草根性。在中国的宗教发展史中,从神话到民间宗教的演变往往根植于这种草根性。
神话和仪式可以被视为神人之间(神话)或者人神之间(仪式)沟通的方式[1]538。神话是民间宗教的源泉。几乎所有的民间宗教都与神话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神话被视为社会结构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折射[1]222。在神话所植根之处,存在着双重对立,“首先是平凡的命运与英雄命运之间的对立,前者履行了安度完整而不能更新的生命的权利,后者出于部落的利益把这种权利置于危险当中。”第二种对立是两种死亡的对立,一种是普通的死亡;另一种死亡是周期性的,以往来于生死之间为特点[1]690。民间宗教则恰恰来源于这个双重对立的不断调和,如妈祖,平凡的人,却与她救世济民的英雄行为融合在一起;普通人的生命结束,却带来了她英雄生命的复活。这也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一个想要安享完整寿命的人会得到一种完整无缺的死法;然而,一个完全出于自愿而放弃生命、追求死亡的人会获得两种酬报:一方面,他会增加他的部落成员所分摊到的寿命;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进入一种以不完整的寿命和不完整的死亡不断交替为特点的状态。”[1]690当普通人的生命与英雄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当普通人的死亡与英雄的死亡结合在一起,进入一种以不完整的寿命和不完整的死亡不断交替为特点的状态时,人就获得了永生,人也就神化了。并且一旦神化的人获得民众的信仰,伴随着专门仪式的出现,民间宗教就产生了。
(三)民间宗教的语言
从上面分析中,可以发现语言、神话与民间宗教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语言是“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5],当我们研究民间宗教的语言时,实际上也就是在研究它的符号系统。人类是利用象征和符号从事沟通,一切都是象征和符号,它们是出现在两个主体之间的媒介[1]475。民间宗教的符号系统主要有四个:神话系统、仪式系统、文艺系统和议事系统。
神话系统。民间宗教首先是一组神话组成的系统。如妈祖信仰,妈祖自降世之时就与神话相伴,有她救父寻兄、祷雨济民、解除水患、湄屿飞升的神话传说,也有她海上救难、梦中送子的神话传说,更有她助剿海寇、助清收复台湾的神话传说等等。可以说,神话构筑起了民间宗教主体的理想追求与心理体验,它可以使信徒沉迷于神的超自然力量之中,依附于它。
仪式系统。仪式系统是民间宗教的核心符号系统。任何宗教都是建立在仪式的基础之上,宗教生活就是一种仪式生活。从仪式中,宗教信仰主体不仅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而且也赢得了世俗的地位。如妈祖信仰的仪式就相当复杂,既有日常生活的“点神烛”仪式、摘“妈花”仪式、“撕龙袍”仪式[6]14,也有正式宗教生活中的祭典仪式、法事仪式、巡游仪式等等。
文艺系统。民间宗教的文艺系统是作为神话系统和仪式系统的延伸物而存在的,除了普通的宗教功能外,它更多充当了民间文化娱乐的功能。如附属于正式仪式的各种文艺表演,特别是戏剧艺术。在妈祖信仰中,不仅在各种妈祖庆典活动(妈祖诞辰日等等)期间会有民间戏剧表演,而且还产生了以妈祖神话为内容的地方戏剧,如《天妃降龙全本》、《妈祖出世》、《天妃庙传奇》等等。当然,这里特别要提一下木偶戏。木偶戏不仅是一种文艺活动,其本身还是民间宗教仪式的一种。在莆田民间宗教生活中,木偶戏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献演给神看的,其仪式的功能往往大于娱乐的功能。
议事系统。议事系统是民间宗教符号的灵魂系统。首先,议事系统自身是各种语言博弈、沟通的中心场所,整体上看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其次,它实质上掌握了民间宗教的话语权;其三,它为民间宗教各种符号系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提供了平台,换言之,它架构起了民间宗教的符号系统;最后,它是民间政治生活在宗教领域的表达。如福建省莆田涵江东坡村的天后宫董事会就是一个典型的议事系统[6]20。
二、民间宗教语言题阈中的城镇化农村治理
城镇化农村是指正经历城镇化的农村和已经实现城镇化的农村。民间宗教语言题阈中的城镇化农村治理是一个融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在一起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民间宗教的话语表达与农村民主自治
城镇化农村治理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农村的民主自治。俞可平认为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7]。就我国沿海农村而言,城镇化农村的治理结构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在正式制度层面上,形成以村民自治委员会为中心的自治结构;在非正式制度层面上,形成以农村民间宗教组织为核心的自治结构。民间宗教组织是农村公民社会组织的主导力量。这里有必要说明一点的是,民间宗教组织与宗教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宗教组织通常以宗教教义为组织原则,以信仰追求为根本目标;而民间宗教组织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议事的非正式机构存在的,它的目标更多的是为民众提供解决问题的平台,尽管某些时候这种平台是建立在民间宗教的基础上。因此,民间宗教组织更主要是作为一种城镇化农村市民①生活的一种载体。
① 此时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已经摆脱或基本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成为了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从业者或其他不再单纯依赖土地谋生的一个群体。
民间宗教组织在城镇化农村治理中往往充当着“影子内阁”的角色,甚至某些时候其作用还超过村民自治委员会。各村的妈祖庙董事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董事会通常由三类精英组成,包括民间宗教精英(妈祖信仰巫师)、经济精英和政治权威型精英。民间宗教精英以巫师为代表,主要从事宗教祭祀或象征的仪式等各种宗教活动。经济精英加入民间宗教组织则主要是受其实用主义心理影响,企图通过民间宗教减轻风险的精神压力和祷求获得经济利益。政治权威型精英[8]96进入民间宗教组织则往往希望借助此载体来增加权威。三类精英控制着民间宗教话语的表达,从而使其与农村民主自治产生互动。
妈祖信仰巫师主要通过民间宗教神话系统、仪式系统来参与妈祖信仰语言系统的构架,控制着神人之间的话语沟通。妈祖信仰的语言系统在宗教层面的架构是巫师以祭祀或象征的仪式等各种宗教活动来完成的。话语沟通是巫师在神灵与信徒进行意志沟通的各种宗教方式,他们是信徒问灾、抽签等结果的解读者。巫师通常只专司于宗教事宜,与农村民主自治间的联系并不密切,他们更多地归属于私人空间,更偏向一种私人的公共生活。经济精英则主要通过议事系统参与妈祖信仰语言系统的构架,并负责着某些方面的的话语表达,但这些行为往往只有到了农村城镇化晚期时才会逐渐出现。在城镇化早期,经济精英更愿意去追求经济利益,而在农村城镇化晚期以后,经济精英在民间宗教话语表达中已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愿意参与政治,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经济优势足以让他们在话语表达方面释放出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在农村城镇化中晚期或完成之间,经济精英对农村民主自治起的作用非常大。政治权威型精英是妈祖信仰语言系统构架的核心人物,他们是妈祖信仰符号系统的谋略者和规划者,他们的影响渗透到符号系统的各个环节中,但主要控制着议事系统,并通过议事系统来遥控其他系统。他们主导着妈祖信仰的话语表达,是农村民主自治中的隐形政治权威。如果把农村政治领导者定义为政治精英的话,那么政治权威型精英则应当是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的一种混合体。他们与农村民主自治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三类精英组成的妈祖董事会在农村民主自治中与村民自治委员会之间是一种权威的博弈关系。董事会控制着农村私域的公共生活空间,而村民自治委员会则控制着农村公域的公共生活空间。近年来董事会有不断侵蚀公域公共生活空间的现象发生,典型的表现就是董事会参与,甚至主导了行政村的某些公共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如修建村里的水泥路、修建路灯、缴纳路灯电费、修缮村所在的小学等等)的提供。这些事情主要由三类精英借助民间宗教组织的平台,通过民间宗教的议事系统表达出来。在议事系统内部,民主是主要的议事原则,董事会成员根据自己的利益宿求对某个问题发表意见,最终各成员意见综合形成的意见就是董事会的意见。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民间宗教组织内部蕴含着民主自治的因素,但也存在着精英的因素,城镇化农村治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这样的组织内部发掘出民主因素。
(二)民间宗教的文化认同与农村稳定发展
文化认同源于民间宗教文化的诞生。民间宗教文化是以民间宗教的符号系统来维系的,符号系统经过历史上漫长的沉淀,形成特定的神话、仪式、制度等等知识,特定民间宗教知识一旦与特定的物质设备相联系便产生了民间宗教文化。宗教是文化的核心,“正如文化在实质上是宗教,宗教在表现形式上则为文化。”[9]文化一旦产生,则会使存在于其体系内的人类,对特定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等产生倾向性的共识与认可,这便是文化认同[10]。文化同时也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11],与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民间宗教的文化认同影响着农村的稳定。以妈祖信仰为例,妈祖信仰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已经形成了妈祖文化。妈祖文化形成了特定的“祭祀圈”和“信仰圈”[12],二者既是仪式空间,也是社会的空间。在仪式空间内,它表现出宗教的特性;在社会空间内,它表现出文化的内涵。那么,在同一妈祖文化系统内,人们首先认识到的是族群的类同,这一类同可能为农村带来稳定,也可能威胁农村稳定。农村城镇化的实质是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后果除了经济上的突飞猛进外,一个重要的隐性结果是文化的多元化。那么文化多元化对妈祖文化的特定“信仰圈”是否构成了冲击?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同一文化的成员,享有共同的身份和情感纽带,从而把自我与他者截然地分开[13],这必然带来本土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给农村的民主治理带来了困难,也成为了影响农村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城镇化农村的治理当中,如何构建一个宽容的文化空间,成为治理者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民间宗教的文化认同对城镇化农村的发展影响深远。以妈祖信仰为例,妈祖文化圈主要集中在沿海海上贸易发达的地区,妈祖文化的认同对该文化圈内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妈祖文化的认同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包括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其次,妈祖文化的认同有利于吸引外资。在我国沿海城镇化的一些农村,妈祖文化成为了吸引外资的一面旗帜。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吸引台湾投资。改革开放以来,台商对沿海农村的直接投资成为了城镇化农村起飞的重要力量。在妈祖文化圈内的城镇化农村在工业化初期通常都是以妈祖文化作为交流先锋,在同一文化内(包括国内、国外)进行沟通,进而以文化交流带动经济交流,这也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商愿意到落后农村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妈祖文化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意义。在城镇化以后,民间宗教组织,如妈祖董事会成为了一个资金集中的地方,信徒的捐金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这笔收入除了用于民间宗教活动外,通常还用来改善所在地的基础设施。
(三)民间宗教的神话仪式与农村精神文明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城镇化农村治理的又一个中心议题。民间宗教的神话仪式与农村精神文明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因此它是城镇化农村治理过程中所必须加以重视的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民间宗教在城镇化农村中较传统农村更易于传播。因为城镇化过程中或城镇化之后,人们发现物质给自己带来的只是一时的快感,而经历快感之后更多的是陷入毫无目标的空虚之中,于是民间宗教成为了人们寄托情感的主要场所之一。最初对人们产生吸引的是民间宗教的神话系统,它以闲谈、问神、故事、说教等语言形式在人群中传播。这些语言形式往往使神话系统对人的吸引更加深切和真实,从而更能抓住人心。接着通过仪式系统,民间宗教对潜在信徒进行了强化。最后民间宗教以文艺的形式把自身与民俗、戏曲、文学等文化形式融合在一起,获得了文化身份。这样,民间宗教的神话仪式也就与农村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
民间宗教的神话仪式是农村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城镇化农村的治理要在精神文明方面取得成就,很难回避农村民间宗教的神话仪式。当然,如果是纯粹的民间宗教神话仪式,它或许并不具有多大吸引力,因为民间宗教自身往往都带有不确定性,其仪式也多为不同信仰之间所共用,很难说会有什么特色。关键是民间宗教的神话仪式一旦文化化,则其影响就不容忽视,因为文化化后,它所表达的并非纯粹是宗教的东西,恰恰相反,经长期历史积淀与变迁之后,它所表达出来的更多是文化的东西,因为依附在神话仪式系统周边的是民俗、戏曲、文学等等各种文化亚系统。这些系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圈,构成了农村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因此,城镇化农村治理过程当中,建设精神文明的关键就是如何把宗教生活、迷信与健康的文化生活做一个科学的界定,从而为抵制迷信活动,尊重宗教生活,弘扬健康文化生活做准备。
① “妈祖髻”:为纪念妈祖,湄洲妇女把头发梳成船帆状;“妈祖装”:一种纯蓝色上衣,配上半截红,下半截黑裤子的服装。参见林祖良:《妈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9页。
② 湄洲岛渔民每逢妈祖诞辰之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前后几天,不下海捕鱼。
以妈祖信仰为例,妈祖信仰的神话仪式在农村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妈祖信仰产生于北宋,如今,妈祖信仰的神话仪式逐渐文化化,成为了妈祖文化圈内农村文化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文化化了的妈祖信仰的神话仪式可粗略分为民俗、戏曲、文学三个方面。首先是民俗。与妈祖信仰相关的民俗非常丰富,如妈祖巡游(皇会、娘娘会等)、谒祖进香、“妈祖装”、“妈祖髻”①、诞辰禁捕②等等。其次是戏曲。与妈祖信仰相关的戏曲不仅仅包括那些在妈祖活动之日表演的戏曲,更重要的是一些直接以妈祖为对象,表演歌颂妈祖的戏曲。如《天妃降龙全本》、《妈祖出世》、《天妃庙传奇》、《海上女神》等等。戏剧形式则包括京剧、莆田戏、歌仔戏、歌舞剧、甚至童话剧(如福建儿童剧院表演的歌颂妈祖的童话剧[14])。其三是文学。妈祖文学自妈祖信仰之日便已经产生,如与之相关的各种神话、字贴(如林藻的《深慰帖》、《天妃灵应之记》帖、贤良港《重建天后祠记》帖)、图画(如清代《天后显圣画轴》)、史志(如清代《敕封天后志》等)、小说杂记(如南明《天妃显圣录》、明代《天妃娘妈传》、施琅的《师泉井记》)等等文学形式。可以说在妈祖文化圈内,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妈祖文化,特别是在精神生活方面。
三、城镇化农村治理中民间宗教的负功能预防
在城镇化农村的治理当中,必须警惕民间宗教负功能的危害。民间宗教的负功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各有其不同的表现,必须加以全面预防。
(一)警惕民间宗教对农村正式权威的挑战
城镇化农村民主自治的正式权威是村民自治委员会。然而在城镇化农村的治理当中,作为非正式权威的民间宗教势力却对村民自治委员会构成了强大的挑战。这一点在沿海发达的城镇化农村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各类精英,尤其是政治权威型精英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自始至终采取一种圆滑的方式来影响农村政治过程。他们很少直接担任行政村的领导职务,因为他们认为这可能会使自己处于村内的各种矛盾之中,如果解决不好可能影响自己威信。他们更愿意利用自己在农村公共生活中已有的权威(如在妈祖信仰组织中的权威)去影响,或控制政治领导者,进而达到实现自己对公域和私域双重控制的目标。民间宗教组织对村民自治委员会主导的公共领域生活空间的不断侵蚀使它的地位变得相当尴尬,村民们有事不再求助于他们;他们专门从事一些诸如计生、收缴房屋基建费等等一些“得罪”村民的事。在某些城镇化农村中,村民自治委员会面临的不仅仅是威信下降的问题,而是已经涉及到了治理的合法性的最低限度问题。
显然,警惕民间宗教对正式权威的挑战,应当从作为正式权威的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治理机制建设入手,首先要加强完善城镇化农村的民主选举机制。领导集体的素质是村民自治委员会权威树立的核心因素。当前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权威受到民间宗教挑战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它的领导集体没有选好,领导集体没有选好的原因则在于民主选举机制还不完善。城镇化农村的选举有时演变成了低级的金钱选举(候选人向村民买选票)、宗族选举、地痞选举(候选人由地痞威胁获得选票)等等,以致于选出一些“异精英”[8]96来主政。其次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机制。城镇化农村正式权威的受损与农村基层党组织思维的单一化、封闭化、固定化不无关系。城镇化农村的主要特点是多变性,无时无刻不要变化,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固守传统“权大于法”、“官本位”,在生产和村务管理中,采用强迫命令和强制性行政手段的那一套显然不利于组织权威的提升。最后必须建立、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权威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把这么一个关键性的要素让给了民间宗教组织,村民自治委员会权威受损的结果是在所难免的。
(二)警惕民间宗教组织的利益集团化倾向
民间宗教组织的利益集团化倾向是城镇化农村的一个突出特点。戴维·杜鲁门认为利益集团是在一种或几种共同态度基础上,为了建立、维护或提升具有共同态度的行为方式的集团。利益构成了共同态度所导向的目标[15]。民间宗教组织本应是公民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以非营利性为基本特点。但是目前城镇化农村民间宗教组织显然已经有了利益集团化的倾向,民间宗教往往成为了他们谋求利益的工具。城镇化农村的民间宗教组织相对村民而言,都是当地强大的经济体,如妈祖信仰中的东坡村天后宫董事会[6]20。在某些城镇化农村中,民间宗教组织的许多成员本身就是当地最富裕阶层的经济精英,虽然这些成员平时并不参与组织的日常管理,但是他们却主导着组织的关键性决策。这些组织在平常往往不表现出利益集团化的特征,但是一旦涉及村里的重大决策时,其特征就表现的一览无余;他们往往通过民间宗教这个平台,谋求自身在本村利益的最大化。
预防民间宗教组织利益集团化倾向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它排除在城镇化农村的公共决策过程之外。当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那么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是公共决策过程必须由村民自治委员会来主导。也就是说民间宗教组织如果要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必须要在村民自治委员会的主导下进行,而不是村民自治委员会因为民间宗教组织愿意出钱,就在它的主导下来提供公共服务。
(三)警惕民间宗教对村民的精神控制
农村城镇化的一个有害的结果是导致村民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这就为民间宗教控制某些村民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城镇化过后,部分村民较他人相比陷入相对的贫困之中,失去了生活进取心,沉迷民间宗教迷信,丧失了主体性。另一部分人则因为在富裕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在精神世界陷入了空虚之中,为了寻求精神依托,丰富精神生活,他们便有心无心参与民间宗教组织的一些活动。这些人构成民间宗教精神控制的主体。显然,民间宗教对村民的精神控制会给城镇化农村的治理带来极大的危害。首先,精神受到控制的村民易为他人利用,影响农村稳定,不利于农村的和谐。其次,这些人拘泥于日常实用、功利主义的宗教心理,限制他们抽象思维和理性思维的拓展,危害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最后,民间宗教原始的崇拜使人们形成了一种狭隘封闭思维和保守的人格,培养了他们政治上的排他性和盲目的优越感,影响农村民主自治。
克服民间宗教对村民的精神危害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在思想建设方面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进行此类教育时应注意避免假、大、空。因为假、大、空不仅不会强化村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反而会对此类教育充满反感。因此必须把此类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把教育融入到对当前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解决中来。也就是说,理想、道德、文化、纪律教育应当同保护、实现农民的切身利益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弱化他们的小农性。其次在文化建设方面,必须加大农村的科学文化技术教育,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农村的城镇化是一个进行普及科学文化技术知识的良好时机,农民正在通过科学文化技术知识获得实惠,因此如何应用好这个时机,就成为城镇化农村治理中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语
民间宗教的语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们不仅构成了复杂的文化系统,也对城镇化农村的治理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城镇化农村的治理当中,如何与民间宗教进行合理的对话,是我们当前新农村建设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对这种对话的基础、机制、目的、工具进行深入思考,因为这关系到城镇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民生的改善、农村的稳定和基层民主的推进。
参考文献: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结构人类学[M]. 张祖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何敦培. 宗教因子及相关问题辨析[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6):52.
[3] 郑明志. 关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与“新兴宗教”之我见[J]. 文史哲,2006,(1):10-11.
[4] 马西沙. 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民间宗教卷[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
[5] 特伦斯·霍克斯. 结构和符号学[M]. 瞿铁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6.
[6] 翁珠琴. 东坡村:文化权力的困惑与妈祖女信徒的命运[D].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人类学,2007.
[7] 闫 健.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M].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1-52.
[8] 朱武雄. 农村公共管理:主体异化及其矫正[J].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7,(6).
[9] PAUL TILLICHI. Theology of Culture[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42.
[10] 郑晓云. 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
[11]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二卷)[M].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2.
[12] 林美容. 妈祖信仰与汉人社会[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3-7.
[13] 罗迫特·达尔. 论民主[M]. 李柏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8.
[14] 林祖良. 妈祖[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140.
[15] 戴维·杜鲁门. 政治过程[M]. 陈 尧,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