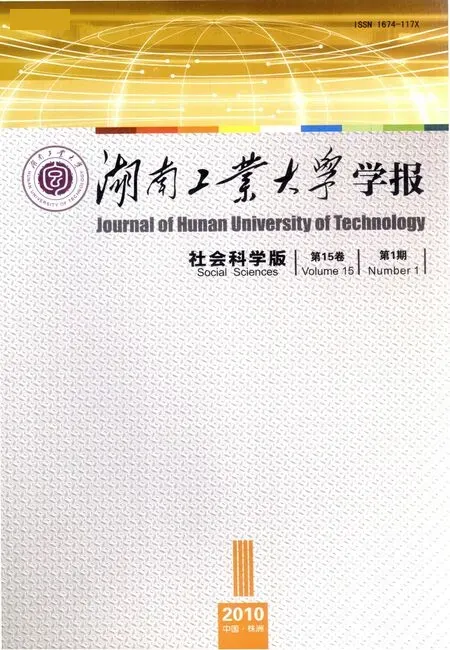知止而后有定
——论“创造性叛逆”的学术定位
张冬梅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株洲412008)
知止而后有定
——论“创造性叛逆”的学术定位
张冬梅①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株洲412008)
既知来处,亦知去处,止行有定,可谓知止。论文从学术背景、学术目标、学术边界三个方面对译介学中的重要命题“创造性叛逆”展开学理透视:在文学社会学的学术渊源、媒介学的谱系传承与当代“文化转向”的历史语境中把握“创造性叛逆”的学术基因以及宽广的社会文化视域,在文学比较与互动、文化比较与互动的学术目标中把握“创造性叛逆”的当行之境,从解释世界、描述现存的认知理性中把握“创造性叛逆”的当止之地。
知止;有定;创造性叛逆;学术定位
《大学》有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世间万物行止各有其时,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方顺理合义。唯以“知止”为始,方能以“得”为终。尽管以现世伦理为关注中心的儒家主要是从人伦的角度来理解“知止”,如《大学》中有“《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但“知止”的启示意义却不可能被固定在有限的人伦视角上。在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的《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苏珊·朗格在她的《哲学新视野》一书中评论说:某些观念有时会以惊人的力量给知识状况带来巨大的冲击。由于这些观念有时能一下子解决许多问题,所以,它们似乎将有希望解决所有基本问题,澄清所有不明了的疑点。每个人都迅速抓住他们,作为进入某种新实证科学的法宝,作为可以用来构建一个综合分析体系的概念轴心。这种“宏大概念”突然流行起来,一时间把几乎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挤到一边……在我们熟悉了这个新概念之后,在它进入我们的理论概念总库之后,我们对这一概念的期待也更加和它的实际应用相适应,它也就不那么盛极一时了。只有少数的狂热者固执那种过时的万能钥匙观点,而不那么迷恋的思想者不久就会定下心来,探讨这个观念真正引发的那些问题。他们试图在可以应用、可以拓展的地方,应用它、拓展它;在不能应用、不能拓展的地方,就停下来。[1]
在学术研究中,不被流行一时的观念裹挟而去,而是定下心来,探讨这个观念真正引发的那些问题,在可以应用,可以拓展的地方,应用它,拓展它;在不能应用,不能拓展的地方,就停下来,这就是“知止”。知当止之地,则志有定向,而后虑有所得。“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源自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一书,经以谢天振教授为代表的比较文学学者引入而开始了其跨越时空的理论旅行。那么,“创造性叛逆”来自何处,意欲何往,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又是什么问题,何处应是“创造性叛逆”的当止之地?本文拟从“学术背景”、“学术目标”、“学术边界”三个方面对“创造性叛逆”展开学理审视。
一 、知来:“创造性叛逆”的学术背景
“理论是有其根源的,理论也是有其‘伟大的传统’的,理论不是三两个人精心策划的骗局”。[2]为了实现对“创造性叛逆”的准确定位,需要采用知识系谱法对其进行刨根问底的寻思,在具体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语境中考察其理路,把握其内在逻辑。
回顾历史的脉络,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一书可谓是“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的原发之地。埃斯卡皮是在论述文学的跨集团、跨阶级或跨民族的传播和消费时提出“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的。他指出,当作者与读者属于同一个社会集团时,文学作品的成功在于表达了该集团正期望着的内容,当作者与读者不属于同一个社会集团时,读者所需要的往往并不是作者原本想表现的东西,这时便出现了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3]在这里,埃斯卡皮用“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概括的是读者阅读、理解的机制,揭示的是文学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基本规律。
如果说埃斯卡皮对于“创造性叛逆”有着首发之功的话,那么使“创造性叛逆”真正成为一个独具研究价值的课题的,当是译介学研究者的功劳。译介学源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梵·第根在其193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论》中系统阐述了法国学派的观点,论述了文学影响和假借的“经过路线”,认为在文学影响的起点(发送者)和终点(接收者)之间由媒介(传递者)沟通,任何一个影响研究都必须沿着“放送者”、“传递者”、“接受者”这条路线追根溯源;从“放送者”出发,研究一部作品、一位作家、一种文体或一种民族文学在外国影响的研究称为‘誉舆学’,从“接受者”出发,探讨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接受了哪些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的研究称为“渊源学”,从“传递者”出发,研究影响是通过什么媒介和手段发生的,称为“媒介学”。[4]早期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即为今天译介学的雏形。谢天振在其1999年出版的《译介学》一书中对译介学做了这样的界定:“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研究。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和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5]这一界定从关注对象和研究视角两个方面指明了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研究之间的学术差异,表明了译介学既脱胎于媒介学同时又超越传统媒介学的特点。
文学社会学把文学看成社会现象,把文学家看成社会性的存在,主要采用社会学研究视角和方法,从具体的文学现象、文学事实出发,探讨文学知识及其知识承担者(文学家)与社会文化脉络之间的交互关系,探讨文学知识在社会文化中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种种社会过程。译介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异质文学翻译互动研究。其学理基础是‘国别文学’与国际文学交流的存在,主要研究译家译作与国别文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也研究译作对输入国文学及其文学史的影响,同时考察国别或国际翻译活动、翻译思潮及其对总体文学的影响。”[4]176文学社会学的学术渊源让“创造性叛逆”从狭义的“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的语言转换过程延伸到了译作的接受与传播过程当中,媒介学的谱系传承赋予了“创造性叛逆”关注作为“媒介者”、“传递者”的翻译对作为“接收者”的输入国文学之影响的学术基因,当下发生在人文社科领域之“文化转向”的历史语境则为“创造性叛逆”带来了广阔的社会文化视域。
心灵并不是白板一块,而是带有种种时代的、社会的、个人的成见和观念。客观、无成见只是一个高尚的但却达不到的梦想。引导和支撑“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是以哲学阐释学、解构主义、权力话语理论等为主要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拒斥那种认为心灵是自然的镜子、客体是中性的材料、而主体则是世界的漠然观察者的隐喻”;[6]324-325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在国际范围内赢得共鸣,并迅速渗透到各个学术领域,以迅猛的姿态向长期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信条、信仰和概念发起挑战的后现代视角主义,“在这种视角主义取向中,没有事实,只有解释;没有客观真理,只有各种个人或群体的建构物”。[6]25
二 、知往:“创造性叛逆”的学术目标
在我国第一篇文本尚存的翻译理论文章《法句经序》中,译论始祖支谦就发出了“名物不同,传实不易”的感叹。肩负“达其志”、“通其欲”、“换易言语使相解”的使命,穿梭在语言边境线上的译者,其根本任务就是要在“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的“五方之民”之间搭起一座沟通与理解的桥梁,可是毕竟“名物不同,传实不易”,诚如法国比较文学家布吕奈尔所言,“翻译者在跨越鸿沟的时候,无形中又在挖掘鸿沟,他既清醒,同时又糊涂,既是在做自己的本分,又在做任务之外的事情。”[7]“创造性叛逆”可谓一语中的,道破了翻译活动与生俱来的内在悖论。
译介学对文学翻译之创造性叛逆的关注,其学术目标不是要在实践理性的层面上指导或规定译者如何去翻译,而是在认知理性的层面上对既成的、已有的翻译事件的阐释,是对译本在生产、流通、接受过程中被遮蔽的、潜藏在表象之下的本真存在方式的揭示。这种阐释和揭示深化了对翻译之社会性与文化性的发掘,让译者本身可能有的偏见、语言本身的限度以及译本背后的力量无所遁形。
在比较文学跨文化的宽镜头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特别鲜明、集中地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受到的阻滞、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5]13译介学对文学翻译之创造性叛逆的关注,其学术目标是要知微见著,将创造性叛逆看作是异质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和交融的表征,以此透视横亘在译入国与源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揭示它们在相互理解和交融、相互误解和排斥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互动规律。
译介学对文学翻译之创造性叛逆的关注,不是要呼应支谦那“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只好徒呼奈何的感叹,而是要通过对文学接受之复杂性的考察,突显接受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揭示文学与文化传递过程中复杂的“媒”与“讹”之“化学反应”,从理论上肯定译者之再创造价值,确认译者在文学史上之地位,彰显翻译文学在推动译语文学和文化革新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和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创造性叛逆’一语是对译者所从事的文学翻译事业的认可,是对译作的文学价值的一种肯定。”[5]17学者们竞相从翻译史上拾取片段,引严复、林纾或庞德等为例,为“创造性叛逆”的文学、文化价值寻求实证依据。于是,“创造性叛逆”以其全新的学术视野为翻译研究走出传统“规范性”研究的桎梏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以其或彰显或隐含的一种消解“规范”的危险为翻译研究埋下了不安的种子。有学者担心,比较文学这种不在乎译作质量高低优劣的超脱态度,是不是在鼓励乱译,是不是对孜孜不倦地追求译文质量的学者和译者之劳动价值的否定呢?[8]那么,学界为何会有此担心,这种担心有道理吗?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所做出的是什么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创造性叛逆”当如何做到“止行有定”?
三 、知止:“创造性叛逆”的学术边界
作为对翻译过程的描述,“创造性叛逆”是研究者们以翻译事实为基础而得出的事实判断,属于描述性研究的范畴。描述性研究面对的是现状,探寻的是一种关乎存在的“实然”的知识,体现的是人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冲力,属于认知理性的范畴。它从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把实际存在的翻译作品置于目标语文化语境中进行多角度的跨学科描写分析,着眼于研究翻译之“事实如何”。从命题本身的性质来看,“创造性叛逆”不是从实践理性的层面上指导译者如何去翻译;而研究者本人的主观愿望也并非鼓励胡译乱译,就是在探讨“创造性叛逆”的译介学专著中,读者也可以时时读到这样的文字,如“传达文化意象问题的提出,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在把译者推到了一个‘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境地。但是,富有才华、事业心的译者不会就此止步的。他们本着对自己钟爱的翻译事业的强烈追求,知难而上,殚精竭虑,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把原作者精心烹调而成的‘佳肴’尽可能完整地奉献给读者,使读者不仅能品尝鱼的美味,也能享受到熊掌的精华。”[5]192-193
那么,“创造性叛逆”为何会给学界留下所谓的“鼓励胡译乱译”的印象?与传统翻译研究相比,译介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将翻译置于一个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正是历史文化语境的还原让我们看到了庞德英译中国古诗的文学史意义,看到了严复汉译社会科学名著的文化史意义。可是将庞德或严复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进而得出其译文中的创造性叛逆具有积极的文学或文化意义,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创造性叛逆都具有这样的积极意义。以一时一地之历史事实为基础得出的价值判断不可不加限定地铺开,重视历史语境的研究者在评价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时不可剥离语境,以偏概全。当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冢幸男说,“对于这种‘创造性叛逆’,原作者应予以尊重。岂但尊重,原作者简直还得致以谢意”时,[9]我们注意到在他的“创造性叛逆”之前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限定词——“这种”,这就是“创造性叛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语境意识。后殖民主义译论家站在历史的高度,揭示了西方前殖民主义国家为了借“文明”之名实现殖民扩张,利用翻译的力量,肆意“操纵”、“篡改”原文,将前殖民地国家“翻译”为“未开化、野蛮、半文明”的国度,在西方读者的心目中虚构了一个“东方”神话,这让我们看到了翻译被异化,沦为政治工具可能产生的后果,看到了译者的责任和翻译规范的须臾不可缺。对这种“创造性叛逆”,料想大冢幸男肯定不会下论断说“原作者应予以尊重,岂但尊重,原作者简直还得致以谢意”。
明确“创造性叛逆”的学术边界,做到“止行有定”,一方面要做到不剥离语境,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对特定创造性叛逆之价值不加限定地铺开,另一方面尚需辨明该价值判断的性质,把握“叛逆”与“忠实”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叛逆”是一种后顾式的历史性研究,也即是说,即便有些“叛逆”真的带来了“创造性”效果,因而可以得到允许或获取谅解,这种“允许”或“谅解”也只是一种事后的“允许”或“谅解”,而绝不是事先被提倡。而且,我们顾及和承认这些“叛逆”,主要还是用作谅解他人,而不是用来纵容自己。假设作为译者的我们出于不得已的意识形态考虑而选择在翻译过程中“背叛”原文,我们所感觉到的是“忠实”原文的义务被一个更紧迫的义务凌驾了,我们会为叛逆性译文所带来的好的结果而感到欣慰,但绝不会为“叛逆”本身感到骄傲或得意。正如《天演论·译例言》中严复所言,“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10]“实非正法”、“学我者病”,可见,对严复而言,“信”仍然是翻译之“应当”。
唯以“知止”为始,方能以“得”为终。文学社会学的学术渊源与媒介学的谱系传承赋予了“创造性叛逆”宽广的社会文化视域以及重事实描述的学术基因。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研究翻译和翻译文学的译介学,其最终的落脚点不在翻译,而在文学和文化。“创造性叛逆”作为译介学中的重要概念,它不是在实践理性的层面上指导或规定译者如何去翻译,而是在认知理性的层面上对既成的、已有的翻译事件的阐释,它体现的是一种“解释世界”而非“改造世界”的哲学,一种描述和解释现存的哲学而非筹划未来的哲学,它没有同时也无法构成对“忠实”命题的解构,无力同时也无意为翻译实践提供指导,不是同时也不应该是胡译乱译的借口。
[1]吉尔兹.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4.
[2]汪民安.我为什么迷恋理论[J].外国文学,1999(5):43-46.
[3]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4]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6]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7]布吕奈尔.什么是比较文学[M].葛雷,张连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16-217.
[8]林璋.译学理论谈[M]//许 钧.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564.
[9]大冢幸男.比较文学原理[M].陈秋峰,杨国华,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102.
[10]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15.
Acme of Perfection HelpsObta in Orientation of Ambition——On the Academic Positioning of"Creative Treason"
ZHANGDongm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8,China)
Attaining the acme of perfection entails knowing both the start and the finish.Thispaper takes"creative treason",an important term in medio-translatology,as its study object,traces its academic origin and background,analyses its academic goal,grasps its academic genes and wide social cultural boundary with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of literary sociology,succession of mesologie and present"cultural turn"and explores its present state while engaging in the interactivities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comparisons,hoping to get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its acme of perfection in cognitive activities of explaining the world and describing the present.
acme of perfection;orientation of ambition;creative rebellion;academic positioning
I046
A
1674-117X(2010)01-0153-04
2009-09-10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在‘是’与‘应该’之间思索:描述性翻译研究反思”(08YBB366)
张冬梅(1974-),女,湖南邵东人,湖南工业大学讲师,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