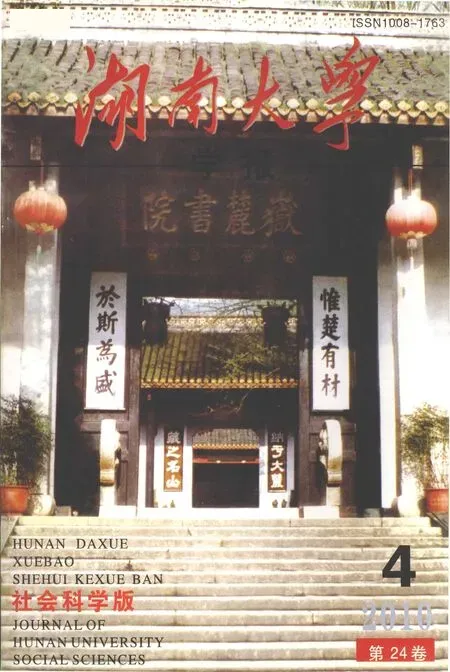20世纪以来文学中乡土想像的文化机制*
禹建湘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20世纪以来文学中乡土想像的文化机制*
禹建湘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乡土想像在20世纪以来成为作家最热衷表现的对象之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性的历史机遇而形成的文化机制造成的。是乡土无意识与现代性历史机缘之下重新激发出来的一种文化心理,是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于传统文化的补偿与救赎心理使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冲突的结果。
乡土想像;文化机制;现代性
Abstract:Native soil imagination is one of the literary trends since the 20th century.It is the cultural mechanism w hich fo rm s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gene betw een the modernity histo ric oppo rtunities.It is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that the native soil unconscious is stimulated themodernity history.It results from the intellectuals that redeem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modernization p rocess.It is the result tha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goes to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native soil imagination;cultural mechanism;modernity
乡土是一个古老的文学母题,20世纪以来,关于乡土的叙事更是成为一条文学主线,作家对乡土进行着形态各异的文学想像。透过乡土母题呈现出来的繁复的想像方式和想像内容,我们可以观察到,20世纪以来的乡土想像,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在现代性的历史机遇中,进行一种现代性的转换,这种转换使乡土成为现代性的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形成了乡土想像的文化机制。
一 集体无意识与历史机缘的碰撞
荣格通过对宗教和神话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原始部落中有着某些相似的原始意象,于是他认为,在人类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原始意象下面,存在着使之生长的共同心理土壤,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一个神话创作层面,这一层面就是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1](P40)荣格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之所以伟大,其根源就在于它能唤起人类共有的感觉和经验,人类通过原始意象的“激活”、“唤起”而回到集体无意识中,并在种种原型的再现中重新审视人类共同的原始经验。所以,在那些有重大影响的传世之作中,人们不难发现,作者常常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去寻找精神的家园。
与荣格持类似观点的是惠尔赖特,他在《论神话创造》中写道:“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的典型心态总的说来是一种介于熟悉与提防之间的张力。前者赋予稳定与信心,一种置根于大地母亲的安全感。洞穴、家庭,也许无意识之中还有子宫,这一切带来的安全感提供了人类生活的概貌。熟悉的处所、人、物体以及事件肯定了基本的归属感”[2](P182)荣格和惠尔赖特的话表明,这种和生命来源密切相关的人类的归属感,正是“还乡”母题的古老原型。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使得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当中,乡土成为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被历史地抒写着。就如有论者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乡村人,乃至每一个中国人心灵深处潜伏着如此独特的恋土和恋家相重合的‘乡土情结’。这是这一东方的古老民族在长期的农耕生存中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种族独特的‘原始意象’(p rimordial)——土地和家乡合一的‘原始意象’的继承和遗传,它成了中国人人格结构中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型。”[3](P35)
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把目光凝聚于乡土,与这一时期里知识分子所处的历史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20世纪以来那些对乡土情有独钟的作家们,大多都曾在乡土生活过,他们离开乡土之前,往往在乡土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正是获得生活经验和形成个性心理的关键时期。早年的乡土感情曾作为显意识浮现在心灵中,而随着时空的推移变化,它会逐渐沉到心灵深处,逐渐与潜意识串在一起,形成了乡土情结。而后,随着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坎坷与磨难,他们在受到客观外界某些人和事的刺激之后,乡土情结就会从心灵深处浮上来而重新成为显意识。这样一来,作家早期经验的具体内容,构成了创作胚胎的因素,对作家的创作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童年记忆成为作家乡土情结的生长基因。鲁迅在人到中年时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4](P132)这些满贮着思乡蛊惑的蔬果,已成为一种寄寓着乡情乡思的象征物,成为贮藏着鲁迅童年温馨记忆的意象了。面对现实的苦难,在人性沉沦中,鲁迅能做的就只能在内心深处保留一方人类童年的净土,这也是鲁迅成为最伟大的“乡土文学”大师的一个重要原因。孙犁在谈《铁木前传》的创作缘起时说,创作契机是由于现实所刺激的童年的回忆,正是这种回忆赋予作品以独特的形式,他说:“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5](P542)
更为主要的是,20世纪以来的乡土想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产物。那些走出惯常生活轨道的现代知识分子,迈步之初就踏上了一条现代“漂泊”之途。“物质”上的富足并不能保证他们“精神”上的安家。他们是生活于都市中的“边缘人”,是乡村羁旅者。强固的乡土文化心理积淀,与陌生的病态的城市生活体验,其间的反差与冲突,使得他们“在”而不属于其置身的都会,他们的灵魂游离都市,漂泊于乡野大地。他们渴望“返乡”却又事实上不曾返乡,于是他们只有在创作的“白日梦”中精神还乡,去营构自己心理上的乡土,去参与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建。
也就是说,西方现代化观念与知识体系全面涌入到中国后,知识分子开始以主体的姿态,自觉思考国家、民族之大业,思考社会人生问题,思考自身以及自身在社会中位置问题,思考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归属感,等等。而这种思考,首先是从乡土开始的,历史的机缘促使他们对乡土进行想像来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鲁迅曾明确指出:“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分子的任务。”[6](P102)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历史地位,有一种思想上超前的自信。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逃离”了乡土之后,“侨寓”于都市生活中,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并且,亲身感受了20世纪第一次最大的中西文化的撞击,经受了一系列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人的觉醒”、“人性的解放”、“促农民觉悟”、“开发”农民“脱去黑暗”等各种先进思想无不冲击着他们,催促他们在重新回过头来看自己幼年时生活过的偏僻乡土时,获得了乡土文学创作的新视角,从而突破从农民文化的内部视角来观察的局限。
在20世纪以来的乡土想像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启蒙语境中对乡土进行文化批判,在革命话语中对乡土进行革命总动员,在民族主义思潮中对乡土进行依恋与寻找,在后现代语境中对乡土充满新的困惑……每个时期的乡土想像,都蕴含着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历史变迁及他们对于乡土的关怀之情。可以说,中国20世纪以来的乡土想像就是集体无意识与历史机缘的碰撞而激发出来的产物。
二 现代知识分子对乡土的补赎
中国现代文学以来的乡土想像包含了知识分子作为“地之子”的“归耕”情怀,以及如赵园所谓的“不耕而食”的“士”对乡土的愧疚以寻求救赎之心理。
赖德菲尔德(R.Redfield)把古代中国称为“复合式的农村社会”,由士大夫与农民组成。[7](P292)复合式的农村社会这一构成,表明了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士大夫本身就来自于乡土。梁漱溟认为中国并不存在阶级对立现象,中国古代“耕读传家”,“半耕半读”是人人熟知的口语,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说:“最平允的一句话,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士与农不隔,士与工商亦岂相隔?士、农、工、商之四民,原为组成此广大社会之不同职业。彼此配合。”[8](P136)金耀基也指出,中国秀异分子(即精英分子)的功能偏向文化性与政治性,而士人与农民这两个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阶层,又是相互流通的,所谓“半耕半读”、“耕读传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当时一种真实的社会现象。[9](P205)这些论述表明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乡土的一员。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乡土的这种互为融合的紧密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知识分子对于乡土的认识和体验,当知识分子脱离乡土来到城市之后,其内心深处常常会有一种潜意识的愧疚感,因为知识分子在摆脱乡间劳作的辛劳之后,在心灵深处有一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自责感。赵园认为,盘桓于城市的知识分子对于乡土可能存在一种隐秘的愧疚:“那种微妙的亏负感,可能要一直追溯到耕、学分离,士以‘学’、以求仕为事的时期。或许在当时,‘不耕而食’、居住城镇以至高踞庙堂,在潜意识中就仿佛遗弃。事实上,士在其自身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在寻求补赎:由发愿解民倒悬、救民水火,到诉诸文学的悯农、伤农。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涤罪意识经三、四十年代的积累,由创作中的相似操作而日益加固,以至成为创作者经常的心理暗示,终于被作为某一类作品中稳固的意义单位的。”[10](P17)不耕而食的知识分子,当他们在城市享用现代性带来的种种便利与满足时,他们对乡土产生了一种愧疚和自责感,于是他们在文学中通过乡土想像来寻求救赎。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知识分子对乡土的负疚感也就越来越强烈,这促使他们返身投向乡土。
李大钊在1919年2月发表《青年与农村》,他说农村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充满幸福,一片光明,空气清洁,所有这些都与城市生活形成对比:罪恶、黑暗、压迫、空气污浊、游手好闲、卑躬屈膝,是“鬼的生活”。杰罗姆B.格里德尔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同情人民的境遇,试图维护他们的利益,希望利用他们的力量,但是人民对于超出其传统眼界的世界毫无兴趣的麻木、无知,使他们受挫,而且反感。所以他说李大钊的遗产留下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视野:“农民和农村世界不仅仅是表示臣服、接受他人赠予解放之处,而且也是解放斗争必须开始之地。”[11](P379)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乡土的想像,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运行机制中展开,即中国的解放首先要从乡土开始,从知识分子走出来的那个乡土开始。
如果说缘于补赎意识,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知识分子通过乡土想像表现了对乡土的关切与怜悯,以及拯救与启蒙的姿态,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政策的巨大变化,这种补赎也随之发生内涵的变化。
在建国初期,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乡土的突出地位,作家对乡土的态度由观照转向学习,其对乡土的情感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刘绍棠说:“在农民身上,尽管存在着小生产者的种种缺点,但是更具有劳动人民的淳朴美德,保持着我们伟大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在我遭遇坎坷的漫长岁月中,家乡的农民不但对我不加白眼,而且尽心尽力地给以爱护和救助;人人在劫难逃的十年,我独逍遥网外,并且写出了作品。乡亲们待我恩重情深,我要一生一世讴歌劳动人民;我在彻底改正五七年问题以后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是像满怀着感恩和孝敬之心的儿女,为自己那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一样,写农村,写农民。”[12](P93)从关照乡土转而向乡土上的农民学习,可以理解为一个更深的补赎行为。
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乡土在与城乡的对比中,其境遇更加困窘,这也激起了作家身处城市而对乡土的怜悯。莫言说:“解放后消灭了阶级,但产生了阶层,阶层的贵贱之分不亚于阶级。由于中国有了这种特殊的背景,就特别强化了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对抗,也使一大批作家,包括知青作家写的作品里呈现了城乡这种强烈的对抗,这种对抗增强农民对城里吃‘商品粮’的人的反感、羡慕、嫉妒、仇视;也同样增强吃‘商品粮’的人对农民落后、愚昧、狭隘的蔑视,这都是城乡差异造成的。很多作品里恰恰是表现这种东西,我想这两个东西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但要是我没有后来这段城里生活的话,如果我站在一个纯粹的农民立场的话,也可能写不出这样的作品。”[13](P161)当下,在三农问题被普遍关注之后,乡土的困顿与危机再次成为焦点,建设新农村被看成是乡土走向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如何补赎乡土再次成为了知识分子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伊瑟尔曾说过,田园诗与世界的关系是隐喻式的,他说:“自从维吉尔以后,田园诗的世界已经被认为指代自身之外的他物,而因为另一世界只能以解释的方式来建立,田园诗只能被隐喻化地阅读。”[14](P64)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乡土,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式微的传统文化的象征,回到乡土,就是寻找失去的文明。
因为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削弱、解构传统文化,从而导致一种文化的落差和消衰,为了重获传统文化,在诸多的乡土想像中,作家采用隐喻式的书写策略,把传统文化投射到现代社会之中来,书写两者的冲突与张力。
如在莫言的《红高粱》里,“这里是性和暴力、生命和死亡的聚合地。红高粱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北方中国农民的生命力的象征。”[15]莫言所说的“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动人,高粱爱情激荡”恰好概括了红高粱的基本特征,它已不仅仅指具体的物象,而是成了种族的象征,人格的象征。莫言的不少作品 ,如《老枪》、《枯河》、《爆炸》、《金发婴儿》、《红高粱》等,大多从文化视角切入,不停留在对乡土生活的一般化、表面化的反映上,而是竭力要写出弥漫于中国北方农村生活中的浓郁的乡土文化氛围和渗入人们心灵深层的文化积淀。
而张炜小说中最富生气的就是那些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这一关系表现于特征十分鲜明的文化冲突,或者说这些特征构成张炜创作的基本模式:农耕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冲突(《九月寓言》);内地文化与沿海文化的冲突(《外省书》);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冲突(《能不忆蜀葵》);个体精神与时代步伐的冲突等方面(《古船》)。这意味着张炜小说贯穿着文化冲突的两元对立,人物及其精神就在这对立冲突中磨砺滋生而成。
南帆指出,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半人半神的身份是文化尴尬的恰当隐喻”。[16]借助朱先生这个形象,寄托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皈依儒家传统的渴望,但这终究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想像性虚构,朱先生形象正表明了这种文化尴尬。南帆指出,一方面,儒家文化的式微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另一方面,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维护传统的信念又在竭力支持儒家文化的复出。的确,进入晚清以后,随着庞大的封建帝国无可避免地败落,儒家文化也逐渐耗尽了自己。狂飙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了另一套阐释历史的理论模式崛起,这是一个不断革命的历史时期,一批与朱先生格格不入的五四知识分子集体登场不久之后,革命话语迅速成为主导,并且以高调的姿态维持了大半个世纪。而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系列业已僵硬的理论预设终于遭到了深刻的质疑,持续不懈的阶级斗争图景逐渐撤出了历史叙事——历史开始寻找另一个时代的文化。革命的激进和摧毁性产生了令人惊骇的副作用之后,传统文化及时出面,劝诫人们退回一个安宁、和谐、“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个时期,尽管没有人公开否定五四知识分子的功绩,并承认它是一个解放的标志,但是,复古几乎同时成为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得到了肯定的评价。革命话语的封条刚刚揭开,禁锢已久的儒家文化立即苏醒了过来,积聚力量,跃跃欲试。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可以视为文学对于儒、释、道的第一波试探性接触,那么《白鹿原》义无反顾地皈依于儒家传统。从三纲五常到仁义道德,朱先生走出白鹿书院,指点历史迷津。这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后,儒家文化最为隆重的文学亮相。显然,儒家文化不仅期待一个复兴的历史机遇,更深刻的意义上,儒家文化正在力图成为后革命时代的历史叙事。在当前,有相当多的人对于数典忘祖的文化倾向深为忧虑,对于他们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叛已是陈年旧事,文化上的不肖子孙才是令人痛心的现状。这时,民族、历史、传统文化以及儒家的仁义道德往往混为一谈,续写汉唐气象成为一个模糊同时又激动人心的号召。但是,这种对儒家文化的皈依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恐怕仍然是一个遥远的传说,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梦幻,正如南帆所说的:“宁静、玄妙的古典文化一去不返;后现代主义的零散、碎片、自由拼贴还是一个理论模型。后革命时代并未修正现代性话语设定的竞争逻辑,儒家文化并未改写竞争失败者的身份。《白鹿原》里的朱先生被现代性话语阻隔于历史之外,无奈地生活在人造神话之中。朱先生不屑于趋炎附势意味的是愤世嫉俗,独善其身;历史不屑于朱先生表明,现在远未到儒家文化东山再起之时。”[16]
毫无疑问,鲁迅作为第一代文化觉醒者已经洞察了传统文化的魅惑本质与吃人历史,然而后来者还是要不断重蹈旧辙,在传统文化的暧昧面纱前裹足不前、无以自拔。从新时期的寻根到90年代张炜(《九月寓言》)、韩少功(《马桥词典》)、贾平凹(《高老庄》)等作家对原乡文化的亲近,都是如此。这样,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如果我们把乡土与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思考,那么90年代小说中的精神还乡主题并没有缓解处于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中人的内在紧张与焦虑感,相反却陷入传统文化的层层重围。[17]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矛盾冲突的历史语境还会持续下去,它会长久地构成乡土想像的一个文化机制。
[1]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型[A].荣格文集:让我们重返精神家园[C].冯川、苏克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2]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90.
[3]徐剑艺.中国人的乡土情结[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
[4]鲁迅.朝花夕拾·小引[A].鲁迅作品精华(第二卷)[C].香港:三联书店,1998.
[5]孙犁.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A].孙犁文论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A].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7]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
[10]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自序[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11][美]杰罗姆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M].单正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12]刘绍棠.乡土与创作[A].乡土文学四十年[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13]莫言.故乡·梦幻·传说·现实[A].小说的气味[C].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14][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疆界[M].陈定家,汪正龙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5]张闳.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特征[J].当代作家评论,1999,(5):58-64.
[16]南帆.文化的尴尬——重读《白鹿原》[J].文艺理论研究,2005,(2):62-69.
[17]金文兵.故乡何谓:论“寻根”之后乡土小说的精神归依[J].江南大学学报,2002,(3):58-62.
Cultural Mechan ism of Native Soil Imagination in L iteratur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YU Jian-x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
I206.6
A
1008—1763(2010)04—0084—05
2010-02-28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乡土文学与现代性想像研究”(0806004A)
禹建湘(1970—),男,湖南双峰人,文学博士,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学批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