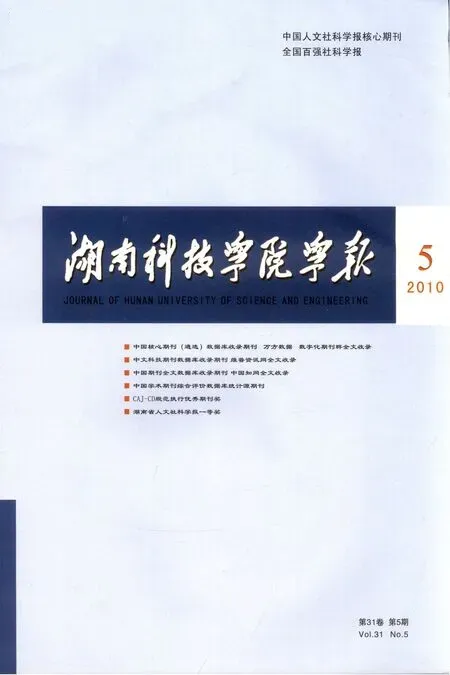“菊花”与“苹果”的角逐
——对约翰·斯坦贝克《菊花》的现实思考
黄 琦(湖南科技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湖南 永州 425100)
“菊花”与“苹果”的角逐
——对约翰·斯坦贝克《菊花》的现实思考
黄 琦
(湖南科技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湖南 永州 425100)
斯坦贝克在《菊花》中,以敏锐的洞察力,不动声色的对话与细节描写,刻画了女主人公伊莉莎的内心自我挣扎与现实世界的矛盾,“菊花”是精神世界的象征,而“苹果”则体现了物质世界的诱惑,“菊花”与“苹果”的角逐是当代社会方方面面存在的危机对人内心真实自我摧残的表现,展现了女性意识从萌芽到发展到毁灭的心理历程。文章试图分析文中暗示的男女性别的抗争、物质与精神的冲突及人与自然的搏斗等各种社会矛盾,以充分揭示女主人公的内心个性意识斗争与自我价值压抑和束缚,以此来呼吁现代社会人们对人的内心冲突的关注,寻求人与真实自我的和谐相处。
约翰·斯坦贝克;菊花;伊莉莎;自我价值
《菊花》是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的优秀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生活在萨林纳斯峡谷的艾伦农场 的女主人公伊莉莎遇见赶车补锅人的短暂经历。被誉为“斯坦贝克艺术上最成功的小说”,“世界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1]但是,《菊花》的主题并不容易把握。有人认为这是宣扬女权主义的作品;有人认为是生态主义的体现;有人从性需求的角度分析女主人公的行为;也有人认为女主人公是个性别界限的僭越者。然而,当我们了解到斯坦贝克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中表述他的创作观念时:“人类一直在通过一个灰暗、荒凉的混乱时代。我们伟大的先驱威廉.福克纳在这里讲话时,称它为普遍恐惧的悲剧;它如此持久,以致不再在精神的问题,惟独自我搏斗的人心似乎值得一写。”
[2]P227不难看出,“自我搏斗的人心”是问题的核心,是所有矛盾与危机的集中体现。男人与女人的性别抗争、物质与精神的冲突、人与自然的搏斗无不是使人内心世界矛盾的直接导向,是种植菊花——精神世界的象征,还是种植苹果——物质世界的诱惑,这种选择在重重矛盾包围之下已经不是女主人公伊莉莎所能随心所欲想种就能种的,这种内心痛苦的挣扎用平实、冷静的语言描写比用痛恨和尖利的笔调来揭示还来得深刻和猛烈。这种深刻与猛烈不仅对当时的社会,而且对当今的社会都带来沉痛的思考。
一 男女性别意识的抗争
作品描写的是美国30年代的社会,在那个特定的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里,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男性世界的排斥和男权势力的压制使女主人公身心都倍感压抑和束缚;她渴求真爱,试图追求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曾以不同的方式反抗过男性世界对她的排斥和男权势力对她的压制;但她的追求和反抗都遭到了失败,最后她意识到了这种挫败并做出了相应的反应。故事中不断涌现性别意识斗争的痕迹及其与现实世界的矛盾。
首先男主人公亨利·艾伦牧场的主人是男性世界的代表,不露声色的维护着男权势力。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大萧条,工业时代飞速发展。这种社会现实决定了男人把精力放在实际的经济利益上。妻子只是排在经济利益之后的一种必需品——能够收拾房子,给他们生孩子,供他们发泄欲望的——物品。波伏娃认为“贤妻”是男人最珍贵的财产,他为她骄傲,“就像为他的房子、土地和羊群感到骄傲一样”。[3]P205当伊莉莎在花园里正忙活着的时候,他在和两个穿工作服的“男人”在谈话,“抽着烟”“端详着那台机器”,无视伊莉莎的存在,心中只想到男人的利益,当伊莉莎为菊花有十寸那么大而高兴的时候,她的丈夫却希望她能种出像菊花一样大的苹果,与亨利一起的男人“每个人的一只脚正放在小福特森牌拖拉机上”预示了男人的共同目标就是追求实际的经济利益。而小说中的另一男性——补锅匠对菊花的虚假热情,骗取信任到牟利,仍是为了赚钱而为的行径。这一切并没有脱离整个社会的男人意识形态——追逐经济利益,男人们就是在利益的追逐中凸显男人的地位和权势。
而《菊花》中的女主人公伊莉莎则是女性世界的代表,也在为女性的权益默默的抗争。首先伊莉莎善于操持家务,是一位称职的家庭主妇,“洁白的农舍”、“干净的泥垫子”显示了女性的尽职尽责,男人无可挑剔。其次,伊莉莎很有种植菊花的天分,象征了她作为女性的才能和自我价值,“表现了女主人公对自我身份和自我价值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种有菊花的花园是伊莉莎唯一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但在现有的条件下,无力涉足于男人的领域,她把精神寄托在种植菊花上,把这“男性社会里一处狭小的容身之地”也经营的有声有色。再次,伊莉莎是一个感情丰富、精力充沛的女性,她不满足于简单、单调而又沉闷的家务劳动,向往外面更宽广的天地,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当丈夫提及她要是到果园干活去种出像菊花一样大的苹果的时候,她的“两眼亮了起来”,并很自信的说“我就是干什么成什么”。当伊莉莎对补锅匠自由的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遭到反对时,她倔强的反驳“你咋知道这不合适呢?你咋能说不合适呢?”伊莉莎的反问表现了她对当时女性被排斥在男性社会之外、社会地位低下的这一社会现实的愤慨之情,这种女性的意识在压抑与束缚中一有机会都会表现出来。伊莉莎男性化的相貌、衣着和言行举止,都显示了“女主人公内心追求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和独立的社会地位的渴望”。但是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独立的自我受到压抑,她们的才能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甚至被排斥在男性世界之外。
可见,男人的主宰地位与女人的附属地位,男人的实用主义与女人的理想主义,男权社会对女性价值的忽视及女性自我的压抑与束缚种种对立与冲突,在工业飞速发展的时代里表现出的都是男女性别意识的抗争。
二 物质与精神的冲突
20世纪以后,西方社会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创造了过去人们难以想像的巨大物质财富。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社会成员的物质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人们却并没有感到预想的幸福。相反,却发生了普遍的深刻的精神危机。人们越来越依靠“物”,成为物质的从属品,精神世界日益萎缩,精神追求日益丧失。
由于男女两性在社会接触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在对待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理智与激情等问题上,男人与女人从整体上构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作为女性的代表,伊莉莎与小说中的两个男性有着内在而深刻的对立和矛盾。与丈夫亨利对物质利益的孜孜以求,磨刀人兼补锅匠更甚的物欲追求相比,伊莉莎则保留着更多属于人的生命感性乃至精神上的追求,这些都与两个男人构成鲜明对比和深刻冲突。
伊莉莎对种植菊花有着独特的天赋,暗示了纯净心灵最原始的精神的追求。菊花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它实质上就是女主人公美、梦想、才能和自我价值的象征,种植菊花的花园就是女主人公精神家园的寄托。然而,种有菊花的花园为伊莉莎提供了一处展示自我价值的空间,但种植菊花也不能完全满足她的精神追求。“就连她拿剪子干活的动作也很利索,并充满力量感。对她来说,这些菊花茎枝显得太小,剪起来太容易了”,这些句子无不透露着伊莉莎身上对自由和浪漫的潜在的执着追求。但是,这种精神的追求又被丈夫物质利益的诱惑而掩盖,而这种物质利益的诱惑也使得亨利对伊莉莎对女性美的追求视而不见。全文对伊莉莎相貌的描述印象就是“壮”。如同当时社会中许许多多男人一样,精于赚钱的丈夫,不关心妻子的内心需求,不会发自内心的赞美妻子,更不会了解妻子对爱的精神家园的渴望。因此,压抑已久的伊莉莎超乎寻常地侍弄菊花,不正常地寄予自己的情感。
而另一个男人补锅匠是个浪漫体贴的人,是伊莉莎情感需求的象征。他对菊花的赞美,在伊莉莎眼里就是对她女性身份的赞美。这使她兴奋不已,更让她看到了光明。而事后证明,丈夫对她“强壮”的评价和补锅匠丢弃的菊花,表明男人根本没有把女人当作一个“女人”来欣赏,利欲熏心的男人根本没有读懂她的精神世界。她刚刚建立起来的女性自信和生活中的光明完全分崩离析了,她仍然逃脱不了一个家庭妇女的命运。当她问起拳击比赛,又说“我不想去,我真的不想去”内心的孤寂和压抑之情溢于言表,意味着伊莉莎在物质与精神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她的情感、希望、理想和追求,都终将只能在“菊花”和“苹果”的抉择中徘徊。
三 人与自然的搏斗
年轻时代的约翰·斯坦贝克亲眼目睹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迅速发展的机械化农业和生产制造业等所取得的人类进步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和蹂躏,这些都影响着这位极富洞察力的作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约翰·斯坦贝克在短篇小说《菊花》(1937年)中以伊莉莎对菊花的情结,以及男主人公亨利和赶车补锅人对菊花的歧视和摧残,延伸到男性对大自然和女性的无情压迫和摧残,体现了这位作家对自然和女性命运同等关注的伟大情怀。可以说,除了女性及其他众多话题之外,人与自然的搏斗也应该是作者关注的重要主题。
故事一开始,作者就用了一段景物和气候描写来说明主人公生活环境之封闭、沉闷与压抑:“灰色的浓雾紧紧地包围住萨利纳斯山谷,使之与世界其它地方隔绝开来。雾就像严实的盖子罩在山脉四周,巨大的山谷俨然一个密封的罐子。”这些自然景物的描写象征性地暗示了当时环境对人性禁锢的社会因素。“灰色的浓雾紧紧地包围住萨利纳斯山谷,使之与世界其它地方隔绝开来。”同时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山谷的人们的思想也被隔绝开了。“冬季是一个安静和等待的季节”,冬季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的季节,寓示一个希望的终结和另一个希望的孕育,安静与等待是一种平和的心境在蓄势待发;“空气是寒冷又温柔的”隐含的是一个严峻而又缓和的氛围,为故事后面人与自然的矛盾发展拉开了序幕。
“自然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中被视为没有发言权的他者和被征服和统治的对象,它被迫成为人类开发的‘自然资源’,用以服务于人的需要和目的。”[4]P58所以,在男权文化和经济中,自然对男性来说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服务于他们的某种目的的资源和商品。“一望无际的辽阔土地上,犁过之处,黑黑的像金属般闪闪发光”,在男人眼里,这里发光的哪里是“土”,简直就是闪闪发光的“金子”;冬季的牧场没有什么活可干了,男人们又商量着他们的买卖,种菊花还没有种水果来得实惠,似乎要用一切手段掘干这片土地带来的所有利润。而自然所回报的是“灰蒙蒙的浓雾”,这正是机械化农业对生态所造成的恶果。土地与男人之间在搏斗。
那么,伊莉莎,一位与自然命运息息相关的女性,在地位和遭遇上与自然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处于被压迫和被统治的地位。35岁的伊莉莎生活在一个“外界隔离”的山谷之中,过着封闭而压抑的生活。只有同大自然脾性相通,伊莉莎才可能对菊性有如此细致入微的了解。当伊丽莎告诉赶车补锅人如何打芽时,伊莉莎与菊的认同性更是得以充分体现。“这只能凭感觉去干。你要把芽打掉,力量要用在指尖上,手指能发挥他们的最大作用。他们能凭感觉去把一个个的芽掐掉,从来不会有错。和植物在一起,你明白吗?我是说手指和植物在一起,你的胳膊能感觉到的。胳膊有感觉,从来不会出错……”[5]当伊莉莎告诉他这种感觉时,那男人只是把目光移开,说:“或许我懂……”[5]可见,男人永远无法达到像女人那样与自然的沟通和融合。这是由女性在生理、心理方面更接近自然的特性决定的,只有女性才能做到与自然息息相通,这也是男人难以想象和理解的,一种男性所没有的且在生理和精神上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本性。
四 现实的思考
《菊花》的情节并不复杂,通篇大量是作者很冷静的、貌似平常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但正如作者所说,读者“不经意地读完故事后会体会到某种很深刻的东西,但都说不出是什么东西,怎样深刻。”[6]P414的确,从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我们可以窥探到男人与女人、物质与精神及人与自然的各个层面的矛盾与冲突,怎么能说得出到底是什么在影响着人们的感受,但是所有层面的矛盾都可以在人的内心世界得到反映,过去如此,现在也是。
斯坦贝克在《菊花》中,以敏锐的洞察力,不动声色的对话与细节描写,刻画了女主人公伊莉莎的内心自我的挣扎与现实世界的矛盾,“菊花”是精神世界的象征,而“苹果”则体现了物质世界的诱惑,“菊花”与“苹果”的角逐是当代社会方方面面存在的危机对人内心真实自我摧残的表现,展现了女性意识从萌芽到发展到毁灭的心路历程。
这种心里路程,不仅是作为女性更是作为人在社会中的生存轨迹。在当代社会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进程中,人类的精神生活日趋萎缩。而在现代这个物质相当丰富的时代,人们普遍忙于对物质利益的追逐,而忽视真实自我的把握;对内心的、感情的生活日渐麻木,心灵世界趋于荒芜、简陋;一切都在朝着务实功利、简单直接的方向发展;更为人担忧的是对美好的精神生活的怠慢甚至波及到爱情领域,对两性间心灵交融的爱情追求已经遥不可及。在这样的社会,对待性别,对待世界、对待自我乃至爱情,斯坦贝克告诉了我们一个词“真实”。无论怎样的社会,怎样的矛盾,是选择“菊花”还是“苹果”,唯有真实的自我是不能逃避的,是必须要面对的,虽然“寒冷”但是“温柔”,虽然是“冬季”但是可以“安静的等待”。
[1]姜淑琴,严启刚.简析《菊花》的叙事结构[J].外国文学研究,2005,(2).
[2]赵金昭,吴少珉.外国文学作品选[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8).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上卷)[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金莉.生态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2004,(5).
[5]约翰·斯坦贝克.菊花[A].张澍智,译.斯坦贝克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弗洛伊德·西格蒙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7]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
[8]胡开杰.菊花——多元象征意义的探讨[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4).
I106
A
1673-2219(2010)05-0049-03
2010-12-23
黄琦(1976-),女,湖南永州人,湖南科技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翻译。
(责任编校:周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