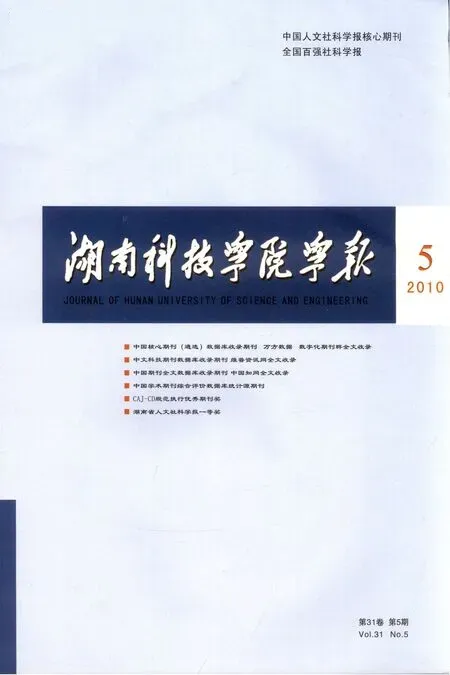巴洛克式宣叙:《蛮荒之海》的“蒙太奇”艺术效果
毕跃忠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南阳 473061)
巴洛克式宣叙:《蛮荒之海》的“蒙太奇”艺术效果
毕跃忠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南阳 473061)
美国后现代主义先锋诗人约翰·阿什贝利的长诗《蛮荒之海》以巴洛克式宣叙为创作基调,由此营造出的蒙太奇艺术效果辐射于诗歌的称谓、用典、意象诸方面。巴洛克式宣叙与蒙太奇式手法互为因果,统领全诗,投射出一幅光怪陆离的后现代主义宏大图景。
巴洛克式宣叙;蒙太奇;《蛮荒之海》;阿什贝利
“巴洛克”(baroque)是一种风格术语,指自 17世纪初直至18世纪上半叶流行于欧洲的主要艺术风格。该词来源于葡萄牙语 barroco,意思是一种不规则的珍珠。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用这个 词来批评那些不按古典规范制作的艺术作品。巴洛克风格虽然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确立起来的错觉主义再现传统,但却抛弃了单纯、和谐、稳重的古典风范,追求一种繁复夸饰、富丽堂皇、气势宏大、富于动感的艺术境界。在20世纪初叶轰轰烈烈的现代主义思潮中,“巴洛克”由艺术领域移植到文学批评领域,用以指称文学文本的兼容性与复杂性,一度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学批评视角。格里梅尔斯是巴洛克文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和倡导者之一。就诗歌的美学实现方法,格里梅尔斯提出了“宣叙”理论。按照格里梅尔斯的观点,诗歌是创造意义的一种方法。其中重要的方法之一,便是通过相距较远的语词的铺陈,或宣叙来创造意义。由于语词“相距较远”,缺乏常规意义上的关联,这种宣叙便表现为一种“巴洛克宣叙”。“巴洛克宣叙”把诸多异质同构的语言成分,奢华地纳入统一的诗歌结构体系中。在这样的诗体结构中,语词处于一种既相互对立、冲突又相互辉映、关联的复杂关系之中,因而使得被吸纳进来的语词的本义,产生扭曲、变异,或使歧义产生,或使本义消隐,或使派生义彰显,这样与语词本义相互辉映,产生类似于电影中的蒙太奇艺术效果。
在约翰·阿什贝利的《蛮荒之海》一诗中,语言成分的“巴洛克宣叙”不仅局限于语言本身,更突出地表现在语言的外延之中。“巴洛克宣叙”渗透于全诗肌理之中,营造出交相辉映、亦真亦幻的蒙太奇艺术效果。
一 巴洛克宣叙之称谓
“称谓”来源于希腊语中“戏剧角色”一词的译名。剧中主角为第一人称,次角为第二人称,其余角色为第三人称,后来第一、二、三人称分别用来指说话人自己、受话者和第三者。在诗歌中,人物指称是言语活动中的参与者或相关角色的符号指称,是诗歌的主体,是活动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在现代诗歌中,第一人称叙述者一般以回忆、幻想、沉思、独白等手段,展现人的内心世界与超验化的内容。第三人称叙述者常常不以诗中人物出现,而是将“目光和声音附着于其他人物之上,跟随他(她)一起沉思遐想,同声同步传达其声音”[1](P117)。第三人称不是言语角色,具有“依赖性”和“限制性”,在语义解释上依赖于一个先行词语,这个先行词语可以出现在对话中,体现在句法、语篇上,也可以存在于交际双方(含阅读)的大脑中。由于这种先行词语,第三人称就获得了确定的指代。这种同指关系,是我们理解诗歌内在联系的重要手段。
《蛮荒之海》中人物指称纷繁复杂,虽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三类,但阿什贝利强调诗歌的“非个性化”,主张诗人应该在作品之外,让叙事者进入来冷静地讲述诗歌。人称多变,因此叙事角度也具有多变性。同时,《蛮荒之海》中频繁使用超常规的语言模式和表现手法,如诗人突破常规的标点限制,把会话中的引号去掉,从而抹去了叙述和对白之间的空隙,这样虽然干扰了人称代词的身份确认,但由于两者之间的转化自然贴切,能有机融为一体,便极大地扩展了诗歌的意义有效空间。
《蛮荒之海》中的指称十分庞杂,各种人物指称纵横交错。这种巴洛克的表现手法,表面上显得很杂乱,实则相辅相成,使主观与客观、行动与思想、对话与独白得以兼容,充分体现了诗作广阔的涵盖量,蕴含了浓烈的象征意义。
《蛮荒之海》主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手法,诗中共119个第一人称代词,其中单数指称共有103个。诗人利用“主观”的第一人称视角来展示被现代社会异化的主体个人的丰富情感。[2](P237)诗中“我”的使用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作为对话中的发话者,如第一章的带天宫图的马丹梭梭屈里士,第二章小酒吧中闲聊的小市民,第三章的泰晤士河三女。二是以叙述者或其他身份频频变换出现的。如第三章中坐在湖畔哭泣的“我”指叙述者,而见证战争创伤的“我”则是帖瑞西士。在第五章中,“我”转指叙述者、信徒或渔王。但无论是作为发话者或叙述者的第一人称,都主要是从“我”的角度出发来体验世界,来描绘客观现实的。
作品中第二人称代词可分为对话中的特指和叙述中的泛指。诗中对话中的特指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如“风信子姑娘”的情人和冷漠的富男。但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第二人称的语义又可“人称泛化”,如在《蛮荒之海》第76行泛指读者,第321行泛指人类。
《蛮荒之海》中作者以冷峻的第三人称全知手法客观而深刻地揭露了现代人失去信仰、幻灭堕落的畸形心态。[3](P574)诗中的作为被叙述对象的第三人称,在“我”和“我们”退隐诗歌之外后,常常成为话语的主体。“他们”以全知的视角,超越时空。诗中被叙述对象的第三人称,有时指代所引神话或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有时又指代形形色色的现代人物。[3](P438)如诗中的“她”,有不容屈辱的翡绿眉拉,引诱骑士的女人,神经质的贵妇,吸食鸦片的丽儿等等。神话或作品原型的“他”有费迪南王子、腓尼基人、复活的耶稣等等。同时,通过丽儿的丈夫阿尔伯特、有自闭症之嫌的独眼商人、饥渴如兽的小职员,彰显“他们”这些现代人的空虚和迷幻心态。
《蛮荒之海》中三种人称时有切换,多点描述、多重视角交互使用,不同的人物指代不断传达出不同人物的内心境况,克服了叙事角度固定于同一人称所造成的视点相对单一的缺陷,各种意象指称虽复杂多变,却有机地统一于同一个内在主题之下。在诗歌中展现出多姿多彩的人物侧面,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内涵。《蛮荒之海》还把男女两性有机地融入一个复杂的统一体“我”中:“我”超越时空、性别和文化,亦古亦今,亦男亦女,“我”是哲理的我,非人格的我,“我”是人类的一个缩影,这样,实现了人物事件和意象指称的高度统一,也实现了主客体的完美并构。[4](P339)
二 巴洛克宣叙之用典
《蛮荒之海》共用典84次,使用了6种语言,涉及到56部前人著作。用典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小说、诗歌、戏剧、自传、神话故事、歌曲、民谣等等。因为《蛮荒之海》用典太多,有些评论家把《蛮荒之海》称为“拙劣的模仿”或“拼凑制作”。阿什贝利也因此被指责为“含混晦涩”。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蛮荒之海》中的用典呢?
《蛮荒之海》围绕着“死海”这一中心意象,诗中的几十次用典至少涉及八个典故。一是渔王的传说。二是《旧约》中有关多神崇拜的描写。三是《城堡》中“这拥挤的城,充满了迷梦的城”,“并无实体的城”。四是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五是剧作家魏布斯特《白魔鬼》中埋着死尸的花园。六是底比斯的米罗斯蒂(典出大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七是被污染的莱茵河(出自瓦格纳根据德国民间史诗创作的著名大型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八是“空的教堂”(圣杯的传说)。阿什贝利正是借助于如此大量的典故,曲折隐晦地表达出作品的主旨:“蛮荒之海”中的人们尽管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但精神领域却是一片荒芜。
《蛮荒之海》中这些典故的“巴洛克宣叙”,并不是简单的罗列铺陈。阿什贝利认为,运用典故如果只停留在原来的意义,没有达到造象的水平,那就还是典故;如果典故能与现代生活相叠加、交融,产生出一个新的意象,那就是典象了。《蛮荒之海》中的用典,是把典故植入新的语境中,不脱原意,而又超乎原意,从而使之饱含深意。
《蛮荒之海》中典故通过“巴洛克宣叙”而成为“典象”,表现为三种方式。一是同一典故具有多重的象征意蕴。如圣杯既与水和鱼相连,能带来使蛮荒之海复苏的生命活水;有取之不尽的银鱼(永不枯竭的生命力的符记),同时又是女性的象征(持剑的骑士寻找圣杯)。诗人着眼于圣杯的精神性内涵,着眼于能够促使文明恢复生机的神奇力量。[3](P339)再如《蛮荒之海》中先后五次提到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丧歌,以此多角度来喻示死亡这一主题。诗中写现代人在火中的煎熬、水中的死亡、掩埋在花园里的尸体等等,暗示死后的再生:当人们以爱、宽恕、和解代替了仇恨,将从肉体到精神都获得新生。
二是把同一典故分割开来,变换形式,多次使用。诗人在第二章提到奥维德《变形记》中翡绿眉拉的故事。翡绿眉拉被自己的姐夫、国王铁卢欧斯挖去双眼,但她始终不屈不挠,在设法告知她姐姐后,姊妹两人对铁卢欧斯进行报复,终至被杀。死后的翡绿眉拉变成了夜莺,她姐姐变成了燕子。紧接着第三章写歌女博尔特放歌的情景后,诗中又响起鸟鸣声,由此构成强烈的对比。在诗的结尾处诗人写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像燕子——啊,燕子,燕子”,暗示只有当人们像翡绿眉拉姊妹那样坚强不屈,美好的春天和生命才会回到人间。同一典故多次变换穿插运用,使诗前呼后应,浑然一体。
三是运用拼贴、镶嵌的手法。诗人把素材或典故分割成许多片断,然后通过重新拼贴、组合和镶嵌,构成了一个新的整体意象。如诗歌结尾处,诗人采用了《从祭仪到神话》、《神曲》、《新约》、《旧约》、《伦敦桥塌了》、《法国民歌》、《圣维纳思的夜守》、《不幸的人》、《西班牙的悲剧》等作品中八个深含喻意的片断,造成一种矛盾复杂的意境,以此表达:尽管迷惘失望,不肯放弃在惨淡中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撑,不肯放弃人生的希望,期待着“出人意外的平安”[5](P261)。《蛮荒之海》通过这种拼贴、组合和镶嵌的手法,做到了神话与现实交织,远古与现代相通,天堂同地狱结合,从而极大地扩充了作品的思想容量,也使全诗更显得博大深沉、意蕴丰富。
阿什贝利旁征博引地用典,尽管很可能带来艰深与晦涩,形成巴洛克风格,然而典故的运用不是堆积罗列,更不是孤立静止,而是根据不同的语境巧妙组合、镶嵌,行文自然流畅,毫无斧痕之迹,使得全诗气势磅礴,极富立体感。正是有了如此多的用典,使《蛮荒之海》更具有横亘东西、超越历史的象征意义。
三 巴洛克宣叙之意象
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作者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则是意的有形载体。作者对外界事物心有所感,便将之寄托于一个所选定的具体形象,使之融入作者自身的某种情感体验。意象是构成某一意境的各个事物的集合,而这些事物往往带有作者的主观印象,这些意象组合起来,就构成了意境。意象是具体事物的投射,意境是由具体事物构成的整体环境和情感的结合。情寄托于景中,景中有情,情景交融。
《蛮荒之海》通过意象表达的最大特点就是意象的巴洛克宣叙,在具体运用过程中表现为使用拼贴法。西方一些评论家称之为拼贴法,是指通过对文本进行分解、综合、再创造来进行创作的一种方法。[6](P297)阿什贝利在《蛮荒之海》中广泛运用拼贴法,使每个独立的象征物构成象征群,各个象征物由此产生叠加性和跳跃性,从而增强了象征的突兀性与立体性,加深了寓意的复合性与形象性。
《蛮荒之海》中的意象繁多庞杂。从诗的题目到五个部分的标题,“蛮荒之海”、“死者葬仪”、“对弈”、“火诫”、“水中之死”、“雷霆的话”,都是一个个独立的意象。诗中的意象包罗万象,水、火、雷电、死者的祭奠、生者的游戏……意象遍及春夏秋冬、花草鸟兽、土木水火、风雨雷电、江河湖海、神话与现实等等,将生死轮回、天上人间、万物兴衰全都囊括其中了。《蛮荒之海》中的众多意象可以分为神话传说、诗文经典与客观现实三大类。那么,《蛮荒之海》中众多的意象是怎样实现拼贴的呢?
不少人认为《蛮荒之海》中众多的意象拼贴缺乏内在联系,显得不连贯。全诗原本一千多行,初稿写成后阿什贝利大刀阔斧地删掉了一大半,后来径直送去发表,也就是现在的版本。这样“全诗更为精悍有力,意象也更具巴洛克特质”[7](P331)。《蛮荒之海》中许许多多的意象,貌似彼此毫无关联的拼贴,实际上却表现出强烈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围绕中心、贯穿主线和前后照应三种方式。第一,全诗的各种意象形成一个有着一定内在联系的意象网络,“蛮荒之海”这个中心意象是意象网络的核心。诗中各种意象无不是“蛮荒之海”的构成要素:如诗行中反复出现的破败、混乱、衰枯、倾塌的“蛮荒之海”意象群:残忍的四月、死去的土地、乱石的垃圾堆、岩石堆成的干涸的群山、背阴处的荒芜的平原,等等。还有曾经辉煌过的都市“蛮荒之海”意象群:缥缈的城、耶路撒冷雅典亚历山大、垮塌的伦敦桥、棕色的雾、尘土满身的树等等。第二,拼贴的意象有主线贯穿,这条主线就是生死之间的不断轮回。以寻找“圣杯”的勇士和在生死之间不断轮回的繁殖之神作为连接点,所呈现的意象构成了一个死、生与繁殖的循环。如死者葬仪是死的意象,对弈是醉生梦死的意象,火诫意味着基督的救赎,水中之死意味着幻灭,雷霆的话象征着再生,这样生生死死不断轮回。第三,为了增强意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蛮荒之海》采用了意象重复的手段,一些主要的意象在全诗中循环重复。如腓尼基水手、独眼商人、菲迪南王子、渔王、铁瑞西斯、死气沉沉的巴黎等等。这一系列重复的意象构成了诗歌在内容层面上的关联,重复意象构成的照应、呼应,加强了意象的内在联系。
[1]Marina,Rimmon.John Ashbery and the Postmodernist Creation of Tradition[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2]Ashbery,John.The Complete Critical Prose and Letters[M]. Michigan:The Michigan Macmillan Press,1986.
[3]Ashbery,John.The Collected Letter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4]Neptune,Henry A.A Reference Companion to John Ashbery[M].London:Thames River Press,1993.
[5]Howells,Jeremy.“Avant-garde and Vanguar: Postmodernism and Surrealism in the Poetry of John Ashbery”[A].Pinnacle Series:John Ashbery[C].New York:Macmillan Distribution Ltd,1997.
[6]约翰·阿什贝利.约翰·阿什贝利诗选[M].肖泽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7]Irene,Ralph.Where Have the Old Words Got Me?: Explication of John Ashberye’s Collected Poems[M].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3.
(责任编校:王晚霞)
Baroque Recitative: the “Montage” Artistic Effect of Sea of Savagery
BI Yue-zhong
(Nanyang Medical College, Nanyang Henan 473061,China)
A poem by John Ashbery, an American precursor of postmodernist poetry,Sea of Savageryadopts baroque recitative as its dominant tone, with montage artistic effect radiating into the appellations, allusions and imagery of the poem. Baroque recitative and montage technique account for each other to predominate the entire poem, projecting a bizarre vista of postmodernism.
Baroque recitative;Montage;Sea of Savagery;Ashbery
I106.2
A
1673-2219(2010)05-0052-03
2010-03-13
毕跃忠(1971-),男,河南新野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