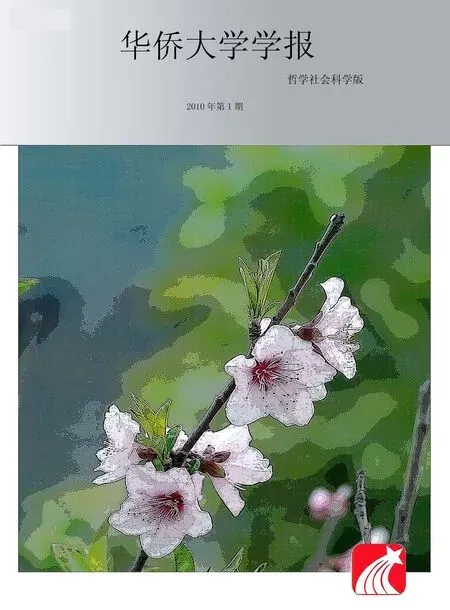透澈澄净的情思表现
——六朝诗歌抒情的一个鲜明特征
○黄 河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一般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这一命题同时意味着:从魏晋开始,中国文学形成了一些一直贯穿其整个发展历程的鲜明独特的特征。那么,从魏晋开始,中国文学究竟形成了哪些既鲜明独特,又影响深远的文学特征呢?这里凭个人体会,谈谈我对此时期文学特点的一点认识。
一
对魏晋六朝文学特征的认识,从根本上说,我以为可归结到确立了抒情性这一点上。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魏晋六朝文学的抒情对整个后来中国文学发展产生的影响,却至为深远。
如果我们可以把钟嵘《诗品序》对诗歌基本特点的说明:“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看作他对魏晋以来诗歌的一个总结的话,他确实是抓住了要害。这正是魏晋以来文学与实用的功利决裂的关键,即在当时,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已从两汉的强调美刺讽谏转向了主张“感荡心灵”的“骋情”。与钟嵘同时的文艺思想家刘勰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论及魏晋作家时,《文心雕龙·才略》指出:“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就是说作为魏晋作家的嵇康、阮籍,已经完全本着自己的性情来创作了,根本不考虑实用的功利。而在钟嵘、刘勰之前论文的陆机,虽然还未完全摆脱“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的功利束缚,但他在论诗时,也明确说明:“诗缘情而绮靡”。魏晋六朝成就最高的三位文艺思想家就诗歌创作所作的上述说明,应该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文学的普遍认识。
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六朝时期的文艺思想家是看到了现实生活作为文学源泉的作用了的。例如钟嵘在《诗品序》中就指出:诸如“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种种,正是促成作家情思迸发的条件。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在论建安文学时也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虽然都谈到生活决定情感,但六朝主流文论似乎更重视的是作家主观的情思表现而不强调诗歌描写和反映现实生活。陆机《文赋》说作家“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是如此。钟嵘、刘勰亦不例外。《文心雕龙》创作论主要就是围绕作家如何表现情感立论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由此角度看,作家在创作中其实不必要也无须对生活作细致观察描写。现实生活的种种现象外貌在创作中它只能作为诗人情感载体而存在。就在这里,六朝文论对物色启发与表现作家情思的特点作了颇有见地颇为生动的阐述。《文心雕龙·物色》论作家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说:“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即可见此。本篇之“赞”则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出心与物之相融,即情感与形象统一的过程:“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返,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这些说明的基本意思,就是五彩缤纷的自然景物,正是作家情感的绝佳载体。作家凭己之情以感物,通过心物间的不断往复吐纳,最终情感与景物融为一体,导致艺术形象的被创造。感物正因如此美妙,它让人如痴如醉。《世说新语·言语》记时人之赏物说:“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即足见此。
何以六朝文论会轻创作源泉而重情思表现?考虑到其时文学刚走上自觉这一背景,也许六朝文艺思想的这一特征并不难索解。毕竟由生活到情感再到作品这一过程较之直接地认为文学是情感的表现更为复杂,且严格说又并不属于直接的创作过程。费大力气说明情感的形成,实不如直接说明情感应该怎样表现于作品中,更能够揭示文艺创作的奥秘。再者,就是魏晋文学自觉的特色既在于抒情,那么,强调情感如何表现实则就是维护文学的自觉了。所以当时人们并没有对情感的形成作更多的思索,他们将精力更多地投入于研究情感怎样与物色融汇,又怎样在物色中体现。但是,六朝文学思想的这一特点,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无论隋唐,还是宋元明清,人们衡量抒情诗歌,往往并不从诗歌的时代社会背景入手,而是侧重探讨诗人之个性、诗歌之气象、声势、韵味种种。我们不妨看看魏晋之后的人们对建安诗歌的一些评价:“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1]“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2]明钟惺评曹操《观沧海》:“直写其胸中眼中,一段笼盖吞吐气象。”[3]清王夫之评曹操《碣石篇》:“不言所悲,而充塞八极无非愁者。”[4]又评《观沧海》:“未有海语,自有海情。孟德乐府,固卓荦惊人,而意抱渊永,动人以声不以言。”[4]着眼处均是作家的个性情感的表现特征。在这些后代主流诗论家看来,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诗歌正因有此一点个性情感的本色精光,便建构了独特艺术价值。相形之下,那些认为建安诗歌的形成乃源于当日天下板荡的社会现实的主张,反倒显得有些另类。如元稹对建安诗歌的认识:“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冤哀存离之作,尤极于苦。”(《元氏长庆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倡导表现现实的“新乐府”的元稹有此认识并不足为奇,问题在于他的认识和陆机、刘勰开创,且被后人一直沿袭下来的强调抒情强调个性的文学思想主潮有点抵触。
二
论及魏晋文人的纵情为诗,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便是玄学思想的影响了。
作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一种哲学思潮,玄学的几个主要理论代表人物,如王弼、何晏、嵇康、阮籍、向秀、郭象,都十分强调自然。强调自然,当然就是主张尊重个性,尊重感情,放纵自我。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玄学与老、庄,特别是庄子主张的反对任何束缚,主张绝对的自由是有区别的。玄学主张的返“自然”、“任自然”,是要求返回到一种原始的清静、明净状态中去,并非一味要求个性解放、情感解放。《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曾引王弼论“圣人有情”的一段认识,充分说明玄学的这一立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从强调自然的立场上看,主张“圣人有情”,那么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圣人也可以放纵自己的感情了。但王弼的意思显然并不在此。他认为圣人还有“能体冲和以通无”的“神明”。这“神明”,其实也就是内心深处清虚超脱、空明宁静的本性了。正是有赖于此,圣人虽有五情,却能不为情所累,应物又不累于物。玄学就这样为自己的既主重情又反对放纵感情的主张作了理论表述。凭借这样的立场,玄学之任自然,当然与任情纵情有大不同。例如嵇康,他是明确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但他“任自然”,具体表现是“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目的在体冲和而非纵情。他在《养生论》中,把这一意思说得更为明确:“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
宗强师在谈到魏晋之际的士风时,曾以曹植死的明帝太和六年(232年)作为界限,认为此前之士风带建安时的通脱任性色彩。而此后由于一批深染玄思之士人之登上历史舞台,士人之心理状态,人生理想,生活情趣与方式,都与建安士人有了很大差别。[5]如果要简要地概括出这种差别的话,我想,可用尚通脱与崇尚与道相契的任自然来说明。士风如此,其时重视情思表现的诗风亦不例外。与率性任情的建安诗歌比较,曹植以后的魏晋诗歌,受玄学思想影响,表现出了一种明净、清澈、超脱、玄远的风貌。嵇康诗堪称代表:“澹澹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6]阮籍诗也有此种特征:“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野外,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7]就诗中所蕴情感言,嵇诗宁静闲适,阮诗愁绪深沉,可谓相去甚远。但就审美风貌言,都展现出一种由心与物化所造就的极富脱俗玄意的清澈明净。
魏晋诗歌的这种审美风貌,又因为它与传统儒家思想所强调的士人不随波逐流遗世独立的为人操守息息相通,所以,即使在魏晋玄思消熄之后,此种诗风不但难以被人遗忘,反而因其既体现诗人人格之高洁,又有高远深沉之韵味而备受后人推崇。清初以“神韵”论诗且又“醇谨称职”、“温厚平易”的王士祯在《带经堂诗话》中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两句,“妙在象外”,正是一例。在前人评价中,最深刻地道出魏晋诗歌这种审美风貌的底蕴的,我以为还属王夫之《古诗评选》对阮籍《咏怀》诗的评价:“如此诗,以浅求之,若一无所怀。而字后言前,眉端吻外,有无尽藏之怀。”又说:“(阮籍)以高朗之怀,脱颖之气,取神似于离合之间,大要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诗人凭“高朗之怀、脱颖之气”,纯任自然,随意抒写,明净清澈,淡泊冲和,忽有所悟,心与道契,看似平淡,却意蕴无穷。魏晋之际由嵇康和阮籍所倡的此种诗歌审美风貌,以诗人遗世独立的人格精神为基础,强调诗人的抒情应与物化一,透澈明净。这也就是中国古典美学所强调的“清”的美学范畴的审美底蕴了。对“清”的重视,实不始于魏晋。但魏晋之前,诸如《诗经》以“清风”喻诗,两汉以“清论”衡议,其实都并没有真正上升到纯精神层面的审美感受高度。只有到了魏晋之际,由于玄学思想的介入与影响,“清”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意义及表现特征才得以凸显。
由上所述,可知建安开创的“师心遣论,使气命诗”之风,在曹植去世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由社会动荡孕育出的慷慨苍凉的任情使性特征渐趋收敛,受玄学思想影响的任自然、体冲和之“清”的审美意蕴越发成为人们共同的追求。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角度看,此际之创作因其追求超脱,强调通“无”,似乎与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此际诗歌所造就出的“清”美,却因其清澈明净,意蕴生动且又体现诗人高洁超脱之怀抱而引起后人瞩目。王国维《人间词话》论“主观诗人”的创作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如果这“主观之诗人”,即是指那种有“高朗之怀,脱颖之气”,又纯“任自然”地抒情,追求与物化一的“清”美的诗人的话,我以为王氏此论对我们认识魏晋时期诗歌的抒情特征,极具启发意义。
三
嵇、阮而后的西晋太康诗人,不断创造出许多与“清”有关系的审美新概念。陆机《文赋》有“清芬”、“清丽”、“清唱”等,其弟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亦有“清工”、“清妙”、“清新”、“清美”、“清省”、“清绝”等。这些概念的出现,我以为即反映出诗之“清”美已经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崇尚和注意。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尽管诗之“清”美为时人所推崇,但从创作实践来看,六朝诗人中除陶潜、大小谢外,能臻此境者寥寥。这似乎又说明诗人要做到诗歌语言清新、清省,凭努力尚可及之,要达到诗境之“清”,单凭后天的勤奋,则十分困难。这里即以陶潜、大小谢诗为例,对诗境之“清”美作些具体说明。
陶诗诗境之“清”,源于他对当时政治由深刻的观察体会而转化成的厌恶厌倦。归园田居对他来说实在是心神的一种解脱解放。他是从内心里欢呼庆幸自己因作出这种正确选择而走出了迷途的。所以当他返乡之后,故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显得那样亲切,那样启他遐想。他将自己内心的这种自由和满足依托于眼前所见之景物以传达,景物则因承载他这种高朗之怀而显得圣洁与飘逸。他不需要详细刻画景物形色,无论是“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之所以动人,关键在于体现出诗人非常人所及的高人情怀。有此情怀,随意抒写,何景非诗,何物不美?即使是为一般论诗者所厌恶的琐细景物罗列,在陶渊明笔下也显得那样生机盎然,意趣无穷。《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即是例证。
谢灵运诗似与陶诗有所不同。他是详细刻画了景物的外形了的。并以其刻画的细腻生动被后人认为是开了吾国山水诗之源头。但如果我们将谢诗之长认定为在于他对景物之细腻生动刻画描绘上的话,似又不合古人对谢诗的认识。以其公认的代表作之一《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为例,诗有傍晚湖畔景色之细腻生动刻画:“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这也是通常人们所称道的谢诗佳处所在了。但古人似乎并不这么看。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说此诗云:“此诗精神全著意一‘还’字”。按方氏此说,是诗对湖畔晚景所作之种种叙述描绘,实不过为“还”而作的铺垫说明。方氏进而指出:谢诗“写山水之景,言己志在此,无与同心,诸篇皆此一意。”这就是说谢灵运诗之所以极力描摹物色之美,所展示的无非是自己对世俗生活的厌倦,以及返归山水后中心的愉悦。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又不得任用,目睹家族式微又无力挽回,身处政治漩涡之中使他终日惴惴,在这种情况下,他看到的湖畔傍晚景色让他惊惶失意的内心得以平静,一种“还湖中”的感觉油然而生。他是将山水作为生命的慰藉来看待的,此“还湖中”与陶渊明的“归园田”并无实质差异。或许对他而言,将湖畔晚景写得越动人,山水作为自我生命栖居之家园的意义就越发生动鲜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他对山水的细腻描写中,看到他的高朗之怀,他的诗思之清亦由是而成。论谢诗只注意到他诗歌写景之佳者,实未得谢诗之神髓。
谢脁诗思之清,与陶及大谢又有不同。这是一种与他的家庭背景、个人气质大有联系的清思。小谢出身世家,受过当时最好的教育,个人感触极其敏锐,但他又全然不谙世情,不懂现实政治,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以致终日惶惶,且又无可奈何。他丰富细腻的感情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引起回应和共鸣的,他只能作为一株不合俗流、飘逸不群的芝兰玉树孤立于现实生活之中。要获取心灵之慰藉,似只有当心与物化之际。其诗《和王中丞闻琴》:“凉风吹月露。圆景动清阴。蕙风入怀抱。闻君此夜琴。萧瑟满林听。轻鸣响涧音。无为澹容与。蹉跎江海心。”[8]即写出当他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之后,在大自然中因与道契合而获得的心灵慰藉。初秋之夜,月光皎洁,惠风入怀,荡涤尘垢,琴声轻鸣,启人遐想,天地明净,物我清澈,于是,飘逸之志顿起,超然之心乃成。这就是小谢憧憬的人生了,这种憧憬带着显而易见的脆弱苍白的特点。王夫之《古诗评选》评小谢诗说:“华净。其华可及,其净不可及也。”方东树《昭昧詹言》则对小谢诗作此比喻:“玄晖诗,如花之初放,月之初盈,骀荡之情,圆满之辉,令人魂醉。”可知这种脆弱苍白的清思因其难能可贵且清澈明净而容易引起人们的怜惜珍视。从这个意义上看,王国维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就是强调某些于现实完全陌生的抒情诗人在他们的创作中应尽量体现出天性中的那种清澈超脱真纯明净的情感,而不必一味地为迁就阅世而损害情思之清真了。
魏晋六朝三位被公认为有清思的诗人,以他们的诗作证明主张心与物化的任自然的玄学对当日诗作的有力推动,并由之导致出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一种极富特色的审美追求。虽然由于人生轨迹的差异,这三位诗人心与物化的基础并不一致,诗歌风貌也有差别,但他们的创作对后人而言,都是一种珍贵且值得回味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曹操卷·敖陶孙[G].北京:中华书局,2004.
[2] 钱仲联.万首论诗绝句·论诗三十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曹操卷·锺惺、谭元春[G].北京:中华书局,2004.
[4] 王夫之.古诗评选:曹操(碣石篇)[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5]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6] 王夫之.古诗评选:嵇康(酒会篇)[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7] 王夫之.古诗评选:阮籍(咏怀篇)[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8] 王夫之.古诗评选:谢眺[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