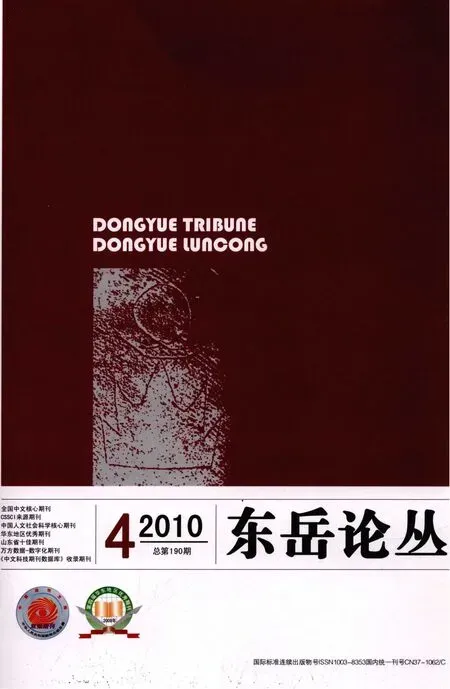晚清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小说观的萌蘖
姜荣刚
(许昌学院文学院,河南许昌 461000)
晚清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小说观的萌蘖
姜荣刚
(许昌学院文学院,河南许昌 461000)
中国的现代小说观萌生于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语境中,晚清留学生对此有筚路蓝缕之功。在域外的学习过程中,留学生的文学观念受到来自异邦的冲击与影响,中国的现代小说观即率先在他们中萌生并得以初步成型。由于受到政治因素、传统小说观的惯性影响以及对域外小说观的接受程度等诸种条件的限制,留学生对中国现代小说观的早期建构呈现出新旧杂陈与多样化并存的特点。
留学生;现代小说观;中国小说现代转型;萌蘖
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小说观的重建是先决条件之一。理清这一问题对认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与此一时期特有的文学表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中国小说的理论发展史来看,中国的小说观成熟很早,而且具有相当的自足性与本土文化色彩。小说发展至明清,创作积累的成就虽已构成推动小说观向现代转型的条件,但在主流文化层面它的本质属性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纪昀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不收通俗小说即为显证。这说明至少在晚清西方文化介入以前,中国的现代小说观尚无自发生成之可能。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小说观萌蘖于晚清是直接受激刺于外来影响。
早期中土人士接触域外小说观念主要有两种可能途径,一是通过来华传教士的间接影响,一是走出国门直接受其濡染。不过就实际情况来看,传教士对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身份与使命限制往往对输入纯文学及其观念不感兴趣①关于此点可参看宋莉华《十九世纪传教士小说的文化解读》的相关论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 1期。,而且其小说活动出于适应中土读者的考虑,也往往被中国化了,因而难以对中国的传统小说观产生根本性的冲击。甲午战争以前,中土人士普遍认为文学唯中国独有,致使早期走出国门的虽不乏其人,但对域外文学往往不屑一顾,时人有诗云:“经史外添无限学,欧罗所作是何诗?”②樊增祥:《九叠前韵书感》,《樊山续集》卷二十四。持有这种态度自然不可能平心静气地去了解对方的文学,更不用谈文学观念的改变了。光绪初年曾任驻英大使的郭嵩焘,说英国“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③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 1984年版,第 119页。。流亡海外数年的王韬与郭嵩焘的看法几无二致,他说:“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词章”④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22页。。对域外文学缺乏基本的了解,自然不免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类似于郭嵩焘与王韬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这也就决定了在中国现代小说观的萌蘖期——晚清,留学生必然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他们修的是何种专业,语言是必过的一关,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方的文学作品与观念。而且出于学习的需要,他们也更注重了解对方的文化风情,对方的文学观念也自然比较容易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事实上,现有的资料也的确表明中国的现代小说观首先是在他们中萌生的。而且在中国现代小说观的萌蘖期,他们所起到的作用也非其他群体所可比拟。因此,本文即以此一群体作为考察对象,以透视中土人士对域外小说观念的接受与变异,试图以此揭示中国现代小说观之萌蘖期的复杂与曲折过程。
一
甲午战争以前,自费留学尚未形成风气,官派留学也仅出现过两次。这两次官派留学均是在洋务派推动下成行的,目的在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第一次是 1872年至 1875年间清廷陆续派出了四批共计 120名留美幼童,但因种种原因这批留美幼童中途被撤回,未能达到原定目标。第二次是 1877年至 1886年由福建船政学堂分三批派出了 81名留欧学生。此一时期留学人数虽少,但在域外的学习过程中却有不少留学生的小说观念发生了明显转变,归国后参与各种小说活动,对中国现代小说观的早期建构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留欧学生中的陈季同与严复。陈季同的身份比严复特殊一些,他是清廷任命的此批留学生的文案,但为了“学习交涉切用之律”,也进了巴黎政治学校 (E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专习交涉律例等事”,所习功课包括交涉、公法、律例、格致、政治、文辞等①参看桑兵《陈季同述论》的相关论述,《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 4期。,因此学界一般仍将其视为留学生。与时人一样,陈季同在留学之前也认为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但进入法国社会后,他却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尴尬,异邦的文学统系里不仅没有中国文学,甚至连日本文学都不如。不过,中国一向鄙弃的小说戏曲,如《玉娇李》、《赵氏孤儿》等,却很早就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赞赏。域外人士对中国文学毫不掩饰的鄙夷态度激起了陈季同的深刻反思,他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实出于两种原因:一是我们太不注意宣传,文学的作品,译出去的很少,译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译得不好,因此生出重重隔膜;二是我们文学注重的范围,和他们不同,我们只守定诗古文词几种体格,做发抒思想情绪的正鹄,领域很狭,而他们重视的如小说戏曲,我们又鄙夷不屑,所以彼此易生误会”。陈季同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勉力做的是:
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过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要免误会,非把我们文学上相传的习惯改革不可,不但成见要破除,连方式都要变换,以求一致。然要实现这两种主意的总关键,却全在乎多读他们的书。
毋庸置疑,域外的学习与生活经历彻底动摇了陈季同的固有文学观念,从而使他认识到中国文学的传统观念必须改变,其中之一就是要重视小说和戏曲。这种态度的转变也促使他对域外文学展开了全面的学习,曾朴曾这样回忆道:
他指示我文艺复兴的关系,古典和浪漫的区别,自然派,象征派,和近代各派自由进展的趋势;古典派中,他教我读拉勃来的《巨人传》,龙沙尔的诗,拉星和莫理哀的悲喜剧,白罗瓦的《诗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论;浪漫派中,他教我读服尔德的历史,卢梭的论文,嚣俄的小说,威尼的诗,大仲马的戏剧,米显雷的历史;自然派里,他教我读弗劳贝、佐拉、莫泊三的小说,李尔的诗,小仲马的戏剧,泰恩的批评;一直到近代的白伦内甸《文学史》,和杜丹、蒲尔善、弗朗士、陆悌的作品;又指点我法译本的意、西、英、德各国的作家名著。
陈季同对西方文学涉猎范围之广、了解之深,在当时来讲是极为罕见的。陈氏的这种文学观念对曾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曾朴事后称与他的交往使他“发了文学狂”,后来他重视并从事小说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陈氏的影响②曾朴:《曾先生答书》,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 4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615-618页。。
陈季同虽然认为中国相传的文学习惯应该改革,但他所做的主要工作却不是“拿进来”,而是“送出去”,即更注重将中国的文学介绍给外国人,以消除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误解与偏见。与陈季同相反,严复则主要做的是“拿进来”的工作。他不仅翻译了大量西方思想界的名著,而且也将西方的文学观念带进了中国。他归国后曾创办《国闻报》,该报登载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即出自于他和夏曾佑之手,文中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①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7页。,严复对小说在西方国家立国之初所起作用的描述与强调对国人参与小说活动产生了不小的鼓舞作用,对晚清小说观念的转变自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该文一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被“视为现代中国第一篇强调小说社会功用的评论文章”②夏志清:《人的文学》,台北:纯文学出版社 1977年版,第 63页。。由于严复并未在文中透露他对域外文学的接受情况,因此他对域外小说功用的描述与强调颇被疑为是传闻异辞。事实上,1907年严复发表的译作《美术通诠·古代鉴别》,其中案语颇多述及小说的文字,此译作向为研究者所忽视,于此可见其对域外文学的接受:
文字分为创意、实录二种,中国亦然。叙录实事者,固为实录,而发挥真理者,亦实录也。至创意一种,如词曲、小说之属,中国以为乱雅,摈不列于著作之林;而西国则绝重之,最古如希腊鄂谟之诗史《伊里叶》,而英之犹斯丕尔、法之摩理耶、德之葛尔第,皆以词曲为一国宗匠,以较吾国之临川、实甫诸公,其声价为缙绅所不屑道者,而相异岂直云泥而已?
这里的“实录、创意”即对应的是“写实、虚构”,“前以思理胜,后以感情胜”。严复感叹属于“创意”的小说“西国则绝重之”,而中土缙绅则不屑道。并说:“斯宾塞尔曰:瀹民智者,必益其思理;厚民德者,必高其感情。故美术者,教化之极高点也。而吾国之浅人,且以为无用而置之矣”③[英]倭斯弗:《美术通诠》,严复译,《寰球中国学生报》第五、六合期。此译作承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皮后锋博士惠赐影本,在此谨表谢忱。。这些无疑对严复小说观念的重建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也是他看重并提倡小说的重要动力。
除陈季同、严复外,第三批留欧学生中的王寿昌也值得注意。他虽然没有留下论述小说的文字,但在归国后他把小仲马的《茶花女》介绍给了林纾。林纾曾说:“晓斋主人归自巴黎,与冷红生谈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生请述之。主人因道,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暇辄述以授冷红生,冷红生涉笔记之”④冷红生:《〈巴黎茶花女遗事 〉小引》,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 40页。。由此可见王寿昌对域外小说了解之深,其小说观念之变化亦可想见。《茶花女》经过二人的合作翻译,书成后即风靡一时,严复曾赋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⑤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周振甫选注:《严复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04页。,可见影响之大。该小说翻译的成功,不仅奠定了林纾翻译小说事业的基础,也对晚清小说观念的转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曾朴在谈及晚清小说观念的转变时,除高度评价梁启超的作用以外,还说:“翻译的小说,如《茶花女遗事》等,渐渐的出现了,那时社会上一般的心理,轻蔑小说的态度确是减了”⑥曾朴:《曾先生答书》,见《胡适文集》(第 4集),第 618页。。这种影响虽主要应归功于林纾,但也不能因此忽略了王寿昌的间接作用。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现代小说观首先是在早期的留学生中萌生,并在他们的推动下,开始现代转型的,因此他们的先驱地位理应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二
甲午战争以后,中土人士认识到“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砲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⑦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83页。。于是,对西方学习的重点开始逐渐转移到政艺法律与思想文化上来。尤其是戊戌、庚子以后,经过一次比一次更为惨重的失败后,国人的自信心彻底丧失,以往尊尚的“圣贤之书”被认为是“残废不合时宜”⑧棣(黄世仲):《小说种类之区别实足移易社会之灵魂》,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 239页。,以致“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18页。。大批留学生的出现,加速了对域外小说及其观念的接受与传播,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转型。
鲁迅说:“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②鲁迅:《〈域外小说集 〉序》,《鲁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61页。。正是留日学生中这种普遍存在的“茫漠的希望”使大批留学生加入到小说的革新运动中去,梁启超事后曾这样描述这些留学生对新思想的输入情况:“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 218页。。作为输入新思想的重要媒介——小说,也成为留学生译述的重要内容,翻译小说亦因此得以迅速繁荣。除撰、译小说以外,留日学生还发表了不少有关小说的文字,提倡与鼓吹小说。出于对小说改良社会的热情,留学生表现出了对小说的极度重视,如《浙江潮发刊词》中就说:“小说者,国民之影而亦其母也”④《浙江潮发刊词》,《浙江潮》1903年第一期。。
光绪二十八年 (1902)十月十五日 (1902.11.14)留日学生杨度发表了《游学译编叙》,此文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同时刊出。杨文虽然不是专论小说的文章,但其中有一大段自成系统之文字鼓吹与提倡白话小说,其观点与梁文颇为类似,但比梁文更注重运用域外文学经验与理论知识⑤由 于通行小说汇编资料多不收此文,故甚少为治晚清小说的学者所提及,具体内容可参看拙作《一篇被忽略的早期小说革新宣言——论杨度 〈游学译编叙 〉中的小说思想及其价值》,第四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文中杨度从实用的角度给予小说以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学人以为经世著书之具,务求为高雅闳博之词,则文学反以阻国民之进步。故不独词章家之以雕琢为诗文,取悦一己而不求人知者之不足厕于一国之文学界也;即有心于当世者,亦以此计其功用之大小,而分其品次之高下焉”。因之唯有小说最有资格厕身于文学,杨度的这种观点来源于他对域外文学的接受,因为他接下来即说:“俄国学者特儿斯特之论艺术也,分广义与狭义,而小说与诗歌、美术等,同在狭义之中。其总论曰:‘艺术者,使作者之感情传染于人之最捷之具也,作者之主题当如何,则必以直接或间接向于人类同腔(胞)的结合,而求其好果,以为感情之用也’。”杨度摘取了托尔斯泰《艺术论》中的三个观点,一是小说为艺术之一种;二是艺术是作者传达感情的工具 (杨度在这里加上了“最捷”二字);三是艺术的使命是为了使人类达到团结与幸福。这三点是杨度提倡小说的理论依据。为了说明上述观点,他还举了彼斯脱洛(裴斯泰洛齐,J.H.Pestalozzi,1746-1827)的例子,说他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大教育家,“以读路索之《也米儿》(引者按:指卢梭的《爱弥尔》)小说一书而成者也”。小说既然如此“有利于国民”,自然也就是“有用之文字”,岂能再加轻视?杨度借助日本学者笹川种郎的话对中国轻视小说的传统作了批判,并由此认为“我国民之不进化,文字障其亦一大原因也”。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完成于 1898年,笹川种郎所著《支那历朝文学史》亦出版于是年,1903年始由上海中西书局译成中文印行。就中土人士自觉运用域外文学理论来讲,杨度恐怕是第一人。
在对小说进行一番正名后,杨度认为“小说文字之所以优者,为其近于语言而能唤起国民之精神故耳”。小说在开化民众方面的整体功效,杨度举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的例子,他说:
意大利之诗人当的编国语以教民族;日本维新之名儒福泽谕吉著书教人,必先令其妻读之,有不解者,辄复更易,以求人人能读,此皆小说之意也。岂非以作一字而非为国民之全体谋公益者,则必不为之乎?然今日竟有意大利统一、日本振兴之实效,则有谓二君不能列于文学界而称为名儒者,其国民能听之否耶?⑥杨度:《游学译编叙》,《游学译编》1902年第一期。
从严复到杨度,域外小说开化民众的这种“正面效应”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事实描述,而是渐趋神话化了。不过,从前引鲁迅的话可知这不仅仅是留学生为宣传的需要而故意制造的一种神话,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他们直接接触域外文学时所产生的一种信念。大约与杨度同时留学日本的许定一①定一《小说丛话》,《新小说》第十五号。此定一,一说为于定一,实误。检《新民丛报》第三年第十七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发有署名“定一”的文章《论公法为权力关系之规定》,文末识语署“许子附志”,考虑到《新小说》与《新民丛报》的特殊关系,故此二“定一”当为一人,即许定一。据《游学译编》第十册癸卯年七月调查之《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载,许定一为湖南善化人,壬寅(1902)正月自费留学日本。也说:“中国小说,起于宋朝,因太平无事,日进一佳话,其性质原为娱乐计,故致为君子所轻视,良有以也”。带着这种小说观踏入异国,域外文学对小说的重视及其文学经验,很容易对留学生造成精神上的激刺,甚至会因此而认为国民之不进步乃是因为小说不发达的缘故。所以欲使国民进步就不能不提倡小说,而欲提倡小说就“必须以普及一法”,“去人人轻视小说之心”②定一《小说丛话》,《新小说》第十五号。。
当时留学日本的鲁迅也对以小说开启民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在《〈月界旅行 〉辨言》中说:“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③《鲁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52页。。
壬寅癸卯间留日学生撰、译的小说及出版的小说刊物在内地相当畅销,从而对扭转本土轻视小说的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过分注重政治目的,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从而限制了他们对域外文学的了解与接受,所以他们对小说观念的输入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坐此为能力所限,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 218页。。周作人在批评晚清翻译小说时也说:“除却一二摘译的小仲马《茶花女遗事》、托尔斯泰《心狱》以外,别无世界名著”,而“所以译这本书者,便因为他有我的长处,因为他像我的缘故”⑤周 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见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57页。。所以从根本上讲,这种输入方式只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一种变相继承,在这样的基础上是催生不出中国的现代小说观来的。
三
由于现实政治的影响,留学生的专业取向正如鲁迅所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⑥鲁迅:《〈呐喊 〉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439页。。这使得大多数留学生对域外文学的了解比较肤浅,在向本土输入的过程中也自然难免“稗贩”之讥。不过在这种“冷淡的空气中”也有一些留学生对域外新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学习。对域外新文学的深入了解使他们脱离了早期的被动与盲目,在接受与输入方面表现出了选择上的自觉,并开始有意纠正时下流行小说观的偏颇,中国的现代小说观即是在他们的这种努力下得以初步成型的。
首先值得重视的是王国维。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留学日本,由于“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⑦王国维:《自序》,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二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96页。。回国后即协助罗振玉编刊《教育世界》杂志,自此撰述日丰,其中颇多论述小说的文字。王国维对西方美学有较深入的了解,所以他的小说观是建立在纯文学基础之上的。王氏首先对以“惩劝为旨”的传统小说观展开了批判,他说中国的“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⑧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集》(第一册),第 182页。,据此他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桃花扇》等世人看重的作品皆无纯文学之资格①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集》(第一册),第 26页。,唯有《红楼梦》“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②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集》(第一册),第 21页。。对于时下流行的功利性小说观,他也同样予以批判,他说:“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③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集》(第二册),第 303页。。他同时还反对将小说视为一种职业:“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餔餟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餔餟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④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集》(第一册),第 26页。。不过,王国维虽然反对赋予小说以实用功能,但也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⑤王国维:《文学与教育》,《王国维集》(第四册),第 9页。。可见他着眼的是长远的国民精神的塑造,而非一时的政治功利。这一点与此后的周氏兄弟取向完全一致。
除此之外,王国维的小说观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通过批判以考证的眼光来解读《红楼梦》的做法,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新的小说观。小说作为“史之支流”的观点在中国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将小说作为“实事”来考索正是这种小说观念的自然体现。王国维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这种态度“实与美术之渊源之问题相关系……美术之源,出于先天,抑由于经验,此西洋美学上至大之问题也”。对这个“至大问题”的回答,他借用的是叔本华的美学观点,即“美之预想存于经验之前”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集》(第一册),第 18-21页。。这即是说小说是精神的创造,是虚构的故事,而非经验事实的模写,从而彻底突破了传统小说为“史之支流”的观点。二是打破了以情节为本位的小说观,从而开始了对“纯文学”小说的自觉译介。他曾在《教育世界》登载的翻译小说《爱与心》按语中说:“近人不知文学为何物,小说为何物,徒以设局变幻,叙事新奇,取餍一时之快意。侦探小说之类,充牣于坊肆。举世嗜好方若彼,而译者乃著笔及此,其不为时人诋以迷信,目以枯寂乏味者,盖鲜矣。虽然,此书在欧洲,声价之隆重,垂垂近二千年,又岂俗子辈所得而雌黄者哉!具慧眼者,必不辞欢迎之矣”⑦转引自陈鸿祥:《王国维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99页。。由此可见,王国维不失为中国纯文学小说观的最早建构者与推动者。
稍后于王国维的周氏兄弟也是中国现代小说观萌蘖期的重要推动者。鲁迅初入日本时学的是医,但很快就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域外新文学的学习上。周作人在他的影响下于 1906年留学日本,对域外新文学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对域外新文学的深入了解不仅使他们很快从梁启超的影响下走出来,而且成为反功利小说观的积极提倡者。周作人在《红星佚史序》(1907)中说:“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繙,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由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桚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⑧周作人:《红星佚史序》,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 252页。。周作人明确指出时下流行的功利小说观与中国传统的“载道”文学观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他认为“说部曼衍自诗”,除王国维外,中土人士从未有此看法。诗作为小说源头的观念源自西方,虽然它的出现已是 18世纪以后的事,但至少在 19世纪已被广泛接受,这种观念也被移植到了日本。太田善男的《文学概论》(1906)就把小说放在“读式诗”下进行讨论,周作人接受的正是太田善男的观点。他在此后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就把纯文学“分之为二:曰吟式诗,中含诗赋、词曲、传奇,韵文也;曰读式诗,为说部之类,散文也”。既将小说纳入纯文学,周氏认为它就应该与“益智”的学术 (或者说杂文学)有所区别,即它“主美”,目的仅在于“移人情”而已。《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对当下“手治文章而心仪功利”的各种小说类型作了系统的批评,然后指出文章的意义暨其使命在于它是“国民精神之所寄”,“虽非实用,而有远功者也”。与王国维一样,他也认为通行的冒险、侦探二种小说虽“颇为一世欢迎”,“要不得谓文章”,“盖其采色浓厚,风味凡浅,为文章之下乘”,从而明确提出了他的纯文学小说观,即:“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①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年版,第 54-57页。。
基于这种认识,周氏兄弟开始有意纠正时下流行小说的偏颇。1909年他们在日本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就是因不满于林纾译小说而进行的一种新尝试,该书“收录至审慎”,所选皆“始入华土”之欧洲“弱小民族”的作品,且“迻译亦期弗失文情”②鲁迅:《〈域外小说集 〉序言》,《鲁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55页。。所以许寿裳盛称鲁迅“是中国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人”③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办杂志、译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21页。,该书“实为译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④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翻译》,第 54页。。但遗憾的是该书出版后,问津者寥寥,二册总共只卖出了四十本,可见影响甚微。不过,周氏兄弟并未因此而改变方针,在同仁或凋零或退出文艺界的冷淡氛围里,仍坚持纯文学小说观的立场,从而为“五四”新文学的探索增加了可资借鉴的新资源,减少了盲目性,这从《域外小说集》受到“五四”新文学家的重视即可看出。
继王国维、周氏兄弟之后,注意小说的纯文学性质与美学特征的尚有黄人与徐念慈二人,但他们并未完全摆脱功利性小说观的影响,观其发表于《小说林》上之作品与理论文字即可明晰此点,其整体程度不及王、周。据《常熟地方小掌故》载,徐念慈亦是留日学生⑤时萌:《徐念慈年谱》,《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第 249页。。
综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小说观主要是在晚清的一个特殊群体——留学生——中萌生并初步成型的,这说明它是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直接产物。由于政治因素与中国传统小说观的强大影响,留学生对域外小说观的接受并非原汁原味,而明显表现出了选择上的主观能动性。多数留学生虽接受小说是文学的观点,在向现代小说观的迈进中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过分强调小说的政治功利性,对区分什么是真正意义的小说不感兴趣,整体上仍未脱出传统小说观的羁绊。即便如此,小说入主文学主流的大趋势毕竟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完成的,这无疑为纯文学小说观的诞生扫清了障碍,其意义仍十分重大。对域外文学有深入了解的留学生在晚清极为少见,他们在以小说改造社会的认识上,与梁启超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但强调的是对“国民精神”的长远塑造,而不再着意于一时的政治目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域外小说及其观念的接受与输入方面已开始表现出了选择上的自觉,在对传统及时下流行小说观的批判中也表现出了对小说本体与范围的自觉体认与区分,这种趋向表明中国现代小说观已开始初步成型。但是他们的努力却不为时人所重,这说明中国的现代小说观只有植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土壤中才能真正开花结果。晚清现代小说观建构的这种新旧杂陈与多样化并存的特点,以及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反映了早期小说革新的艰难历程,揭示这一过程对深入认识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早期型态及其源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留学生与晚清小说”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9-QN-083。
姜荣刚(1976-),男,许昌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I207.42
A
1003-8353(2010)04-0103-07
[责任编辑:曹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