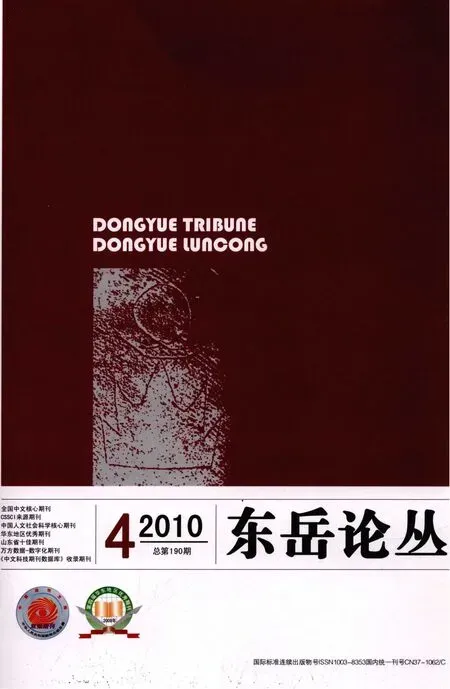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影响下形成创作个性——老舍创作艺术探源之一
石兴泽,石小寒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影响下形成创作个性
——老舍创作艺术探源之一
石兴泽,石小寒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老舍的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的形成源于很多方面,东西文化和文学影响是重要的生成机制。东西方幽默讽刺艺术的影响在老舍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老舍“取益”于狄更斯及中国传统小说的幽默艺术,而某些弊端也可以从那里找到根源。老舍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下,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形成了检讨传统文化、批判国民性的创作个性。
老舍;创作个性;改造国民性;幽默讽刺艺术
老舍是风格卓异、个性独特的作家。其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的形成,源于很多方面的因素。其中,视野所及的文化和文学是重要方面。我们曾经在《参照东西方文学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就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风格等问题作过分析。在此,谨就充分显示其创作个性的幽默风格和批判国民性主题做些简要分析。
一、在狄更斯及中国传统小说影响下形成幽默讽刺的艺术风格
老舍作品以幽默讽刺闻名于世。幽默,在老舍看来首先是一种心态,也是天赋:幽默的人,心宽气朗,独具慧眼,能从事物中看出可笑之处,既不掩饰回避,也不呼号叫骂,而是以温和的心,巧妙地指出来,引人发笑。老舍幽默心态的形成,按他自己的解释是生活境遇所致:“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楞挨饿不肯求人的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同情心,”所以,“我要笑骂,而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①其实,老舍得了幽默,却没有失掉讽刺。幽默和讽刺交汇相邻,很难分开。即使用老舍的标准分析他的作品也不难发现,他虽然不像鲁迅、张天翼那样讽刺得淋漓尽致,但仍然可以说他的幽默里包含着讽刺,或者说他动摇于幽默与讽刺之间。当他的笔触对着社会渣滓、民族败类的时候,他有时并不幽默。文学评论家李长之认为,“与其说老舍的小说以幽默见长,不如说是讽刺,更恰当地说,他的幽默是太形式的,太字面的。不过作为讽刺用的一种表现方法,”“是讽刺的外衣”②。老舍对自己幽默心态形成的解释是准确的,但用于分析内涵丰富、风格宽泛的作家作品却不全面。他创作的幽默讽刺之波除了生活和性格的原因之外,还可以从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海洋里找到渊源。
心有灵犀一点通。带着这种天性和修养,他从大量的西方作家作品中找到了狄更斯这个幽默大师作为精神朋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和狄更斯具有同样的天赋:能从日常生活中看到并揭示出可笑之处,创造趣味无穷、幽默滑稽、才华横溢的艺术画面。狄更斯使他萌动了创作念头,也传授给他书写方法。狄更斯对他影响之大超出一般。他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具有与《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匹克威克外传》相同的艺术风格:幽默流于滑稽,机智多于讽刺,荒唐的“笑料”中蕴藏着温暖而严肃的心。其后,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他“转益多师”,但丁、阿里斯托芬、萨克雷、迪福、辛克莱、玛克·吐温、契诃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组成一个阵容整齐的借鉴体系。在众多老师的“培养”下,他幽默讽刺的艺术风格日趋成熟。
那么,东西方幽默讽刺艺术的影响在老舍创作中留下了哪些迹象呢?
首先,用喜剧艺术手法处理悲剧题材的创作艺术。无论狄更斯还是吴敬梓都不是流着眼泪描写悲惨事实,而是以超然物外的喜剧性笔触加以表现。《儒林外史》“戚而能谐”:周进头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王玉辉劝女殉夫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悲剧,但作者却涂上了喜剧色彩,读后令人忍俊不禁,却又很难大笑出声;笑后流泪,也深思:这些可怜的知识分子何以如此?狄更斯更是善于以喜剧性笔墨表现悲剧事实:饥饿驱使奥利佛尔在吃完他那可怜的一份稀饭之后,要求添一点,济贫院餐厅却立刻炸了营,管事被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吓呆了,清醒过来后用杓子照着他的脑袋敲了下,然后朝着正在开董事会的那间屋子奔去,报告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因为这是收养的儿童们从来不曾有过的放肆行为。悲剧性的内核包裹着喜剧性的外壳,令人苦笑不得:儿童的命运令人辛酸,济贫院的荒唐却令人破肚,可悲可笑就这样胶合在一起。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离婚》、《牛天赐传》都显示出这一特色。他以轻松的文笔讽刺了老张、赵子曰、马则仁、张大哥、牛老者,通过他们反映中国可悲可笑的现实和生活在这现实中可笑可悲的灵魂。但无论老张的可恶可笑,赵子曰的胡涂可笑,还是马则仁的迂腐可笑,张大哥的折中可笑,牛老者的圆软可笑,都不能笑得轻松愉快,因为“嘻笑唾骂的笔墨后边”蕴含著作者“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③,也蕴藏着社会和民族悲剧。
其次是艺术手法的借鉴。东西方艺术大师们幽默讽刺的对象不同,艺术手法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很难确切地指出老舍借鉴于何处。比如,他早期作品中常常利用表现形式与表现内容的不相称突出对象的矛盾可笑,收到幽默讽刺的艺术效果:说到无关紧要甚至荒谬绝伦的事情时,常常摆出一副庄严而深思的神气,或者平静而自然的声调,以致把完全荒谬的想法当作无可辩驳的真理告诉读者;而说到至关重要的事情,则又故意用漫不经心的诙谐荒诞的语气表现出来,似乎有意告诉读者“这没什么”——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狄更斯式的,但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中国“古已有之”,只是运用得不够充分、表现不甚明显罢了。
这一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词汇搭配艺术。如果说,语言色彩有浓淡之分的话,那么,幽默讽刺作家为了取得理想的艺术效果,往往一反常规地搭配色彩:该淡的地方浓或者相反,该红的地方着绿或者白,通过内容与形式的明显反差制造或幽默或讽刺的艺术画面。打牌是一种消遣娱乐,但在狄更斯笔下却成了“庄严的仪式”,用“态度庄严”、“举止文静”这些重色彩的字加以修饰,使得牌场一派“静穆”,“玩牌”之说就成了“很大的不敬和污蔑”④。这样用词不伦不类,却是幽默讽刺的重要途径。这给老舍很多启示,他也学习狄更斯的榜样借助于语言文字的“错误配置”制造笑源:如张大哥夸奖李太太的好处“像慰劳前线阵亡将士似的”,说老李与妻子不和是“断绝了国交”,牛太太经常骂牛老者是“温习功课”……你可以批评这是效颦,描写过分,流于滑稽,但是,却不能否认它确实制造了喜剧性的效果。
如果说这种幽默讽刺在于作家使用语言的才能,多少有些刻意追求的“嫌疑”,那么,下面的方法则依赖于作家洞悉的观察,忠实的表现,透露着自然,显示着讽刺幽默的力度。作家善于抓住现实生活中可笑的人和事加以冷静客观地表现,幽默不是靠语言技巧等外在的方式表现,而是靠这个或那个情节的内在特质实现。这是幽默艺术最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吴敬梓以此剥下了儒林社会的光华外衣,暴露了荒唐的社会现实与荒诞的灵魂,鞭挞了科举制度。狄更斯则以此暴露了被美化成歌舞升平、井然有序、繁荣发展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腐败和荒谬。老舍从现实中提炼出人事的荒唐,不动声色地加以表现,制造出一个个幽默讽刺场面,暴露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和市民社会的可悲可笑。正是这些事实充作骨架,才使他早期的创作免进滑稽的沼泽。在具体表现中,吴敬梓尖刻辛辣,常常是当场揭露人物动机与表现、语言与行为、不同场合之间的矛盾,令其出丑;狄更斯则出于英国人的涵养或者幽默艺术的需要,揭露得含蓄、隐沉、婉转,留有余地,不让人物当场难堪。老舍远承吴敬梓,近袭狄更斯,就便师法,合二而一。如蓝小山,他的谎话连篇令人想到金格尔、庞德贝,也想到狄更斯对金格尔、庞德贝的态度;他的吃薄而小的黑糖芝麻酱饼喝白开水补肚子则令人想起吴敬梓笔下的严贡生、牛布衣。中西“合艺”,将一个混迹于社会边缘地带的文人小贩的丑陋嘴脸刻画得不动声色却又淋漓尽致。
夸张是任何幽默讽刺作家所共用的手法。根据事物发展逻辑给予艺术夸张,使人事更突出,是幽默讽刺的必要途径。没有夸张就没有讽刺和幽默。斯奎尔把窗户拼成 winder透露着滑稽,吴敬梓描写胡三公子买鸭前先拔下耳挖戳戳脯子上的肉肥不肥显示着辛辣;效果不同,夸张是共同的。老舍同前辈大师一样,带着放大镜看取事实,也用放大尺描绘事实,他笔下的事实像哈哈镜里的影像透着怪诞和变异。如写老张爱钱如命,生平只洗三次澡,在他的审美观念里连青青的荷叶都像铸着袁世凯脑袋的大钱;赵子曰名为大学生却糊涂得近乎白痴,考试倒数第一,照着镜子勉励自己“倒着念不也是第一吗?”以此寻找心理平衡;张大哥热心敷衍人事,是“一切人的大哥”,“大哥味”浓到别人以为“连他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牛老者作为生意人马马虎虎,毫无经营头脑,而又软若豆腐,连给人赏钱都不敢和太太持平……问题不在于这些描写是否在现实中找到对应关系,而在于通过夸张,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凸现事物的本质,增强喜剧性的艺术效果。
最后就是对于网络环境对学生的综合性影响。对于高职生而言,不健康的网络环境不仅仅会影响学生的思想观念,甚至可能会导致学生形成扭曲错误的伦理判断,而对于网络环境的肃清问题上,我国显然还处于努力的阶段,尚且不能够保证给学生带来一个健康、稳定的网络环境。在这些特性的综合影响下,加之对于学生英美文化教学活动的开展,很容易导致学生逐渐出现思想滑坡、跑偏的现象,开展思政工作,让思想政治教育引领英美文化的学习,以此来共同推动学生进步是非常关键且重要的。
应当指出的是,老舍于寂寞中摹仿狄更斯画稿子时,缺乏足够的文学修养和创作准备,其借鉴常常兼收并蓄,精华糟粕一口吞。精华使他成功,糟粕却误导他走向歧途。他学习狄更斯的样子大胆放野,一任幽默,时时滑入招笑的泥坑,正像人们所指出的那样,早期创作中,虽有事实作骨干,却敌不过四面八方埋伏下的“引笑弹”⑤。他自己事后也承认,到了把“幽默论斤卖”的时候,讨厌是必不免的。他有时讽刺过火,描写失之张皇,伤于溢恶,违背真实——陷于清末谴责小说杂集话柄的泥潭。有时“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跳出艺术描写之外现身说教——这既有谴责小说的遗迹,也有狄更斯的影响。某些动人格言、有关社会文化、道德问题的议论和冗长的国民心理分析,自然源于狄更斯,而那章节开端频频出现的解释和议论则于无意中陷入“三言二拍”模式。凡此种种,游离于作品情节,既破坏了整体和谐,冲淡了幽默,也削弱了艺术魅力。
有些遗憾的是,老舍也像狄更斯那样,把幽默当作调料,把温爱廉价出售,其结果简化了现实,缓和了社会矛盾。卢那察尔斯基指出,狄更斯“把强烈的感受化为戏谑,或者至少是把世界观(以及它在政治和小说里的反映)中的悲观因素同这种温和亲切的戏谑,同对人类弱点一笑了之等因素糅合在一起,”“使他对沉重的恶梦似的现实加以容忍”⑥。这种批评同样适用于老舍。对于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于作恶多端者如老张、欧阳天风、小赵等,采取温和态度加以表现,宽容了丑恶,冲淡了正义感,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总之,老舍的幽默讽刺得益于狄更斯及中国传统小说,也“取弊”于他们。其缺点,有的很快克服,有的却伴随着他走了很长的路程。
二、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影响下致力于文化检讨和国民性改造
寻觅老舍文学世界的艺术源流是不能不注意思想内容方面的。正像老舍所说,欧洲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首先是在思想方面。传统文学的影响同样如是,但它给人的印象是以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即作家们打的是批判传统文化、否定旧文学的旗帜,但在文化和审美意识深处谁也没能摆脱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的制约。面对东西方文化和文学艺术海洋,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汲取,不同的汲取形成了不同的创作个性。老舍的创作个性就在于他对以北京市民为代表的国民性批判和表现。追溯其创作个性的艺术根源,我们首先想到了狄更斯。
老舍操着那支不太灵活的笔叩击文学艺术大门伊始,就自觉地拜狄更斯为师。艺术技巧的借鉴明显突出,如上文所述,思想内容也隐然可辨。狄更斯的艺术视野虽然比较广阔,上至国会议员,下至乞丐盗贼,但最具特色的是伦敦市民社会。在他笔下,伦敦市民社会的形形色色——商人、店员、客栈老板、绅士、流浪汉、囚徒、食利者、高利贷者——都得到突出表现。狄更斯以他那特殊的艺术慧眼看到并表现了“他们满肚子自高自大、矫揉造作,小气暴戾及愚昧无知,”他们的庸俗无聊。老舍从狄更斯那里找到了切入社会、看取人生的思想方法。他像狄更斯描写伦敦社会那样描写北京市民社会,也用与狄更斯相同的艺术笔调表现这一社会的形形色色。正像人们所指认的那样,老舍是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市民社会的各色人等,风俗人情,生活命运,文化心理在他笔下都得到出色的表现。把两位大师笔下的市民形象加以对比就不难发现,除了民族差异的某些规定性之外,他们有不少相似之处。你可以说老舍的艺术视角和艺术表现是由他的生活经历和艺术修养决定的,但是,你却不能排除狄更斯的影响。随着老舍阅读视野的扩大,他的借鉴也由“单一”走向“综合”,进而走向“化合”。就表现市民社会的灰色生活而言,影响他的还有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而在“决定”因素中,内容是复杂的,影响也是多重的,中西兼备,东西杂糅。他认知狄更斯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东西方文化和文学交融交汇的过程。中国白话小说是交汇的广阔而深厚的思想艺术背景。白话小说在市民社会中产生,伴随着市民阶级的发展而发展,且始终以表现市民阶层的生活情趣和精神面貌为主要内容。对此,老舍非常熟悉,也深受影响。我们固不能说早期老舍的文化心理构成是市民型的,但是,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说,他的美学情趣和艺术追求、他看取社会的眼光和艺术表现乃至思想倾向都带有市民性。正是这样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倾向使他偏爱狄更斯。而当他在狄更斯影响下表现市民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时候,中国古代文学的意识积淀也自然而然地发挥着作用。
但就创作思想影响而言,对老舍影响最大、也是最终帮助他建立创作个性的则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的创作传统。
事实上,狄更斯的影响是直接的,由于民族、时代、国情的差异,这种影响又是有限度的。随着老舍艺术实践的深入,其局限性越发明显;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间接的,却是深厚的;是积极有效的,也是精华和糟粕并存的。且不说“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及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就是那些被视为精华者如吴敬梓及其谴责小说作家对儒林官场的批判也与老舍的创作意图有一定距离。因为他们的艺术重心在中上层,暴露的目的是希望上层改良,悉心向善,老舍则注重下层,目的是唤醒民众的社会和人生自觉。惟有新文学与老舍息息相通。新文学对社会人生的表现和批判,改造社会变革现实的伟大主题均与老舍共鸣交振,启发着老舍的思考,吸引着老舍加盟助阵。他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他接触了新文学,给他以巨大的思想影响,“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⑦,又说,“像啊Q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们简直没法不受他的影响”⑧。他在初涉文坛开始思考社会和人生的时候,就自觉不自觉的接过了鲁迅等人改造国民性的接力棒,在其后的创作中,他持棒前进,直到走完文学创作的整个路程。
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长途跋涉的每一步都印刻着新文学影响的痕迹,也凸显着老舍的个性追求——接力棒传到老舍手里,增添了新的色彩。
批判国民性首倡于鲁迅。其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杂文,都深刻地剖析老中国儿女的精神垢病,警世钟般地告诫社会的疗救者,国民劣根性不根除,中华民族很难摆脱危机走向独立。老舍与鲁迅精神相通但艺术表现不尽相同。老舍习惯于全景式把握和文化检讨。《二马》通过比较中、英两国国民精神现状突出中国国民劣根性。“出窝老”马则仁带着传统文化走进西方文化的重镇伦敦,立即陷于可悲可笑的境地。他愚昧麻木,挥霍懒散,一次次吃亏,被捉弄,被嘲笑,却全然不觉,阿Q式的自高自大洗刷着失败的痛苦和被捉弄的耻辱,东方文化积垢消蚀了他的人格和尊严,愚昧狭隘更早已泯灭了他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自觉。对马则仁,老舍是矛盾的,既愤慨于英国人对他的捉弄侮辱,同时又无可奈何:“在二十世纪文化天平上,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马则仁像狗一样被侮辱捉弄罪不在他,甚至不在于英国人,要对这一切负起全部责任的是古老的民族文化。老舍并没将马则仁丑化,他的一举一动都合乎中国文化规范。通过马则仁,老舍检讨了民族文化,剖析了国民劣根性的根源。这种暴露和发掘在《猫城记》中得到同样深刻的表现。不同的是,《二马》写的是一个“出窝老”,侧重于“纵”的发掘;《猫城记》则是“横”的扩张,笔涉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教育、历史、风俗人情等方面,在此我们看到愚昧、狭隘、畏怯……等国民劣根性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体国民共同的属性。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猫城记》与《二马》也是相通的。在《二马》中,我们曾听到这样的愤言:“民族要是老了,从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在《猫城记》中,愤言成了艺术现实:国民劣根性导致了国家黑暗社会腐败,猫国终于在自身溃烂之后灭亡于帝国主义侵略。老舍以猫国灭亡的悲剧敲响了改造国民、变革现实的警钟——似乎比鲁迅还显得忧愤深广。
时代不断赋予老舍批判的契机。老舍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思考角度,充实批判内容。二十年代末期郭亮被杀引出了鲁迅的《铲共大观》,也引出了阮明被枪毙和大鹰为国捐躯。阮明被杀为老舍提供了批判契机,其议论警世骇俗,入木三分;大鹰捐躯使老舍悲愤不已,他以挤死三位老人、两名妇女将国民的无聊无义暴露无遗。抗战开始后,老舍写《火葬》,而后又写《四世同堂》,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火与血中检讨国民性格。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对国民性格的表现和批判虽曾搁浅,但《正红旗下》这部未完成的巨著的开头几章,充分显示出老舍改造国民性的思考深度和创作意图。老舍的超前之处还在于:他不仅批判了“出窝老”,也敏锐地看到并艺术地表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汇过程中民族性格的新现象。其中,有那些既接受了新文化影响而又背负着传统精神枷锁的半新不旧的不安定的灵魂,老舍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了他们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同时又十分遗憾地表现了他们追求的失败:由于周围习惯势力的制约和自身懦弱,他们往往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如王德“浪子回头”做稳了封建家庭的“奴隶”,如老李在失败后辞职离开北平市民社会逃到乡下,通过他们,老舍不仅批判了国民劣根性,而且表现了劣根性怎样固守封闭的圈子,拒绝新文化,腐蚀新思想,说明改造的艰难;也有东西方文化糟粕孕育出来的怪胎:老张虽然代表十八世纪文化,但他那钱本位的哲学分明是封建积垢与资产阶级拜金主义“媾和”的结果,而代表“二十世纪文明”的蓝小山、小赵、欧阳天风则是洋场恶少和纨绔子弟的混血儿,其它如冠晓荷、瑞丰、王举人等则是封建化了的洋奴。对此,老舍深恶痛绝,揭露了他们的丑恶灵魂,挖掘其赖以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着墨不多,但足以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类人物:他们虽然喝着民族文化的乳汁长大,但留学国外几年,欧风西雨剥蚀了他们的灵魂,成为西洋文化的奴隶,其衣食住行都以外国精神为准则,生活和工作都在中国社会,却全然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对这种失了“根”的精神洋奴,老舍在无情地暴露他们的丑恶灵魂之后,毫不客气地送他们进疯人院(如《牺牲》中的毛博士)。
由此,又表现出老舍创作思想的另一个侧面:传统文化固然有待批判,但精华却是基本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根。现代人既要批判传统文化糟粕,也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吸收世界文化的积极成分,促进民族文化更新。老舍是冷静的,对国民精神的批判与赞扬同时进行。如在《老张的哲学》中,他冷静地表现了被封建伦理道德腐化了灵魂的赵姑母怎样怀着善良的用心把自己的娘家侄女李静送进虎口,暴露了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同时又热情地赞扬孙守备、李应叔父的古道心肠。在《赵子曰》中明确指出“一个民族有一种历史的骄傲。这种骄傲便是民心团结的原动力”。他高度赞扬李景纯为保护天坛古迹而献身的精神。他以创作表明:每一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都是错误的。老舍不仅是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者,也是优秀传统的表彰者,捍卫者。这又显示出老舍改造国民性的另一特点:即他是带着国民性思考改造国民性问题、批判和塑造国民性的。这并不排除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西方的思想武器一到老舍手里就变了颜色,民族化了。西方的人道主义化而成为东方的侠义心肠,求真务实、民主科学等资产阶级思想精华和无阶级革命意识不仅为东方的伦理道德所稀释、所改造,而且道德化了。他拿着道德武器批判国民性,塑造国民灵魂。这就决定了他既不能提出正确的改革社会的药方,也不可避免地对那些貌似健康实则庸俗的国民精神予以过多地赞扬,如狭义心肠、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平天下等传统意识,都在他的创作里找到了栖居处,得到阐扬。他站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交汇点上塑造健康的国民精神,但这种精神却夹杂着亚健康的因素。他所理想的国民并没有超出传统的道德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舍的批判力量和塑造质量。他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摆脱这种局限。这显示着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
质言之,老舍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影响下接过新文化革命的接力棒,致力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他曾超出前人,显示出不同的思考和创作个性。但是,他却没有彻底摆脱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包括某些负面影响。
[注释 ]
①老舍:《我怎样写 〈老张的哲学 〉》,《老舍全集》(第 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 165页。
②长之:《离婚》,载 1934年 1月《文学季刊》创刊号。
③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1944年《抗战文艺》第 9卷。
④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年版,第 83页。
⑤赵少侯:《论老舍的幽默与写实艺术——(评)〈离婚〉》,载天津《大公报》副刊《文艺》第 18期,1935年 9月 18日。
⑥卢那察尔斯基:《狄更斯》,《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 452页。
⑦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载《解放军报》1957年 5月 4日。
⑧老舍:《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老舍全集》(第 16卷),第 581页。
石兴泽(1954-),聊城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石小寒 (1982-),聊城大学讲师。
I206.6
A
1003-8353(2010)04-0098-05
[责任编辑:曹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