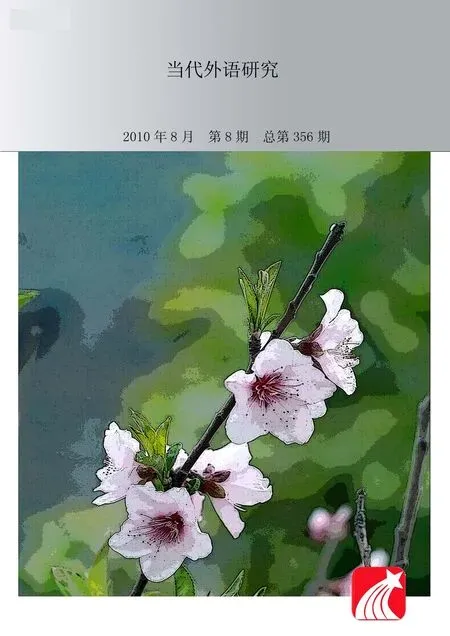赛义德与后结构主义:反拨,还是延续?
——《爱德华·赛义德的遗产》评介
綦 亮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215009)
2009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出版了威廉·斯潘诺斯(William V. Spanos)的新作《爱德华·赛义德的遗产》(TheLegacyofEdwardW.Said)。斯潘诺斯是纽约州立大学宾哈姆分校英语和比较文学特聘教授,美国著名的后现代文艺思想家,曾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存在主义的后现代诗学概念,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最早应追溯到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在《赛义德的遗产》中,斯潘诺斯通过追溯赛义德批评思想的哲学根源,重新思考和定义了赛义德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关系。
1.
赛义德批评理论的归属性,特别是赛义德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理论关系,一直是西方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斯潘诺斯在第一章“赛义德与后结构主义”中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赛义德的世俗批评与其说是对后结构主义的反驳,不如说是它的延续。以《开始:意图与方法》为切入点,斯潘诺斯发现赛义德与后结构主义在两个层面上具有一致性。首先,同后结构主义者一样,赛义德也将本体论作为理论建构的出发点,致力于寻找自启蒙运动以来统治西方的如存在、人性等总体化概念的替代品。其次,通过解构西方对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再现,赛义德和后结构主义者一样,试图从存在的动力空间化和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的哲学和文化传统中恢复对存在的理解。从另一个角度看,后结构主义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同时,同样关注并反思西方对“他者”的平面化和总体化处理,而这又符合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批评精神。因此,在斯潘诺斯看来,赛义德与后结构主义之间更多的是继承、而非对立的关系。
为了更全面和有效地揭示赛义德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亲缘关系,斯潘诺斯在第二章“海德格尔、福柯和‘帝国的凝视’”中阐述了海德格尔与福柯之间的理论关联。考虑到斯潘诺斯的哲学主张,这种分析思路无疑是合乎逻辑的。斯潘诺斯认为,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本体论批判和福柯的谱系学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和互补性。他质疑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等批评话语对海德格尔的偏见和边缘化,反对将海德格尔和福柯完全对立看待,认为这会模糊福柯与赛义德之间的理论关系。斯潘诺斯(2009:28)认为,海德格尔与福柯之间是一种“对抗性的协作关系”(intimate strife)。一方面,认识到西方身份的基础是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是海德格尔和福柯的批评话语的共同起点。另一方面,如以对方的批评框架为参照,海德格尔和福柯的批评话语又显现出各自的缺失:海德格尔对本体论的关注使他无法从社会政治层面分析现代性;福柯对社会政治权力的强调使他忽视了谱系学中的本体论因素(2009:49)。因此,斯潘诺斯主张将海德格尔和福柯的批评话语从看待它们的传统语境中剥离出来,转而将它们置于对方的批评体系中进行考察。
在福柯谱系学的观照下,斯潘诺斯重读了海德格尔的《人文主义信札》,以及海德格尔关于《巴门尼德篇》的见解,挖掘了海德格尔的谱系学论点,即欧洲的哲学和政治身份的起源不是古希腊文化,而是罗马对希腊思想的殖民(2009:29-30)。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扩展了在《存在与时间》中对现代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批判,揭示了现代人文主义话语和民主国家的社会政治实践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共谋性。在海德格尔关于罗马帝国实践的一系列论断中隐含着一种典型的福柯式假设:真理与权力、知识生产与压迫之间具有连续性,并且是共谋的。斯潘诺斯指出,以福柯的谱系学为参照解读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本体论批判,可以清晰揭示现代权力的演化轨迹:从罗马时代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对“他者”的控制,到启蒙时代权力的辖域化、管理和控制的倾向,再到现代社会中以权力的监视为特点的社会政治策略(2009:42)。
因此,再由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批判反观福柯的谱系学就会发现,福柯关于现代性源自启蒙时代的认识论断裂的论断有其局限性。斯潘诺斯认为,福柯所阐述的以监视为特点的现代权力机制早在启蒙时代之前即已存在,它实际上是一种由后苏格拉底希腊哲学引入、并由罗马帝国的知识分子确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由此推断,福柯所借鉴的边沁(Jeremy Bentham)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概念并非代表一种历史断裂,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暂时释放了一直潜伏于西方形而上学思维之中的压迫潜能,并让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话语实践的压迫性规训谱系变得可见(2009:56)。换言之,圆形监狱说明了在后启蒙时代,由形而上学促成的传统全景敞视图解(panoptic diagram)被赋予的多重实践功能。虽然福柯强调全景敞视惩罚机构的重要性,但不应忽视这一事实,即这种古老的图解正被应用于如医学、心理学、阐释学和文学批评等各种机构性话语和实践中(2009:57)。因此,福柯对规训社会的谱系分析具有一种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暗示;他所揭示的不仅是压迫性政治权力的作用,还有海德格尔的批评话语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即在理性和自由的名义下,以殖民人类思想为目的的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态势(2009:59)。而这正是赛义德在《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试图证明的。斯潘诺斯认为,隐藏在《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背后的是海德格尔式的福柯。
2.
以前两章的论述为基础,斯潘诺斯在接下来的三、四章中详细论证了《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对后结构主义思想的继承和拓展。正如《规训与惩罚》中的福柯一样,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同样关注文化和政治话语。但斯潘诺斯(2009:74)指出,赛义德在强调启蒙的帝国和殖民计划的同时,没有回避西方对存在的本体论阐释。在《东方学》中,赛义德很少从本体论的层面阐述西方的知识生产,但在他用于揭示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和政治支配的谱系学修辞中存在大量的形而上学思考(2009:77)。这一点在赛义德分析东方学形成的第一阶段,即古希腊至中世纪这段时期中有明显的体现。在这一时期,西方本体论视角的确立与对东方的“他者”再现是同步的,因此赛义德着重分析了欧洲对东方的早期再现的形而上学基础。拿破仑时代对埃及的军事远征代表了东方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萌发了对东方的科学知识的自觉认同和对东方空间的政治支配,同时见证了从早期的总体空间化,到内在于对人类生活历史性的辖域化中的策略潜能的转变过程。伴随现代性的出现,欧洲看待东方的“文本态度”(textual attitude)转变为切实的东方学,成为科学研究的客体,这是东方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斯潘诺斯(2009:92)认为,赛义德对东方学第三阶段的分析类似于福柯关于现代性的洞见,即现代性中对存在的早期和无效的空间化转变为辖域化的生成性策略。因此,赛义德对构成现代东方学的“想象地域”(imaginative geography)的理解与后结构主义关于西方对存在知识的空间化和辖域化的理解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进入20世纪后,尤其在美国,科学东方学演变成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管理技术,这是东方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在斯潘诺斯看来,赛义德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赛义德谈到了东方学的“生成性”(productive)逻辑的完成;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它即将消亡的征兆。但斯潘诺斯继而指出,如果从海德格尔关于“哲学的终结”这个角度分析,赛义德的矛盾性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的最终实现也意味着它的自我毁灭(2009:108)。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进一步展现了这种似非而是的状态。
相当一部分评论家认为,与《东方学》相比,《文化与帝国主义》的结构零散、不成体系。斯潘诺斯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该书有相当严谨的深层结构(2009:113)。对经典文化作品(包括文学和音乐作品)的解读构成了《文化与帝国主义》深层结构的第一部分。帝国文化对殖民地居民的非存在化处理是赛义德在这一部分中关注的问题。通过解读奥斯汀和吉卜林的作品,赛义德说明,英国的存在与殖民地的非存在之间的对立贯穿帝国的文化话语。因此,赛义德从本体论的角度揭示了小说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共谋。斯潘诺斯认为,赛义德对叙事艺术与西方帝国主义实践共谋性的揭示背后有着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从广义上讲,赛义德对文化生产与帝国主义实践之间关系的分析处处暗含他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赛义德对从19世纪到20世纪现代主义文化生产的分析构成了他对现代帝国文明谱系分析的第二阶段。赛义德的分析表明,英国帝国主义的逻辑在现代主义阶段、也就是其鼎盛时期自我消解,而这又类似于海德格尔的观点,即西方的存在——神学传统的帝国形而上学哲学在技术现代性中最终实现并终结。赛义德对后殖民阶段的分析构成《文化与帝国主义》结构的第三部分,帝国主义的总体化逻辑在这一时期最终完成并消解。伴随这种完成和消解过程的是帝国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演变:在现代主义时期,帝国的“他者”只是作为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总体意象侵犯帝国的意识,而在后殖民时期,帝国的“他者”开始以身体的形式困扰帝国,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在斯潘诺斯(2009:136)看来,《文化与帝国主义》的结构是反结构的,是一种反叙事(anti-narrative)或对位(contrapuntal)的过程,拆解了传统的西方小说和话语叙事,它们的二元逻辑,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帝国主义的阐释假设。通过将西方对存在的再现理解为一种从本体论到文化(叙事)、再到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实践之间的稳定接替,将西方的终结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理解为从虚无或无法再现之物,到反叙事,再到挑战西方全球霸权的大量移民和流浪者的稳定接替,赛义德尝试将帝国的“他者”表现为真实的、物质的存在。在此意义上,赛义德克服了海德格尔和早期后结构主义者仅从本体论和语言方面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局限(2009:139)。
3.
赛义德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批评家,还是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是西方批判性人文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斯潘诺斯在第五章中重新解读了赛义德的人文主义立场。赛义德的人文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中。在这本演讲集中,赛义德划清了与以福柯为代表的“反人文主义者”(anti-humanist)之间的界线,以批评世俗性为出发点,从政治性和批判性两个维度重新定义了人文主义。在赛义德看来,“反人文主义”姿态是让后结构主义批评丧失世俗性和政治性的根本原因。赛义德的人文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者的“反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主要体现在他们看待人类能动性的态度上。“反人文主义”,特别是福柯的谱系学否定主体的权威和建构功能,批评矛头直指作为理性主体的“人”的概念,是一种反总体化和本质化的批评话语。而赛义德受教于维柯,始终强调主体的重要性,坚信人类具有形成知识的能力,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
事实上,赛义德的人文主义观是一个极具有争议性的概念。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阿贾兹·阿赫迈德(Aijaz Ahmad)和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等著名学者都曾从不同角度批判过赛义德的人文主义立场。R.拉德哈克瑞希南(R. Radhakrishnan 2008:117)甚至认为萨义德的世俗人文主义是“非常个人的,是一种个人癖好”。也有论者从正面评价赛义德的人文主义观。美国《批评探索》杂志主编汤姆·米切尔(转引自陶家俊2008:318)就将赛义德的人文主义立场称为“世俗占卜”。在为《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撰写的前言中,阿基尔·比尔格雷米(赛义德2006:5)指出,赛义德的人文主义可以让我们把他的知识遗产“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哲学背景中”考察。
而斯潘诺斯正是从哲学的高度相对客观地分析了赛义德的人文主义思想,阐述了赛义德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理论一致性。他认为,就拒绝接受构成西方文明史的对存在的形而上学阐释,并继而颠覆身份与差异的二元对立而言,后结构主义理论同样建构了一种关于自由意志和人类能动性的激进观点(2009:185)。因此,赛义德的人文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反人文主义”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斯潘诺斯(2009:166)指出,后结构主义者看待人类能动性的态度可能太过悲观,但考虑到知识-权力关系在西方社会中的刻写,赛义德也许过分乐观了。最后,斯潘诺斯将赛义德的人文主义置于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的宏观政治语境中加以考察,认为既然美国的帝国主义视角有其深厚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根源,那么如果人文主义不像早期的后结构主义者那样审视自己的谱系,便无力抗拒美国支配世界的欲望(2009:196)。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斯潘诺斯追忆了与赛义德的交往,以及赛义德对自己的世界观和学术观点的影响,为这次理论之旅平添了一丝温情。作为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赛义德以其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知识分子的良知给世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和批评资源。如何梳理赛义德的“遗产”,从而更好地继承,斯潘诺斯无疑作了一次有益且有效的尝试。
Radhakrishnan, R. 2008.History,theHuman,andtheWorldBetween[M].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爱德华·赛义德.2006.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M].北京:新星出版社.
陶家俊.2008.思想认同的焦虑:旅行后殖民理论的对话与超越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