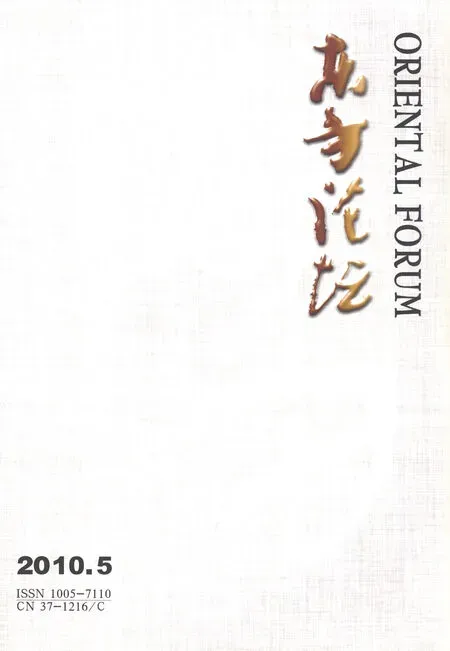《世说新语•贤媛》女性人物形象浅说
梁 克 隆
(中华女子学院 公共教学部,北京 100101)
《世说新语•贤媛》女性人物形象浅说
梁 克 隆
(中华女子学院 公共教学部,北京 100101)
《世说新语•贤媛》中的女性形象,或为具高风亮节、品格也敦厚纯粹之“贤”女子,或为有远见卓识、气象亦超凡拔俗之“伟”女子,或为理性、果敢并聪明伶俐之“奇”女子,或为刚强、正直且傲岸不屈之“烈”女子。这些女性用她们庄严的生命意志与澎湃的诗情强烈地宣示出这样的真理:虽然封建社会给予女性以极不公正的对待,使之遭遇了悲惨、酷烈的命运,蒙受了巨大的痛苦,但她们依然顽强地生活和奋斗着,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显示出永恒的生命活力。
《世说新语•贤媛》;女性形象;人格魅力
作为“轶事小说”的杰出代表,《世说新语》以其生动简练的文字叙述、细致入微的刻画描写、丰满鲜活的形象创造以及故事本身的哲理、隽永而著称于世。虽然《世说新语》所记载的名人言行大多为片言只语和琐事常行,可由于深涉社会上层之间的政治斗争与当时的风俗习尚、思想文化、艺术文学的缘故,所以能够比较鲜明地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幻。特别是《世说新语》还别开生面地创立了《贤媛》这一门类,为那些“有母仪”与“才智”①余嘉锡说到《贤媛》时强调:“本篇凡三十二条,其前十条皆两汉、三国事。有晋一代,唯陶母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智著……”参见《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63页。的女子树碑立传。尽管《贤媛》的篇幅不长,其记录者的立场、观点也没有完全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但是,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和对待这些女性形象本身,已经是“善莫大焉”了。第一类为具有高风亮节、品格也敦厚纯粹之“贤”女子,第二类为具有远见卓识、气象亦超凡拔俗之“伟”女子,第三类为具有冷静理性、果敢并聪明伶俐之“奇”女子,第四类为不卑不亢、正直且傲岸不屈之“烈”女子。如此这般的女性形象,既表现出她们自身的聪明睿智,也表现出传统女性的理想情操。
(一)以陶母为代表的第一类女性。她们所表现出的母爱,像婉转的溪流一样自然而平静地流淌。她们不仅自己认真实践着所信奉的道德信条,而且把这种美好信条浇灌到子女的心田,演绎着民族精神的世代相传。如《贤媛第二十》载:
一、《世说新语•贤媛》中的四类女性形象
《贤媛》列《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之第十九,有故事三十二则,计两千四百余字,不属于鸿篇巨制;且每则故事的字数也不多,最多的不到二百字,最少的仅二十九字。《贤媛》中的故事,尽管表现得都是女性,却各有不同,各具特色。仅就这些人物的形象划分而言,大略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鲊饷母。母封鲊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②此节所引《贤媛》的文字与以下所引的《贤媛》文字,以及《言语》《轻诋》中的文字,均出自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故只标篇目,不再一一注明。
这位“陶公”就是大诗人陶渊明的曾祖,即后来“剑履上殿”[1](P1773)的东晋重臣陶侃。他早年担任“鱼梁吏”这一地方小官时,曾把自己管理范围内的“坩鲊”(一种经过精制加工、类似“鱼罐头”的高级食品)送给母亲品尝,陶母在看到儿子所送礼品竟然是“官物”之后,不仅原封不动地予以退回,而且还批评儿子“乃增吾忧”。表面看,陶侃把“稀罕之物”献给母亲是为了尽孝,他无疑是个孝子,因而,陶母的做法似乎颇悖人情;可实际上,陶母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她这样做是为了更长远的目标,即培养一个真正“仕人”的道德品质。
传统的主流社会,对于人生终极追求向来有所谓“三不朽”的说法,即“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2](P1979)。同时,对于任何一个怀有“修齐治平”理想的人来说,他的抱负又是与其品格修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3](P4)这种不知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的人生理想与自我修养模式,自然也应是陶侃之类士人的本色追求。陶母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批评陶侃的。尤其可贵的是,她把子女的品格养成放置在这样一种既崇高又平凡的高度上时,其作为母亲的绝大精神力量也就彰显无遗。正是这种绝大的精神力量,使陶侃在凭借自身道德规范处世、行事的同时,也牢记母亲教诲,从而使其理想追求与品格修养变得更加坚实有力。陶母所代表的这种真切的“母亲教育”,也是封建社会中一种传统而有实效的家庭教育,它深入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道德水准,也维系并推动了整个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陶母在对儿子赠酢问题上的“坚决”是有原因的,她曾为儿子的 “仕进”付出过代价: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髢,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贤媛第十九》)
为了儿子的前途,陶母不惜剪长发以换米,割屋柱以为柴,毁草垫以为马草,殷勤而周到地接待了时为名人的范逵,从而为陶侃将来的仕途发展铺平道路。陶母称得上是“家庭励志”的楷模,她的身上充溢着“母仪”的光辉。而她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的魄力和胆略,一方面是母爱的力量,她希望儿子能够尽快地步入仕途、有所成就;另一方面则源自传统教育“薪尽火传”的激励。她的这种家庭教育方式庄严地延续了民族教育的传统,这种传承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特有的“家庭励志”文化现象①从欧阳修、岳飞,甚至到朱德、老舍、胡适等人,都不难看到母亲“家庭励志”教育的影响。。
如果说陶母的故事注重的是品格的个人修养层面,“赵母教女”的故事注重的则是品格的社会伦理层面:
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贤媛第五》)
赵母“甚勿为好”的告诫实际上是一种激励,也就是说,你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一般的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好上加好!因为传统社会对“之子于归”是寄予厚望的,是将“她”与他的家庭乃至家族的繁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要“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4](P50);如此艰巨的任务,只有做得极好、最好才能够完成!旧时的社会家庭存在方式,要求“新妇”应当具有使小家庭和大家族都能够兴旺发达的能力。尽管封建社会没有给广大妇女以应有的地位,但“慎勿为好”的嘱托还是为妇女在传统家庭所起的特殊、有效作用进行了极为恰切的诠释,尽管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所进行的诠释。
(二)以谢道蕴为代表的第二类女性。她们志向高远,学识修养也鲜明突出。尤为难得的是,她们显示出的人格尊严与道德学问非但普通女子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就是相当的士子才人亦无法与之比肩。如: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贤媛第二十六》)
谢道蕴的悲剧在于她的“曲高和寡”:一方面是世人对其丈夫王凝之的推许,他出生于贵族之家,其父为大书法家、右将军王羲之,谢氏叔父谢安认为他“人才亦不恶”,即有一定的才华;而另一方面则是谢氏的“大薄凝之”,即非常地看不起自己的丈夫,并且叹其与谢氏群从有“天壤”之别。实际上,并不是王凝之有多少缺点,只是他无法与谢道蕴相提并论!谢道蕴这般的才女,不仅王凝之不能与之抗衡,就是学问再大、更为能言善辩的士子亦多不是其对手:
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蕴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鄣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1](P2516)
在小叔子王献之理屈词穷之际,谢道蕴却能扭转被动局面,使“客不能屈”,获得论辩的胜利。谢道蕴确实是天才纵横的学问家和辩论家!
天资聪颖固然使得谢道蕴卓然独立,难能可贵的是,她并没有自恃其才,而是始终坚持后天学习。正因为如此,她对“都不复进”的兄弟极为不满,甚至颇为尖刻地批评他们,就连颇具雄才大略的谢玄也不能幸免:“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贤媛第二十八》)但谢玄不以为意,依然“绝重其姊”(《贤媛第三十》)。
谢道蕴不仅以其道德文章获得了世人的称赞,还以她处变不惊的勇气和胆识赢得了必欲置其于死地的敌人的异常敬畏:
及遭孙恩之难,举厝自若,既闻夫及诸子已为贼所害,方命婢肩舆抽刃出门,乱兵稍至,手杀数人,乃被虏。其外孙刘涛时年数岁,贼又欲害之。道蕴曰:“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其如此,宁先见杀。”恩虽毒虐,为之改容,乃不害涛。[1](P2516)
晚年的谢道蕴虽然历尽坎坷,却风采依旧,仍然能赢得士人们的尊敬:
太守刘柳闻其名,请与谈议。道蕴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于帐中,柳束修整带造于别榻。道蕴风韵高迈,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涟,徐酬问旨,词理无滞。柳退而叹曰:“实顷所未见,瞻察言气,使人心形俱服。”[1](P2517)
谢道蕴是以其天才秀逸的奇绝而载入史册的,山涛妻韩氏则以其善“知人”而名垂千古: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贤媛第十一》)
韩氏虽然没有谢道蕴的才华,但她的眼光、见识,特别是“知人”的本领则远非常人所能比拟的!对嵇康、阮籍二人,韩氏能够一睹而辨英才,其眼力实在不凡。倘若能够也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相信韩氏一定会有超过山涛的建树。因为“知人”是一切用人智慧的前提,没有“知人”,也就谈不上善任、多谋与善断了。
(三)以许允妇为代表的第三类女性。她们头脑灵活,沉着理性,既善于分析判断,又富于逻辑推理,且不乏辩驳能力。或许她们并不都是聪明绝顶,但其审时度势的才能、机敏与伶牙俐齿都使其显得卓尔不群。如许允之妻: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 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贤媛第六》)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于是乃释。……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云:“勿忧,寻还。”作粟粥待,顷之允至。(《贤媛第七》)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曰:“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贤媛第八》)
以上三则故事都是围绕着“所乏唯容”的阮家“丑女”而展开的。许允娶妇一事中,阮氏女凭借对许允心理的揣摩、把握及其富于进攻性的口辩和过人的聪明才智,不仅摆脱了一进门便被冷落的尴尬地位,而且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展现了自己的人格魅力。许允“多用其乡里”与“为晋景王所诛”二事则更多地表现了许允之妻处理突发和重大事件时的理性与果断:前者,她把握住“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的基本规律,告诫丈夫须实事求是地“讲道理”,因为历来的所谓“明君”都特别相信自己的“聪明头脑”,一味求情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后者,许允妇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能够清醒地预见到“无豫诸儿事”,因为他们“虽佳”,但“才具不多”,再兼“少问朝事”,自难成为晋景王之忧,从而指导诸儿远避灾祸。或许因为“许允妇是阮卫尉女”的缘故吧,她了解政治上的种种“玄机”,因此才能够做出如此正确的判断。但她清醒的政治头脑和超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不能不使人敬佩。
谢夫人是《贤媛》中记载的又一个头脑灵活、善于推断的典范:
谢公夫人帏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暂见,便下帏。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贤媛第二十三》)
谢夫人的所作所为带有非常的“精警”特点,她不允许、也不创造谢公犯“错误”的机会!或许她真的略有“醋意”,但其“醋意”却如此生动别致、饶有兴趣:
谢太傅刘夫人,不令公有别房。公既深好声乐,不能令节,后遂颇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达此旨,共问讯刘夫人,因方便称《关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讽己,乃问:“谁撰此诗? ”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
也。”[5](P695)
这样的理解和回答,虽有过“妒”之嫌,但其敢恨、敢爱的性格与绝妙的行事风范,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四)以卞太后为代表的第四类女性形象。她们果敢坚决,既有疾恶如仇的朴素情感,也有从容不迫的忍耐坚强。她们体现了传统女性的善良与正义,也反映了传统女性“柔弱胜刚强”的力量。如: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贤媛第四》)
“有母仪德行”的卞太后①关于卞太后,《魏书》曰:武宣卞皇后,琅邪开阳人,以汉延熹三年生齐郡白亭,有黄气满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问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纳于谯。性约俭,不尚华丽,有母仪德行。本来也是为文帝病痛焦急不已的,《论语》即云“父母,唯其疾之忧”[3](P55),然而,当她看到其“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并且又是武帝刚刚去世(“正伏魄”)时过来的,便不肯前去,并愤怒斥责文帝禽兽不如的行径,甚至直到文帝死,她也不肯去看上一眼。这鲜明的憎爱之情真切反映了卞太后的道德原则和善良天性。汉民族一直拥有严格的伦理道德规范,并且将这种伦理道德规范直接应用于家庭事务,因此,日常生活中便多了许多无形的约束,其中对儿子与相当于“母亲”辈份的父亲的“爱幸者”之间的约束尤为严格。这也是汉民族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卞太后不能容忍文帝超越伦理规范的卑鄙丑恶,她痛斥文帝行径的言行不仅反映出其“有母仪”的美德,而且就像“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一样反映了宫廷妇女的善良和美好!
同样反映了宫廷妇女的正义观的还有王昭君:
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贤媛第二》)
这个故事反映了正直者的悲剧。王昭君自身“姿容甚丽”,“志不苟求”,然而却被“毁为其状”,以致遭遇冷落和排挤,只落得远嫁匈奴的悲惨命运。王昭君因坚守信念而展现了一个正直者的悲剧故事,李丰女展现的则是刚强女性不屈的人格魅力:
贾充前妇,是李丰女。丰被诛,离婚徙边,后遇赦得还。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听置左右夫人。李氏别住外,不肯还充舍。郭氏语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刚介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去。”郭氏于是盛威仪,多将侍婢。既至,入户,李氏起迎,郭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贤媛第十三》)显得非常完美,如女娲补天的乾坤重造,如精卫填海的不屈不挠,如嫦娥奔月的潇洒奔放等等,她们所反映出的创造精神与永恒、博大之爱,都犹如甘美的清泉,滋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长。尽管如此,女性及其艺术形象的诸多特点,尤其是具体的情节与细微的风貌,总不免略带遥远与抽象之嫌,缺乏真切感人的鲜活,甚至有些还有着相当的变异与弱化。这种情形随着魏晋思想解放的深入进行,特别是随着当时人们对两汉以来传统礼教拘束所产生的反叛开始有所变化。于是,主张放任性情、争取身心自由的呼声逐步成为一种潮流,并且上升到只有“这种生活态度是符合自然原则的,也是符合人性的”[6](P178)程度。这充分反映出人
郭氏本想在“盛威仪,多将侍婢”的气势下给因父罪受牵连离婚后复返的李氏一个下马威,但“刚介有才气”的李氏早已使她产生一种潜意识里的自卑、畏惧心理,因而当亲睹李氏的超人气质之后,她竟不自觉地屈膝跪拜。郭氏的自卑在于其缺少内容与形式都充溢着美的气质精神,而曾“作《女训》,行于世”的李氏,却拥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素养与内在的精神魅力。们对自身认识的深化程度及其探索精神,因而,无论是其内心追求、还是其理想憧憬,都表现多元化的趋向。这也就是说,当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人”这一具体概念和意义的时候,外在的男女性别上的差异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对人本身气质的关注,特别是对奇才异能、卓然独立的肯定已经足以博得赞许。因此,如果说《世说新语》是以人格美的“风流”①见冯友兰《论风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三松堂学术文集》第609-617页)。按冯先生的说法,构成真风流有四个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作为主要标志而存活于中
二、《世说新语•贤媛》中女性形象的文学意义
《贤媛》中除去以上四类女性形象之外,像王晋母亲的品德、王武子母亲的智慧与人生经验以及“东海家内,则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内,范钟夫人之礼”的大度从容,也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以上四类女性人物形象,无疑是最具代表性与最高存在价值的。她们集真、善、美于一身,并且还体现着才智、能力、勇敢与坚强等诸多的美德。这就使她们不但在“晋之妇教,最为衰敝”的时代里具有绝大的意义,而且也在更高的层面上表现出传统女性形象的典型性格。正是这些典型性格的作用,使她们一方面充实了中华民族典型形象画廊中的角色系列,另一方面又作为具有中华民族美德精神的形象而光照千秋。
《贤媛》中的女性形象,首先是作为鲜明而真切的正面形象而出现的,这应当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不论是在“蒙昧”时代的群体生活中,还是在当时的家庭生活中,女性及其艺术形象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发挥出无与伦比的作用。但是,在长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历史传统中,女性及其艺术形象的特质往往被修改,或者被轻视。神话传说中的有些女性艺术形象确实国文学史的话,那么《贤媛》无疑就是以“褒扬之意比较明显”[7](P190)而登堂入室的。
其次,《贤媛》中的女性艺术形象一方面表现出理想女性形象的精神追求,一方面又体现和折射出中华民族思想上的显著特点。从理想女性形象的精神追求来看,所谓“乾,天也,故称于父;坤,地也,故称于母”,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就应当是平行、平等且相辅相成的,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反映“一阳一阴之谓道”的本来意义。然而事实上,男女之间的关系已演化为极不合理的从属、依附关系,从而造成“女娲”在现实社会中没有自己地位的极端现象。而女性所要争取的无非就是作为“阴阳”存在的平等和谐以及真正的“人”的尊严,然而,不论是在以前,还是在当时,女性的这一理想都没有实现。尽管一直没有实现,女性的追求却始终没有停止。《贤媛》中的这些女性,不论是“贤”、“伟”,还是“奇”、“烈”,她们所表现出的自由、平等意识和独立尊严都闪烁着理想追求的光辉。另外,从体现和折射出中华民族思想上的显著特点来看,所谓“不离现实而别求天国,亦即于现实生活之中而具有超脱意趣,未尝沉溺于物欲”,“所以思想极表现一种沉深、雄厚、伟大、闳肆、创造、前进气息,勤奋、勇猛、而又稳重、宏阔”[8](P156)。而早期中国思想上的诸多特点,又无不表现在《贤媛》中的女性形象上。尽管她们不是思想家,但她们的言行都带有“思想者”的光环和“践行者”的悟性,呈现出一派天章云锦的自然气象。
不仅如此,《贤媛》在叙事和人物性格描写上的艺术特点,也异常鲜明而突出。首先,是飘逸潇洒的襟怀风致。所谓“记言则言远冷俊,记行则言简瑰奇”[9](P38),指的固然是文字上的简洁清俊,同时指的也是这种富于浪漫的色彩与气息。像“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疏朗明快,气韵生动;像“桓车骑不好箸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催使持去。妇更持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含蓄隽永,富于哲理;像“王汝南少无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遂为王氏母仪。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以此知之”,奇特不俗,饶有兴趣等,无不浸透着浪漫的特性与潇洒不羁的精神。尽管随着故事的展开,或者因刻画人物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但浪漫的气息则是一以贯之的。这不仅使人物的性格变得更加丰满,还使故事的发展更符合逻辑规律。这或许就是“使我们今日能亲见魏晋南北朝时代‘清谈为经济,放达托人生’的一批活灵活现的人儿”[10](P65)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对比手法的运用。《贤媛》三十二则故事的描写刻画中,运用得最多,也最成功的艺术手法,就是对比手法。这里有善良与丑恶的对比(卞太后、王昭君与魏文帝、画工及灾难社会),有天才纵横与学问平庸者的对比(谢道蕴与王凝之及那些辩论者),有母仪的光辉与才智胜利的对比(陶母、赵母与许允妇等),有柔弱战胜刚强的对比(李势妹、李丰女与郡主、郭氏)等,正是这些对比手法的运用,编织出“贤媛才女”活动的一片天空,也成功展示出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如王经母亲从“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的规劝,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耶”的大义凛然,前后的对比,显示出她的刚毅坚强。又如,许允妇从其结婚时的“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的聪明伶俐,到许允初次犯事时诫其“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的机智勇敢,再到最后的“早知尔耳”及“无豫诸儿事”的智慧旷达,反映了她的“成熟”。也正是这种“成熟”,使一个智慧与天生极富政治才具的形象脱颖而出。
再次,是人物语言的恰如其分与准确传神。《贤媛》中的女性,无论是“贤”“伟”“奇”“烈”,她们的话语都极符合人物的身份。像陈婴母亲的“不可”“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既表现出老人家的谨慎与见识,又不乏普通“老妇人”的退缩和局限。又如表现王武子母亲的言语中,“诚是才者,其地可遗,然要令我见”一语极为精到地展现了其贵族出身的特点、主持家庭大事的气派与母亲的威严;而“此才足以拔萃”、“必不寿”等语不仅有掷地有声的效果与架势,还表现出王夫人的性格特点。另外,劝谏“由新而旧”的机智,“恐伤盛德”的绵里藏针,“不意天地之中,乃有王郎”的失望和慨叹,都令人咀嚼再三而余意不绝。
《贤媛》中的女性形象,用她们庄严的生命意志与澎湃的激情,明确而强烈地宣示着这样的真理:虽然封建社会给予女性以极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是悲惨酷烈的命运,使之蒙受巨大的痛苦,但她们依然顽强地生活与奋斗着,宛如铿锵的玫瑰,绽放出绚烂而美丽的花朵。
《贤媛》中的女性形象以其纯正的品格、超凡的器识、高雅的趣味以及刚毅果敢、沉静淡定的独特人格魅力存活于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殿堂之上,并给予后世以积极的影响。
[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孔颖达.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朱熹.四书集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8]张岱年.张岱年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
[9]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0]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责任编辑:潘文竹
An Analysis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Worthy Beauties of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LIANG Ke-long
(General Courses Section,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In Worthy Beauties of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the various outstanding women revealed such a truth with their will of life and strong poetic feelings: in spite of the unfair treatment and wretched fate they suffered, they lived and struggled stubbornly, their life shining forever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Worthy Beauties; female image; charm of personality
book=52,ebook=95
I207
A
1005-7110(2010)05-0052-06
2010-01-23
梁克隆(1955-),男,北京人,中华女子学院公共教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