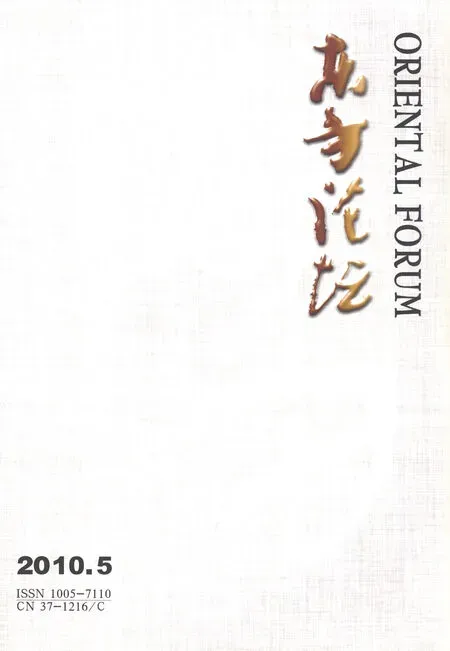《聊斋志异》异类仙化现象研究
王 海 燕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266071)
《聊斋志异》异类仙化现象研究
王 海 燕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266071)
与之前的志怪小说相比,《聊斋志异》对异类形象的态度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价值偏向:异类仙化倾向。这种异类仙化倾向源自《聊斋志异》对民间传统中狐仙观念与唐以来文学中仙妓合流意识的继承,更出自蒲松龄对异类观念的创新与道德理想的寄托。蒲松龄对聊斋中美的异类女性的褒美乃至“仙化”,是其理想人性追求及浪漫诗心的体现。
异类仙化;狐仙观念;仙妓合流;道德讽谕;浪漫诗心
《聊斋志异》以“异”名篇,记载了大量神鬼怪异故事,其中以异类化为美好女子与人间男子恋爱故事最具代表性,也最具成就。这类小说,通过对异类形象的“仙化”描写进行褒美,在审美价值与道德判断上都表现出与传统志怪小说迥异的倾向。这类小说皆具寓言寄托性,有着对现实生活的道德讽喻意义,也包含作者对于人性的诗化理想。“异类”的概念,顾名思义,固然指非人类,神仙、鬼、妖,皆可网罗其中;然而中国志怪小说中的“异类”,特用以指精怪类,或可包含鬼类。本文主要采用后一种定义,这主要出于研究方便,也大体符合《聊斋志异》中异类观念。①聊斋中除少数仙人自称异类外,异类的概念主要指妖异类,例如:《青凤》中有“望无以非类见憎”之语,《胡氏》中亦云“实无他意,但恶其非类耳”,《青蛙神》则曰“君家尊乃以异类见憎”,等等。又,“身为异物”也是一切来到人世的鬼的遗恨,如《宦娘》。本文所有引文均出自《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一、《聊斋志异》中的异类仙化现象
神、仙、鬼、怪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重要题材类别。曹丕《列异传》是续补《列仙传》之作,继神谱之后,续以鬼怪,以大批鬼怪题材开辟了一个鬼蜮的世界,其神仙、鬼、怪三大群体,奠定了中国神怪小说的体系。此后,《搜神记》则把神、仙、鬼、妖、怪、异(人间怪异故事)综合起来,具有集大成的意味。神仙故事、鬼故事和妖异故事,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主要内容,并大体框定了后世志怪小说的题材范围。《聊斋志异》继承了《搜神记》题材的综合性,以“志异”名篇,兼指多端。六朝是神仙故事衰落、鬼怪故事大盛、妖异故事勃兴的时期,妖、精、怪,或称妖怪、精怪、妖精,是六朝志怪反映最多的对象之一,妖异题材多样,构成了鸟、蛇、獐、蚁、鱼、鳖等故事系列,以狸精系列最为典型,大约当时人们持妖怪变化观念,而狐被视为善于变化,其智通灵。《玄中记》较早出现狐妖的描写:“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1](P458)这里的妖狐记载虽没有具体情节和形象,但它对狐妖基本特性的勾划,为当时和后世小说狐妖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基础。后世的狐精形象可谓万变不离其宗:能变形,善蛊惑,与人类交接,年代愈久则道行愈高。《搜神记》载妖怪故事极多,主要集中在今本卷一七至一九;狸精故事有“阿紫”、“燕昭王墓斑狐”、“吴兴老狸”、“宋大贤”等多则。“阿紫”确立了女狐媚惑善淫的类型特征,对后世狐妖故事产生了深远影响。[2](P419)由于志怪小说中妖异类女性多寄托了人们的性爱幻想,所以,异类形象以女性为多。似乎早期志怪小说对不同物种的异类形象并不持差别成见,兼且由于魏晋六朝偏美的审美观念,异类化人大多为美貌女性。但在宗教领域,“妖精害人”的观念深入人心,影响所及,志怪小说中的妖虽有灵性,却多是害人的恶物。美丽的外表与危害人类的恶行,赋予妖异形象以一种变态的不和谐的美。内外皆美的异类,到唐传奇中始出现,如沈既济《任氏传》中的美丽专情而薄命的狐女任氏。总体来说,在历史上相当长时期人们秉持异类害人观念,以往小说中的异类形象主要体现为妖精害人和妖异化描写,在审美价值和道德判断上,是批判和否定的,一直到《封神演义》和《西游记》,还认为妖精害人,都该杀却。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延续了对于异类美的外型的塑造,其中的异类女性形象可谓美不胜收,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它出现了新的审美价值偏向:异类仙化倾向。以狐女形象为例:
视其女,嫣然展笑,真仙品也。——《小翠》
略睨女郎,娥眉秀曼,诚仙人也。——《黄九郎》
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青凤》
俄见一少女,经门外过,望见王,秋波频顾,眉目含情,仪度娴婉,实神仙也。——《鸦头》
这种仙化倾向,在其他异类形象描写上也表现得颇为一致:香獐精花姑子“秋波斜盼,芳容韶齿,殆类天仙”(《花姑子》);鬼女宦娘“貌类神仙”(《宦娘》);公孙九娘“笑弯秋月,羞晕朝霞,实天人也”(《公孙九娘》);聂小倩“或请觌新妇,女慨然华妆出,一堂尽怡,反不疑鬼,疑为仙”(《聂小倩》)。
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划分三界,就是神仙所在的天界、鬼魂所在的幽冥界(又叫阴司)以及妖精所在的妖界。而道教观念中,仙、人、鬼被称为宇宙三界。齐梁道士陶弘景在其《真诰》中称:“上则仙,中则人,下则鬼。人善者,得为仙,仙谪之者更为人,人恶者更为鬼,鬼福者更为人。仙之谪者更为人,人恶者更为鬼,鬼福者复为人,鬼法人,人法仙。”[3](P495)意思是,宇宙万物分三个层次,最高的一个层次是仙,中间是凡人,等而下之的是鬼;人行善修福可以上升为神仙,神仙受到罪罚贬谪人间就成为凡人,凡人作恶降为鬼,而鬼积德行善就可复生为人。可见,三界地位高下泾渭分明:仙是道教观念中最高的境界,也是民间传统中的最高的境界,是高于人类的,妖、鬼则是低等的“异类”。因此,《聊斋志异》将妖、鬼等低于人类的异类形象仙化,其观念与道教和民间传统显然已经大异其趣,标新立异,值得探讨。
二、传统狐仙观念与文学中仙妓合流意识
在民间传统中,狸精俗称“狐仙”,被认为是智慧,善变的,神通广大。《聊斋志异》中,一些篇章仍遵循了传统“狐仙”观念,如《上仙》篇直呼“狐仙”;《张鸿渐》中的狐女舜华自称“我狐仙”。再如,《董生》中写书生冬夜归斋,以手探被,则腻有卧人,“急火之,竟为姝丽,韶颜稚齿,神仙不殊。狂喜,戏探下体,则毛尾修然。大惧,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问:‘君何往?’董益惧,战栗哀求:‘愿仙人怜恕。’女笑曰:‘何所见而仙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这里,董生已知女为狐,称其为仙,实是出自民间约定俗成的“狐仙”观念。另外,《胡相公》篇称狐“仙人”,写狐有灵,“凡有所思,无不应念而至”;《武孝廉》、《郭生》、《狐妾》、《丑狐》、《狐女》等篇也都大写狐之法术和灵性,以之作为小说主要目标。自然,还有不少篇章仍保留了“狐祟人”与妖精害人的描写,如《贾儿》、《捉狐》、《伏狐》等可为代表。在《聊斋志异》几乎所有的异类小说中,异类都会展现其特异功能与灵性,正如鲁迅先生所谓“偶现鹘突,知复非人”[4](P216),例如白秋练有术预知物价,莲香、花姑均精通医药等等;类似地,《猴静山》中有“猴仙”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方面,更多体现了聊斋对民间习俗观念的尊重和沿袭。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指出,在唐代以来的诗文与小说创作中呈现仙妓合流倾向。六朝道教禁欲意识下,女仙形象沦为仙道思想宣传家,情感缺乏而失去女性魅力。而唐代,在思想开放与文人狎妓经历的双重作用下,诗文与小说中的仙女与妓女呈现合流关系,大致可分为仙妓与妓仙两类:前者是把妓女比作或称作仙女,在这些妓女身上体现出一种超越于封建社会现实人生的仙气,有的还采用妓女死后仙化这一模式;后者写妓化的仙女及其风流韵事,仙女成为妓女的代称。[5](P79)在此影响下,唐以来的遇仙小说经历了一次质的变异,以致明清时出现了众多艳情小说和有艳情描写的其他小说,其描写经历了从“遇仙”到“遇艳”的变异,女性形象的拟仙化成为明清艳情小说的一个普遍特征。所谓拟仙化,是指女性形象完全脱却仙的外衣,而仅仅以“天仙”“仙女”来比拟女性的美貌与风韵。由于艳情小说中的女性都是荡妇淫娃,都是纵情交欢的性开放者,因此,这种拟仙化便表现了一种对女仙性色彩的暗示和认同。总之,遇仙小说在明清时期向着艳情化方向发展。[5](P253)这或许也能部分地解释聊斋爱情题材小说中异类仙化现象的成因。这种仙妓合流观念,在《聊斋志异》艳情故事中也有部分遗留,这类故事有《董生》、《甄后》、《伍秋月》、《鸦头》、《葛巾》、《香玉》、《章阿端》等。如董生看到被中美女“神仙不殊”的第一反应是妓,因此才有“戏探下体”的举动;《甄后》的情节构成“何处天仙,未曾拜识。……曲尽欢好”,显然是在仙妓合流观念下产生的。另外,《彭海秋》中写彭好古眼中的妓女娟娘“年二八以来,宛然若仙”,《章阿端》中卫生见鬼女阿端“对烛如仙,渐拥诸怀”,《伍秋月》中王鼎梦醒后见“少女如仙,俨然犹在抱也。虽知非人,意亦甚得;无暇问讯,直与驰骤”,这些描写均应是唐人小说仙妓合流现象的遗留。但是,仙妓合流意识在聊斋婚恋故事中并不占主流。《聊斋志异》中的异类仙化倾向,当别有其重要成因。
三、妻之、友之、仙之
《聊斋志异》异类化人故事不再以表现妖怪法术为主,也与艳情小说的情色态度有别,而表现出新的偏向,即在审美价值和道德判断上,对美的异类女性充满尊重、赞誉之情。其态度和评价主要通过爱情故事的男主人公表现出来,这些男主人公对异类女性的态度主要有三种:妻之、友之、仙之。妻之者,有小翠、婴宁、辛十四娘、红玉、莲香、青凤、凤仙、黄三娘、白秋练、葛巾、香玉、黄英、阿纤、竹青、青蛙神、十娘、连琐、李氏、巧娘、聂小倩,伍秋月、小谢、秋容等;友之者,有娇娜、封三娘、绛雪等;俞慎之于素秋,则“友爱如胞”。这些女性虽为异类,却以其内外兼修、真诚美好赢得了人间男子的爱情、婚姻和亲情。即使人间男子得知其所爱者为异类,也往往并无嫌憎,如:
若得丽人,狐亦自佳。——《辛十四娘》
生神志飞扬,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青凤》
丁嬖之(水仙),竟不复娶。……刘亦更不他娶。——《凤仙》
(黄生)始悟香玉为花妖,怅惋不已。——《香玉》
彼(指鬼女三娘)虽异物,情亦犹人。况又慧丽,娶之亦不为戚党笑。——《巧娘》
鱼益欣感,宛如夫妻之久别,不胜欢恋。——《竹青》
这些异类女子往往在人间男子患难之际伸出援手,患难过后,她们多要离开人间,这就不能不让男子生出无限眷恋,如:
生裸跪床头,涕不能仰。——《红玉》
生闻,泣伏不起。……生哀泣如前日。……生悲怛欲绝。——《辛十四娘》
公子入室,睹其剩粉遗钩,痛哭欲死,寝食不甘,日就羸悴。——(《小翠》)
中心营营,寝食都废。……然思阿纤不衰。——《阿纤》
这些描写,可见人间男子对其异类妻子的深情,这当然是在双方同甘苦共患难中培养出来的深情,是一种以爱育爱的回报。这种态度,不仅与传统妖精害人的观念迥异,也与以往艳情小说中男子对待女子以亵玩与情色为主导的态度判然有别。至于少量男子知异类而见憎,蒲松龄往往持批判态度,如常生知葛巾为牡丹而生疑,其“癖好牡丹”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故而蒲松龄对这一爱情悲剧深表感叹:“惜常生之未达也!”(《葛巾》)
《聊斋》通过男主人公对这些美丽异类的友爱表达了作者的爱恋、尊重和赞美。不仅如此,小说还将对异类女性的赞美之情升华到“仙之”的境界。前文述及小说通过人间男子的视角对异类女性外貌进行了仙化描写,聊斋还通过异类女性成仙结局达到对其形象进一步仙化的效果。《聊斋志异》采用了神仙道教“修炼”的概念,但有别于宣扬仙道之作,它并不以表现修炼过程为主,往往只在故事结尾简单告知异类修炼成仙的结局。有的作品通过人物自我陈述交待其修成正果之仙化结局,如:胡四姐说自己已“名列仙籍”,竹青告诉鱼生“妾今为汉江女神”,辛十四娘托人“致意郎君,我已名列仙籍矣”,封三娘修道成仙后自云“倘色戒不破,道成当升第一天”①。有的作品则借文中叙述隐晦地透露出来,如素秋虽为蠹鱼,但她
①道教的天数,指神仙所居的三十二重天界(又有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六诸说),三十二天是修仙由低向高的阶梯。虽然道教经典对三十二天的划分有不同说法,但均认为三十二重天皆为神仙所居,每重天都有天尊主宰。慧黠灵秀,擅长变幻法术,不仅会易容术,还能变幻“云绕韦驼”②①韦驮菩萨现天大将军身时,为四天王座下三十二将之首,是佛教中护法金刚力士的代表之一,担当佛教中驱除邪魔、保护佛法的重任。以退贼,分明类仙;小说结尾写说:“聊斋的三界故事在意蕴上有所分工,神仙故事主要承载作者真善美的理想。”[6](P225)或许正是其蹈海而隐,“尘雾迷障天”,后俞慎村人遇老奴托言“秋姑甚安乐”,联想《仙人岛》、《云萝公主》等篇,可知仙人所在,远矣远矣。另如红玉能为冯生经营家纪,并提前为之复衣冠,“生益神之”;而且,“女袅娜,如随风欲飘去,而操作过农家妇;虽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自言二十八岁,人视之,常若二十许人”。“给爱一张不老的容颜”,其中不正体现着蒲松龄塑造异类女性的良苦匠心与爱憎情感吗?
对异类女性的仙化,更多地反映了作者的态度和评价,这种态度和评价主要借助篇末“异史氏曰”的方式进行。如俗云“獐头鼠目”,蒲松龄却说獐精花姑子“始而寄慧于憨,终而寄情于忍,乃知憨者慧之极,忍者情之至也。仙乎,仙乎!”将知恩图报的异类提升到“仙乎仙乎”的高度境界。再如,他赞美狐女小翠多次报恩,“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称云翠仙为“远山芙蓉,与共四壁,南面王何易哉!”说冯生被冤,“苟非室有仙人(指其狐妻辛十四娘),亦何能解脱囹圄,以再生于当世耶?”夸无名之狐“有狐若此,则聊斋之笔墨有荣光矣!”(《狐梦》)即便是“三易其夫不谓贞”的霍女,蒲松龄也说“女其仙也?”霍女以性行侠,即利用女性的特殊身份行侠,“为吝者破其悭,为淫者速其荡”,使贪鄙好色之徒人财两失、使怀刑自爱之贫士成家立业,具有对污浊世风拨乱反正的作用,因而具有正义性。其中表现的对异类褒美的观念,都是非常新颖,前所未有的。
四、道德讽喻与人性理想寄托
异类仙化使得传统志怪小说中的遇仙题材在《聊斋志异》中空前扩大。遇仙题材分为凡人偶入仙境与神仙下凡入世两大类。聊斋中不乏人间仙踪的描写,如巩仙施展袖里乾坤,化作有情男女的洞天福地(《巩仙》);丐仙能避火烧,还能将严冬园林幻成五彩世界(《巩仙》);雹神助济善人,不伤禾稼(《雹神》);就连观音菩萨也能化为人间老母,护佑人间亲情、爱情(《菱角》)。神仙偶然游戏人间,便成为苦难人间的救助。《聊斋志异》中神仙助人的故事写得很多,表现出蒲松龄渴求知己、向往理想的遇仙情结;但这类故事以显示灵迹为主,还留有道教神仙小说的遗迹。而人神之恋的故事,多是表达其生活理想、人性理想的。马瑞芳老师曾在这种遇仙情结作用下,《聊斋志异》中出现了有意混同仙妖的倾向。如《青蛙神》、《西湖主》、《莲花公主》、《荷花三娘子》、《葛巾》、《香玉》诸篇中的异类分别是青蛙、猪婆龙、蜂、荷花、牡丹,是妖不是仙,但作者有意混淆仙妖之界,让人分不清是仙是妖,具有较多的理想性。聊斋中大量的异类化人的爱情故事,与神女下凡故事异曲同工,其中的异类女性和神女都入世成就了与人间男子的爱情,完全脱离了宗教宣传,成为诗意的爱情佳话。这些人妖恋、人鬼恋故事,与人神恋故事类似,寄托着蒲氏“报名贤”的心理。如《凤仙》篇里,异史氏呼吁:“嗟乎!冷暖之态,仙凡固无殊哉!……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生矣。”又如《小谢》篇中,异史氏说:“绝世佳人,求一而难之,何遽得两哉!事千古而一见,惟不私奔女者能遘之。”再如《青梅》篇结尾,异史氏叹云:“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人妖恋、人鬼恋故事与许多人神恋故事承载了近似的托讽之意。
仙化是对异类女性的褒美,是蒲松龄对异类题材的杰出创造。首先,他最表层地体现了对异类女性外在形象的美化,而这些美总是通过人间男子的视线才得以展现。如狐女系列中,婴宁“容华绝代,笑容可掬”,胡四姐“荷粉露垂,杏花烟润,嫣然含笑,媚丽欲绝”,辛十四娘“容色娟好”,莲香为“倾国之姝”。最为典型的是《狐梦》中毕怡庵梦见的四个狐女,从年过不惑到垂髫之女,皆美丽异常:年逾不惑者“风雅犹存”,年近二旬者“淡妆绝美”,及笄女郎则“态度娴婉,旷世无匹”,最少之女亦“艳媚入骨”。再如其他异类中,鼠精阿纤“年十六七,窈窕秀弱,风致嫣然”,白鳍精白秋练为“十四五倾城之姝”,菊精黄英乃“二十许绝世美人”,牡丹精香玉、绛雪为“艳丽双绝”,鬼女李氏“軃袖垂髫,风流秀曼,行步之间,若往若还”,聂小倩则“肌映流霞,足翘细笋,白昼端相,娇艳尤绝”,小谢、秋容,“并皆姝丽”。《聊斋志异》对异类女性美的出色描写,让人感觉美不胜收。其次,蒲松龄不但把异类女性写得外貌美如天仙,还将其道德品质抬高到“仙乎仙乎”的审美境界。与其俊美外表相匹配的,是她们超越凡俗的心灵美和道德美。如阿绣、宦娘称得上美和艺术的不懈追求者,小翠、阿英、阿纤都有着独立自尊的美好灵魂;而婴宁、白秋练、葛巾、香玉等,或纯真烂漫,或深情执著,或刚烈决绝,或温婉灵秀。在女性拥有的优秀品质中,作者最强调的还是她们的助人为乐和知恩图报,感戴之情一直是蒲松龄最为重视的传统美德。如为报答王太常幼时的无心庇护,狐母遣女儿小翠对王家三次报恩,不啻再造;獐精花姑子父女对安幼与报恩,生死不辞,义薄云天;红玉、莲香、小谢、秋容等都称得上狐鬼中之侠者;封三娘、青梅、宦娘等则都有爱人如己、成人之美的品德。同时,聊斋中的异类女性都自尊自爱,是尊重和维护人间伦理亲情的贤妇,如阿英、聂小倩、阿纤、阿霞。
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对异类女性的美好情操和道德行为的描写总是伴随着对人类丑恶行为的对比和批判,体现其道德讽谕之意。在聊斋故事结尾他多次评价道:
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顾失声于破甑,何其鄙哉!(《小翠》)
天下所难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之,遂至覥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莲香》)
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类所难,而乃于狐也得之乎?唐君谓魏征饶更妩媚,吾于鸦头亦云。(《鸦头》)
所以,聊斋中的异类仙化现象,更多出自蒲松龄的异类观念的创新与道德理想的寄托。这些异类故事皆是寓言托喻的有为之作,出自蒲松龄对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现实的反讽,同时寄托了他对人性美和理想的人间法则的向往。有的异类故事,表现出人性美的诗化境界,如《香玉》以空灵诗意的笔调描写了胶州黄生与牡丹花精香玉、耐冬树精绛雪建立真挚的爱情与友谊,在人性与物之自然性的统一中找到了新的精神归宿,小说创造出更适宜抒情表意的精神自由型人格,树立了高超的人性境界。
聊斋中这种理想化笔墨与诗意的人性境界,还延伸到一些异类男性与人间男子的友情刻画。如表现人鬼友谊的《司文郎》、《王六郎》,写人狐友谊的《黄九郎》、人神友谊的《陆判》。《王六郎》中,许姓渔夫洒脱有义行,故得鬼之侠者王六郎为道义交,王六郎也因其一念恻隐被封为神。作者对许某的遭际是羡慕的,云:“其隐于渔者也?”《陆判中》,陆判是少有的貌狞恶、品德高的异类,书生朱尔旦性豪放,然素钝,学虽笃,尚未知名,其与绿面赤须的鬼判相结交,称之为“髯宗师”,可谓脱俗,而陆判官与之论文,又为之更换一颗聪慧之心,报之不可谓不深!一人一鬼,寒夜对酌、欢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蒲松龄在此小说结尾说:陆判“媸皮裹妍骨”,倘其有灵,“为之执鞭,所忻慕也”。由此可见,《陆判》这类故事岂非聊斋先生之寓言乎?我们从中仿佛又听到他在《聊斋自志》中的感叹:“知我者,岂在青林黑塞间耶?”世无知己,吾谁与归?
以此观照,人妖、人鬼恋故事也表现了蒲松龄的遇仙情结与浪漫诗心。对于美的异类仙化描写,是蒲松龄对异类女性极致美的发扬,是其对志怪小说杰出的创造,及其理想人性追求与浪漫诗心的体现。清代余集说蒲松龄“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悟对”[7](P6)。聊斋中遇仙题材的扩大化,反映了蒲松龄的寻求知己、对现实绝望的心路历程。这种遇仙情结,有其深刻悲剧性,正如《连城》结尾所说:知希之贵,“顾茫茫海内,遂使锦绣才人,仅倾心于蛾眉之一笑,悲夫!”《罗刹海市》结尾亦感叹:“呜呼!显荣富贵,当于海市蜃楼中求之耳!”对于现实的失意与绝望,或许正是蒲松龄创造聊斋异类仙化题材的深层动因,从而加深了此类故事的思想内蕴。
[1]郭氏.玄中记[A].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干宝.搜神记[A].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日]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朱越利译.真浩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A].鲁迅全集:第九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6]马瑞芳.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7]余集.聊斋志异序[A].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潘文竹
A Study of Alternative Immortalization in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WANG Hai-y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shows a new aesthetic value preference in its attitude toward alternative images: a tendency towards alternative immortalization. This is an inheritance of the idea of fox spirits in the folklor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immortal and prostitute in the post-Tang Dynasty literature. The praise of alternative females or even their immortalization by Pu Songling is an embodiment of his pursuit of ideal humanity and romantic poetic heart.
alternative immortalization; idea of fox spirit; combination of immortal and prostitute; moral irony; romantic poetic heart
book=47,ebook=64
I207
A
1005-7110(2010)05-0047-05
2010-07-13
王海燕(1967-),女,河南封丘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