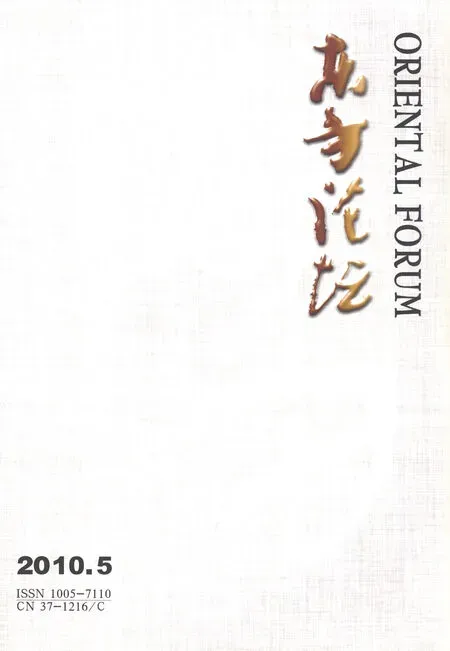学术生活断片
洪 子 诚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871)
学术生活断片
洪 子 诚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871)
1960年代不知不觉培养了朴素、节制的文体意识。进入新时期以后,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逐步开始寻找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建立的内在关联。文学的“外部”与“内部”不再是互相分离的因素,文学也不仅是作家作品,同时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义生产和传播的整个过程。当代文学史学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寻求更妥切、有效的学科概念与叙述方式,另一是对原有的概念和叙述方式的清理。前者着眼于寻找更合适概括以取代“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后者则是留住这一概念以真切认知它的历史。我觉得自己有一定条件做后面这项工作,也就是“设法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试图呈现这些核心范畴和叙述方式的内在逻辑,揭示它们如何建构自身,产生怎样的文学形态。
当代文学史;文学;历史;清理;学科概念;叙述方式;内在逻辑
“自反”式思维
说到我和“学术”有关的事情,应该从“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开始。不过,1950年代上大学和1961年毕业后留校工作那几年的情况,对后来的教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影响。
1958到1959年间,我读大学二、三年级,参加了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和集体科研的运动;这个运动被形象地概括为“拔白旗,插红旗”。我先后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戏曲史的编写,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写郁达夫、叶圣陶两节,戏曲史好像让我写明代传奇的两个作家。这两个项目后来都不了了之。倒是和谢冕、孙绍振、孙玉石、刘登翰、殷晋培他们合作的《新诗发展概况》,由于在1959年的《诗刊》连载四个部分,当时尚有一定影响。这个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在《回顾一次写作》①谢冕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中已经有详细的讲述,也有各自不同的反省。写《新诗发展概况》,主要是徐迟先生(当时任《诗刊》副主编)的主意,也是他具体组织的。倒不是写空头文章,我们从北大图书馆、北图(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以及中国作协图书室借出来几百部现代诗集、评论集,集中读了一段时间。不过,就成果而言,不论材料还是观点,都难说有自己的发明,依据的是1950年代主流文艺界建构的那种两条道路斗争框架和语言方式,让不同的诗人、流派、艺术方法,按照主流与逆流、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来站队。现在有人说,当年年轻人的浪漫情怀,他们的反学院(学术)体制的精神也不应该否定,不过,这种“情怀”一开始就被导向单一的,建立僵化体制的道路上去。学术价值既谈不上,就对待前辈学人(也就是我们的老师)的那种态度,那种粗暴、不容讨论的大批判方式,回想起来也应该汗颜。
自然,从我的角度,这些经历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以先验的观念去粗暴剪裁、肢解材料的这种工作方式,这种毫无弹性的操作,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痕。后来身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理论、方法创新的热潮,我既认识到理论方法革新的重要意义,却也警惕着对它们的迷信,注意区别新的概念、抽象是对现象的丰富,还是窄化——这可以说是在1950年代因得病而获得的某种免疫力吧。值得怀念的另一点是,大学五年,我们的生活与社会并非完全隔绝,不是处于封闭的象牙塔之中。这一点也是今天难以复现的。尽管当年我曾经为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的下乡下厂苦恼,甚至厌憎。即使从最低限度的意义上,个人因此也获取值得回想的生活段落。我体会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遇,问题,对别一代的辉煌其实无需羡慕,自己的那怕是难堪的日子也不必后悔。
因为运动不断,大学五年系统听课、读书的时间并不多,只是头一年多和临毕业的一年。不过,也还是读了不少书,也上了一些记忆很深的课。当年为弄懂人民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弄懂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弄懂真实性、倾向性、典型、党性、倾向性、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弄懂无冲突论、干预生活,弄懂光明与黑暗,歌颂与揭露,香花与毒草,有益、有害与无害,弄懂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常有陷于迷魂阵中的感觉。不过也不是没有好处——逐渐了解当代文艺那些常常以激烈方式出现的论辩、争斗的根源和展开方式,也让我知道这些纠缠变幻的语词,既寄托着人们的理想、激情,也消耗着他们的宝贵生命。
大学课程中,印象很深的有吴组缃先生讲明清小说(《红楼梦》、《聊斋》、《儒林外史》);从他那里,见识了生活阅历、写作经验、艺术感觉互相渗透、支持所达到的境界。还有就是常被说到的林庚先生讲唐诗。他讲李白,也如李白那样的神采飞扬,解读者与对象似已融为一体,主体和客体相互投射。尽管模仿吴、林两先生的后学者不少,其实他们不是可以容易复制,因为他们的着重点属于生命,而鲜活的生命总属于难以复制的个体。倒是朱德熙先生讲课的“方法”,是我后来经常复习的启示。朱先生主业是现代汉语语法,当年运用的是索绪尔、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记得他著名的论文是《说‘的’》。结构主义在那时的中国大陆好像还不大为人所知,成为“显学”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由于无知,当年我对语言课程没有多大兴趣,也就没有动过选修为高年级语言专业开设的语法课。但他的作品分析听过多次(写作学、文章学是他的副业),有《传家宝》(赵树理),《欧游杂记》(朱自清),《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羊舍一夕》(汪曾祺)。与别的教授不同,他看重的不仅是提出和论证结论,分析所涉及的词汇、句式、结构安排,还会提出多种可能进行比较,从中发现较佳的处理。当然也有他自己更认可的选择,但接着常会“自反”地质疑这一看法,不把这一选择绝对化。孙绍振对这一方式的概括是:“并不要求我信仰,他的全部魅力就在于逼迫我们在已有的结构层次上进行探求,他并不把讲授当作一种真理的传授,而是当作结构层次的深化。”①
“文体”意识
1961年我大学毕业,那年22岁。虽然出于好奇,出于对“远方”的虚无缥缈的想象,填报分配志愿时,第一志愿是西藏。可能是看我完全没有社会生活经验,最后是留我在学校教写作课。这个课程工作量很大,要批改很多的作文。教中文系的还好说,文科“外系”的,一个班多至一、二百人,每个学期要写五次作文,花费精力可想而知。因此,不少教师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明确留校就是教写作,所以想做专业研究的,都选择去北京师院(现在的首都师大),人民大学。毕业之后几年和“文革”十年,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学术”研究,只写过一些散文随笔,还有就是刊登在北大学报(已经记不清是哪一期了)上的《〈社戏〉的艺术技巧》。他们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稳定写作课教师的“军心”,证明写作也是学问。这个期间,我并没有将心思全部放在写作教学上,仍持续关注当代文学的情况;这为以后的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60年代前期,学校没有太多的运动 ,我也就读了不少书。补读本来应该在大学阶段读的一些作品和理论著作,唐宋诗文,明清著名小说,特别是现代中国小说。西欧特别是俄国的作品也读了不少,还有就是读了一些西方古典文论。当年的阅读,许多可能没有真正理解,意义是视野得到开拓,明白文学、人生其实有未被当代反复纠缠的问题所涵盖的领域。读得认真的是鲁迅的杂文、小说。领到第一次工资时,就跑到北大附近的五道口新华书店,用自行车驮回十卷本的《鲁迅全集》。还有就是《世说新语》、《红楼梦》、《聊斋》等,还有曹禺的剧本。这个期间还读了那时翻译过来的全部契诃夫小说和剧本。有些书,如《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艺术哲学》等,现在却想不起来当年细读的动机。这五、六年读书的心情比较放松。到1963年我才从见习助教转为助教,单身教师都住集体宿舍,要当上讲师那还是猴年马月的事①1960年代初,北大中文系百十多号人,教授大概不到二十人,讲师则只有陈贻焮、赵齐平等四位,其余的都是助教。。没有紧迫的职称、考核的压力,也没有十分确定的专业方向,读书也就没有非常切近的功利目标。书籍的选择,阅读的感受,有较多随意性,较多的快乐。还有一点是,因为教写作,自然会留心语言、修辞的方面②在1950-1960年代,北大中文系和文科各系的写作教学小组,归属汉语教研室,强调的不是文学创作,而是解决文从字顺,篇章结构等方面的语言运用问题。写作教学的这一性质,与当时朱德熙先生的指导思想有关。。这对自己后来的写作,和指导学生的写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①孙绍振《我的桥和我的墙——从北大出发的学术道路》,收入谢冕等著《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那些年,不知不觉培养了某种“文体意识”。说是“文体”,放大来说是一种“世界观”也无不可。这就是朴素、节制。节制,现在分析,就是关注事物(包括语言,情感)的限度。上高中和刚上大学那几年,喜欢的多是热情、浪漫的抒情,夸张的描述。这个时候兴趣和标准悄悄发生改变。一个具体例子是,大学一年级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③那时读的,应该是蒋路先生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的版本。,和同班一个同学十分着迷拉赫美托夫,模仿他为着崇高目标而实行自虐式的苦行,以检验肉体、精神在非常情境下的承受力。但是1960年代重读,感动已经有很大减弱,觉得那也许只是一个抽象的,夸张的符号④当时这个评价可能是失当的。只要想想19世纪俄国激进革命者,那些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事迹就能说明这一点。。因此,当年虽然长篇《红岩》名气很大,很轰动,我却不能喜欢:还不是思想观念上的原因,而是那种强烈的“构造性”,那种极度夸张、渲染的倾向,那种所有细节都直奔“主题”的观念性结构。
这种节制的意识,与阅读的积累有关,但主要也是性格使然。虽然也向往浪漫,激进,追求“进步”,其实内心向往的是安静;有更多的时间独处,回避着和陌生的人、事的接触。这种退缩的本性,在这个时期的阅读中得到支援而加强。1962年读高尔基回忆契诃夫的文字,注意到他经常使用“朴素”、“真实”的字眼。他说,在契诃夫面前,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起一种愿意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是自己的欲望”。在什么地方还说过他“像害怕火一样害怕夸张”。高尔基写道:“他常常是这样的:他热烈地、认真地、诚恳地说着,可是忽然间他又笑起来了,他笑自己和他自己讲的那些话。在他这种温和而悒郁的笑容里面,我们看出了一个知道语言的价值和梦想的价值的人的敏感的怀疑。”⑤高尔基《回忆录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巴金、曹葆华译。我1960年夏天购得这本书。里面回忆的人物有列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夫人、契诃夫、柯罗连科、柯秋宾斯基、普利什文等。高尔基对托尔斯泰有复杂感情,对契诃夫就单纯得多,他们之间也有更多的共通点;尽管在“当代”,他们一位被称为无产阶级作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父”,另一位则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虽然并不能认同梅烈日柯夫斯基的评价,但他指出这一点却很有道理:契诃夫的知识分子就是高尔基的那个流浪汉;高尔基的流浪汉们尽管有着大众化的外表,内心却是贵族。参见梅烈日柯夫斯基《先知》中的《契诃夫与高尔基》。《先知》,赵桂连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出版。热烈、诚恳却突然转换至怀疑,这很少见,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节制:不忘记边界的存在,既不夸张看待事物,也明白认知者情感、能力的限度。而且,说到底,也就是意识到人类的悲剧性,大多来自日常生活的琐碎卑微方面。这种审美的,或文体的倾向,在1980年代得到加强。特别是在读到诸如休谟、梁实秋、李健吾、朱光潜、袁可嘉,以及卡西尔、苏珊•朗格等的论述之后⑥1980年代初,刘西渭(李健吾)的《咀华集》还没有再版,我读的是《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那是当年让我惊喜的一本书。至于梁实秋的《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则是1980年代末才读到。主要收录1940年代后期批评文章的袁可嘉的《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我尤其欣赏其中关于“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的论述。苏珊•朗格符号美学的《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当年也给我很大影响。。符号学一些论著的阅读,也助于我怀疑人文主义有关灵感、独创性、主体等的神话信仰;这应该也属于我所说的“节制”的范畴。
低俗与崇高
“文革”的经历应该和“学术”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却对后来的生活,对教学和研究产生深刻影响。关于那些日子,谢冕先生在一篇讲到我的文章里说:“我们当时的立场是避开派性斗争,选择了游离于两派之间的‘中间地带’。为了生存和自保,我们自己寻找‘符合大方向’的大批判——即所谓的‘文艺黑线’——的事来做。在这段近于‘逍遥’的日子里,我和洪先生合作写了一些言不由衷的大批判的文字。这些,与其说是我与洪先生的文字交,不如说是我与他的心灵交,一切尽在不言中——即使是在动乱的年月,我们也总在寻求属于自己的可怜的那么一点点的尊严与宁静。”①谢冕《一束鲜花的感谢》,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中间地带”和“消遥”,指的是66年到68年的两年,我们既不满北大“校文革”、聂元梓的所作所为,也不愿加入到对立派“井冈山兵团”之中,而成立了游离的,不愿“上山”的“平原战斗队”。在“寻求属于自己的可怜的那么一点点的尊严与宁静”的艰难上,谢冕的体验肯定比我深刻得多。1968年夏秋工、军宣队进驻北大之后不久,他和严家炎、唐沅、曹先擢等先生,就被莫须有地定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小集团”,在中文系全系和各个班级反复进行批判。
谢冕说的不错。“大批判文字”我写过多篇。“文革”前夕(1965年)批判过电影《早春二月》——尽管当时我喜欢这部电影;批判严家炎先生“宣扬中间人物论”的大字报——尽管当年我从严先生的研究文字里学到许多东西;1967年和谢冕、严家炎等先生,在中国作协编写流行颇广的《文艺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各种场合有过不少呼应潮流的表态、发言。当然有“为了生存和自保”的违心,也有惟恐落伍而自愿表现之举。这些年难以忘怀的,一是自己内心分裂的难堪和痛苦,另一是现实生活中的肉体和精神的暴力,以及普遍性的语言的平庸化。在这样的时候,人的思想、心理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抛弃个人把握到的事实和感受,而拥抱“正确性”的“真理”和“本质”。另外的情形则是,试图坚持自身由“观看”获得的经验,抵抗来自他并不信服的“真理”的压力,这在一个思想、立场没有自由选择的环境中,必然陷于言行、表里的分裂,遭遇内心痛苦的折磨。由此,精神的独立和自由的可贵,便被特别地感觉到。
至于语言的平庸化、暴力化的倾向与后果,因为被外在的,肉体的暴力所掩盖,一直到现在,仍没有得到应有的严重关注。回想当年我自己的发言、文章,为着当代文学研究翻阅当年报刊资料,有时候会有一种难堪的触目惊心。1990年代重读1967年1月到1968年夏天各地“革委会”成立的社论和“致敬电”,真的让我感慨不已。说从这里面,见识了现代汉语大面积的丑陋和低俗化,恐怕并不过分。在市场化的今天,人们对文化的低俗倾向有了警惕,但其实,更需厌憎的是那些包围着我们的假以“崇高”面目的恶俗。
批评与文学史
1977年,和许多大学一样,北大中文系也成立了当代文学教研室,并开始编写当代文学教材。由于中文系写作课取消,我便加入这个教研室,开始上课和编写教材。教材就是《当代文学概观》②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出版修订版时,改书名为《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由张钟、我、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合作,出版于1979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集体讨论,只是各自写分工的部分。我承担诗歌和短篇小说两编。在此之前,当代文学在中文系还不是独立课程,因此这些都带有“开拓”的性质,需要花许多气力。这也让我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能够静下心来,系统翻阅相关资料,包括报刊、作品、评论集等等,让我对十七年和文革的文学状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和许多人一样,那时我对“新时期”以前的当代文学持更多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认同“新时期”是“文学复兴”,又一个五四。我承认前30年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不少作家、批评家也有过艰苦的,有成效的探索。但总体上说,由于将某种文学理念、路线定为一尊,以暴力方式阻遏其他的选择和“越界”的行为,导致文学全面的贫困。“文学的贫困”是我那时拟想,却没有动笔的书稿题目。文学史教学、写作首先要遇到时期划分。1980年代“当代文学”分期方法最常见有三分法和四分法;前者是分切为“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后者则以1957年为界,将“十七年”又划分为两个段落。我的讲课则以“文革”前后为界的“两分法”。1980年代初上课,曾用了不少时间解释这一方法的依据。尽管后来我的解释发生许多变化,但这一分期始终体现在我的著作中③1986年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1990年代初与刘登翰合作的《中国当代新诗史》,1997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十七年”被“文革”激进派指认为是“黑线专政”,周扬等也沦落为阶下囚。因而当时认为“十七年”和“文革”是截然不同时期的普遍看法不无道理。但换一个角度看,这三十年也有它内在规范的连续性,是一种文学理念、设计的实践,和它的极端化的历史过程。“文革”文学是“十七年”主流文学的激进化,以及这种文学在“文革”之后整体性的崩溃、离散,而出现重要的“转折”,这两点是当时形成,后来也没有改变的基本看法。
在“新时期”,以变革、创新为核心的文学潮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文学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现状批评成为“当代文学”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存在,众多才俊投身其中。我自然也为它所吸引,跃跃欲试,极想大显身手。不久就发现根本缺乏做这样的事情的能力。知识、才情所支持的敏感的不足且不去说它,更要命的是没有必须的心理准备,那种面对歧见和争论的坚忍的心理承受力。这样,便从半自觉到自觉地离开批评,而转向“文学史”。这是意识到自己不能做什么之后的又一次“退缩”。那时候,“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关注的人很少,争论也不是很多。准确点说,那时社会主义文学的信仰者的反省、辩护与坚守,已得不到“主流文学界”的关注,没有许多人愿意理睬。因而,面对“历史”者将会比较“清静”,当然也孤独。记得1980年4月在广西南宁开“全国诗歌讨论会”的时候,与会者都为北岛等青年诗人的评价动容,激烈争论,我提交的论文是不合时宜的“田间的诗歌艺术”,讨论的是艺术概括、象征的“前景”问题。不过,我那时还年轻(在那个特殊岁月,四十刚出头仍被归入“青年”的范围),心魂所系的还是新鲜、激动人心的现实,只是避免对现实问题直接评断,而放置到历史之中,寻找、勾勒联系、衍变的线索,或从争论中离析某些有历史内涵的理论性问题。这就是我出版于1986年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的基本线索。后来,有论者称这种方式为“一种带有历史品格的‘深度批评’”,是试图建立文学史当代性与历史性的关联,但它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在一个需要明确判断的时候回避做出判断,总归是精神、学术上懦弱的表现。
文学的超越性
1980年代初,司马长风和夏志清文学史在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很大影响,我也先后读过他们的著作①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共3册,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1980年出版。记得是从北大中文系资料室借阅的,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则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的版本,那时台港出版的书还很难看到,不知道是否是从乐黛云先生那里借到的。。后来常将它们并列其实很不确当,夏志清书的价值哪里是司马长风的所能相比;后者更多的可能是助燃简单的意识形态火焰。我当时很赞同夏志清有关文学超越性的论述。当年在社科院文学所办的内部刊物“文学研究参考”上读到1960年代普实克和夏志清由《中国现代小说史》引发的争论,更多的认同是在夏志清一边。不过,我对文学超越性的理解有一点不同,也可以说是融入了普实克主张的某些成分。也就是说,超越性不应仅理解为“上升”到人性的“高度”,而且指关切、处理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时候作家的独特视角②到了19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对夏志清和普实克争论的看法,我有了一些调整。具体的观点,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三联书店2002出版)一书中有所涉及。。
依照我对当代文学缺陷的理解,和习惯地认为作家和作品是“文学”的主体,便认为问题症结在于作家的“精神结构”。黄秋耘先生1957年评论《在桥梁工地上》等作品时说的“灵魂锈损的悲剧”,这个说法给我印象深刻。导致文学“贫困”的原因,就是作家精神的“锈损”。而这个“锈损”,当时认为最重要的是失去精神、思想独立性,出现普遍的对权力的依附、臣服,文学也因此未能建立相对独立的传统。为了思考这个问题,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我杂乱、毫无秩序地读了许多相关的材料,鲁迅的,瞿秋白的,胡风、冯雪峰,余英时、李欧梵、李泽厚、刘再复的,托洛斯基、日丹诺夫、卢卡契的,纪德,罗曼•罗兰、加罗蒂的,伊格尔顿、佛克马的……。现在检讨,那些时候的阅读,并未清楚理清不同主张自身的内在线索,未能在比较的基础上将问题深入展开。1988年北戴河文学夏令营③由河北秦皇岛市文联和北大中国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在“夏令营”里讲课的还有汤一介、乐黛云、严家炎、谢冕、钱理群、江枫、刘宁、任洪渊等先生。,我讲的是这个题目,同年一篇讨论诗歌现状的文章中也着重涉及④《同意的和不同意的》,刊于《文学评论》(北京)1988年第4期。,它也成为《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这本书的论述核心。当时我理想的文学是超越现实政党政治,超越意识形态僵硬立场的文学。这是我十分厌烦当代呼应、证明某一政治观念、路线的文学潮流的心理相关。我看到这一潮流并未应“新时期”的到来而消减,1980年代众多“改革”、“反思”的作品中仍接续不断。在一个“政治”过分泛化,侵入到生活每一角落的环境中,提出文学的“非政治化”是有它的理由的。如果这个说法很可疑,也可以换一个说法:“非政治”的文学也可能有它的“政治”涵义和能量,也可能参与一定的“政治实践”。
作家自主性,独立精神的缺失,开始我更多看作是性格、精神的因素。后来逐渐意识到,文学的问题,与物质“制度”,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环节紧密相关。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在当代,对‘一体化’文学格局的构造和维护,从较长的历史过程看来,最主要也最有成效的保证并非来自对作家和读者的思想净化运动,而是来自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①《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1980年代反思当代史的时候,常说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地位地下,命运悲惨。还有总是将知识分子描绘为受政治权力体制压制的群体。我在看材料的时候,发现事情并非如此。一是知识分子也处在“体制”的网络之中,扮演不同角色;另一是他们的命运其实很不相同,这要视其与“体制”的关系而定。与那些描述相反,不少作家进入“当代”,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经济收入,要比在“旧中国”“荣耀”、舒适得多。当然,有的(或有时)也可能很悲惨。
1980年代后期,我开始在课堂上讨论这些问题。涉及的文学体制,包括作协这样的“文学团体”,文学刊物的性质和运作方式,作家的社会身份、经济收入,文学的管理、控制方式,作品流通体系,读者的构成,以及文学的评价、奖惩机制等。开始是零星涉及,待到1991-1993年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当代文学课上,才形成系统性分析成果②在东京大学的讲稿经整理,以《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为名初版于1997,香港,青文书屋。应该说明的是,在国内中国文学研究界,比较早研究制度与文学形态之间关系的著作,是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从理论与方法上,应当是得到像埃斯卡皮这样的文学社会学论著的启发③(法)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1980年代在大陆、台湾有多种译本,如安徽文艺出版社版(王美华译,1987),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符锦勇译,1988),台北南方丛书版(颜美婷译,1988),台北远流版(叶淑燕译,1990)。我当时读的是于沛选编的浙江人民出版社版(1987)。④这类报告、文章,典型的有周扬第一次文代会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1956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邵荃麟刊发于1959年10月《文艺报》的长篇总结文章《文学十年历程》等。,但根本原因是基于对现实问题探究的动力。这是研究范围的拓展,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建立内在的关联。这也多少改变了我对“文学”的某些理解:“外部”与“内部”不再是互相分离的因素,文学也不仅是作家作品,同时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义生产和传播的整个过程。如果说到认识上的缺陷,就是那时“体制”在我脑子里带有负面的意味。没有明白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于真空之中;没有了解到体制与文学生产的关系要复杂得多。
终点与起点
因为张钟和我是中央电大当代文学课的主讲教师,1987年9月曾参加在安徽黄山的电大教学研讨会。一次聊天,我对张钟说,我们编写的教材(指1986年版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的开篇的话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历史的巨手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的篇章。” 我说,为什么“共和国”一成立,文学就出现新篇章?“历史巨手”指的是什么?它是怎样揭开的?……书中并没有清楚解析。张钟听过点头说,是应该找时间讨论讨论。不过,他很快到澳门任教,一去就是四年,讨论也就没有实现。
我当时想,许多话大家都那样说,似乎理所当然,其实未必。我对自己参加编写的,以及当时通用的当代文学教材的不满意,主要还不是理论框架不够“新”,而是不少概念、说法没有得到清楚解释。因为多次读过周扬、邵荃麟,以及中国作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描述文学状况的报告、文章④,明白1980年代当代文学史的使用的概念、总体框架和叙述方式,基本上是没有得到有效反思的延续;尽管作家、作品和文学事件的评价发生变化。这当然不是说,周扬他们的概念体系、叙述方式都要不得,都必须全部推翻,而是说对这些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建构,有必要弄清楚其特定历史内涵,和这种历史叙述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联,不把它们看成自明的“自然物”。我最初有关“历史”与“叙事”关系的并感受,主要来自生活经验,以及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的一点了解。后来,读了一些有关解构主义、阐释学、新历史主义的论著,加深了这方面的认识,在1990年代中期,有意识地开展有关“ 当代文学”建构的清理。我认为当代文学史学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寻求更妥切、有效的学科概念与叙述方式,另一是对原有的概念和叙述方式的清理。前者着眼于寻找更合适概括以取代“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后者则是留住这一概念以真切认知它的历史。我觉得自己有一定条件做后面这项工作, 也就是“设法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试图呈现这些核心范畴和叙述方式的内在逻辑,揭示它们如何建构自身,产生怎样的文学形态。这一清理的,类乎知识学的工作,需要降低评价的冲动。尽管这有时候难以抑制,不过因为认识到“文学性”不是亘古不变的事物,还因为性格上的因素,多少还是能够做到。我是个不自信的人,在《1956:百花时代》这本书的前言里说到:“现在的评述者已拥有了‘时间上’的优势,但我们不见得就一定有情感上的、品格上的、精神高度上的优势。历史过程、包括人的心灵状况,并不一定呈现为发展、进步的形态。”“我们”其实是在讲我自己。所以我说“对自己究竟是否有能力、而且是否有资格对同时代人和前辈做出评判”并没有信心。这种“清理”的,探究历史如何被讲述的思路,有助于隐藏自己,缓解我面对判断时的焦虑,紧张感。说起来,这是将难题搁置,其实包含着避难就易的畏怯的逃避。
基于上述理念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1996)、《“当代文学”的概念》(1998)这两篇论文中,也体现在后来《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部分章节中。
个人的文学史
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概用了两年时间。自然,许多材料和看法,都是过去的积累。没有想到出版后会有比较好的评价,更没有想到个人署名是一个被关注的因素。我其实并没有所谓“独立撰史”的自觉意识,事情有一些误解。我的观念里,个人署名和集体写作不是一个问题。不过,它之所以成为问题,也有历史原因。我上大学的时候,读的文学史都是“个人”的。林庚的,刘大杰的,郑振铎的,王瑶的,刘绶松的。当然,从1958年开始,集体编写文学史成为主导潮流。这个大趋势的出现,是要倡导精神生产的“集体主义”性质,且对资产阶级阵地的占领也需要集体动员。实际的考虑,可能是便于实现统一的“正确性”论述,通过集体的“监督”以尽量降低离经叛道的成分。在文学史编写中,1958年开始的这一传统,在八、九十年代没有多大改变;特别是涉及教科书性质的文学史。在这样的情境下,“个人”编写也就为大家所关注。但归根结底,个人署名还是集体编写,不是决定一部文学史水准的必要条件。
大概是1996年底,北大当代文学教研室就筹划编写一部新的当代文学史,以取代不大适用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不过事先都没有意识到,已经不是1980年代了,我们之间在文学观念,文学史意识和对“当代文学”的看法上,分歧可能比共识要来的多。我们各自提交几份提纲,其间的差异可以说无法调和捏合。在这个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有了个人写作的念头。为了写这本书,材料准备花费的力气自不待言,基本面貌的构思也颇费时日。那时,创新是首先想到的目标,为此翻读了不少类型的文学史著作,却总也没能找到满意的形式。因为考虑到它作为大学文科教材的性质,最后还是打消了“别开生面”的幻想,选择了平实的,与传统教科书体制、叙述方式有更多承续的方式。不过,在如何处理研究界的“共识”和个人的“异见”的关系上,却也有许多苦恼。因为不是个人的学术专著,只能尽量寻找之间的平衡点。但还是抑制不了想更多讲出一些“异见”的冲动。“定性”的不大确定,也就造成双重的缺憾。这个文学史,如果说有一些值得肯定之处,首先是将“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做出一种知识性、学术性的处理,而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比较起来,我对这三十年文学的描述比较有把握,问题切入点比较犀利。其次,将我对历史的描述,与这段历史在此前的建构加以交错,而具有并不单一的视角,加强了它的“历史感”。另外一点是在叙述体例、叙述语言上提供的东西。正文尽量使用减弱评价的描述性语言,并将较多史实放在注释中的那种做法,以及点到为止不做渲染的有意追求,在读者那里也是褒贬不一。
自然,对这部书也有许多批评。一个主要问题是,对八、九十年代文学的评述比较一般化。2006年的修订版想改变这个状况,好像也没有很大奏效。书出来后,另外的批评集中在“一体化”的问题上;这方面的争议颇多,我也就此写了文章做一些修正,也做进一步的解释①《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不过,我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争论,其症结主要还不是论述周全与否,而是对“当代”各个时期文学的基本估计上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是文学的,也是有关当代中国历史的,有时且与意识形态立场的分裂、对立相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从逻辑修辞上去做修补;那是超越文学层面的大问题,它不是我所能真正把握的。
含混、不确定的希望
上世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实发生很大变化,思想文化界也一样,许多事情在很多人内心引发震撼的体验。不过,我1991年去了日本1993年秋天才回到北京。这两年很重要,可是由于资讯不畅,加上当时身体不好,情绪低落,也就在异邦过着自我隔离的日子。回到北京,就遇上《废都》、顾城、人文精神讨论等事件。那时候,1980年代的那种人文主义精英意识仍支配着我,是我观察事物和做出情感反应的主要依据。所以对上海学者人文精神失落的焦虑强烈共鸣,也陷于深深的失落情绪之中。一个感受是,1980年代,个人与社会之间有一种紧密呼应的关联,现在却分明感到了阻断。1990年代初,谢冕先生在北大中文系主持“批评家周末”,我回来后也被叫去参加。1995年初在一次“当代文学的理想”为主题的讨论会上,我也呼应众多参加者有了情绪激动的发言。它后来和谢先生的发言一起,刊登在多家报纸上,题目好像有点“耸人听闻”:《文学“转向”和精神“溃败”》①记起来的有北京的《中华读书报》,上海的《文学报》等。。我认为1980年代提出的“精神独立”、“文学自觉”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因而才在变化的历史环境下出现这样的文学“ 转向”和“溃败”。因为对“新时期”的“旗帜性作家”王蒙先生有些不满,觉得他不应该为这种“精神溃败”推波助澜,便在文章中旁敲侧击地说,“以曾经被流徙于社会底层、对中国现实和下层民众有深刻体察的权威姿态,来宣扬一种认同现状和‘流俗’的世界观”,“对那些质疑现实、对精神性问题进行探索的作家,给予‘虚飘’、‘虚妄’的批评和嘲讽”,“用提倡‘宽容’、‘实行费厄泼赖’,来对抗当代人为的社会争斗的后遗症,……也一次消解精神领域中并非总能调和的对立”。
现在倒不必为这些激烈言辞检讨,失当之处我不久也就意识到。在金钱、利润成为价值核心,1980年代有关“世界”、“未来”的想象面临破灭的情境下,又一次失去“精神家园”的作家、知识分子,1990年代初都在为自身,为他们想象中代言的群体,或坚定,或游移不决地重建精神的“家谱”②参见王安忆小说《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张承志小说《金牧场》、《心灵史》,史铁生散文《我与地坛》,西川诗集《虚构的家谱》等。。我自己并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力。从文学角度而言,能够真切追忆的,大概还是我曾经想简单离弃的一些东西。这个期间,我重读了国内外一些“左翼”(广义的)作家、批评家的论著,为他们追寻“乌托邦”的实践所感动,而调整了我对中外“左翼”文学理念和实践正当性、合理性,和历史中具有的创新活力的认识,从他们也许是悲剧性的命运中,发现了人类绵延不断的,最可宝贵的那种精神品质——而这些,在“后现代”的今天,似乎正在不可阻挡地消亡。因而,“左翼”思潮及其文化成果,不再简单地看作是人类思想艺术传统中的异端,对它们有了新的认识和同情。“我不是将中国的‘左翼文学’看作一开始就站在错误的起点上,而是重新认识其发生的合理性”。当然,我也不能认同那种激进的“新左派”的翻转式立场:“我充分理解在90年代重申‘左翼文学’经验的历史意义,但也不打算将‘左翼文学’再次理想化,就像五、六十年代所做的那样”③《回答六个问题》,《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收入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退休之前在北大中文系的最后一次课中,便用较多的时间来讨论中国“左翼文学”的历史命运,讨论它的合理性、创新活力。我对它的宿命性的两难处境,其实充满同情,有一种没有明言的伤感。④参看《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再版。这样的立场,这样的处理方式,批评者认为是立场的含混,是一种“历史混合主义”,表扬者则说是在试图建构“历史复杂性”的阐释学。在我这个方面,只是因为我在一个乱象丛生的年代,有点怀念当初曾有的“乌托邦”情结而已。
有学者这样认为,“对后现代精神而言,纯粹自主的自我已不再可能。然而尽管历尽磨难,几度转型,却到底并没有被抹杀。……后现代的主体现在已知道:通向现实的任何道路都必须穿越我们语言的极端多元性和整部历史的含混性。”又说,“不管他们本人如何,所有这些后现代作家即使不能给我们幸福的许诺,至少能够给我们某种希望的许诺——正是希望授权他们以写作作为其抵抗行动。”
我想这些话说得很好。
责任编辑:冯济平
Fragments of My Academic Life
HONG Zi-cheng
(Dept of Chines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75, China)
In the 1960s, I cultivated a simple and restrained stylistic awareness. In the new era, I began to look for the inner conne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outside and inside of literature were no longer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literature was not only the works of a certain writer, but also the whole process of meaning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under particular historical condition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faced with two problems: looking for more suitable and effective disciplinary concept and mode of narration, and sorting the concepts and modes of narration already in existence. The former aims to find something to replace the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the latter tries to keep this concept to trace its history. Personally, I feel qualified for the latter. I mainly attempt to disclose the inner logic of these core categories and mode of narration, how they form themselves and what literary forms they produc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literature; history; sorting; disciplinary concept; mode of narration; inner logic
book=39,ebook=49
I03
A
1005-7110-(2010)05-0039-08
2008-08-26
洪子诚 (1939-),男,广东揭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理论研究。发表的论文和学术著作主要有:《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当代文学”的概念》、《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与刘登翰合著)、《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