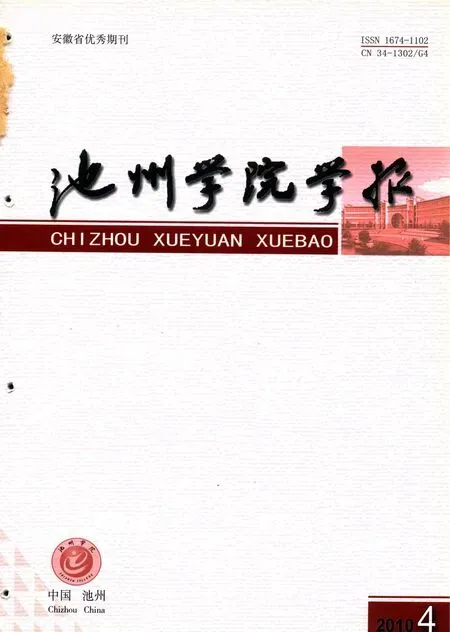《红楼梦》与张恨水小说
许思友,陈广士
(池州学院中文系,安徽池州247000)
《红楼梦》与张恨水小说
许思友,陈广士
(池州学院中文系,安徽池州247000)
张恨水在中国通俗小说领域有着崇高的地位,他的文学成就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学坚实的土壤上,这其中尤以《红楼梦》对他的影响最著,特别是其小说的人物性格、表现方式和梦境描写等三个方面的影响最深。
张恨水;红楼梦;人物性格;表现方式;梦境描写
范伯群光生曾经这样高度评价张恨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意义:“正因张恨水在通俗文学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所以有的研究者提出了‘双峰对峙’说。即在纯文学作家中,鲁迅是高峰;在通俗文学作家中,张恨水是高峰。……张恨水研究是一个重要而庞大的课题,非深入开掘不可。因为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研究离不开这座通俗文学的高峰;而现代通俗文学的理论建设也要向张恨水研究‘索取’许多从创作上升为理论的规律性的东西”[1]。显然,这座高峰并不是绝地而起的空中楼阁,如果说鲁迅这座高峰受到过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欧风美雨的滋润,那么,支撑起张恨水这座高峰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学坚实的土壤。张恨水从十二岁开始就广泛地接触 《红楼梦》、《西厢记》、《水浒》、《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 等中国传统文学精品,并且“除了对故事生着兴趣外,我便慢慢注意到文章结构上去”[2]。这种难得的阅读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后来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也使得他的小说不可避免地打下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烙印,这其中,尤以《红楼梦》对他的影响最为显著,他说:“我收拾了一间书房,把所有的钱,全买了小说读”“第一件事,我就是把《红楼梦》读完”[3]。又说:“《金粉世家》之是何命意?都可不问矣,有人曰:此颇似取径《红楼梦》,可曰新红楼梦。吾曰:唯唯”[4],可见《红楼梦》对其影响之著。以下笔者试从三个方面来探索《红楼梦》对他的影响。
1 人物性格的“红楼”模式
张恨水小说中最早显示出其与《红楼梦》密切关联的当属《真假宝玉》,《真假宝玉》是张恨水的第一部白话小说,创作于1919年,并于当年发表在上海的《民国日报》上。作为张恨水的早期作品,这部小说谈不上较高的艺术成就,但对其后期成熟的小说,却有不容忽视的经验意义。顾名思义,我们会发现这部小说与《红楼梦》的直接关系,这一点在人物性格塑造上更加显得突出。《真假宝玉》只是一部片段式的短篇,其人物自然也只能局限于了了二三人而已,但人物性格却几乎与《红楼梦》完全一致,若不是内容与《红楼梦》相比太过于摩登,我们即使在《红楼梦》原著中找个地方将之插入其中,也未必会引起初读者的怀疑。小说一开始写晴雯见宝玉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书,便说:“仔细冷着呢。又要……”[5]此时宝玉不以为然,她又嗔道:“呀,我晓得了,没有这个人(指袭人)在屋子里,你就不高兴哩。我们的话,只是耳边风”[5]。当麝月出来说动宝玉起床后,她又没好气的说:“怎么样?我们的话一千句,还抵不了人家的一句呢”[5]。短短三句话,第一句体现出晴雯对宝玉发自内心的体贴,后两句又展示了她掐尖要强,尖酸刻薄的性格要素。这种“心比天高,风流灵巧”而又直爽透明的性格,以及字里行间隐隐显现出的对宝玉的温情关爱,与《红楼梦》中的晴雯几无二致。
《金粉世家》有一个近于贾府的金总理大宅,这里的冷清秋就是一个摩登林黛玉,金燕西亦可称得上是一个时装贾宝玉,其他如贾母、贾政、贾琏、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诸人,可以说应有尽有。金燕西的三角恋爱关系与贾宝玉也颇为相似。同林黛玉与薛宝钗一样,冷清秋、白秀珠两位女主角也都是一弱一强,一贫一富。白秀珠有钱有势,又有表姐即金家的三奶奶王玉芬作内应,她在与冷清秋的爱情争夺战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即使最终赢得了这场爱情的是冷清秋,然而,正如宝黛的爱情一样,金冷婚姻还是以悲剧告终。就象《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后来选择了出家一样,金燕西最终也没有选择白秀珠,可见,在类似的爱情游戏中,林黛玉与薛宝钗是双输的,冷清秋与白秀珠自然也是双输的。也可以说,《金粉世家》是对《红楼梦》中爱情与婚姻的另一类演绎,金燕西的选择及其结果告诉我们,即使贾宝玉最终选择了与林黛玉结婚,也注定同样是一场悲剧。这似乎是“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一个宿命。
在《林黛玉》一文中,张恨水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对林黛玉的独特见解“……林姑娘之不得志于贾府,是其恃才傲物,自有以取之,非众人妒之忌之之故也。使其以事父母者,视贾政夫妇。待姊若妹者,视园中诸姑娘,更以待紫鹃者,视各位丫头。与人无犯,与物无争,朝起夕眠,尽其在我。虽有宝钗袭人之腹剑森森,亦无术而夺其宝玉矣!何则?才本令人可爱,复有德以感之,则爱者更爱,不爱者,亦无所憾于其人也、如是,谗言无隙可生矣”[6]。凡看过《金粉世家》的人都不会否认冷清秋的身上有着林黛玉的影子,她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如美貌非凡才气横溢,又如质本无暇憧憬爱情等等方面。作者对林黛玉的这种认识,也鬼使神差般地体现到了冷清秋的身上,才貌双全的冷清秋如果性情上再温婉点,她自然会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少奶奶,这从金荃夫妇一开始对她的喜爱中完全看得出来。可惜红颜命薄的冷清秋的余生如她的名字一样的冷清。在同心上人结婚仅仅一年以后她就带着一个孩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以至于最终不得已卖文为生。生活环境的不同,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固然是现实存在,但是她那种没了爱,宁愿一切都不将就的书生意气,也使她的结局有了一点悲壮的意味。
显然,张恨水凭着自己对《红楼梦》的深刻理解,在自己的小说人物性格塑造上巧妙地借鉴了《红楼梦》中人物性格的模式,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系列。
2 小说表现方式中的“红楼”笔法
《红楼梦》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由外向内,由反映社会重大矛盾向透视家庭琐事的真正转变,它将关注社会风云的眼光尽量收缩,并聚焦在家庭这个细胞上面,这种转变不仅是空间变换,更是观念更新,即通过最熟悉、平淡和琐细的家庭人事反映社会人生。这种由小处着眼,通过多种表现方式写出“神韵”和画出“灵魂”的描写方法,往往具有“绣花针”的穿透力,也具有“点石成金”的神奇效果。张恨水的小说也常用到这一手法。《金粉世家》同样是将笔力集中在家庭小事,通过人物的日常平凡生活来表现现实社会,以达到以小写大的艺术效果。曹雪芹是“以多写少”的妙手,“黛玉落泪”这一细节在《红楼梦》里反复出现,以映衬她孤独寂寞、多愁善感的性格;并暗示了她悲惨的命运。张恨水笔下的冷清秋也是时常落泪伤怀,这显然也有着林黛玉的影子。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上,《红楼梦》经常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式来安排人物出场。为表现王熙凤的泼辣放肆,作者这样写道:“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着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7]。这种写法更有助于表现人物鲜明的个性。在《金粉世家》里,张恨水也常用这一艺术技巧,而且运用得相当广泛和娴熟。在第14回中,作者这样写三少奶奶王玉芬:“敏之还没答话,只听门外一阵笑声,有人说道:‘这是谁长得这样标致?把秀珠妹妹比得这样一钱不值。’在这说话声中。玉芬笑着进来了”[8]。一边“笑”,一边大声地说话,这多么象王熙凤的性格。而《真假宝玉》中麒麟童的出场则是这样写的:“那美人一句话未了,只听见桃花石背后,破锣也似的答应了一声‘来了。’当时用目瞧去,……就象喝醉了酒的焦大一般”[5]。果然是个如芳官所说“哪个不骂他”的人物。
在一些小说的情景设计方面,张恨水的作品简直可以说与《红楼梦》的类似情景异曲同工,如《春明外史》第22回写妓女梨云临终时情景:“梨云将杨杏园的短棉袄一拨,看见他腰上系着一根古铜色的丝带,说道:‘你这根带子颜色很好,我很喜欢,你换给我罢。’说时她伸手到被窝里去,将自己一条宝蓝色的丝带拿了出来,给杨杏园。杨杏园明知她的用意,连忙就将带子换了,把自己的交给梨云,梨云也拿进被里去系上[9]。”再看看《红楼梦》第77回 :“晴雯拭泪,就伸手取了剪刀,将左手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铰下,又伸手向被内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并指甲都与宝玉道:‘这个你收了,以后就如见我一般。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就象还在怡红院的一样了。论理不该如此,只是担了虚名,我可也是无可如何了。’宝玉听说,忙宽衣换上,藏了指甲。晴雯又哭道:‘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 ”[10]。两者对照之下,一条丝带、一件红绫袄,将有情人生离死别时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又细致入微:同是有情有意,临终却不能尝夙愿的恨别,两部小说对同样的情景的表达如同同出一辙,这里显然有《红楼梦》对张恨水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因素。
张恨水曾经这样赞赏高鹗对《红楼梦》的续作:“而第一件,就是高氏能猜得曹雪芹的意思,打破中国小说团圆的旧套,用悲剧来作终局。因为这样,惹了天下痴心儿女不少的眼泪,抬高红楼梦不少的价值”[11]。张恨水对《红楼梦》悲剧情调的理解自然也渗透到他自己的作品之中。张恨水的《夜深沉》、《春明外史》、《秦淮人家》等大多作品均以悲剧结局,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作者更叹息道:“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吾有家人相与终日饮食团聚,至乐也。然而今日饮食团聚,明日而仍饮食团聚否?未可卜也。吾有吾身,今日品茗吟诗,微醺登榻,至逸也。然则今日如此,明日仍如此否?又未可知也。最亲近者莫如家人,最能自主者莫如吾身,而吾家吾身,吾终莫能操其聚散生死之权。然而茫茫宇宙间,果何物尚能为吾有耶”[8]?恰在此时,作者又失去了自己的爱女,现实的心境与难以摆脱的红楼情结缠绕在一起,于是,作者让我们看到,金总理一死,再加上一场无情的大火,曾经是巨富之家的金家便如《红楼梦》所言的那样“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呼啦啦似大厦倾”,“金粉世家”的金家这样悲剧性地了结了。
当然,张恨水小说表现方式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红楼梦》乃至于中国传统文学借鉴这个层面上,他同样有效地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心理描写等重要表现方式。在塑造自己故事里的主人公时,他选择表现方式的依据是如何把这个人物活生生地带到读者的面前。
3 梦里人生与梦境描写
不管曾经遭遇怎样的质疑,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所提出的色空观还是让许多红学研究者深信不疑的,顾名思义,《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名字就是一个最恰当不过的隐喻──人世的繁华不过是红楼一梦而已。而对于张恨水,美国学者麦克莱伦曾经指出其小说中有一种“如梦的色彩”和“浪漫的感伤主义”,“给现实涂上一层如梦色调,意在安慰读者,而非激发、鞭策他们”[12]。《金粉世家》快要结局的时候金太太的那番感慨正好印证了这种观点,当寂寞地在西山别墅度其残生的金太太回首热闹繁华的北京城时,她不禁感叹道:“我们在那里混了几十年了,现在看起来,那里和书上说的蚂蚁国招附马,有什么分别?哎!人生真是一场梦”[8]!
《八十一梦》是张恨水在抗战时期的一部讽世力作,这部作品由作者的十三个“梦境”构成,这些“梦境”虽然在表面上毫不关联,却在思想上构成了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的不正常现象的讽刺。如果抛开思想上的因素,仅仅从形式的角度来给二者作一下比较,《真假宝玉》简直就可以成为《八十一梦》中的“第十四个梦境”。
两者的相似同样源于《红楼梦》对作者的影响。《红楼梦》每当写到宝玉梦入“太虚幻境”时,并不是刻意地写主人公如何进入梦境,而是让其自然而然地进入其中。如《红楼梦》第五回“开生面梦演红楼梦 立新场情传幻境情”这样描写宝玉进入梦境:“那宝玉刚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正胡思之间,忽听山后有人作歌曰……”[7]这样,读者初看上去,并没有意识到作者是在写梦境、幻境,而是习惯性地认为主人公进入了一个现实世界的真实领域,最后又通过与现实生活迥异的幻境的展示来提示读者,让读者最终明白这是个梦境。这样一来,梦境与真实之间相互掺杂,造成一种亦真亦幻的效果,从而让我们领略到作者那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感慨,最终明了作者以虚构的小说来讽喻生活的现实的良苦用心。
类似的情形在《八十一梦》中也是比比皆是,如第十梦《狗头国一瞥》先写作者在传统小说《镜花缘》、美国电影《狗之家庭》中的见闻,此为实,再写自己狗头国的经历,则已入梦矣。
通过这样的叙写,二部作品都同样巧妙地达到了在主人公入梦时让读者不知不觉,而入梦后又让读者似知似觉,出梦时却令读者大知大觉的效果。
曹雪芹在书中写了大小 33个梦幻,“托之于梦,折射生活”的创作理念使得《红楼梦》把国人的历史性生存状况归结于“梦”,这也是《真假宝玉》与《八十一梦》的共同特色。在《真假宝玉》中,作者通过宝玉的所见所闻,让当时的名角都在同一个“梦”的舞台里表演了一番,从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言,在这里写宝玉是假,评时下流行的戏曲演员才是真。这种有意为之形象化的戏曲论既能达到评论的目的,又能游戏文字,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可以说是从形式到内容都投合了鸳鸯蝴蝶派供人消遣的创作目的。到了《八十一梦》,时事的发展和文人的良心使得作者再也无法游戏消遣了,因而生活的折射由仅供消遣的戏曲转向了严酷的社会现实。作者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之下,用平常的手法写小说而又要替人民呼吁,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之,他使用了中国文人的老套,“寓言十九托之于梦。”既是梦,就不嫌荒唐,放手写来,将神仙鬼物一齐写在书里。这样一来,无论是哪个有权势者对作者如何刁难,威逼恫吓,但小说究竟是小说,何况还是写“梦”呢。
既然是梦境,又是现实,作者在写作时就不得不两者兼顾,让读者能“读得懂”。为此,作者又不得不以暗示的方式把梦境和现实联系到一起。在《真假宝玉》中,作者是用梦境中的现实环境的营构来实现这点的,作者写道:“……只见那省亲别墅牌坊上,对联却换了,一面是欧风美雨销专制,一面是妙舞清歌祝共和”[5]3。这里,作者以空间环境与时间环境错位的形式,将读者的思绪一下就从梦境拉到了现实之中,读者从而恍然大悟,原来作者的“梦”是有所指的。同样,在《八十一梦》中,这样的暗示也比比皆是,如第三十六梦《天堂之游》中,天堂神仙开起了银行、介绍所,他们的会议形式竟然与人间的现代会议如出一辙。古代美女潘金莲竟然穿着性感时髦,甚至坐上了小汽车。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真假宝玉》仅限于对现实的客观评论,而《八十一梦》显然是对不合情理的现实世界的讽刺。
由此看来,张恨水在做着一个曹雪芹似的梦,这个梦使得他时而怅然若失,时而又义愤填膺。
综上可见,作为一位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对《红楼梦》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这种见解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论文中,同时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从而使得他的许多小说都留下了某些《红楼梦》的影子。当然,张恨水生活的时代已经不是《红楼梦》产生的乾隆盛世了,时代潮流和作家的文学追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恨水只是借用了《红楼梦》的一些外壳而已,他笔下的主人公们已经不是大观园中的才子佳人了,他们忠实地体现着另一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感受并表达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1]范伯群.张恨水研究与中国通俗文学理论建设工程[J].通俗文学评论,1994(4):23-25.
[2]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张恨水.张恨水作品经典·散文与杂文[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7-8.
[4]张恨水.金粉世家·序[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
[5]张恨水.真假宝玉[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6]张恨水.林黛玉[N].立报,1935-10-01.
[7]曹雪芹.脂本汇校石头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8]张恨水.张恨水文集·金粉世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9]张恨水.张恨水文集·春明外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85.
[10]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金城出版社,1998.
[11]张恨水.红学之点滴[N].世界日报,1927-09-03.
[12]麦克莱伦.从梦幻浪漫主义到噩梦现实主义[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章建文
Abstract:Zhang Henshui has a high status in Chinese popularnovel circle.His literature achievement is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among whichA Dream of Red Mansionexerts great influence,especially on the personal characterization,manifestationmode anddescriptionofdreamworld.
Key Words:Zhang Henshui;A Dreamof Red Mansion;Personal Characterization;Manifestation Mode;Description ofDreamWorld.
ADreamofRedMansionandZhangHenshui’s Novels
XuSiyou,ChenGuangshi
(Chinese Department,ChizhouCollege,Chizhou,Anhui 247000)
I206
A
1674-1102(2010)04-0053-04
2010-06-2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ZW091);池州学院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XK0916)。
许思友(1969—),男,安徽桐城人,池州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艺学;陈广士(1971-),男,安徽青阳人,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理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小说研究、张恨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