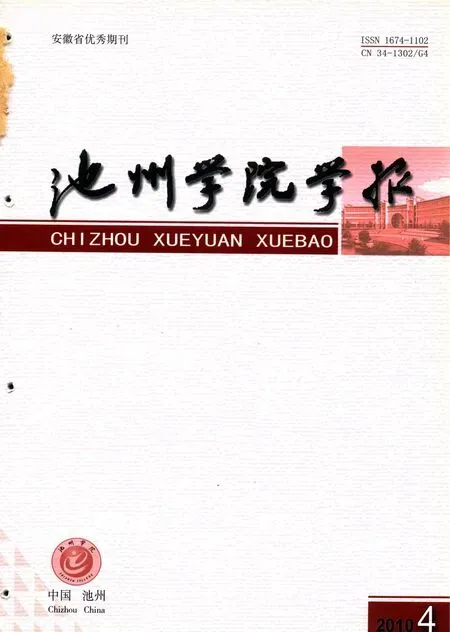李清照晚年再嫁悲剧
——从易安居士与池阳有关的人和事说起
丁育民
(池州日报社,安徽池州247000)
李清照晚年再嫁悲剧
——从易安居士与池阳有关的人和事说起
丁育民
(池州日报社,安徽池州247000)
生活在两宋之际动荡年代的一代词宗李清照,是一位经历坎坷极具争议的非凡女子。千年以来研究李清照的学者如云成果丰硕。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李清照与古池阳这一特定地域时空,联系她连遭夫君暴亡、晚年再嫁、百日离异的人生悲剧作深入、具体的考证和探讨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李清照坎坷人生和古池阳(池州)这一地域文化提供一些新的视角、新的史料和新的线索,以正某些差误。
李清照;再嫁;池阳;悲剧
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的晚年在两宋之际战乱颠沛流亡中曾两度涉足池阳(即池州,有时又称“池阳郡”),因此池州人以此而荣,津津乐道。然而,殊不知李清照与池阳有关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偏偏与她晚年在病中连续发生的夫君暴亡、晚年再嫁、百日离异、九天牢狱的人生悲剧有着某些牵连。
正因为李清照与池阳有了这一段含悲的因缘,笔者才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沿着时光的隧道,走进古老的池阳,寻找她苦难的行踪,探考她晚年的悲剧人生。
1 何时何因 涉足池阳
自古以来,人们讲起李清照,总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有景仰,有感叹,有褒有贬,褒贬不一,竟有天壤之别。
褒者,是因她独树一帜千古流芳的旷世杰作。虽说她流传至今的清丽动人的作品,仅存50余首词、10余首诗、8篇文章,然而,她的这些作品确是光耀千年的不朽精品。尤其她的词被誉为 “易安体”;她杰出的才华,被尊为“婉约词宗”,曾倾倒了古今多少心高气傲的男子汉诗词大师们。公元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竟用这位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女词人的芳名,命名水星上的一座奇峰[1]。于是,“李清照”这个名字,与日月同辉,照耀世界!
贬者,则由于她晚年再嫁、百日离异而产生的千古遗恨。果真应了“红艳薄命”这句老话。
那么,李清照究竟在何时、原何因来到池阳的呢?还得由“易安难安”的坎坷人生从头道来……
1.1 夹在新旧党争中颠簸
李清照(1084~约1155),山东济南章丘明水镇人,享年七十三岁[2]。父亲李格非(字文叔),“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官居礼部员外郎,中书省正六品,系追随苏轼的“保守派”、旧党人物。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18岁的李清照,与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字德甫,一称德父)结为伉俪。赵明诚是宰相赵挺之的季子,以父荫,历任州郡地方官,是位著名的金石鉴赏家、收藏家。赵挺之系改革派王安石变法集团中重要的新党人物。由此可见,李清照的父亲是旧党要员,公公又是新党头目。她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夹在激烈的新旧党争之中,遭受颠簸沉浮是不可避免的了。
李清照婚后第二年(1102)七月,其父李格非被打入“奸党”“元祐党人”之列,全家被逐出京都,李清照被迫离开了御赐宅第汴京府司巷,回明水老家栖身[3]58,与新婚良人,劳燕分飞;大观元年(1107)三月,公公赵挺之被罢官后5天去世,死后3日,丈夫赵明诚和他两个哥哥存诚、思诚,一起被捕入狱。七月获释,一齐被赶回老家青州。李清照又随夫“屏居”(隐居,或称闲居,但不许做官)青州十年之久(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有:“后屏居乡里十年”句)。政和元年(1111)初,朝廷为赵挺之平反昭雪。一年之内,三个儿子相继官复原职。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金兵破东京,史称“靖康之变”。翌年四月,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俘,与宗室、后妃、辅臣、乐工、工匠等数千人和大量珍贵财物被劫,汴京洗劫一空,北宋亡。五月,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继皇位,尊高宗,改年号为“建炎元年”,建立南宋王朝。这年(1127),44岁的李清照举家南渡逃亡,七月[3]283,复起直龙图阁赵明诚受诏出守江宁,兼任江东经制副使。七月议定,八月上任[3]294。谁知这里竟成为赵明诚人生中致命的一个坎子,自然也必将影响到作为江宁“第一夫人”李清照的命运。
1.2 蒙羞千古的“缒城宵遁”
南宋建炎三年(1129),早春二月,赵明诚刚刚接到调任湖州知州的诏令。这时,御营统制官王亦率京都御营军队驻扎江宁。王亦的官职虽低于赵明诚,但御营统制的军队直属朝廷,不归江宁府管辖。王亦利用新知州尚未到任,赵明诚调湖州又未离去的交接之机,在江宁谋变,以夜间纵火为号,起兵谋反。江宁是京都要地,事关朝廷安危。这事让江东转运副使、直徽猷阁李漠得知。李漠急向尚未离任的赵明诚告密。哪知赵明诚认为自己已经调离江宁,此事与己无关。李漠见赵明诚对这样十万火急的军情不予理睬,就果断地采取单独行动,组织平叛,使王亦阴谋失败,伧惶斫开南门逃跑。拂晓,李漠匆匆跑去向赵明诚报告平叛详情,哪知赵明诚与江宁府通判毋丘峰、观察推官汤允恭三位州府首长,竟在夜间,趁兵乱之机,从城墙上吊下绳索,弃城逃命去了。 这就是史称 “缒城宵遁”之劣迹[3]83。
三月,赵明诚以“弃守建康城”获罪,被罢官。毋、汤二人各降二级官衔。这样,赵明诚江宁就没法待了,湖州也去不成了!怎么办?前思后想,“是非之地不可留”,“三十六计走为上”。决定举家出走,暂避风头。朝中之事,由两个复官后的兄长出面走走关系,通通关节。于是,与夫人李清照雇了一艘大船,带上家中的几个老仆和旧部,载上从青州带来的十五车大小几十箱珍贵古董文物,匆匆离开了京都建康(建炎三年五月八日,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今南京)。李清照撰写的《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后序》),是最详细、最系统介绍她与丈夫赵明诚一生经历的信史资料。文中记载了赵明诚罢官后,夫妻乘船西行的经历:
己酉春(建炎三年)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
这是李清照第一次来到池阳。池阳有幸,与千古第一女词人李清照,结下了历史之缘。
2 生离死别 泪洒池阳
2.1 初到池阳
赵明诚于建炎三年三月罢官,与夫人李清照带着家佣、旧部乘船西行,从江宁溯江而上,经当涂,过芜湖,原来打算到江西赣江之滨安家定居的。五月初夏,来到了山清水秀的池阳。
赵明诚和李清照到池阳,并非盲目而来。他在池阳并非举目无亲,曾有几个人际关系。赵明诚作为京都太守,在州郡地方官吏中自然名声显赫。因此,他在池阳郡至少有三个同朝为官的熟人。
一个是,池阳郡守刘子羽(字彦修),福建崇安人,资政殿学士刘韦合之子。宣和末,韦合守真定,金人入寇,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韦合死于“靖康之难”。刘子羽建炎三年知池州[4]。这个刘知州,是赵明诚携家来池阳,并决定临时在池阳安家的重要关系;
另一个是,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人,时任江东宣抚使,守池州及太平。“建炎元年(1127)十一月,(金兵)真定军张遇陷池州,知州滕祐弃城逃亡。制置使刘光世讨张遇于池州”[5]卷12《兵事》。 也许刘光世与知州刘子羽一样,也是赵明诚来到池阳安顿定居的重要关系;
再一个是,驻劄御前亲军都统制程全。刘光世和程全二人的官衔,都在知州刘子羽之下,但他们的部队都直属朝廷,“都受兼江淮宣抚使守建康(江宁)的杜充节制”[5]卷12《兵事》。
江南五月,初夏和风。李清照一家所乘的舟船,溯长江而上,抵池阳,入内江,从城北清溪镇(今下清溪)沿清溪河而上,直达古老的池阳郡府城南通远门外桃花渡。那里古时有一座浮桥,名叫“济川桥”(明代水毁,建石桥,改名“通济桥”,俗称“南门大桥”)。李清照来时,浮桥北岸东侧,有一个府城最大的水运码头,俗呼“南门水埠头”[5]卷6。在这里,赵明诚和李清照夫妻受到了池阳知州刘子羽一班人的迎接。当时赵明诚在朝廷也是很有名望的人物。在官场上,他是京都府衙首长,非同一般;在金石学术上,又名闻朝野;加之夫人李清照诗词独倡一家,“文章落纸,人争传之”[6]卷14,饮誉文坛。这些当时都使他夫妻俩成为闻名天下的人物。再加这次举家来到池阳,满载珍贵文物,更是引人注目。于是,李清照夫妇的到来,一时轰动了古老的池阳城。
2.2 码头送别
李清照一家来到池阳,受到池阳州官刘子羽的礼遇。不几日,大约在五月底或六月初的一天,突然郡守刘子羽兴致勃勃地来到赵明诚的住处报喜,送来了高宗皇帝重新任命赵明诚为湖州知州的诏令。刘热情挽留赵明诚和李清照把家在池阳城内安顿下来。李清照见池阳古城古色古香,江南水乡,风光雅丽,且民风纯朴,与外地相比,显得多了几分安逸,欣然赞同,暂居池阳,让赵明诚独自赴京应召。
算来,从二月罢官,到五月底或六月初“被旨知湖州”,前后仅仅三个月,就官复原职,怎不令赵明诚和李清照喜出望外呢!个中原委,唯赵明诚和李清照心知肚明。据后人猜度,认为他俩有几个在朝中为官的亲人起了作用:明诚的两个妹婿,一个兵部侍郎李擢,另一个礼部员外郎傅察;还有一个是清照同父异母的小弟任敕局删定官的李迒。他们所任都是朝中要职,系“皇帝身边的人”。还有明诚的两位兄长存诚和思诚,分别担任广州和泉州的州官,都属封疆大吏。因此,笔者认为,此说颇有几分道理。
按照朝廷的惯例,赵明诚在接到皇上的任职诏令后,应立即进京“过阙上殿”,晋见高宗皇帝,面受圣谕。根据赵明诚当时的心情,可说是绝处逢生,深感皇恩浩荡,感恩不尽,定然是要立马进京,例行召对。于是,他重托刘知州照应家眷和所带文物家产,并决定将家暂时安顿在池阳郡府附近定居,自己骑着郡守刘子羽提供的马匹,单身从陆路官道赶往京都“赴召”。李清照事后在《后序》中,有赵明诚在池阳城南桃花渡南门水埠头,与夫人李清照匆匆分别时的精彩记载:
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
李清照这段以她第一人称的文字,活脱脱描绘出了她与夫君在池阳南门水埠头分别的感人情景:在(建炎三年)古历六月十三日,考虑到当时载着这么多珍贵金石文物从水路走已不安全,时间又慢,明诚急于赴京面圣,以表感恩之情。就不能像来的时候那样乘舟缓缓而行了。明诚将简单的行囊从船上搬上岸,放到马背上,弃舟骑马,准备出发。临行前,我在船上依依不舍地望着他坐在池阳南门桃花渡水埠头上的样子。只见他身穿棉麻混织的夏衣,头上扎着汗巾,露出宽阔净亮的前额,显得十分潇洒、十分兴奋。神情如虎,双目明亮,灼灼射人,深情地望着船舱里,与我告别。在这兵荒马乱南宋小王朝风雨飘摇之际,我将与丈夫突然在异乡分别,留下这么多珍贵的文物古董,千斤重担落在了我一个女人的肩上,我既难过,又恐慌。如何安排呢?希望明诚临行有个交待。于是,对他喊道:“如果你走后,池阳城里发生了危急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明诚站立在池阳南门码头上,远远地用手比划着回答:“你就随大流,跟众人逃吧。如果真正情况危急,万不得已时,你就先扔掉那些笨重的家具;再不行,就甩掉衣服被褥之类东西;还不行的话,你就丢掉那些书籍、书画卷轴;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最后你就扔掉那些古董器皿吧!唯独只有祖宗灵牌等宗室礼器,你一定要以生命保护,一定要亲自把这些珍贵的礼器牢牢抱在怀里,誓死与这些传家之宝共存亡。你千万千万不可忘记了!”说罢,他遂策马飞驰而去,再没有回头。
赵明诚在岸上千叮咛万嘱咐,船舱里李清照含泪连声应诺。池阳城南门桃花渡水埠头留下了一幅千古流传的“李易安码头送夫”的情景。
2.3 悲泣建康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七月底,李清照在池阳送别夫君赵明诚赴京面圣才仅仅一个多月,池阳郡守刘子羽匆匆送来了丈夫赵明诚病卧建康的告急家书。
李清照见信,得知明诚冒着酷暑,一路之上,鞍马劳顿,中暑染疫,病卧京都,大惊失色,万分焦急。她在《后序》中追述当时的心情。曰:
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
李清照深知丈夫性子急。去京都时,就怀着罢官不久又得圣恩的感恩之情,所以才冒着酷暑,日夜兼程,劳累过度,感染疟疾,病倒在帝王行宫所在的京都建康。李清照又懂医道,知道疟疾这种恶病,发作时全身忽冷忽热,颤抖不止,齿寒作响,痛苦万分。明诚如何耐得住这般折磨,必定会服用大量退烧的寒性药物,就容易患痢疾恶病。这样两病并发,寒热交加,生命就危在旦夕了!李清照愈想愈可怕、越想越焦急。在知州刘子羽的关照帮助下,留下两名跟随明诚多年的老部下,看管留存在池阳城临时住宅里的古董珍宝。自己带着贴身老仆人,连夜乘轻舟启程,顺江而下,一天一夜航行三百里水路,直驰建康。
丈夫暴病,来得太突然了,犹如五雷轰顶。原以为夫君奉旨面圣,领取诏命,很快就会返回池阳,带着她一道同往湖州赴任的。哪知池阳,竟成为他们夫妻生离死别的地方,成为她命运走下坡的一个可怖的转折!
待李清照火急火燎赶到建康,见到病危中的赵明诚时,果不出所料,他服用了大量去热的寒性中草药,不仅疟疾没得到控制,又患上了可怕的痢疾,腹泻不止,病上加病,病入膏肓!这时,已是回天无术了!她在《后序》中继述道:
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屦之意。
李清照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又不忍心问奄奄一息的赵明诚临终遗嘱,对后事的安排。建炎三年八月十八日那天,赵明诚自知再也起不来了,临终取笔作绝命诗,写完就溘然去世了。根本没有像曹操临死那样留下《遗令》,作“分香卖履”之嘱,对妻妾的生活作了周到的安排,就这样丢下我,撒手而去了。这里李清照用“分香卖履”之典[3]34,正说明赵明诚生前“曾经有过蓄妾之事”,印证了李清照对她与明诚夫妻生活中存在的难言之悲苦。“殊无”二字,又含有“赵李无嗣”的隐衷。印证了她“只能采取怨而不怒,或不怨不怒,甘愿‘从夫’的态度”[3]35。
这年,正值赵明诚49岁,李清照46岁,一对相知相伴二十八个春秋的恩爱夫妻,就这般匆匆生死永别了……
无限悲痛的李清照,当时曾为亡夫赵明诚写下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后人称作《祭赵湖州文》,可惜全文早已散佚失传,仅剩文中“四六”骈文[7]的一对颇寓深情的残句:
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
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
李清照在这对残句中,引用了两个典故,表达了自己丧夫之痛。前一句,“庞翁”,乃唐代著名禅宗居士,临终前,令其女儿灵照,出门去看看太阳到了什么时辰了?女儿回来告诉说,日头已至中天正午,并说日边有晕。庞翁闻报,也出门去观看日象。哪知女儿灵照趁机坐到父亲的座位上,合十化灭。庞翁回屋见状,惊叹女儿悟性高超,禅机非凡。后一句,“杞妇”,乃春秋时齐国大夫杞梁之妻。杞梁在进攻莒国的战争中阵亡,杞妻悲伤痛哭,竟哭塌了莒城。李清照以此典自比杞妻,因失去丈夫而悲痛欲绝。
这年(建炎三年)是闰八月,李清照料理完丈夫的丧事,感到孤苦伶仃没有地方可以投靠。这时,时局已越发紧张了。她在《后序》中所言“朝廷已分遣六宫”,指的就是这年七月,隆祐(即哲宗赵煦后孟氏)皇太后率领六宫逃往洪州(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之事。又听说为了阻击金兵,长江都要封锁禁渡了。李清照万分担心留在池阳临时住处的两万多卷古典书籍、两千多卷金石刻本和所存的足可供上百客人使用的家俱、被褥,以及相当数量的古董器皿等贵重物品,不知如何是好?急中生智,她想起了赵明诚的妹夫李擢,是护卫隆祐太后率领六宫逃往洪州的兵部侍郎,只有将这些珍贵文物送到洪州去交给他代为保管,是最为保险的了。亡夫重托,是未亡人心中天大的责任。于是,李清照顾不得沉疴病痛,立即带上老女佣和赵明诚生前手下旧部吏,抱病重返池阳的临时住处[8]144。
这是李清照第二次到池阳古城。
李清照第二次池阳之行,拖着病体,急急忙忙,慌慌张张,形如救火,十分仓促,时间十分短暂。当她赶到池阳郡府衙门北边与池州府儒学之间的塔上街临时住处,见到留下的两位明诚生前“故吏先部”,看管的数十箱未曾拆封的珍贵古董文物安然无恙,心中万分感激。当即在池阳郡守刘子羽的帮助下,雇用可靠船主。李清照又千叮咛万嘱咐,托付这两位“故吏先部”,负责押运这批文物珍宝,送往洪州,面交妹夫李擢。李清照自己只捡了一小部分轻巧的小件稀珍文物,随身携带,就是她后来在《后序》中所说:
“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抄)写本李 (白)、杜(甫)、韩(愈)、柳(宗元)集,《世说》、《盐铁论》(西汉桓宽著),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李清照在送走了“故吏先部”去洪州的舟船之后,连夜带着老佣人乘船沿江而下,告别池阳,返回建康。
李清照来去匆匆,刚刚离开池阳不久,池阳城就发生了重大变故。“建炎三年秋冬,(金)兀术(兵)下太平(今黄山区)。分兵向池州。池州驻御前亲军都统制程全,以众寡不敌,欲坚壁待援。时受建康知州兼江淮宣抚使杜充节制。(杜)充檄(令程)全出战甚急。(程)全不得已,率麾下与金兵激战,败溃死亡”[4]。所辖在池阳的驻御前亲军溃散。李清照闻此噩耗,大惊,甚感不幸中之万幸,免遭此劫。不料洪州局势骤变。由于隆祐太后所率六宫一行,浩浩荡荡,目标太大,引得金兵穷追不舍。直追至洪州时,守臣弃城逃亡抚州(临川郡,今江西临川),太后一行则退去虔州(即赣州),李擢和他的父亲也都早已逃之夭夭。入冬十二月,洪州失陷。李清照托明诚生前两位“故吏先部”,从池阳运去的这么多辛辛苦苦从青州千里迢迢运来的十五车珍贵文物古董,“又散为烟云”,丧失殆尽矣!李清照闻讯,深感有失夫君生前重托,懊伤至极,又大病一场,“仅存喘息”……
这时,李清照在走投无路之际,只有“往依”“任敕局删定官”、继母王氏所生的小弟李迒,紧紧追赶朝廷御舟而行,却又时时扑空。李清照在金兵的追击下,带着病体,在浙东一带经历着颠沛流离惊恐凄惨的逃亡生涯……
3 再嫁匪人 缘起池阳
真是老天不灭南宋。建炎四年(1130),浙东海上一场风暴海啸,吓退了不习惯海战的金兵,仓皇逃亡中的高宗皇帝赵构,才得已脱身,驻跸越州州治会稽。翌年,改元“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以州名为府名。期间,高宗数次下诏,褒录“元祐忠贤”。李迒也由宣义郎再转(升)一级官职。
绍兴二年(1132),是李清照陷入人生悲剧的又一个年头!这一年春,李清照追随朝廷到临安(即杭州),四五月间,病中再嫁,所遇匪人。“匪人”者,“取义于李朝威《柳毅传》的‘不幸见辱于匪人’。李清照的再嫁酷似洞庭龙女远嫁泾河小龙之不幸,所遇均为行为不正当之‘匪人’”[3]90-91。 这一年,亡夫三载、年届四十有九、双鬓苍苍、重病缠身的李清照,在她孤寂凄惨的生活之中,突然闯进了一个卑劣匪人!
这个“匪人”,姓张名汝舟。
3.1 张汝舟何许人也
张汝舟,浙江归安人。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霍端友榜进士,北宋时仕履不详。绍兴元年(1131),任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参见《浙江通志》卷一二四;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四三、卷五八。)以承奉郎特迁一官往池州措置军期事务[8]149。担任驻军的“职筹军务审计”。这个军中小吏,是负责检查审核军队粮草、军需供给和军中官员的俸禄待遇等事务。大都是在新组建队伍时,才委派这类军中官吏前去“职筹”“审计”。所以他官衔品级虽不高,但在军中却举足轻重。
据考,“池州自孙吴时,为濒江兵马之地。”“(北)宋(时),江南分东、西路。江东(路)置宣抚使,守太平及池州,而池州有驻劄御前诸军统制。南渡后,以建康、太平、池州系要隘口,共一十九处,领集民兵,共相把截。建炎四年,复合江东、(江)西为江南路,置帅(统帅部)于江、池二州,时有安抚制置使。未几(翌年,绍兴元年),以二州地僻隘,罢帅(撤消江南路统帅部)。仍以东路还建康,西路还洪州。而池州水军,有都统制、有副都统制,皆领军事,时则乡兵有‘勇敢’;水军有‘清溪’、‘雁汊’,控海军千五百人”[5]卷12《武备志·兵制》。 这个军中张汝舟到池州,正是为“措置”这一时期程全统制的池州驻劄御前亲军溃散后,朝廷对池州驻军进行改编的“军期事务”而来。他来到池阳,就住在驻劄御前亲军驻池阳郡城营都司衙(后为池州兵备衙,又称“都司署”),位于郡府衙门北边,与池州府儒学之间的塔上街,和前年李清照、赵明诚夫妻在池阳由郡守刘子羽帮助安排的临时住处,相距很近。这个张汝舟来到池阳后,就听到池阳人有关李清照和赵明诚的许多传闻[8]152。
有说“赵太守(明诚)远道而来,特地在我们池阳城里安家呢。赵太守是什么人?他是京城建康的太守呀! ”
有说“赵太守的夫人李易安,是天下第一女词人!她相貌端庄,举止文雅。这样的才女一年之内,两次来池阳,与池阳有缘,是池阳之福啊!”
更有说“啧啧,赵大人和清照夫人,来到池阳时,带来了整整一船金石、文物、古董。从南门大水埠运到住处,整整搬了三天呢!不要说多,就是搬一车子宝贝,我们老百姓一辈子也吃喝不完呀!”
…………
这些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张汝舟这个军中行伍小吏、卑劣小人,大小也是个进士出身,略通文墨,深知官场名望的重要。他对李清照享誉朝野的才华词名和花容月貌,早有耳闻,令他倾倒。这次听到她竟然拥有这么多稀珍文物,可说是价值连城啊,怎不令他垂涎欲滴!
其实,当时赵明诚收藏稀世文物珍宝的名气的确很大,朝廷上下想图他手中古董财宝的人,大有人在,就连高宗皇帝宠幸的太医局医官、和安大夫王继先,在给赵明诚看病时,病没有看好,却看上了赵家珍藏的大量古董。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提出要用三百两黄金全部买下赵明诚手中的稀世珍宝。幸亏赵明诚的表兄、兵部尚书谢克家出面,给高宗皇帝上了奏折:“恐疏远闻之,有累盛德,欲望寝罢。”说这事以权势夺人所爱,传出去恐有损圣德,影响不好。皇帝发话,才被制止。这件事,在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七中,已记录在案。可想而知,连皇帝老儿的宠臣尚且如此,何况这个军中小吏卑劣匪人张汝舟呢。岂不更是见财眼开,不择手段了!
3.2 同名同姓 两个张汝舟
说来也巧,查考史料,两宋时期,朝廷确实有两个同名同姓都叫“张汝舟”的官员:
一个张汝舟,毘陵(江苏常州)人,北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进士,宣和二年(1120)任殿中侍御使,因忤上意,于宣和五年降授宣教郎、直秘阁权知越州郡绍兴府。南宋建炎年间,为朝奉郎守明州(唐置鄞州,后改明州,宋初改明州奉化郡)。(建炎)三年(1129)底,高宗奔明州,因其能粗供粮草,不甚扰民,而得迁一官。同时下诏,让明州知州张汝舟与高宗护卫军刘洪道二人对调。由行伍出身的刘洪道暂知明州;朝奉郎张汝舟改任直显谟阁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翌年,又任命为直显谟阁兼管内安抚使,复知明州时,张汝舟请求奉祠,被改为主管江州太平观的官吏[8]149。
另一个张汝舟,乃浙江归安人,就是这个派到池州去办“军期事务”的军中小吏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
两个张汝舟。一个是政声斐然,名闻朝野的明州太守;一个是池阳军中小吏,朝中无名之辈。这就给军中小吏张汝舟有了鱼目混珠的可趁机之机,也成为李清照和李迒姊弟俩之所以“轻信匪人”、上当受骗铸成再嫁悲剧的一个原因。
3.3 受骗再嫁
要讲清楚李清照晚年再嫁悲剧的来龙去脉,她在事后致赵明诚的姑表兄、翰林学士綦崈礼的一封感谢信:《投内翰綦公崈礼启》[9]298-299(以下简称《投綦启》)中,详细叙述了她重病中受骗、晚年时再嫁、经诉讼入狱、方百日离异的悲剧全过程。这封《投綦启》给姑表兄綦崈礼的感谢信,是迄今遗留下来佐证李清照这一段悲剧历史最权威的信史资料。
这里先让我们了解一下綦崈礼其人吧。綦崈礼,字叔厚。山东高密人。北宋政和八年(1118)进士,官历吏部侍郎、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宝文阁学士等。《宋史》有传,曰:“(綦)廉俭寡欲,独覃心辞章,洞晓音律,酒酣气振,长歌慷慨,议论风生,亦一时之英也。”他不仅是赵明诚的姑表兄,而且还是高宗皇帝身边的亲信重臣。建炎三年十二月,高宗在金兵的穷追不舍之下,逃入东海中,这时,跟随御驾南渡的大臣们,一个个各自逃命去了。只有极少几位大臣护驾随行,其中就有綦崈礼。患难之交,倍受重用。他在拯救为难之中的李清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李清照在这封著名的《投綦启》感谢信中,开头一段血泪文字,就诉述了她受骗再嫁,酿成悲剧的真相。文曰:
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蚁不分,灰钉已具。尝药虽存弱弟,膺门惟有老兵。既尔苍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
这段文字,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因近来一直在病中,已将病入膏肓,无法挽救了。她在这里引用了“牛蚁不分”一个典故:晋人殷仲堪父病虚悸,听见床底下蚂蚁响动,以为是斗牛之声。神志恍忽如此,形容病情十分严重。家中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封棺用的铁钉和石灰。明诚去世之后,我身边递汤药照顾我的只有生性懦弱的小弟李迒一个亲人,看管门户照应家务的惟有跟随多年的老佣人、老部下了。廖廖数语,道出了她膝下无儿无女孤苦伶仃的凄惨景象。又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和生性懦弱的小弟李迒,才会如此轻率地相信了匪人张汝舟巧嘴如簧的谎言,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张汝舟见我年近半百,病成了这个样子,膝下又无儿无女,弟弟又老实可欺,才敢与媒人串通,送“官文书”上门来说媒。像南朝始安郡的温峤公说媒时,赠送玉镜台作定信物那样做了假,也未可知啊。我们姐弟难察真伪呀!遂轻信了媒人欺诈之言。
那么,媒人带来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官文书”呢?竟然使见多识广才学过人颇具男子气概的李清照惊恐害怕得“身几欲死”了呢?这无疑是张汝舟和媒人施出的毒计,威逼李清照再嫁的卑劣手段呀。要解开张汝舟派媒人送来的这张“官文书”之谜,还得从李清照撰写的《后序》中寻找答案。文曰:
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遂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廷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
大意是说:明诚在建康重病的时候,阳翟学士张飞卿带了一把玉壶来请明诚过目鉴定。明诚看完后,张飞卿就把玉壶带走了。其实,他带来的玉壶不是真玉的,而是一种与玉近似通称“珉”的石头壶。这事,后来不知被那个别有用心的人造谣生事,无中生有,把这把假玉壶说成是国宝,诬陷明诚将这把国宝玉壶暗地里献给了金国,卖国求荣,当了汉奸。这就是所谓“玉壶颁金”之说。后来李清照又听到传说,有人已经向朝廷告密,要以“玉壶颁金”的罪名,检举、弹劾已故明诚。这可是个通敌大罪呀!明诚虽然死了,他历史上又有“缒城宵遁”被罢官的劣迹,在这兵荒马乱之际,谁会去为莫须有的“玉壶颁金”罪名作调查、帮辟谣呢?我一个女子,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呀。如果一旦事发,朝廷真要追究查办起来,事情就闹大了,不但死去的赵明诚要获罪,被革职除名,就连遗孀我李清照,轻则入宫为奴,重则发配充军,甚至招来杀身之祸。我怎不惊骇,“大惶怖,不敢言”呀!遂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珍贵古董,进献朝廷,以表示对皇上的一片忠心。可是皇帝让金兵追得在浙东一带四处逃亡,无有定处。当我带着古董一直追赶到越州绍兴时,皇帝却已移驾四明了。
因此,如果说媒人带来的“官文书”上写的是“玉壶颁金”之事,是弹劾已故赵明诚的状子,以此要挟李清照逼婚的话,才会使李清照“大惶怖,不敢言”。看来,只有这一种解释,比较合乎情理。才有《投綦启》感谢信中所说的受骗结局:
“僶俛难言,优柔莫决。呻吟未定,强以同归。”
意谓:我在仓促之中,犹豫不决,重病呻吟,身不由己,其情难言,不容分说,只得“强以同归”了呀!这里一个“强”字,道出了匪人张汝舟欺病中李清照孤身弱弟,胁迫她再嫁的全部真相。
3.4 百日离异
李清照病中受骗,仓促再嫁。婚后不久,张汝舟原形毕露,将李清照的人生悲剧,推向了极点!
细加考究,我认为其原因应属两方面的。先说军中小吏张汝舟。他之所以那么主动积极、千方百计、软硬皆施地要把李清照骗婚到手,心里怀着两个鬼胎:一是,倾慕李清照名门之后,才貌出众,一代词宗,“文章落纸,人争传之”,名闻朝野,一心想娶到她为妻,抬高自己的身价,以求仕途飞黄腾达;二是,贪图李清照手里由赵明诚遗下的大宗古董文物,价值连城,一心想只要娶了李清照,就可霸占她手中的珍贵文物财宝,一步登天,成为巨富。有了钱,就可以买高官,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再说李清照。她之所以轻易上当受骗,晚年病中再嫁“匪人”,其原因有三:一是,自丈夫赵明诚染疾暴亡,前后三年时间,一个独身女子,年近半百,重病缠身,孤苦伶仃,精神上需要有人关怀,要有家庭的温暖;生活上也需要有人体贴照顾,安度晚年;二是,三年来拖着重病的身子,颠沛流离,四处逃亡,吃尽苦头,亡夫遗下这么多珍贵的古董文物,在兵荒马乱中丢失了许多,使她雪上加霜。这时,作为一个女人,她是多么希望能有个依靠,能有个人保护年老多病的自己,也能保护亡夫遗下的珍贵文物,不负亡夫生前的重托;三是,为张汝舟花言巧语所迷惑,也为他“官文书”的欺诈恐吓、软硬皆施所威逼就范。
纸是包不住火的。李清照“强以同归”再嫁张汝舟之后,很快就看清了这个匪人的卑劣的面目,自知受了这个小人的骗。把他与前夫赵明诚相比,无论才学、志趣、品德、感情的恩爱等等方方面面,都不可同日而语,有天壤之别。性情清高的李清照,实在是难与这样的匪人相处。
同时,张汝舟很快发现自己受了骗。原以为娶了李清照,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可以霸占她手中的稀世珍宝,发大财,买高官。哪知将她娶到家,她手里根本没有当年池阳人说的那么多古董珍宝,她手中仅存的一点珍品,还死死抓住不让他沾边,时不时还遭她冷嘲热讽。再说李清照当年最怎么才貌出众,名闻朝野,这时已是年近半百的病老婆子了。他当年倾慕之情,也已荡然无存,更不用说甜蜜的夫妻生活和情感了。于是,这个生性粗野的匪人张汝舟,就撕下了一切伪装,竟采取强硬手段,拳脚相加,毒打重病在身的李清照,欲至她于死地,谋夺她劫后余剩的古器书画。
一向清高气傲的李清照,怎受得了这般的凌辱、摧残!她在《投綦启》中,作了血泪的控诉:
视听才分,实难共处;忍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才。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彼素抱璧之前往,决欲杀之。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局天叩地,敢效谈娘之善诉;升堂入室,素非李赤之甘心。
李清照痛心疾首地诉说道:我为自己竟然将晚年之身,许配给这样一个市侩掮客,自己贞洁之身,已被张汝舟这个臭恶之人玷污,万分后悔,万分懊伤,痛不欲生。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摆脱这个卑鄙小人,离开这个凶残恶棍。“彼素抱璧之前往”,其典出“(卫庄公)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与汝璧。’己氏曰:‘杀汝,璧其焉往?’遂杀之,而取其璧。”(《左传·鲁哀公十八年》)意为这个军中小吏张汝舟,正是想用这种法子来杀人夺宝。“遂肆侵凌,日加殴击”。李清照以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文弱书生刘伶自比,怎受得住蛮汉“石勒”老拳的毒打呢。自己再怎么担惊受怕小心翼翼,也怎么敢像南北朝时期乐舞中的“踏摇娘”那样诉苦叫冤呀(《太平御览》卷573)。况且我从来也没有与这种腥臭污秽之人同流合污之心啊!
可是,在古代女子要提出与丈夫离婚是大逆不道之事,朝廷法典上是决不允许的。除非男方主动休书,或是男方另有重罪在身,女子方可提出离异。面对这样男女不平等的封建“王法”,李清照陷入无限痛苦之中,病情越发加重。小弟李迒也因自己的懦弱上当受骗,使病中老姐姐陷入火坑,遭此恶运,自责不已。他心想这个张汝舟,既是朝廷命官,怎么这等卑劣?他是朝廷的敕局删定官,朝中几乎所有一定资历和品级官员的任命告身,都要经过他这里审核备案的。这时他想起了利用敕局删定官之权,查一查这个张汝舟究竟是个什么货色?立即查阅了他当初任官时的档案。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很快就发现这个军中小吏张汝舟的底细。他根本不是那个为官清廉的明州知州张汝舟,而是一个犯有严重舞弊罪行、劣迹斑斑的无赖匪人。
宋朝的官制严格规定,官员升职,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举主”推荐和担保。被推荐的官员如果出了问题,举主就要受到牵连,遭受惩罚。朝廷对此向来是非常认真的。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含糊。据史料记载,连包拯这样的清官也不例外。北宋57岁的包拯“(仁宗)至和二年(1055),(因)坐失保任事,由刑部郎中,左授兵部员外郎,出守本州(池州)。”即包拯因“荐举属吏柳州军事判官卢士安,为凤翔监税”。哪知这位监税卢大人,辜负了包公一片苦心,上任不久,他就大肆贪污枉法,连累包拯由陕西转运使被贬到小郡池州来做知州[4]那么,这个军中小吏张汝舟究竟犯了什么事呢?原来他在由“外任”转为“京官”的呈报中的“举主”人数是虚报的[10]卷59。李迒查得了张汝舟这桩舞弊罪证,立即告诉了姐姐李清照。李清照立即状告张汝舟舞弊之罪,并诉讼要求离异。
可是,根据大宋刑法《新详定刑统·斗讼律》规定,妻子状告丈夫,属“告周亲,以下罪。”“虽得实,徒二年。”就是说,即使所告丈夫的罪行属实,妻子也要因“地告天”的犯上行为,受坐牢两年的惩罚。面对这样严酷的刑罚,李清照宁可身受牢狱之灾,也要状告张汝舟,与他一刀两断。可见她的决心,何等的坚决。这就是敢作敢为的李清照。她这一“地告天”的罪,幸得姑表兄、官居三品的翰林学士綦崈礼出面营救,竟然得到高宗皇帝亲自过问这个案子,下诏:将张汝舟除名,流放到柳州编管[10]卷58。因此,李清照只在诉讼开始时,作为“嫌疑人”在狱中被关了九天,就宣布无罪释放,并解除了与张汝舟的婚姻关系。
这时,正是绍兴二年九月。从再嫁到离异,前后三个多月,正如李清照在《投綦启》信中所言:“友凶横者十旬”的再嫁百日的婚姻、“居囹圄者九日”就宣告离异,结束了遗憾千载的晚年病中再嫁的悲剧。
3.5 千年余波
李清照晚年再嫁、百日离异之事,在古代也是一件惊世骇俗之举!这事发生在李清照这样一位才华出众、性情清高、誉为“婉约词宗”的杰出女词人身上,蜚闻传言,掀起千年余波,就不足为奇了。既然这些流言蜚语中牵涉到的人和事,又多少与池阳有点关连,因而,引起池州人的关注也是必然的了。
自古以来,人们对李清照再嫁匪人张汝舟的评说,褒贬皆有,且都事出有因。
持贬见者,大都是南宋时与李清照同时代的文人。他们有的是出自维护封建礼教的卫道士;有的是由于李清照才华太优秀而怀妒忌之心;还有的是因为李清照在诗词要求上对人过严,无意中得罪了一些文人。这类人在评价李清照晚年再嫁之事,语调尖辛刻薄,贬之又贬,百般讥讽嘲弄。比较典型的有:
南宋胡仔:“(李)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崈礼)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11]。(撰稿时李清照尚在世)
南宋王灼:“(李)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 晚节流荡无归”[12]卷2。 (撰稿时李清照尚在世)
南宋朱彧:“(李清照)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无独厚其才,而啬甚遇,惜哉!”(约稍迟于王灼之后,撰《萍洲可谈》卷中)
南宋陈振孙在李清照去世后成书《直斋书录解题》武英殿聚珍本,卷二一文中,评说李清照“晚岁颇失节! ”
明叶盛:“抑再适张汝舟之后欤?文叔不幸有此女,德夫(甫)不幸有此妇。其语言文字,诚所谓不祥之具,遗讥千古者欤”[13]卷21!
持褒见者,大都是明清时代的文人。他们是一些崇拜李清照词才,惜词宗才女的名声,兹意否认李清照有再嫁离异之事。认为李清照才德双馨,生性清高,且为赵太守的夫人、朝廷命妇,又年近半
百、重病在身,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再嫁之事的,纯属诬陷、恶意中伤。具代表性的有:
明徐火勃:“李易安……作序(《后序》)在绍兴二年,李五十有二,老矣!清献公之妇,郡守之妻,必无更嫁之理。……更嫁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太诬贤媛也”[14]卷7。
清陈文述:“李清照再适说,向窃疑之。宋人虽不讳再嫁,然考序《金石录》时,年已五十有余。《云麓漫钞》(宋赵彦卫著)所载《投綦处厚启》,殆好事者为之。 盖宋人小说,往往污蔑贤者”[15]外集卷7。
清俞正燮:“易安,老命妇也,何以改嫁复与官告”[16]?
清沈涛:为元人画李易安小像索题。沈赋七绝:“月上新词最断肠,缠绵儿女意堪伤。不应人比黄花瘦,却道全无晚节香。”又说:“易安何等女子?况未亡时,年已垂暮。 汝舟之适,亦恐近诬”[17]卷下。
其实,李清照本人对自身受骗再婚的不幸遭遇,也悔恨交加,痛苦不堪。她在写给綦崈礼的《投綦启》感谢信中,直抒心中懊悔之情:
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
在这种尴尬困境,李清照也曾求助于亲戚綦公,曰:“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
有道是,“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李清照一代杰出的女词人,晚年留下难堪的悲剧,已是历史的事实,我们无须为此作无谓的粉饰。我们在关于她悲剧人生洋洋洒洒切切生悲的文字中,却是“病蚌成珠”,使我们看到了古代封建社会一个女词人悲惨的命运,使我们在这些流传千载的纷纷评说中,越发地唤起深深的同情,越发地敬重她出众的才华,越发地欣赏她留下的那些不朽的旷世杰作。
古老的池阳,只是女词人李清照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曾经的驿站,留下了她艰辛的足迹,也留下了她深深的遗憾,更多的则留给后人深沉的思考。
[1]康震.康震评说李清照[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陈祖美.李清照评传·李清照年谱[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209-297.
[3]陈祖美.李清照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明]王崇,校刊.嘉靖池州府志[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5][清]陆延龄.光绪贵池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6]赵彦卫.云麓漫抄[O].别下斋丛书本.
[7]谢汲.四六谈麈[O].学津讨原本.
[8]邓红梅.李清照新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候健,吕智敏.李清照诗词译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10][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60《丽人杂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2]王灼.碧鸡漫志[M].知不足斋丛书本.
[13]叶盛.水东日记[M].中华书局,1980.
[14]徐火勃.徐氏笔精[O].芋园丛书本.
[15]陈文述.颐道堂诗选[O].清嘉庆刻本.
[16]俞正燮.癸巳类稿·易安居士事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17]沈涛.瑟榭丛谈[O].清道光刻版.
[责任编辑:章建文
Abstract:Li Qingzhao,wholivedin the times ofturbulence duringSouth SongDynastyand North SongDynasty,is remarkable and controversial woman suffering a lifetime of frustrations.Based on the former research,the pape makes further and specific stud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between Li Qingzhao and ancientChiyang,herhusband death,remarryingin herlateryears and devoicing afterone hundred days.It provide some newperspectives between Li Qingzhao's hard life and ancientChizyang(Chizhou),and newhistorical data and clues soas tocorrectsome discrepancy.
KeyWords:Li Qingzhao;Remarrying;Chiyang;Tragedy
RemarryingTragedyofLi QingzhaoinHerLaterYears——FromYi’anjushi andPeople andThings RelatedtoChiyang
DingYuming
(ChizhouDailyOffice,Chizhou,Anhui 247000)
I206
A
1674-1102(2010)04-0044-09
2010-06-12
丁育民(1933—),男,江苏宜兴人,池州日报社主任编辑,主要从事李白、李清照、杜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