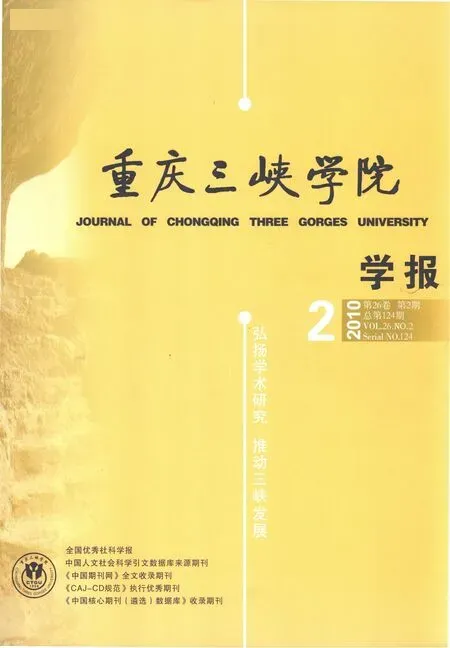何其芳的悲秋情结
——从何其芳大学时期(1930~1935)诗文看
赵思运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何其芳的悲秋情结
——从何其芳大学时期(1930~1935)诗文看
赵思运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何其芳大学时期的诗文显示出浓厚的“悲秋”情结。何其芳与“悲秋”母题的亲和力一方面是由于他的传统文化积淀,另一方面又是他的精神世界与“悲秋”母题的契合。通过对他人生的解读与对他诗文的解读,我们可以探触到他孤僻的心理个性与其人生的无指向痛苦交融成的忧郁、迷茫、孤独的心理场。这一心理场与传统文化的“悲秋”意识是异质同构关系。这种异质同构,使得悲秋意识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积淀下来,而何其芳的精神世界又以文化通约的方式予以接纳。
何其芳;悲秋情结;积淀;精神个性
尽管何其芳在共和国时期是以毛泽东文艺战士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双重身份经历着文坛的风风雨雨,但他却是以一个京派文人的身份,唱着“我爱那云,那飘忽的云”走上文坛的,是在《梦后》的《独语》中走进文学史的。而他的京派文人身份在他的大学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在这一时期,他的诗文有一个共同的情感基调:忧郁、迷茫、苦闷。本文拟就“秋”意象探讨一下何其芳的“悲秋”情结。
一
何其芳1930年同时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年秋天入清华大学读书。不到半年,由于中学文凭问题,被清华大学开除。1931年秋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毕业。所以,何其芳的大学时期应该是1930年秋至 1935年夏。这期间的作品主要刊于诗集《预言》、散文集《画梦录》,以及在 1931年6、7月份自办的《红沙碛》1~3期。
《何其芳全集》[1]之一所收诗集《预言》,共分三卷计35首。其中一、二卷写于大学时期(第一卷收1931~1933年18首,第二卷收1933~1935年12首)。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秋”情有独钟。第一卷18首诗中有9首直接写到了“秋”,11首写于秋天。尤其是有3首写秋天的诗,写于春、夏季节:《脚步》写于1932年5月1日;《昔年》写于1932年7月21日;《秋天(一)》写于1932年6月23日。
何其芳大学期间的散文除《老蔡》、《窗》、《金钥匙》外都收入了《画梦录》,计16篇。情感基调与基本意象和同期的诗歌是十分一致的。忧郁、迷茫的调子以及频率极高的“秋”、“梦”、“夜”、“暮(墓)”等意象,几乎出现于每一篇文章,情感的力的图式是向下的。
《墓》是《画梦录》的第一篇。故事很简单,写雪麟哀悼思念纯洁的农家女孩玲玲。作品动人的不是故事,而是弥漫全篇的忧郁迷茫的情感、情绪。他是借助关键词“秋天”放在“秋天”的背景下来表现的。作品又用了10个“梦”字,与“秋”、“暮”结合起来,形成了苦梦情调。《墓》的结构和话语方式是封闭性的。开篇是:“初秋的薄暮。……”结尾的一段是:“晚秋的薄暮。田亩里的稻禾早已割下,枯黄的割茎在青天下说着荒凉。草虫的鸣声,野蜂的翅声都已无闻,原野被寂寥笼罩着,夕阳如一枝残忍的笔在溪边描出雪麟的影子,孤独的,瘦长的。他独语着,微笑着。他憔悴了。但他做梦似的眼睛却发出异样的光,幸福的光,满足的光,如从Paradise发出的。”以“秋”始,又以“秋”终,情感的氛围从“幽冷”变成了“荒凉”与“残忍”。
由于何其芳的散文基调是“秋天”般的忧郁、压抑,所以文本内部情感的力的图式是向下的。以千字文《秋海棠》为例。虽然题目是“秋海棠”,但是文章的最后一节才写到了秋海棠,前面的文字都是为秋海棠做情绪氛围的铺垫,而这一氛围是通过外物向下的力的图式表现出来的。
第一段就奠定了基调:
庭院静静的。仿佛听得见夜是怎样从有蛛网的檐角滑下,落.在花砌间纤长的飘带似的兰叶上,微微的颤悸,如刚栖定的蜻蜓的翅,最后静止了。
然后,
一缕银的声音从阶角漏出来了,尖锐,碎圆,带着一点阴湿,仿佛从石砌的小穴里用力的挤.出.,珍珠似的滚.在饱和着水泽的绿苔上,而又露似的消失了。
粒粒星,……闪跳着,发射着晶莹的光,且从冰样的天空里,它们的清芬无声的霰雪一样飘堕。
阶下,一片梧叶悄然下堕……
她的灵魂那么无声的坠入黑暗里去了。
大颗的泪从眼里滑到美丽的睫毛尖,……不可重拾的坠下……
关于思妇的描写,有几句话单独成段,依次是:“寂寞的思妇凭倚在阶前的石阑干畔。”——“她举起头”——“她更偏起头仰望”——“她的头又无力地垂下了”。可以看到,其行为动作的力的图式是逐渐向下的,而这一动作正是她的情感、情绪下落的外化。
著名的格式塔心理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认为,力的图式存在于物理领域和心理领域、艺术世界中,它们三者都可以统一于力的基本图式之中。“外在的力”与“内在的力”由于共同的表现性特点而产生同构,也就是说,我们在知觉某种特定的外物时,内心会经验到与外物相同的力——如扩张与收缩、冲突与一致、上升与降落。我们接受作品时,不仅仅看到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事物,而是通过这些表面现象,去感受外物由于运动而产生的情感的力。“声音从有蛛网的檐角滑下”、“声音从阶角漏出来”、“霰雪一样飘堕”、“一片梧叶悄然下堕”、“坠入黑暗里”、“大颗的泪……不可重拾的坠下”,以及思妇的动作,都不仅仅是普通的物理运动,而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它们所构成的向下的力的图式,既是外物所蕴蓄的氛围场的力的图式,又是下沉的情绪之力的图式。
《墓》和《秋海棠》作为《画梦录》的前两篇,以“秋”的萧瑟和秋叶一般向下的力的图式,又为全书奠定的情绪情感的调子。
另外,我还注意到,他早期曾用“萩萩”、秋若”、“秋子”等笔名。1930年11月29日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写的长诗《莺莺》发表时用的是笔名“萩萩”。这是《何其芳全集》里保存的最早的文字。何其芳的《红沙碛》时期一直用笔名“秋若”。自创刊号上创刊词《释名》(1931年5月22日写,6月1日创刊号刊出)起,1931年6、7月于《红沙碛》1~3期发表的12首诗,1932年写于北平、1935年3月刊于《万县民众教育月刊》的《拟古歌一章》,刊于1933年3月5日成都《社会日报·星期论坛》副刊的《无题》诗、《三月十三日晚上》、《初夏》,刊于1935年1月《万县民众教育月刊》的《箜篌引》,近20件文学作品,发表时署名“秋若”,断断续续近5年的时间跨度,充分说明了何其芳对于秋天所拥有的一种独特的况味。
那么,何其芳何以对“秋天”如此迷恋、何以对悲凉、迷茫、苦闷的“秋意”有如此强大的亲和力?我认为,“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母题意象,何其芳与“悲秋”母题的亲和力一方面是由于何其芳的传统文化积淀,另一方面是因为何其芳内心精神世界与悲秋母题相契合。
二
“悲秋”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母题,成为古代诗词的一个意象原型。原型总是共时性地蕴涵着人类的心理感受,使后代人接触以后,即时性地产生共鸣。“秋”,在中国文化里是“忧”、“思”的代名词,往往意味着忧郁、伤感、痛苦。
秋,作为原型意象,有其历史发展过程。《毛诗正义》:“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秋展示的是自然界的转折,展示了自然界由生机勃勃向萧索凋敝的演变,由温暖热烈向寒冷寂寥的滑动,使外界的“冷”与审美主体内在的“冷”形成一种同构性。因而,秋的内涵是物理结构、生理心理结构与社会情感结构的三位一体。秋,意味着时间在年度单位的轮回中趋向终点,故“秋”常与死亡、孤独、忧郁、迷茫有关。
在《诗经》中,对悲秋的描写还大多停留在对时令的客观状写,比如:“喓喓草虫,翟翟阜螽,未见君子,忧心仲仲”(《召南·草虫》);“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秦风·蒹葭》),对秋物的状写只是作为抒情手段起到比兴的作用,还没有真正成为审美主体的心灵对应物。自觉地将“秋”作为客居游子和失意文人的心灵对应物,始作俑者是宋玉,他在《九辩》中第一次自觉地以个体生命的角度感知世界:“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宋玉将“秋”转化为个体心灵对应物,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羁旅漂泊无家可归者的情感世界,他的自觉意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创作。随着个体生命的觉醒,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生命的短暂与无家可归的流浪感,遂与“秋”形成同构,逐渐产生了“被抛”的感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共同弹奏回声不绝的协奏曲。
悲秋作为集体无意识也积淀着社会经验。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战事连绵,每年秋季,大都举行征戍、徭役、刑杀、战争。“孟秋之日,……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礼记·月令》)这种一年一度秋季进行的社会活动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征夫、思妇、游子,面对肃杀的秋之悲冷。
所以,悲秋,不仅具有审美的生命意识的因素,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广阔的民俗背景。这种意识年复一年地积淀在人们意识深处,因而成为跨越时空的集体无意识。
何其芳对于古今中外的诗词、小说、戏剧等文学史颇为熟稔,就中国古典文化来说,他12岁就接受旧小说,13岁读《礼记》,中学时读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聊斋、《红楼梦》、《昭明文选》、《唐宋诗醇》。[2]1931~193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阅读了《全唐诗》、《宋六十家词》、《元曲选》,《庾信诗集》、《世说新语》。他的古典功底很深,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就破译了别人写的晦涩难懂的充满了生僻典故的两首七律爱情诗。[3](42-43)这样,何其芳在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接受时,“悲秋”意识就会不可避免地积淀到他的心灵世界,“萩萩”、“秋若”、“秋子”等笔名,可谓悲秋这种情调的产物。
三
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悲秋”意识对何其芳的积淀,并不一定是单方向进行的,悲秋意识之所以在何其芳的早期诗文中如此集中、如此显豁,必须还有一个前提,即何其芳的精神世界、精神个性与传统的悲秋母题的契合。正因为他自身的精神因子与悲秋的精神情调有着共同的基因,他才会自称为“秋子”。那么,何其芳大学时期的精神个性究竟是怎样的呢?是怎样的精神基因接通了“悲秋”文化呢?
为了更好地把握何其芳的精神世界,需要把对他人生的解读与对他诗文的解读结合起来,也叫双重证据法。文学作品是作家灵魂的肖像,何其芳1930~1935年间即大学时代的作品都有一种忧郁、伤感、迷茫的“悲秋”基调。那么,何其芳是什么样的精神肖像接纳了这一基调呢?
1931年8月20日他在给吴天墀的信中说:“人比如是一辆火车,人生比如铁道。假如在这长长的铁道上,排列着适宜的车站,比如第一是家庭的爱,第二是学校生活的快乐,第三是爱情,第四是事业,……那就是幸福的一生。如真是缺少了,或者排列错了,那火车就没有停留的地方,只有寂寞的向前驶去,驶到最后一站。最后一站是幸福与不幸福的都有的,只是幸福的人到得迟而不幸的到得早而已。”[13]1933年剧本《夏夜》也说:“人生如一条车道似的,沿途应该有适宜的车站。比如第一站是温暖的家庭;第二站是良好的学校教育;第三站是友谊与爱情;第四站是事业;最后一站是伟大的休息。在这条道上,缺少了某站或者排列颠倒了都是不幸的。……(我)缺少了一些又排列颠倒了一些。”这可以作为何其芳 1935以前人生感受的凝结和他的人生观,也是打开他的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从万县到重庆,到上海,再到北京,曲曲折折的不长的人生之旅令他感到了他自己人生车站的缺失和颠倒,也使得他对人生道路的苦苦探索处于茫然阶段。
何其芳的学生时代是十分忧郁的,经常有老之将至的人生伤感,充满了对死的感受。1931年8月20日给吴天墀的信中说:“我们的缺点,是我们的兴趣领域太狭小了,这是危险的事。一年年,喜欢的,喜欢去做的东西渐渐减少,在减少到最后一点,再一下消灭,那就是死。近来又常常感到死于我是如此亲近,比我活着有关系的任何人还要亲近。‘死之鞭子,不过如情人的刺伤,足以伤人,而又是很盼切的。’莎士比亚的话很对。”[4]1931年 4月 25日致吴天墀信中有诗《即使》:“即使是沙漠,是沙漠的话,/我也要到沙漠里去开掘,/掘一杯泉水来当白茶;/即使永远,永远都掘不着呀,/总可以那坑作为坟墓吧。//即使是沙漠,是沙漠的话,/我也要到沙漠里去寻花,/寻来伴我墓中的生涯;/即使一朵,一朵都寻不着呀,/总有风沙来把我埋葬吧。//即使是沙漠,是沙漠的话,/我也要到沙漠里去住家,/把我飘零的身子歇下;/即使那水土不适宜于我呀,/总适宜,适宜于我的死吧。”[4]他是一个执著的寻找者、人生的探索者,但他没有寻到明确的目标。他人生之途的每一个站牌都是模糊、暗淡的。这大概是他整个青年时期一直忧郁、迷茫的原因。
我们可以简单考察一下他这几站的缺失。
第一站:家庭。他出生在四川万县农村的一个封建家庭。他的童年生活是很孤寂的。祖父很守旧。“我时常用寂寞这个字眼,我太熟悉它所代表的那种意味、那种境界和那些东西了,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到现在。我怀疑我幼时是一个哑子,我似乎就从来没有和谁谈过一次话,连童话里的小孩子们的那种对动物、对草木的谈话都没有。一直到十二岁我才开始和书本、和一些旧小说说起话来。”“对于正面的生活,对于人,我都完全没有怀疑过它们,我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我不能想象它还可能更好一点。我承认了它。”[2]在散文《楼》里,也有他的自画像:“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叔叔们常常晚上带着狗和仆人到山林里去打猎,我却毫无那种野孩子气,一次也没有参加,现在回想起来很悲哀,仿佛狂欢之门永远在我面前关闭”,“大概生活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异国里”。他说自己是悲观主义者,“悲观的来源不在于经历了长长的波澜起伏的人生,而在于孤独。孤独,是的,是我那时唯一的伴侣。”
第二站:学校生活。“我所上的私塾是封建性很浓厚的,完全不适合儿童的智力和兴趣的。那种乏味的私塾生活使我的童年过得很暗淡。由于私塾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暗淡,我从十二岁起就养成了在假期中自己读书的习惯。起初是迷恋旧小说。我常常从早晨一直读到深夜……”[2]后来是诗词文赋。1928年在万县上初中的时候,因初级中学校长问题闹学潮,何其芳被牵连开除,赴重庆上治平中学。当时他有绰号“大海茫茫”。他在《梦中道路》里说:“我过了一年半放纵的学校生活。直到一个波浪把我送到异乡的荒城中,我才重获得了我的平静,过分早熟地让自己关闭在孤独里。我不向那些十五六岁的同辈孩子展开我的友谊和欢乐和悲哀,却重又读着许多许多书,读得我的脸苍白。”1929年在上海进中国公学预科,在这里,“我乖僻到不喜欢流行的、大家承认的、甚至于伟大的东西。在上海住了一年,我讨厌体育运动,我没看过一次电影,而且正因为当时社会科学书很流行,几乎每个同学的案头上都有一两本,我才完全不翻阅它们。在一个夜里,我写了一首诗,我说我爱渺小的东西而且我甘愿做一个渺小的人。”(《一个平常的故事》)1930年5月19日写给吴天墀的信中,由对死去的深甫的哀悼,写到自己的人生感触:“近来,近一向来,我否定了一切,我觉得十分飘飘然,十分自然,然而,也于是空空然了!空空然,是倾向于死的道路。……至于这里所说的死,含义是很广的。”[4]1930年同时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秋入清华大学。半年后,因高中毕业证书作假问题被开除。1931年4月25日也是他被清华大学开除后的日子里,给吴天墀的信里说:“生活过得昏迷之至,很不愿向及它,何况细细向人说!除了生活,还有什么闲话?”[4]1931年秋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就上哲学系了。结果却出乎意料以外,我原来有的那一点点对于思想史的兴趣,在学哲学的过程中几乎全部消失了。”[4]大学一年级正是“九一八”事变爆发那一年。中国和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接着日本进一步侵略,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对外不抵抗、对内屠杀人民,全国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日益高涨,但何其芳对时局尚不太关注,还在“留连光景惜朱颜”(1956年《写诗的经过》自语)。他在大学里精神仍然很苦闷,不少的散文、创作谈、书信都有所提及。
第三站:友谊与爱情。他很早熟,十二三岁就懂得了早熟的情感世界。[5](26)赴重庆上治平中学,“我不向那些十五六岁的同辈孩子展开我的友谊和欢乐和悲哀”。[6](188)关于他的爱情生活,几乎找不到很直接的文字,但是从他的自述性文字里可以知道,大约1932年他经历了一场刻骨而绝望的爱情,“而且在北平的那几年,我接触的现实是那样狭小……而更深入地走到我生活里来的不过是带着不幸的阴影,带着眼泪的爱情。我不夸大,也不减轻这第一次爱情给我思想上的影响。爱情,这响着温柔的、幸福的声音的,在现实里并不完全美好。对于一个小小的幻想家,它更几乎是一阵猛烈的摇撼,一阵打击。我像一只受了伤的兽,哭泣着而且带着愤怒,因为我想不出它有什么意义”。[2]
第四站:事业。他整个青少年阶段都感觉人生道路是迷茫的。“我回顾我的过去:那真是一条太长、太寂寞的道路。我幼年时候的同伴们,那些小地主的儿子,现在多半躺在家里抽着鸦片,吃着遗产,和老鼠一样生着孩子。我中学时候的同学们现在多半在精疲力竭地窥伺着、争夺着或者保持着一个小位置。我在大学里所碰到的那些有志之士,多半喜欢做着舒适生活的梦,现在大概还在往那个方向努力。从这样一些人的中间我走着,走着,我总是在心里喊,‘我一定要做个榜样!’我感到异常孤独,异常凄凉。”[2]父亲一直梦想他大学毕业后回去做寨主,何其芳却愿意放弃家乡已有的田地和其它产业。他不愿意像那样“平生都只蛰居在故乡,从未走出里门的二十里以外。”[3](41)他否定了父辈们给定的人生道路,但是他却又找不到自己的未来之路。他打算搞文学,但哲学专业却扼杀了他(1956年《写诗的经过》)。
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一下何其芳大学时期的精神状态了。所谓的精神状态,就是说他对他所处的世界与他自己的愿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对所处的主客体关系的价值体验和价值期待。这种价值体验和价值期待就构成了他的精神世界。那么,再具体地说,他在当时有没有他对自己的强劲的自我期待?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我要什么”他是不明确的,“我不要什么”他是明确的。一般的人是我知道要什么,我得不到就会有痛苦。何其芳不是这样,我到底要什么,他不知道。在《何其芳全集》里我们找不到任何实证性的文字可以归结出确切的痛苦根源。他不是有所肯定而得不到的痛苦,而是无所肯定,这是另一种痛苦,甚至更痛苦。他和王国维不一样。王国维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他的痛苦是天才情结引起的,很明确。他所处的世界、他所处的家庭背景、他的身体衰弱、他的社会地位的卑微,都在阻碍着他实现天才情结。所以他的灵魂痛苦是很容易描述的。但是何其芳也痛苦,何其芳的痛苦首先是一种无指向的痛苦,他不明白“我到底要什么?”但是他得到的都是他所不要的。这一种痛苦是没有着落的痛苦。所以,我觉得这个痛苦是何其芳式的痛苦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一般的痛苦是指有欲望与欲望不能实现之间的关系,就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情结,但这个情结实现不了,就会痛苦。那么何其芳的痛苦更迷茫,是无指向的痛苦,因为他没有很明确的目标。要结束他的痛苦,看上去家庭是不行的,学校是不行的;他又那么孤僻,爱情和友谊也是缺位的;从事业角度来讲,小地主他是肯定不做的,争权夺利他也不愿意,过一种过于安逸的大学者生活好像又不是他的所求。1933年何其芳给吴天墀的信里说:“到北平来已三年,日子混得这样快使我惘然,人生二十,尚不能找到自己的路途认真地走,是危险的。”说得很明确。《一个平常的故事》也说:“在已逝去了的那样悠长的岁月里,除了彷徨着、找寻着道路之外,我又作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何其芳是孤僻的、内敛的,自审的,他既自恋又无法摆脱,他也在努力地去爱人,在《一个平常的故事》里他回忆了大学读书时对于卖报童等下层人的人道主义之爱。但在这个社会里,他似乎还没有找到个人的定位,《街》和《梦后》有相同的句子:“对人,爱是一种学习,一种极艰难的极易失败的学习。”《楼》里“楼”意象其实就是一个象征。他说:“昨天那样的高楼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可望不可及”,应该具有双重隐喻意义:“我们都有一种建筑空中楼阁的癖好”,有“登高眺远的兴致”。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追求和渴盼。他也意识到:“万念灰灭时偏又远远地有所神往,仿佛天涯地角尚有一个牵系。”[7](96)对这一牵系即人生价值根基之所在,他是不明确的。他的人生价值之困惑、角色自期之迷茫于此可见一斑。
于是,他孤僻、抑郁的生理、心理个性与其人生的无指向痛苦水乳交融地形成了一个忧郁、迷茫、孤独的心理场。这一心理场与传统文化的悲秋意识是异质同构的关系。尽管他作品中频繁出现“秋天”意象未必是有意为之,但是,由于这种异质同构,就使其悲秋意识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积淀下来,何其芳的精神世界又以文化通约的方式予以接纳了。
[1]何其芳.何其芳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M]//何其芳全集(2).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3]朱企霞.忆早年的何其芳同志[C]//何其芳研究专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4]何其芳.致吴天墀[M]//何其芳全集(8).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5]甘永柏.读遗诗 忆故人[C]//何其芳研究专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6]何其芳.梦中道路[M]//何其芳全集(8).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7]何其芳.梦后[M]//何其芳全集(1).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On He Qifang’s Autumnal Melancholy from His University Poems
ZHAO Si-yu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Hangzhou 310018, Zhejiang)
Pronounced autumnal melancholy can be found in HE Qi-fang’s literature in his university era(1930-1935). Autumnal melanchol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ermeated his inner world through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and was accepted by his confused, heavyhearted mental field. His life tracks and works indicate that the failure of family, education, friendship and love and cause makes his unassured agony and unsociable and eccentric personality, which agree with traditional autumnal melancholy.
He Qi-fang; autumnal melancholy; permeation; mental individuality
I206.6
A
1009-8135(2010)02-0066-06
2009-12-29
赵思运(1967-),男,山东郓城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郑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