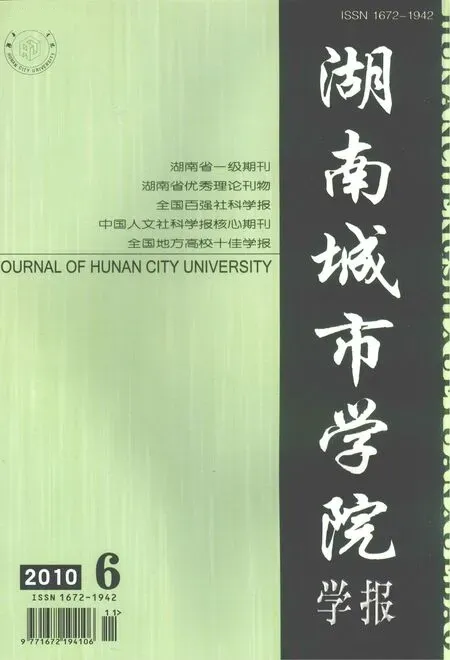两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女人——论祥林嫂与田晓娥形象的异同
赵 斌
展开20世纪中国文学画卷,女性形象成为作家观照的轴心之一。其原因可能是,呼请个体独立的五四启蒙运动其艰难的任务是女性的觉醒,女性视角也很自然成为“疗治”国民性的突破口。其中鲁迅和陈忠实两作家对处在世纪文学两端的祥林嫂和田晓娥两个人物所作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当然,祥林嫂的麻木、田晓娥的淫荡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两个人物似乎怎么也走不到一块。但笔者认为两人物虽然表面上有很多的差异,但揭去遮蔽物,会发现两人物有着更多相同的遭际。从最根本上看,她们都是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都受到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迷信的残害;都曾自我挣扎、自我救赎、甚至本能反抗;都最终“想做奴隶而不得”,结束悲惨的一生。
一、失去“做奴隶”的资格
鲁迅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1]26但祥林嫂和田晓娥却是两个“异类”,“想做奴隶而不得”,欢喜不起来,一生救赎,一生挣扎都没有获得“做奴隶”的资格,只有悲惨死去。
祥林嫂是封建买卖婚姻的受害者,是个童养媳;田晓娥是封建多妻主义的殉葬品,是个合法“二奶”。他们的婚姻都是“畸形”的,幼丈夫或老丈夫更加速了她们不和谐婚姻的猝死。祥林嫂的婚变也许是天意弄人;田晓娥似乎是自我造孽。其实并非如此。假如田晓娥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其结果又如何呢?她不过多做几年郭大财主延年益寿的工具,也就变成了第二个祥林嫂了,暂时的奴隶也就做不成了。“守节”与“失节”的二难选择一样横亘在田晓娥的面前。当然,在中国封建社会一般会选择“守节”。也就像鲁迅《我之节烈观》一文所说:“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1]6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三纲五常”的封建社会里,女人们信守着“从一而终”、“好女不嫁二夫”的封建观念,女人寡而再嫁,会背上不贞的罪名,更无辜地被人们加上“不祥”的罪名。但祥林嫂无法自主选择,丈夫死后,她逃到鲁镇做工,渴求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做奴隶的权利。但她婆婆恃凭着族权的威势,把她抓回去,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去失了“节”。从此祥林嫂“不祥”了,“做奴隶”的资格也被剥夺了。和祥林嫂不同,田晓娥是一个小女人,又比祥林嫂美艳,加之性饥渴,很快失了“节”,田晓娥“红颜祸水”的形象也就风靡白鹿原了。“白嘉轩闲时研究过白鹿村同辈和晚辈的所有家庭,结论是所有男人成不成景戏的关键在女人。有精明强干的男人遇着个不会理财持家的女人,一辈子都过着烂光景;有仁义道德的男人偏配着个粘浆子的女人,一辈子在人前头都撑不起筒子;更不要说像黑娃拾烂菜帮子一样拾掇下的那种货色了,黑娃要是有个规矩女人肯定不会落到土匪的境地。”[2]“万恶淫为首”,女人的淫荡更是十恶不赦,万劫不复。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中,“女人的‘性’从来只是为了取得妻子和母亲的合法席位,满足男性繁殖与传宗接代的欲望……或者只是为了充当男性的性工具……”[3]也就是说,性的终极目标也是最理想的归宿是有一个孩子,成为做母亲的女人。“母凭子贵”,孩子是做奴隶的资本。如祥林嫂,第一次婚变使其像水中的浮萍,无所依凭。第二次婚变后,儿子阿毛是其救命稻草,但没有抓住。所以两个女人命运是一样的,都没有做奴隶的砝码,没有一个孩子来固守家庭的合法席位,又都失了贞洁,结局的悲惨也自然一样。寡妇祥林嫂的再嫁,在讲理学的鲁四老爷看来就是“败坏风俗”。即使祥林嫂捐门槛赎罪,也仍然未能得到人们的承认和饶恕,她始终被看成是“不干不净”的浊物,成为新年祭祀的边缘人、多余人。田晓娥被当成伤风败俗的“灾星”,从没有获得“做奴隶”的机会。宗法制的族规死活不允许田小娥夫妇进入宗祠拜亲祭祖,两次受人诱惑而失足的田小娥更是被用刺刷毒打,最终被“做稳了奴隶”的亲翁鹿三杀死。即使死后还被白嘉轩烧毁了旧居,且被压在塔下,永世不得翻身。
二、“奴隶”身份认同的焦虑和转型
祥林嫂第一个丈夫死后,渴求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做奴隶的权利。所以当她在鲁家做工时,她是“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到年底,扫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鲁家)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而满足。但好景不长,厄运来了,祥林嫂不甘心,用生命来抗婚,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撞得头破血流。但“烈”得很显然不够,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1]6所以“不守节”的祥林嫂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要受到残酷的惩罚。“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柳妈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祥林嫂却不甘于受人歧视,更为了获得合法的奴隶地位,用了全部积蓄十二元大洋“捐门槛”“赎罪”,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解脱。但四婶的一声“你放着罢”判决剥夺了祥林嫂“奴隶”的身份,使她的精神彻底的崩溃。做工、抗婚、捐门槛的自我救赎之希望彻底破灭。最后,祥林嫂既恐惧死后受阎王惩处,又想见到儿子阿毛。内心的矛盾发出了天问式的质疑,怀疑灵魂的有无。当然,祥林嫂这个灵魂的拷问者不可能做出理性思考,只是一种本能反应。因为祥林嫂一生都本能地把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故而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
相对于麻木愚昧的祥林嫂,田晓娥要进步一些。祥林嫂一生无法摆脱无爱婚姻的困扰,田晓娥却追求着有爱婚姻;祥林嫂一生在隐忍中度过,田晓娥却要摆出复仇者的姿态。所以,如果祥林嫂是从自我救赎者、本能反抗者走向灵魂拷问者的身份认同,那么田晓娥就是从自我救赎者、本能反抗者走向本能复仇者的身份认同。田晓娥一开始作为老财主延年益寿的工具,还受正室压迫,辛苦劳作。在忍气吞声的同时,她偷换用尿泡枣,勾引黑娃,报复别人对她的压制。她在柔顺软弱的同时,也有着大胆勇敢的一面。后来他却与黑娃真心相爱了,当黑娃娶她,便产生了守着黑娃过一辈子,为她生儿育女孝敬公婆的想法。但白鹿原不可能容忍这样一个伤风败俗的女人走进家门,踏入祠堂。她只得与黑娃在村外的窑洞生活,虽然艰难,却很满足。但命运多变,为救黑娃,委身于鹿子霖,“虽出于无奈,但也带着出卖性质。社会遗弃了她,她也开始戏弄社会;她是受虐者,但也渐渐生出了施虐的狠毒。”“这个‘尤物’、‘淫妇’以仅剩的性为武器在白鹿原上报复着,反抗着……”[4]148“性”是她存活的凭依,也作为武器去报复这个冷血的社会。当然田晓娥的报复是本能的,是绝望后的反抗、报复,也是盲目无力的。但死后的反抗、报复却造成了灾难性的严重后果,为白鹿原引来了一场大瘟疫,使很多人葬身其中,但最终还是被镇压在六棱砖塔之下,永世不得超生。这些相对于祥林嫂,田晓娥已是难能可贵了。所以,雷达在《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一文说“在勾陷孝文成功后的‘狂欢’之夜里,性事完了后她却‘尿了鹿子霖一脸’!这个奇怪的举动,可说是她对鹿子霖卑鄙人格的一种最奇特、最恶谑、最蔑视的嘲弄,只有她才干得出来。这一笔堪称绝唱。”[4]149
[1] 鲁迅.鲁迅选集[M].北京:线装书局, 2007.
[2] 陶春军.〈白鹿原〉中白嘉轩话语权缺失原因探微[J].语文学刊:高教版, 2007(3):104-106.
[3] 马春花.被缚与反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M].济南:齐鲁书社, 2008:173.
[4] 雷达.陈忠实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祥林嫂的悲剧原因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