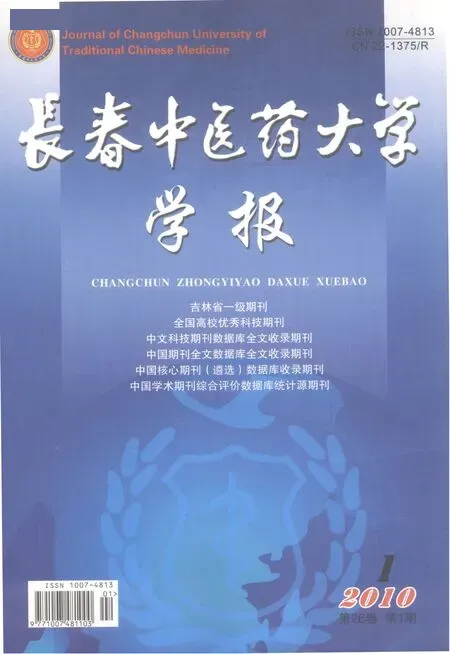耳鸣从心论治
丁玉发,王 淼
(1.新乡第一卫生学校,河南新乡 453000;2.河南中医学院中医理论与临床应用研究所,河南郑州 450008)
耳鸣从心论治
丁玉发1,王 淼2
(1.新乡第一卫生学校,河南新乡 453000;2.河南中医学院中医理论与临床应用研究所,河南郑州 450008)
心与耳在经络、脏腑与官窍上密切相关,心的病理变化可以影响人的听力而发为耳鸣。从心与耳的联系入手,明确耳鸣症状的发生与心之功能异常有因果关系,耳鸣当从心论治。
耳鸣;心;辨证论治
人群中耳鸣发生率为13%~18%[1]。近年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加,耳鸣发病有逐年增多的趋势[2]。由于耳鸣具有主观性特征,且其发生的机理比较复杂,与疲劳、睡眠、月经周期、情绪、脑部血液循环等都有关系,所以目前西医治疗所用的掩蔽、药物、手术等方法均没有被医学界公认为有确切疗效的治疗效果[3]。今从中医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以耳鸣从心论治的观点进行探讨,有所慧悟,介绍如下。
1 理论依据
1.1 心寄窍于耳 耳为肾之外窍,此论广为所识,然耳窍也归心所属。《临证指南医案◦耳》有载:“肾开窍于耳,心亦寄窍于耳,心肾两亏,肝阳亢逆,故阴精走泻,阳不内依,是以耳鸣时闭。”此即为耳窍所归属脏腑之论提出了依据,以心寄窍于耳之论,说明心在人的听觉功能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心主血脉,可濡养滋润耳窍,心气充盈,血脉蕴通畅达,精明之气得以上达耳窍,听觉聪灵;若心之气血不足,肾精亏损,阴不足以内敛阳热,则肝阳上冲,阴阳不得相互依存,耳窍功能不能正常发挥,则听力下降,甚至引发耳聋。关于耳窍与心之关系的论述,历来也有很多。如《医贯》云:“肾开窍于耳,故治耳者以肾为主。或曰:心亦开窍于耳,何也?盖心窍本在舌,以舌无孔窍,因寄于耳,此肾为耳窍之主,心为耳窍之客尔”。
1.2 心与耳在经络上有着密切关联 《灵枢◦经脉》载:“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络心……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即是说该经循行路线起自手小指尺侧端(少泽穴),沿手掌上行,后经肩胛部进入锁骨上窝,深入体腔,联络心脏……其分支又退行至耳中(听宫穴)。既然心脏与耳在经络上有着直接的联系,那么随着经气的循环往复,此二者在机体功能正常和异常的时候都必然会相互影响。又云:“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散络心包……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心包络为心之外围,有保护心脏的作用,心包络与耳相通,被包于其内的心脏自然也相连与耳。此皆表明,心与耳由经络相连,经气在循行流注过程中抵达心与耳,两者之间经气循环往来,其气相通。
1.3 心肾相交 肾开窍于耳,肾之为病,可以从耳上得到反映,耳部病证,亦可从肾而治。心与肾两脏相互作用,互相制约,以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心火能制肾水泛滥而助真阳;肾水又能益心阴而制心火,使不致过亢为害。故陈士铎于《辨证录》中曰:“凡人心肾相交,始能上清下宁,以司视听,肾不交心与心不交肾,皆能使听闻之乱。”心肾相交,水火相济,心之为病,可以及肾,从而间接影响耳的功能。心阳不足、肾失温煦或因肾阴不足、心火偏亢,皆可以引发听觉失聪,发为耳鸣。
2 辨证论治
2.1 以心论治而不局限于心 临床见耳鸣一证,多可从心而治。症见安静之时自闻有声,或夜间耳鸣,或鸣声低微,或眠差之后鸣响加重,常伴有心悸、肢冷、困倦、失眠、多梦、面色淡白或萎黄,或兼见心烦、五心发热、盗汗等。其辨证多责之在心,应以补益心之气血或泻心中烦热为要。但是,也不应该一味以心为治。若耳鸣同时兼有畏寒肢冷、腰膝酸软无力、头晕目眩或齿松、骨蒸发热等则往往责之在肾,应治以温补肾阳或滋补肾阴之法;兼有烦躁易怒、面红目赤者则应以调肝为法;或有浊腻阻碍清阳者应以健脾为治。
2.2 明辨虚实方为治 临床上,耳鸣有虚实之分。如《景岳全书》卷二十七云:“凡暴鸣而声大者多实,渐鸣而声细者多虚;少壮热胜者多实,质清脉细,素多劳倦者多虚。”《医贯》卷五认为:“耳鸣以手按之而不鸣,或减轻者,虚也;手按之而愈鸣者,实也。”实症多由外邪或脏腑实火上扰耳窍,亦或瘀血、痰饮蒙蔽清窍所致;虚者多为脏腑虚损,清窍失养所致[3]。实证多见耳鸣如蛙聒、如潮水,暴鸣而声大,伴有面红目赤、烦躁易怒、声高气粗、舌苔厚腻、脉象弦滑有力等表现;虚证多由肾阴亏损或中气下陷所致,症见耳鸣如蝉、如箫声,常鸣而声细,或兼见气怯声低,乏力欲睡、形瘦肢冷、纳呆面黄、苔薄脉弱等。临证治疗时,应详分虚实,做到心明志清,对证用药,方可奏效。
3 病案举例
花某,女,40岁,2007年6月9日初诊。诉双侧耳鸣两月,加重1周,以左侧为重,耳中鸣响时断时续,如蜂在耳,时感头晕,偶见气短、心中悸动不安,平素神智恍惚、悲切欲哭。刻诊:精神困倦,乏力,欲睡,面色萎黄,舌体胖嫩、苔白腻,脉象沉细无力。证属心气不足,夹有湿滞。治当养心益气,健脾祛湿。方选苓桂术甘汤合甘麦大枣汤加减。处方:茯苓30 g,桂枝10 g,白术10 g,丹参15 g,郁金10 g,浮小麦 30 g,生龙牡各30 g(先煎),夜交藤15 g,薏苡仁30 g,黄芪30 g,甘草6 g,大枣10枚。每日1剂,早、晚分服。服药7剂后复诊,自诉乏力、心悸减少,仍觉耳鸣。察舌按脉,见痰湿之象已减,仍有心气亏虚之征,故以首方加减继服。3诊:耳鸣锐减,心悸、头晕症状消失,精神状态佳,脉象缓和。效不更张,再以前方继服5剂而善后。1年后随访,未见复发。
按:此例患者双侧耳鸣如蜂在耳,时断时续,兼气短心悸,神悲欲哭。以《灵枢◦本神》所云“心气虚则悲”之论,辨证为心气不足;其舌胖嫩、苔白腻,脉沉细无力为脾虚夹湿之象,故当以养心健脾为治。方选苓桂术甘汤合甘麦大枣汤加减治疗;同时以丹参、郁金、龙牡、夜交藤、浮小麦清心安神;黄芪、茯苓、白术、甘草、大枣、薏苡仁健脾益气。诸药同用,共奏养心安神、健脾化湿之效。
:
[1]Cooper JC Jr.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of 1971-1975 PartⅡ.Tinnitus,subjective hearing loss,and well-being[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udiology,1994,5(3):37.
[2]王永钦.论耳鸣治耳鸣治心的方法与实践[J].中医药通报,2008,7(1):21-13.
[3]曾丽霞.中医治疗耳鸣近况[J].甘肃中医,2005,18(12):2-3.
R246.81
B
1007-4813(2010)01-0025-02
丁玉发(1981-),男,大学本科,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中医学教学、临床与科研。
(
2009-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