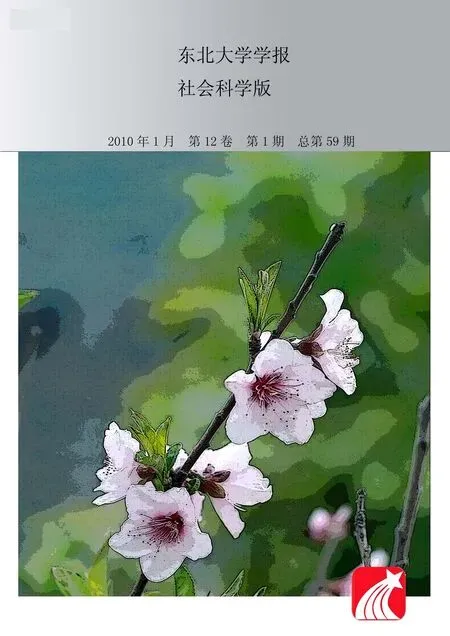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与转型
金春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世界思想文化界一度掀起轩然大波,其解构启蒙理论波及中国文学界,致使世纪之交以来文化思想界的“反启蒙”思潮越来越具话语霸权,许多学者纷纷将近现代梁启超、鲁迅等树立的启蒙传统列为质疑、否定乃至弃绝的对象,“启蒙时代的终结”、“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解构启蒙之声不绝于耳。启蒙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统摄性话语与主要的思想史主题,在现代性、后现代、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思想文化的夹击下,日益边缘化和狭隘化。不可否认,世纪之交特殊的历史语境、文化氛围和价值结构,使得启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资源,在文化内涵、叙事立场、启蒙对象、本体认知、启蒙策略等方面也相应地发生着一些转型。但正如福柯所言,启蒙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20世纪“旧启蒙”自身体系在新时代的不适应性并不代表启蒙的落伍与终结,文化转型和启蒙反思反而孕育着新启蒙的诞生。不过这种新启蒙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逐渐潜入暗流和夹缝,以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启蒙之声,但其精神内核在新世纪的叙事空间却并未中断。新启蒙的建构和阐释,对我们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五四”传统,重新评价鲁迅等新文化启蒙先驱的意义,以及从文化和历史的维度把握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态势与走向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
一
1898年梁启超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使中国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历史跋涉,20世纪之初的“五四”精英以欧洲社会历史的现代化发展为版本,在古老的中华土地上开始了本民族追求全方位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企图实现民族复兴和强国之梦。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鲁迅等一批先觉知识分子通过思想启蒙试图在大众中培植科学和民主理念,并以此作为文化精英群体参与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的介入方式,从而将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思潮掀起,并形成了新文学史上极其宝贵的以“启蒙”、“批判”、“立人”为己任的“鲁迅传统”。但在“救亡压倒启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历程中,启蒙传统却未能很好的延续、发展和深化,特别在当代文学史中,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话语霸权,启蒙与反启蒙的斗争更加艰巨和复杂。直到新时期80年代文艺政策的调整才使得启蒙精神在当代得以复苏,呼唤“人”的价值、“人道主义”的讨论等,都是启蒙精神重新重视人之价值的佐证,文学终于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中国知识分子欢呼雀跃于精神解放与写作自由,并在新时期重新争夺回话语权,也开始了重新恢复鲁迅启蒙传统的企图。
但源自于西方的启蒙思想在中国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历程中,也有着自身诸多无法逾越的发展承继困境:晚清启蒙和“五四”启蒙因其强调个人至上主义的民主价值理念与风起云涌的历史剧变和革命伦理的内在要求之间的内在抵牾而被压抑,三四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在未完成对民众的国民性改造的任务之后,却转向了依靠民众实现民族自立的救亡,80年代“回归五四”的启蒙思潮同样也因侧重民主与理性的文化批判而与现代化建设的意识形态话语相左而被文学主流话语边缘化。20世纪末的启蒙精英准备执著地将鲁迅的启蒙精神继续传承下去时,始料未及的文化约束却将其幻想击得粉碎:一方面是经过“文革”拨乱反正之后政治的高压态势使得他们“过分”地强调个人价值和自由理性,必然要与当时“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经济政策相左;另一方面文艺复苏使中国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汲取外国文化甘露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陷入全球化的后现代文化语境,知识分子的精英身份开始被颠覆。特别是经济浪潮的席卷将这群有识之士逼于一隅更为尴尬的境地:理工科兴起以适应现代化的强国梦时,人文学科却因与这一浪潮的不相适应而被边缘化,知识分子在新型的以经济实力确立社会地位的世纪末,失去了社会精英的身份和文化引领的角色。世纪之交诸多文化浪潮的席卷,是一个混合着世界性与全球性文化因素、更强大以至无法抗拒的文化语境,这种语境的强大渗透性,正改变着中国文学的地域版图、权力格局、作家身份乃至文学概念本身。一切在人为的试图建构中获得的却是文化逼迫下的解构,启蒙连同鲁迅、“五四”、理性、现代性在本雅明、德里达等思想的影响下不断地被后现代质疑和解构。这让信仰与秉承鲁迅传统的当代知识分子精英忧心忡忡,但沸沸扬扬的“人文精神”讨论,其结局仍然是不了了之。这样的身份尴尬和文化侵袭发展到当下更是愈演愈烈,金钱主义、欲望主义盛行,当代小说开始展览日常的庸俗,猎艳于市场趣味,“身体写作”、“私人写作”甚至“下半身写作”反而得到诸多人的热捧。全球化语境下,传统启蒙思潮不仅没有得到发扬光大,反而被质疑者所指责,将当下极端的自由化、个体化、仿西化的率性写作都归结于启蒙强调“个性”与“独立”的恶果。于是重新审视政治的整合性,审视本土文化的资源潜力和文化深度等成为“反启蒙”主义者的法宝,传统启蒙在全球世纪末强劲的“反启蒙”历史境遇中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贯穿20世纪文化领域的启蒙运动始终处于未完成时状态。
五四启蒙主题的被质疑、被解构逼迫着启蒙坚守者和践行者进行内在的理论反思,从而也为启蒙本体和策略的嬗变和建构奠定了基础。新世纪启蒙话语之“新”、之“变”在于将旧启蒙中的科学、理性的强行植入转为健康合理的人性的自觉复苏,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背景下,由于文化的良莠不齐导致的人性、道德和价值困境等,更使得这种侧重于人性匡正的新启蒙的引领,有着独特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价值。世纪之交以来,传统现代性不断被西方后现代话语所质疑和取代,在追求多元性和包容性的民族现代化进程中,却忽视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性的人性结构、政治体制等本土问题,在将西方极具特殊文化背景和历史传承的后现代理念植入人们思想核心之时,后现代性的理论体系和价值理念也驱逐了“五四”启蒙本身所具有的合理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启蒙本体和策略的嬗变就应能恢复被后现代所遮蔽的人性和理性的本真面目,如由于当下消费主义、大众欲望、享乐主义泛滥而导致的诸多新的人性异化问题,“在现代人的千年盛世说(chiliasm)的背后,隐藏着自我无限精神的狂妄自大”[1]。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长期处于政治话语的约束之下,在世纪之交开始了摆脱宏大叙事的努力,但其摆脱桎梏的状态却是过激的,甚至是一个从政治极端滑入了欲望极端的荒谬过程,经济文化的霸权话语对精英话语的冲击,使许多人认同了文学中的放纵感性的欲望化叙事,殊不知他们无形中却陷入了另一个异化欲望话语泥淖,更有如许多“70后”作家将情欲、金钱和隐私为主题的欲望化文本视为自我个性解放的途径,这种对个性价值的误读来自于对启蒙语境的误解,西方的启蒙解构是在理性过度膨胀导致技术化的状况下的解构,中国的解构启蒙却是在理性还未成熟状况下的幼稚放纵。因此启蒙之嬗变就既要纠偏传统启蒙脱离本土的宏大叙事误区,纠正其在启蒙实践中的某些强制性和偏激性统治话语,又要面对、恢复和匡正为突破和解构传统启蒙理性弊端所引发的新的道德和人性问题,因此启蒙在当下芜杂的思想语境中仍是一项未完成且颇为紧迫的文化工程。
二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在思想文化领域,大众文化、网络文化、消费文化的话语霸权以及商业化、信息化、技术化的流行,使得这一时期文化与文学思潮发生了本质的转型。借助于政治和道德进行启蒙的本土启蒙话语明显地表现出挣脱本土的要求,甚至超出了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范围,启蒙主义面临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在商业价值观的全面冲击下,传统启蒙话语逐渐丧失了应对现实问题的力度,整个知识界开始了自我反省与学理审思,启蒙话语也经受着他者和自我的双重拷问,文学规避了对社会和人生应承担的责任也进入了世纪末的集体失语状态。
首先,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背景下,文学退居边缘而呈现出个人化和多元化的开放面貌,但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成熟也导致了市场与权力的联手在世纪之交呈泛滥趋势,在大众媒体和精英政治的合谋下,现代性和后现代因素构筑了一个新的垄断性话语,这在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中成为一个主要的批判主题,“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行政干预经济现象大量存在,因此出现‘官商勾结’现象”,“凭借特权占有国家资金,垄断市场”[2]。其次,世纪之交消费主义成为话语中心,其合法性加剧着欲望的膨胀,个人写作走向了欲望写作,文学活动被转化成为一种“符号消费”的过程。“消费的社会逻辑根本不是对服务和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占有,……它不是一种满足的逻辑。它是社会能指的生产和操纵的逻辑”[3],是一种符号的生产与操纵,消费者的欲望是被精心的策划所刺激和调动起来,符号操作将消费者纳入了它的结构之中,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波德里亚说:“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与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4]符号消费成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进行区分的重要标志,这些观念正是当今流行时尚文化的生产地,也是关于消费的“今日神话”。正是这“神话”的言说,刺激和调动起了消费的需求,培养着大众消费的态度。第三,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建构起的新的话语霸权,造成了当下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弱化,他们的价值观从对世俗化认同,发展到当下对世俗价值的宣扬,文艺的人文关怀意识逐渐淡化,商业属性逐渐增强,文学的休闲、娱乐功能日益凸显,在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上趋向于私人化和先锋化,写作基本不负载人生与社会的主题,只求精神上的娱乐与宣泄,身份的标志与荣誉,正如陈晓明所说:“他们的存在与写作处在同一平面,他们不再需要文学表达激进的社会变革。他们占据的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文化空间,相比较起背负着历史重压和文学经典传统的那几代作家,他们面对这个时代更具有先天的优势”[5]。在新型文化语境的冲击下,文学作品呈现出世纪末消费主义的情绪与氛围,这正是当下真正秉承启蒙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忧虑。第四,传统启蒙思潮的几起几落无论在目标诉求还是在方式选择上都遵循着“五四”启蒙的传统,反对一切权威和固有成规,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将自身树立成了另一权威,强大的和声共鸣遮蔽了启蒙的内在分歧,本意上的启蒙是解除原有桎梏的目的,但却先将启蒙本身变成了镣铐,造成了无法挣脱的尴尬境遇。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长期以来的宏大叙事对个体的遮蔽使中国人的个体意识非常薄弱,而致力于个性解放的启蒙理性却在长期的统摄过程中被神化,从而成为一套新的霸权价值理念。新世纪文学的非理性化叙事便是意在抵抗启蒙理性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使个性解放在新世纪得到进一步的弘扬。
在这样的文化转型背景之下,启蒙话语面临着质疑、反思以及言说背后的思想困乏和无法言说的尴尬困顿,于是开始了民间化和边缘化的审美探寻,启蒙不再是明确的理想预设,而是一个充满了未知数的历史事件,但是中国文学的启蒙话语,在逐步拒绝必须“支持”或“反对”的简单处理的同时,也深化了对启蒙的本体建构和理论体系的内涵延伸,以适应对当下社会的现实敏感度和批判需求。而就启蒙本体论的嬗变而言,传统启蒙是指18世纪西方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人”、理想与真理为向度,力求实现人的尊严、个性、心灵自由。但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启蒙运动侧重于探求启蒙精神的实用价值,却忽视了启蒙本应具有的内在精神建构。西方启蒙理念与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逐渐孕育了“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启蒙,它们彼此之间有着程度不同的冲突但又存在程度不同的关联性。正因如此,近代中国启蒙“争论的焦点是富强、民族振兴或民族尊严的重建的条件”,成为“各种各样的救世方案或使中国摆脱可悲困境的药方的支配权的争夺”战场[6]133。它当然就“不是纯粹的思想运动、学术运动,而是把理论、行动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运动”[6]106。因此中西方“启蒙”遵循完全不同的发展逻辑:“在西方,启蒙主义是要解决个人的解放或个人的自由问题,在中国,启蒙主义要解决富强的问题。……在西方,民主与自由被视为最后的价值,理性王国的根本的特征;在中国民主与自由被视为实现富强的条件或工具。”[6]137但当我们赋予启蒙太多的功利之后,启蒙也远离了它本身的逻辑,使我们无法辨清启蒙的本来面目。今天我们面对的启蒙问题不再是启蒙应该如何,而是如何深化启蒙。与其引入或创造新思想,不如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当下社会所呈现的各种社会失衡的根本原因,即社会失衡导致的人性失衡,因此我们所提倡的新启蒙就应将重心定位于人文精神的层面,这样启蒙本体就从政治启蒙、社会启蒙,逐渐延伸为人性启蒙。
三
正如新启蒙论者张光芒指出,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亦非单纯的非理性存在物,情与理的矛盾是推进启蒙文化演变发展的动力,启蒙不是赋予知识者的特权而去教导别人,启蒙应是个体对自我心灵的启蒙。人性启蒙包括了人性解放,即欲望和本能的解放,然后是从欲望的解放中生发出情感,在欲望与情感中生发出理性,并让情感和理性在现实矛盾中相互激荡,最后上升为人格完成,从而使个体塑造出一种自由意志或理性精神,进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境界[7]。同时启蒙还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它既包含了个体的自我启蒙,同时也包含了整个社会的启蒙,只有“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叠加时”才有启蒙,这样启蒙便成为一种人的生存态度与生命姿态,是使人具有自由、道德、善的意志,这种终极性的人性超越性因素进入自我启蒙的内涵结构之中,就成为人实现自我本质的标志,这样传统启蒙便在本质上深化为一种人性启蒙,最终转变为一个哲学和本体论的根本问题。
传统启蒙主义者所运用的启蒙策略,是先立人而后立国,最终求得人与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的和谐与平衡,即外生态与内生态的平衡。所不同之处在于20世纪之初的启蒙背景以及试图改变的对象是政治秩序的混乱,人伦阶层的森严,经济科技的匮乏,精神世界的贫瘠;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背景与启蒙意图是政治与大众健康关系的回归,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恢复,以及社会文化经济的逐步健康发展。而从9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启蒙背景已经是社会物质财富的较为丰富、文化的多元共处以及先觉启蒙者所最期望的民众素质的不断提高,国家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和法制制度已经逐步完善。但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失衡,社会结构出现“断裂”,并在新世纪出现“固化”,如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等所折射出的问题,正是新启蒙的历史使命。
新启蒙并没有抛弃“五四”传统启蒙,但却将传统精英启蒙的实质性内容以“走向民间”的形式进行了置换,政治意识形态或权力话语让个人的自由话语向民间话语认同,并借着民间话语消解个人话语,实现了启蒙精神的内在策略性嬗变。在启蒙结构中存在“天帝”、“民众”与“恶魔”三者[8],前两者是一个互动互换的统一体,如阿Q要么失败就是民众,要么成功就是天帝,而恶魔则是向民众启蒙的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帝失落就会成为“愚民”,“愚民”得势就会成为天帝,而恶魔的出现成为天帝和民众转换的障碍,新的启蒙权力话语者要想继承启蒙传统,则必须回归到天帝和民众的民间立场,隐蔽而策略地回归到天帝与民众的统一体中。但新启蒙者文化观念上的现代性丧失以及向传统性和民间性的回归,并不是让新文化的承担者回归天帝,回归到后现代芜杂的文化与封建性传统的统治秩序之下,认同民众,而是迂回地达到对民众的间接启蒙。然而,当启蒙话语越出了权力话语容忍的限度,就会受到排斥和打击,从而使得新启蒙必须采取新的策略发出自己的隐秘而深刻的启蒙与批判之声。
虽然底层文学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明确内涵,但正如南帆所说,底层是属于多重被压抑的群体。由于底层文学更加贴近现实,关注民众的生存与精神,所以诸多学者将底层文学和左翼传统联系在一起。就其本质而言,底层文学不仅具有左翼替大众代言的特征,而且还闪现着启蒙思想的理性之光。虽然许多作家在底层写作中,以感性的方式抒写了对苦难的体验,但透过这样的感性抒写,以及道德价值判断的表象,作家们其实隐含着对由于当代经济秩序的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阶层不公的批判,导致的对人的价值践踏的不满,他们的启蒙意图是恢复社会的理性、良知、平等和博爱,因为一切启蒙思想的核心都是以“人”为本,都有着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个体生命和尊严的敬畏。当然,启蒙者的策略是有所调整的,由于知识分子在当下社会已经失去了像“五四”和80年代那样的精英地位,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身份“伪装”成大众,以大众代言人的身份喊出切肤之痛,这就是其表象上的“平民立场”;他们的启蒙意向也有所调整,即将寄希望于直接个体启蒙改变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秩序转变为寄希望于国家政治和社会大众,在他们看来,能改变这一格局的只能是通过政治政策手段的实施,以及整个社会大众理性精神、博爱精神和道德智慧的恢复。如果说“五四”启蒙者们的振兴中华民族的思路是“立新人”到“立新政”进而“立新国”,那么新启蒙者则在当下“以人为本”、“科学和谐发展”的意识形态主流下,寄理想于政治的干预,于是有了新世纪文学创作的“政治文化”回归潮流。这并非如“十七年”和“文革”时期那样,是文学依附于政治的倒退,而是在国家政治、法制、民主基本健全的现代化发展时期,启蒙者启蒙策略的调整。政治的合理和完善始终要依靠民众对启蒙思想的接纳,这样启蒙者就实现了为树人而从政治出发,而政治的完善又须根植于民众,最终回归到人的启蒙的目的,也与“五四”文学的启蒙起点实现了历史的对接与呼应。而社会的和谐、平等、民主,民众精神的健全和理性精神的恢复,既是一切启蒙精神概念中的核心主题,也是真正实现社会与人的现代化,实现内生态和外生态的健康、和谐和平衡的重要途径。
新启蒙策略的调整,使得启蒙精英成为“在场”的“他者”,既能以“在场”的身份,以平民视角入乎其中,体验这一弱势和被压抑群体的悲苦辛酸,“写出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离合”,也能作为“他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底层文学的书写中,我们在为底层人的生存心酸和精神苦难而“哀其不幸”时,也会为其自身性格和精神状态而“怒其不争”。底层是一群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备受压抑,从乡村漂流到城市,在乡村、城市底层或社会边缘苦苦挣扎的群体,他们怀有对美好未来的幻想,也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尊严,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却往往迷失自己,甚至走向无法回头的罪恶深渊。他们首先面对的是物质利益的诱惑,却因过分的追求和沉溺而丧失了基本的良知和道义,经济文化和享乐主义以其无法抗拒的渗透力扩散于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意图努力从边缘跻身于主流中心的底层群体,有时却被欲望折磨而疯狂。如果说20世纪的启蒙者意图让僵化麻木的中国民众以理性而科学的头脑“行动”起来改变命运,那么,21世纪的启蒙者则希望这群为了“改变”命运而“行动”得“过火”的群体能够以理性而科学的头脑恢复常态,坚守健康的人生原则和人性本质。如在新世纪文学叙事中,“资本强权的嚣张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戕害着底层民众并给他们带来苦难的,实际上还有权力体系中的败类和那些委身于资本强权的帮凶”[9]。许多作品在感性控诉的同时,也传达出作者对底层群体由于长期的“官本位”思想的毒害,缺乏基本的法制和民主意识的批判,而当他们一旦有机会爬上基层权力组织时,仍然是一群欺压他者的强权者,不由地让我们将这样的国民劣根性和精神特征与阿Q的“革命”联系起来,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21世纪的底层写作,从本质上来说与20世纪的启蒙思潮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过由于特殊的历史语境、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21世纪的启蒙对象转变成为在经济和强权重压下,人性的坚守、欲望的遏制以及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平衡,即启蒙对象不但是人,还包括整个社会群体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甚至由精神启蒙延伸到了人性启蒙的范畴,从个体到群体的痼疾,从精神到文化病态,这一切颇类似于一个大“阿Q”,这就注定了新启蒙的对象是无形的却是无处不在的,也注定了这种启蒙状态的悲剧性与悲壮感。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北京:三联书店, 1989:96.
[2]杨春时. 中国文化转型[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4:118-119.
[3]马克·波斯特. 第二媒介时代[M]. 范静哗,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114.
[4]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204-206.
[5]刘永涛. 青春的奔突----论80后文学[J]. 理论与创作, 2005(5):50.
[6]胡传胜. 观念的力量----与伯林对话[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7]张光芒. 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M]. 上海:三联书店, 2006:4-17.
[8]高旭东. 比较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96-98.
[9]何言宏. 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J]. 南方文坛, 2008(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