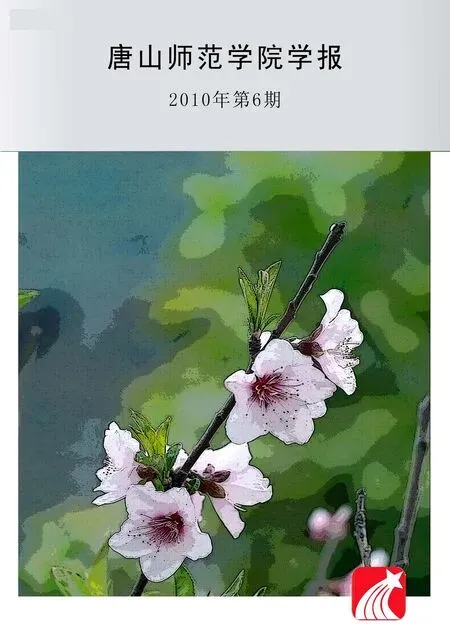言简意更深,微处见真情
—— 鲁迅小说的简凝之美
王吉鹏,李 瑶
(1.辽宁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辽宁 大连 116029;2.辽宁师范大学 中文系,辽宁 大连 116029)
埃德加·斯诺曾在《鲁迅——白话大师》中说过:“鲁迅作品的最大魅力在于他的风格。”鲁迅小说有着其自身独特的风格特点,同时这种风格也是鲁迅本人性格、人格、审美观点和审美情趣的一种表现形态。而这其中,简凝之美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项,在鲁迅小说风格的长廊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从鲁迅小说简凝之美的表现形式,其个性特征及简凝之美的渊源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一使鲁迅的作品“言简意更深,微处见真情”的独特风格特征。
一、鲁迅小说简凝之美的表现
简洁和凝练,的确是许多大作家所共有的特点,这种写作风格可以说并不鲜见,然而正是这一看似普通平常的风格,在鲁迅身上却放射出了夺目的光彩,达到了杰出的成就。鲁迅的小说,不仅在用笔上惜墨如金,凝重有力,而且在整个艺术构思的过程中,都体现了简练的原则,以最简短的篇幅,概括了最丰富最深刻的内容。
(一)精炼传神的生活细节
细节是平凡的、具体的、零散的,如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细节很小,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但它的作用不可估量,有时一个细节就能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鲁迅的小说塑造了多种多样的典型人物和性格,正是凭借从实际生活中选择和提炼了大量富有特征的细节,加以具体的描写和刻画,才显得那样鲜明、生动、丰满、形象。从鲁迅小说中走来的生活,大都不是英雄伟业,也不是传奇冒险,而是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挣扎在晨昏日暮里。鲁迅小说的艺术表现也正是通过对人物日常生活形态的把握和概括,来白描性格,刻画肖像,所以从生活中提炼和选择细节显得至关重要。精炼传神的生活细节描写作为鲁迅小说简凝之美的表现形式之一,焕发着耀眼的光彩。
如《阿Q正传》中对赵太爷的描写:“赵府上晚饭早,虽说定例不准掌灯,一吃完便睡觉,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其一,是赵太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其二,便是阿Q来做短工的时候,准其点灯舂米。”此外,为了购买阿Q偷来的便宜货,派人去把阿Q找来时,也曾“为此新辟了第三种的例外:这晚上也姑且准点油灯。”这定例和破例的细节,虽是一个概括性的简介,但却刻骨地描画出了赵太爷极端吝啬,吸血剥削劳动者以及贪图便宜等地主阶级典型的丑恶嘴脸。
《高老夫子》里高干亭改名的细节也很说明问题。黄三发现他桌上有一张贤良女校敦请尔础高老夫子的聘书,问他是不是改了名字。鲁迅写道:“但高老夫子只是高傲地一笑,他的确改了名字了。然而黄三只会打牌,到现在还没有留心新学问,新艺术。他既不知道有一个俄国大文豪高尔基,又怎么说得通这改名的深远的意义呢?所以他只是高傲地一笑,并不答复他。”在这里,鲁迅特别加重“改名的深远意义”,一针见血地戮穿了高干亭投机新学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当黄三没有看出他的伎俩时,他居然还能够嘲笑黄三,并且是高傲地嘲笑,仿佛他真做得有理一样。足见他不仅欺人,还要自欺。不仅如此,高干亭把高尔基理解成姓“高”名“尔基”,他又何尝真懂什么新学?鲁迅仅仅通过一个改名的细节,总共不过用了一百字左右,就揭了高干亭两个底,语含辛辣的讽刺,而且鞭辟入里,简练有力。这样的例子在鲁迅的小说中不胜枚举,高度概括又充满了个性化表现的生活细节与人物的性格、故事的发展息息相关,使得鲁迅的小说血肉丰满了起来。
(二)只字也惊人的语言艺术
在人类社会里,语言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1]。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古今中外的伟大文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不在语言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鲁迅当然也不会例外,他在语言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在我国新文学史上至今仍是无与伦比的。不论是人物的对话还是直白的叙述,那简洁、明快、洗炼的言辞既冷隽又犀利,既深刻又辛辣。他还曾经在《花边文学·看书琐记》里说过:“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他自己还亲自体察到隔壁听人讲话,久而久之,就能分辨出人物有哪些,是些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一贯强调人物的对话要精炼、简短,抓住人物个性化的语言特点,就能够写逼真、贴切,含义深广,使读者闻其声如见其人。
《药》里的革命义士夏瑜被清廷杀害后,鲁迅写了刽子手康大叔与茶客们的一段对话: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在这里,夏瑜本人的言行很鲜见,假如通过叙述人的语言来写,也只能勾勒出夏瑜一个人的粗略轮廓。鲁迅却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来评介夏瑜,造成了康大叔、驼背和花白胡子对夏瑜的反衬,不仅使夏瑜的英雄形象显得更加光彩夺目,而且还多刻画出了康大叔的反动嘴脸和花白胡子、驼背两人的奴才相。四个人物由此描绘得栩栩如生,这是多么简凝的笔墨啊!还有《孔乙己》中对孔乙己涨红了脸辩解窃书的描写,《故乡》中迅哥儿与闰土两次相会个性化对话的对比,以及《风波》中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口头禅的重叠……活化了一个个纸上的人物,使得他们不再扁平,变得新鲜真实了起来。经过艺术加工的、有独创意味的“炼话”技巧作为鲁迅小说简凝之美的表现形式之一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三)速笔绘就的背景勾勒
鲁迅很少绚丽繁复的背景描写,有时只是寥寥数语,像中国传统的舞台布景与年画,读者意会即可。鲁迅的作品的确不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有大量的细节的描写,广大的生活面,精致的花边与纹路,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鲁迅的作品就不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或生活,他自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鲁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的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2]“这方法”对于鲁迅的艺术创作来说不但不是局限,而且更加有助于他简洁、凝练的艺术风格的表现,富于典型意义的速笔勾勒往往比浓墨重彩更加能够体现出鲁迅不俗的艺术作为。如《在酒楼上》对于废园里的景色的一段描写:
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
那“斗雪开着”的老梅,那“在雪中明得如火”的山茶花,作者只疏疏地画了几笔,给人的印象却十分鲜明突出。“著物不去,晶莹有光”八字,真正抓住了江南积雪的特点,也是片语传神的写景佳句。鲁迅描写环境,特别是描写自然环境,吸取了我国水墨画的方法,不用细笔,不施重彩,抓住景物的主要特征加以渲染,着墨不多,却神态逼真。再如《祝福》开头,写“我”刚回到鲁镇,见到鲁四老爷的情形:
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也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
短短的篇幅,就道明了鲁四老爷的近况,还逼真描画出了他的性格和立场。没有赘言,可谓增一字则嫌太多,减一字则嫌太少。可见,鲁迅背景勾勒建立在他广大的视野、渊博的知识和对社会现实的细密分析上,是小说创作简凝之美的成功表现形式。
二、鲁迅小说简凝之美的特征
鲁迅的小说对关于简洁和凝练的要求几乎达到了“洁癖”的程度。他曾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这样说过:“我作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总希望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得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正是因为鲁迅对于艺术创作抱有这样臻求完美、精益求精的态度,小说的简凝之美才具有了自身独特的个性特征,使得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文章”在鲁迅手中化百炼钢为绕指柔。
(一)简凝之美美在真切
鲁迅在写作时反对瞒和骗,粉饰现实,表现虚伪的思想感情;提倡去伪饰,存真意,揭示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及其本质,实事求是,忠于生活和自身的思想感情。所以他在艺术表现上常常是力求朴素的,避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卖弄自己的才学,或者故意渲染、夸大,以致歪曲和掩盖现实的本质。阿·托尔斯泰就要求作家去求得“金刚石似的语言”,也就是能正确表现思想的“唯一的一句话。”[3]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典范,他不唠叨、不啰嗦、不附加任何陪衬和拖带的简凝文风使得小说更加真实、确切,读来有如人物在身边说话,景物在眼前呈现。他从不在文中用华丽的词藻、多样的修饰给读者造出幻境,使欣欣然如坠入五色彩云中,他是冷静而残酷的,就用最简单的言语把血淋淋的事实剥开来给你看。
如《风波》中,传说“皇帝坐了龙庭”,而且要辫子,但七斤已经没有辫子了,使七斤嫂“觉得事情有些不妙”:伊一转眼瞥见七斤的光头,便忍不住动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绝望起来,装好一碗饭,搡在七斤的面前道,“还是赶快吃你的饭罢!哭丧着脸,就会长出辫子来么?”“怪”、“恨”、“怨”三个字就把当时七斤嫂对七斤的那种极为复杂的心理状态真实确切地刻画了出来。而一个“搡”字,不仅表示了用力推这个动作,“怪”、“恨”、“怨”的感情色彩也包含在其中了。再如,《一件小事》是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一篇作品,真正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展现了人物的真情实感。人力车夫在“北风小了”的时候“跑得更快”,自然是为了多拉几次,多赚来几个钱。因此,尽管鲁迅没有只字片语描画人力车夫此时此地的心理状态,但鲁迅对车夫行动上的简洁描写,却把车夫冒着严寒多拉快跑的心情和希望真实地表现了出来。《阿Q正传》中对于阿Q形态的描写,《祝福》中对于祥林嫂死亡前夕的描写……都是那么简洁凝练而又真实确切,真正做到了去伪饰而存真意。
(二)简凝之美美在形象
鲁迅善于使自己所描写的人物浮雕似的出现在读者面前,使所描写的景象就像写生画那样生动鲜活,做到这样的境界,除了精湛的艺术技巧,形象化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象性是鲁迅小说简凝之美的独特个性特征之一。体现语言的形象性,动作的形象性,景物的形象性,首先要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把一般的说明变成具体的描写,但这具体的描写又不是大量和繁冗的,从这一点上就足见鲁迅的创作功力之深。另外,做到形象逼真,还必不可少要用到各种修辞手法,在遣词造句上也要多变化,不能显得呆板平淡,鲁迅在完美地做到这些的同时,却并未影响到其简凝的文风,可谓一举兼顾。
小说《故乡》在写“我”和农民闰土20年来相爱之深和相念之切以后,再写他这次回到故乡,闰土和他一见面就恭恭敬敬地称起老爷来。在旧社会里,“老爷”本是下层人民对上流社会的人普遍的称呼,一般人都习以为常,不加注意,但突出地说明了阶级隔阂的严重性,而且这样的行为是符合人物性格和境遇的,短短两个字就体现了小说的形象性。《离婚》中写七大人处理爱姑的婚事纠纷,鲁迅只用了一小段话让他把基本意见说出来,再不多加一句。因为在当时的环境里,七大人的话就是命令,就得服从,用不着反复的解释和劝说。鲁迅的笔力全用在对七大人的排场、架子的渲染上,什么玩屁塞呀,什么唤“来——兮”呀,看似与纠纷无关,实际上却极有关系。这些对爱姑造成了先声夺人的精神威压,从而促使问题得以按照七大人的意图迅速解决。对七大人的语言和动作描写也极为简练,而且形象生动,贴合情境和身份,读来确实犹如七大人嚣张跋扈的嘴脸就在眼前。
(三)简凝之美美在蕴藉
《文心雕龙·隐秀》篇中说:“隐者也,文外之重旨者也。”这就是说的蕴藉。作家的观点、见解、思想感情,不是全都行诸笔墨,裸露无遗,而是意在言外,寓丰富的内容、强烈的感情于不言之中;或是刘知几《史通·叙事》中的“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鲁迅的小说就具有这样的蕴藉性,而这蕴藉性又是与其简凝的表达分不开的。鲁迅用其精简、平实的笔触化合了真实深刻的生活内容和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或讽刺,或幽默,或寓情于景,从而使作品表现出蕴藉性,达到这一境界,创作者的功力非同一般。
《明天》中,鲁迅这样描写单四嫂子埋葬夭儿之后的心情:
他越想越奇,又感到一件异样的事——这屋子忽然太静了。他站起身,点上灯火,屋子越显得静。他昏昏的走去关上门,回来坐在床沿上,纺车静静的立在地上。他定一定神,四面一看,更觉得坐立不得,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他,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他,叫他喘气不得。
因为“太静”所以感觉房子“太大”“太空”,感情上的重压就愈加汹涌。鲁迅并没有写她如何哭天抢地,沉痛不能自已,而是单纯只写了这样一个意境,但已经足以表达一个寡妇失去唯一爱子后痛苦、悲伤的心情,这不能不说是含蓄而蕴藉的。
《幸福的家庭》中有一段对“青年作家”的讽刺,鲁迅写这位作家做“猫洗脸”来逗引被妈妈打哭了的三岁的女儿时,简练中语含幽默,含义却是深邃的。《社戏》描写月光下的乡村景色:“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胡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简短却优美的景色描写,用词准确精当,抓住了景物最突出也最吸引人的地方描画出来,不枝不蔓,自然清新。同时作者融入了自己深厚的感情色彩,使得景中蕴情,情中有景,细品那深邃的思想和深沉的感情,也觉回味无穷。
三、鲁迅小说简凝之美的渊源
鲁迅作为文学大师,他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他能够自己创造伟大,更加在于它能够将别人的伟大收为己用。鲁迅小说的简凝之美除了是鲁迅自身的伟大创造,当然也不能磨灭中外艺术对作者的深刻影响。从鲁迅小说中,我们既能够体会出中国古典文学的神韵,也能够领悟到外国文学的先锋与进步,当然,简凝之美也不例外。
(一)古典文化的渗透
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说:“看看对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尽管如此,鲁迅仍然坚持自己的写作原则,摄取最能表现人物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的人物语言、行动,以高度简洁概括的笔力描绘表现出人物的灵魂,以形传神,形神一体。
这样的笔法在中国古典文化中亦是有迹可循的。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七写到:“武帝崇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金陵安乐寺四白龙不点眼睛,每云:点睛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二龙未点睛者尚在。”这里记述的就是人们常说的“画龙点睛”的故事。古人也明白抓住精神实质的道理,推而广之,后人做出了规律性的论析。古人强调艺术创作必须讲究神韵,而神韵必出自形神兼备之笔。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形似是神似的形体基础,只有抓住最能体现精神、神韵的形体并予以“画龙点睛”的描写,才能揭出精神实质,达到以形传神。
鲁迅有着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精湛的研究和深邃的修养,他的创作中无不浸润着古典文学的滋养,这是构成他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也是使他与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的古典作家们保持历史联系的根本原因。鲁迅赞美过《儒林外史》、《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白话小说,从中受益良多;他还喜爱魏晋文章,认为汉末魏初的文章清峻、通脱,这“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然而鲁迅的汲取继承带有创造性,是有发展的,并不是简单地模仿,他的吸收和学习经过了融会和贯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鲁迅小说时而好似一幅幅勾勒写意的水墨画,时而好似简化代意的戏曲演出,时而又好似意深言约的诗歌词曲,无一字赘言却仪态万千,自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
(二)民俗文化的熏陶
民俗文化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概念,它几乎包括了一个国家和民族足以影响和约束人们的各种风俗习惯,通过语言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民俗事象。我们读鲁迅的小说,就像浏览一幅幅民俗风情画,活泼、幽默、悠远、沉郁、凝重、精炼的画面,透出的是忧郁的美和迷人的魅力。那素笔勾勒的生活画面,或喜或忧的矛盾心情,都是与鲁迅的生活环境相关的,同时也是他对民间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的结果。
鲁迅幼年到少年所生活的环境,是江南的水乡绍兴——一个相对闭塞但乡风淳朴浓厚的保守之地,使他从小就浸润在各种民俗礼仪的说教之中,这使他对故乡的民俗文化有着别样的感情。所以我们在鲁迅的小说中能够看到记忆中比珍珠还要闪亮的罗汉豆,那是使人思乡的蛊惑;能够看到在过年的喜庆气氛中愈加悲惨的祥林嫂,那是一声苍凉的叹息;还能够看到江南水乡旷野里举行的春赛、面对着“神棚”演社戏的习俗,那是浑浊黯淡的现实生活中的一脉清流激越至今。
鲁迅从自己的生活记忆中提炼饱蘸民俗文化的片段并写进小说中,寥寥几笔却意象无限。白描手法的广泛运用,夹叙夹议的评论点拨,用简洁的线条描写场景和人物,涵盖了大量的风土人情、民间传说、世俗风貌。时而明丽欢畅,时而浪漫温馨,时而沉重暗哑,时而又尖锐辛辣。为文者善恶分明,有赞有弹,对于那些残酷的现实和“美好”的不现实,未明言却已暗示得非常泾渭分明。
(三)外国文学的影响
鲁迅从开始写作起就涉猎钻研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从众多的名家名篇中汲取有益之处,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思考和生发,并得出了自己的深刻感受,融进了自己的作品中。
许多外国作家、艺术家、文艺批评家都对文章的简凝性有着独到的见解。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第三章第一节“美的个性”中以“眼睛”喻指显示人物灵魂的窗口,说明艺术描写的妙笔就是要让人们透过这生花妙笔看到人物内在的精神、神韵。鲁迅青睐俄国文学。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同时代人》里也写道:“艺术性在于:以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生动而完整地表现出若不如此,也许用十本书都说不完的东西。由于这缘故,凡没有艺术性印记的作品,就特别冗繁而累赘。艺术家与此相反,他不用费很多话:他只要一个特征、一句话去表示思想就够了,而光是说明那个思想,有时就非得写一整本书不成。”
鲁迅曾在书信《致韦素园》中说过:“倘如霁野所定律令,必须长至若干页,则是一大苦事,我以为长短可以不拘也。”可见鲁迅对于文章的简洁和凝练是十分在意和看重的。鲁迅在借鉴的基础上有自身的艺术追求,他并没有一味地去模仿外国作家那样大段的心理描写,而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简洁、凝练的写作风格,融会到小说中,焕发出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