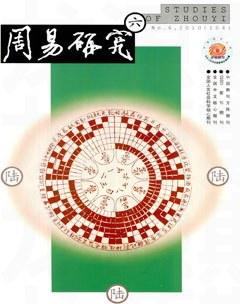简论朱子易学在元代发展的基本面貌
谢辉
摘要:易学是朱熹学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易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元代时期,朱子易学在政府的推崇下,逐渐成为官方学术;同时学者也积极地以师徒相传、朋友讲习与读书自得等方式,传承朱子易学;此外,元代学者还通过研究朱子的易学典籍、发展与批判朱子的易学观点,以及调和朱于与程子的易说等多种途径,对朱子易学作深入探究。这三个方面即构成了朱子易学在元代发展的基本面貌。
关键词:朱子;易学;元代;基本面貌
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10)06-0054-07
朱熹是我国古代的理学大师,同时也是易学大家,其易学思想一方面在其理学思想中占据了纲领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在易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可谓朱子学术中的精华。元代时期,朱子易学的官方地位不断提高,学者对其传习与研究的热情也不断高涨,可以说是朱子易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有必要对朱子易学在元代发展的基本面貌,进行一番较为详尽的探讨。
一、朱子易学在元代的官学化
元朝政府推尊朱子之学,而易学作为朱子学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成为了元朝的官方学术。朱子易学在元代官学化的倾向,首先表现在一大批深于朱子易学的学者,出仕为元朝政府各级官员,如在学官系统内,丁易东曾任沅阳书院山长;黄泽任景星书院与东湖书院山长;胡炳文先仃江宁教谕、信州路学录,再辟道一书院山长,调兰溪学正,不赴,后又任明经书院山长;王申子曾被举荐为武昌路南阳书院山长,且其易学著作《大易缉说》亦是由官府出资刊刻;涂溍生任赣州濂溪书院山长;胡震曾任南康路儒学教授;梁寅曾辟集庆路儒学训导,以亲老辞;鲍恂曾任温州路学正;朱升于至正四年举于乡,后授池州路学正;张理先任泰宁儒学教谕,后又升任福州勉斋书院山长,终于福建儒学副提举;龙仁夫任陕西儒学提举。非学官系统者,如李简曾任泰安倅;曾贯曾任绍兴府照磨;陈应润由黄岩文学起为郡曹掾,后调明幕,又凋桐江宾幕;保巴曾任侍郎,继任黄州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又迁太中大夫,终于尚书右丞,元仁宗为太子时,保巴曾奉旨为其讲授易学,且将自己的易学著作献上。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本身仕履不详,但曾经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过一定功名,如熊良辅于延祐四年曾经“以《易》贡”,解蒙则“中天历己巳江西乡试”。这些学者中,如胡炳文、熊良辅等本身即是朱子易学嫡传,其余虽非专主朱子一家,但都对朱子易学有较深的理解,并在对朱子易学的接受、批判、改造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易学体系。他们的出仕为官,可以说为朱子易学增添了显著的官方学术的色彩。
朱子易学的官学色彩,还可以从科举考试中朱子易学所受重视的程度反映出来。按照元朝政府的规定,科举考试中《易》以程、朱义为主,同时可兼用古注疏。但从目前留存下来的一些科举程文和拟文中来看,应举者对朱子易学的关注程度,似乎要在程子易学与古注疏之上。具体而言之,这些程文与拟文中,有一部分倾向于合会程朱之义而作答,如至正辛巳科湖广乡试第一名谭圭,其程文开篇云:“程子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之则一事,专言之则包四者。朱子曰:元亨利贞天道之常,仁义礼智人性之纲。合二说而互言之,明问可无疑矣。”此即是兼用程朱义。另有一些文章则倾向于以朱子义为主,如元代涂溍生作《周易经义》,专门仿照科举考试拟题作文,给学者作为榜样,其中“乾文言体仁足以长人”一题,涂氏拟文曰:“尽人事之当然,以明天德之自然,非至健之功不能行也。夫德之在天,即事之在人也,然非至健之君子,何以能合天人而一之哉?”这实际上是从君子以人合天的角度立论。程子在注释《乾》卦《文言传》此段文字时仅云“行此四德,乃合于乾”,说得比较模糊;而朱子则云:“元者善之长以下四句,说天德之自然。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以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其在君子所当从事于此者,则必体仁乃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斡事。”又云:“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可见,涂氏之拟文,从立意到文句基本都来源于朱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程子《易传》不注《系辞》、《说卦》、《杂卦》,因此若于此数篇中出题,则基本上都要据朱子义回答。如至正丁亥科江浙乡试,《易》义之题目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白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此段文字出自《系辞下》,程子无注,因此在一篇署名傅常所作的程文下,考官林宗起即批曰:“今制,《易》主程朱,兼用古注疏。此题程子无传,朱子《本义》惟日:乾坤变化而无为……此作主朱子《本义》,而兼用注疏,盖今制所许者也。”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作文时以程子义为主而不取朱子义的情况,就显得较为少见。由此可见,对于元代科举考试中《易》的部分而言,朱子易学的重要程度应是排在第一位的。这同样可以表明,在元代的官方学术中,朱子易学占据了一个较高的地位。
总之,在元代理学与朱子学地位提高的大势下,朱子易学出现了显著的官学化的倾向,治朱子易学的学者纷纷出仕为官,同时参加科举考试的应举者也越来越倾向于用朱子易义。可以说,日益成为官方所认可的学术,是朱子易学在元代发展的基本态势之一。
二、元代朱门后学对朱子易学的传承
除了官学化的色彩日益明显之外,朱子易学在元代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即是越来越多的朱门后学,开始从事于对朱子易学的传授,并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传承谱系。其传授的具体形式,可以分成师徒相传、朋友讲习与读书自得三类。
作为我国古代学术传承的主要方式,师徒相传在元代朱子易学的流传中占据了首要地位。元代学者中,目前明确可知以朱子易学相传授者,如胡炳文传《易》于其父胡斗元,斗元则从朱子从孙朱洪范“得《书》、《易》之传”。同时胡炳文之弟子中,从其受《易》者又有金震祖、徐骧等。熊良辅“早师同邑遥溪熊凯学《易》,复得《易》传于凯友进贤龚焕”,凯、焕师饶应中,应中学于饶鲁,饶鲁则师朱子弟子黄斡。吴澄学于程若庸。其学亦出于饶鲁,同时其弟子鲍恂亦从其受《易》。胡震“长饶先生鲁之门”,也是自饶鲁传《易》。胡一桂学《易》于其父胡方平,而“饶州德兴沈贵宝,受《易》于董梦程,梦程受朱熹之《易》于黄斡,而一桂之父方平及从贵宝、梦程学”,因此胡一桂之易学乃是“得朱熹氏原委之正”,其弟子中又有董真卿曾“从先师新安双湖胡先生读《易》武夷山中”,又得胡氏易学之传。程荣秀曾“从山屋许氏受《周易》”,“山屋许氏”乃许月卿,亦曾从学于朱子易学的正统传人董梦程。熊禾曾问学于朱子再传弟子徐几,徐几精于《易》,熊禾当是从其传朱子易学。丘富国为“徐进斋门人”,其易学应该也是来自于徐几,同时其弟子中,又有郑仪孙、张复、张谅得其易学之传;玉井阳氏世代传《易》,其易学乃是“自其五世祖得之型莲荡,莲荡得之晦庵,渊源有自”,爱莲荡即爰渊,其门人中有阳枋、阳罍,均有《易说》行世,即玉井阳氏之祖,可见阳氏之易学亦是直接出自朱子。这些学者的易学,源头都能追溯到朱子,可谓得朱子易学原委之正,成为元代朱子易学流传过程中的一股中坚力量。其传承关系可见下图所示:

与师徒相传相辅相成的,是通过朋友讲习的方式而实现的对朱子易学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的影响力,虽不如师徒传授之大,但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较为著名者,如胡一桂曾访熊禾于武夷山,与其讲论易学,所谓“留山中三阅月,相与考订,推象数之源,极义理之归”。可见,胡氏所传之朱子易学,除了来自其父,还有赖于与熊禾的讲论。另一位学者陈栎,则与胡一桂、胡炳文都有交往,其讨论的很多问题都集中在朱子易学身上。如陈栎曾致书胡炳文,就朱子《易本义》中二条注文提出疑问,胡炳文回信详加解答,陈栎得信后,又答书表示赞同胡炳文之说;同时陈氏亦曾致书胡一桂,讨论其父胡方平《启蒙通释》中揲蓍之说。陈栎、胡一桂、胡炳文均为元代朱子易学名家,他们的讨论对推进朱子易学研究的深入,也有一定意义。又如上文所提到的玉井阳氏,五世传朱子易学,曾与元代另一位易学家王申子进行过辩论。由于王氏《大易缉说》不专尊朱子,阳氏“特编二帙”与王氏论难,其中很多论述都是援朱子之说为据。如王氏认为太极乃理气象数之混沦未分,玉井即“举晦庵之说”以难之云:“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王氏对此说法并不接受,又撰文以捍卫自己的观点,并将其写入《大易缉说》之中。这次正统朱子易学与非正统朱子易学之间的交锋,也是以朋友讲论的方式出现的。而宋元之交的学者俞琰,其最初接触朱子易学,是“幼承父师面命,首读朱子《本义》,次读程《传》”,对朱子易说较为尊信;但此后在与朋友的讲论中,却渐渐对朱子易说产生了怀疑,如俞氏自已所说的那样:“长与朋友讲明,有程朱二公所未言者,于心盖不能无疑。”据俞氏的记载,与其讲论者有“西蜀荀在川,新安王太古,括苍叶西庄、番易齐节初”。就其可考者而言之,王太古即王茔翁,曾与朱子易学的重要传人许月卿有往来,其说以九宫图为河图,以五行生成图为洛书,又认为“先天方图未可面南看”,遂反而刊之,都与朱子之说相悖;齐节初即齐梦龙,其易说乃是“彖辞与彖传混为一说,爻辞与爻传亦混为一说”,亦与朱子分别经传之旨不同。正是在与这些非正统朱子学者的讨论中,俞氏才开始转变其尊朱的态度。其易学著作《周易集说》、《读易举要》等,虽然仍是以朱子易学为主,但已有很多不同于朱子,甚至反驳朱子之处。这种原本尊朱,但在其后的讲论中逐渐改变的情况,代表着元代以朱子易学相讲习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之外,朱子易学在元代的发展,还有一条途径,即在未有师友传述的情况下,通过渎朱子之书,而契悟朱子易学之旨。如元代较为早期的学者李简,其学易首先自王弼《周易注》与曾檀《大易粹言》人手,《粹言》集二程、张载、杨时、游酢,郭忠孝、郭雍七家之说,李简据此而学到的,大约只是北宋的义理派易学。此后李氏举家迁往东平,此时方得见“胡安定、王荆公、南轩、晦庵、诚斋诸先生全书”,开始接触到朱子易学。今其所著《学易记》中所包含的朱子易学的成分,可能就是在此时通过研究朱子易学著作而逐步形成的。虽然李氏在学易的过程中,也曾与朋友进行过讨论,如其所说:“岁在壬寅春三月,予自泰山之莱芜,挈家迁东平,时张中庸、刘佚庵二先生与王仲徽辈,方聚诸家《易解》而节取之,一相见遂得厕于讲席之末。”但参与讨论的学者中,张特立以通程子《易》闻名于金末,刘肃曾集各家之说作《读易备忘》,二人均非朱子易学学者。王仲徽则为道士范圆曦之弟子,大概属于道教易学家。朱子易学在他们的讨论中,不太可能占据主要地位。因此李氏之朱子易学,仍当以其读书而自行体会者居多。又如宋末元初的丁易东,其学并无师承,以至《宋元学案》都未有著录,同时与其有交往的刘辰翁、姚燧等人,也并不以朱子易学名家。因此,丁氏对朱子易学的了解,也应该是来自于其渎书思考。从其学《易》的过程来看,丁氏早年接触到朱子易学,就是从读朱子之易学著作开始,如其所说的那样:“予少而学易,得王辅嗣之《注》焉,得子程子之《传》焉,得子朱子之《本义》焉。”其后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朱子易学有不足于象数之弊:“其于象数也,虽于《易学启蒙》述其大概,而《本义》一书,尚多阙疑。”因此才会产生以象解《易》的念头。可见,丁氏易学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朱子易著的阅读与反思的基础上,是丁氏“思之思之而又思之”的结果。
以上所述者,即是朱门后学在元代对朱子易学进行传承的大致情况。这些传承的途径虽然各不相同,其所传者也并非全为正统的朱子易学,但却成为了维系朱子易学在元代发展的重要力量。相比较于官方的力量而言,元政府虽然通过提高朱子易学学者的地位及在科举考试中使用朱子易学,来达到推尊朱子易学的目的,但实际上,有不少朱子易学学者,如胡一桂、熊禾、俞琰等,均拒绝出仕,同时元朝前期科举制度曾长期停废,科举恢复之后,士人之治《易》者仅求中试,而不愿对朱子易学作深入探讨,又导致了朱子易学的浮浅与僵化。而朱门后学对朱子易学的传承,则秉持着传续道统与治学求真的精神,这一方面保证了朱子易学在未成为官方学术时仍能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又使得朱子易学在流传的过程中始终充满活力。其在元代朱子易学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
三、元代学者对朱子易学的研究
在元朝官方的提倡与学者们的积极传播下,元代学者对朱子易学的研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其研究形式也显得多种多样:既有对朱子易学著作进行的专门研究,也有对朱子的易学观点进行的阐发、批判、改造,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对程、朱易说之间的差异进行调和。这种对朱子易学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可以说是朱子易学在元代发展的又一大特点。
元代学者研究朱子易学的第一个方面,是对朱子的易学菩,乍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朱子的易学著作进行注释者。其具体的注释方式包括集注式与通释式。集注式的代表著作有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注》、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熊良辅《周易本义集成》,这种注释形式的特点是兼收并蓄,集诸家之说以羽翼朱子。如胡氏《易本义附录纂注》,其体裁为“以朱子《本义》为宗,取《文集》、《语录》之及于《易》者附之,谓之附录;取诸儒《易》说之合于《本义》者纂之,谓之纂疏”,即是博采众家的典范。而通释式的代表著作则为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这一类型的著作重在由博返约,力求简明准确地对朱子易学著作作出解释,如胡炳文在作《周易本义通释》之前,先作有集诸家《易》解之《精义》,大致亦是集注体,但其后自己却觉得这种注释形式“失之太繁”,失去了“学有统一”之旨,于是改用通释的形式,以朱子《本义》为准,而将诸家之说融会贯通为一以释之,所谓“取有合于《本义》者,或一字,或一句,或一段,或用其意不用其辞”。第二类是对朱子的易学著作进行阐发者,属于这类的著作有熊禾《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以及胡一桂《周易本义启蒙翼传》。这类著作的共同特点是,并不对朱子易学著作作直接的注释,而是采取多种形式,对朱子易说进行多样化的阐发。如胡一桂《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从其名称上来看,是解释朱子《易本义》、《易学启蒙》的著作,但完全没有登
载二书的本文,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体系:以内篇上篇为天地自然之易、伏羲易、文王易、周公易、孔子易;中篇为三代易、古易、古易之变、古易之复、易学传授、易学传注;下篇为举要、筮法、辨疑;外篇为对《易纬》以下十余种非《周易》传注之书的评价。其目的显然不是对朱子易学著作进行逐章逐句的注解,而是对朱子易学思想的一种全面阐发。熊禾《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虽然分为“本图书”、“原卦画”、“明蓍策”、“考变占”四部分,从形式上与朱子《易学启蒙》似乎保持一致,但只登载了《启蒙》中的一部分易图,而未录朱子之说;同时即便是所登载的朱子易图,也颇有改易,且其中插入了大量自作的易图与自己的解说。可见,此书亦只是“发挥《启蒙》之旨”,而非注释《启蒙》之作。这类著作在形式与内容上,显然更具创新意义。
关于朱子易学著作的研究,可以说是元代学者研究朱子易学中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部分,但却决非全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对朱子易学中的相关观点,以多种方式作出了进一步的阐发与辨正,这构成了元代学者研究朱子易学的另一个方面。如许衡《揲蓍说》,通篇皆是解释朱子筮法,但其解释并非是简单地疏通文字,而是用数学的方法,在朱子筮法的基础上“演八卦静变往来之数”,通过演算各卦的概率,来阐发朱子筮法中“阴阳之体数常均,而用数则阳三而阴一”的阴阳体用的含义,同时驳斥其余各家筮法中阴阳均平之失。张理《易象图说》,则对朱子的河洛之学进行了推阐。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朱子以河图洛书为《易》之源的说法上,而是从朱子之说出发,进而寻找河图洛书之源,并最终将河洛图式的源头推到了陈抟《易龙图》,《龙图》通过一系列变化,方能变得河图洛书。这无疑是对朱子河洛之说的一种极大的丰富。对朱子易说进行辨正者,如王申子即不同意朱子“《易》本卜筮之书”之说,而提出卜筮乃是“易之流”,非“易之道”。俞琰则对卦变之法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卦变不能用于解经,同时又批评河图洛书之说为牵合附会,都是对朱子之说的指责。李简、雷思齐等人虽然承认河图洛书的存在,但却并不同意朱子所提出的河洛图式,如李简即曰:“文公此说,甚惬愚意,然仆所取之图,则亦不能尽同也。”雷思齐对朱子之图的指斥更加严厉,甚至说其是“专己自是,张其辩说,不克自反,一至于此”。丁易东在《大衍索隐》中,不取朱子以五乘十的大衍数说,认为这是“未有得夫五十数与四十九之全者”,又在《周易象义》中,取杨忠辅的揲左不揲右之筮法,而不取朱子筮法。此外,尚有李简不取朱子之太极本体论,陈应润批评朱子所传的周敦颐《太极图》为老氏之学,丁易东、胡震等人改变朱子所定《周易》文本的经传排列次序,等等。这种对朱子易说勇于加以辨正的现象,可以说是元代朱子易学发展中一个极大的特色。
最后,元代还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将朱子易说与程子易说进行调和。其调和的具体方式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方式是将程子与朱子的易学著作合编为一者。属于这类的著作有赵采《周易程朱传义折衷》,以及董真卿《周易会通》。赵氏之书,其体例为在《周易》经传的编次上沿用经传混排之旧本,每句经文之下,先引程子《易传》,再引朱子《本义》或《语录》中有关部分,最后再系以己说。董真卿《周易会通》,采用的既非程子所据的经传混排之本,亦非朱子所定的经传分离之本,而是自行创立了一种新的编次方式,以各卦所属的《彖传》、《象传》、《文言传》等易传,分附于每卦之后,试图以此实现程、朱所据之本的会通;在注释形式上,则采用了元代通行的纂疏体,每句经文下先列程子《易传》与朱子《本义》全文,是为“集解”,再列程子与朱子之语录,是为“附录”,最后附以诸儒之说,是为“纂疏”。这类著作较为引人瞩目的,乃是力图通过汇编程朱易著这种形式上的折衷,而实现二家思想上的折衷。但由于二家易著的体例与解说本身差距很大,因此在合编的过程中便常有扦格难通之处,也由此招致了另一些学者的批评。另一种方式是不列程子与朱子的易学著作原文,而是将程朱之观点融合在一起,以自己的语言加以重新叙述。这一类型的代表著作为梁寅《周易参义》。在其《自序》中,梁氏明确阐述了其对程朱易说的看法:“程子论天人以明《易》之理,朱子推象占以明《易》之用,非故为异也。其详略相因,精粗相贯,固待乎学者之自得也。”正是在这一看法的指引下,梁氏才撰成《周易参义》,其所谓“参义”者,实际上就是参用程、朱二家易义,亦即其所谓的“参酌二家,旁采诸说,僭附己意”。而其参用二家的具体途径,则是用其意不用其文,其书中直接引用程、朱原文之处可谓少之又少。这种方式的特点在于真正实现了融二家之说而为一说,与第一种方式相比显得较为自然,彼此抵牾之处也较少。
以上所叙述的便是朱子易学在元代发展的基本面貌。总的来说,朱子易学在元代,既获得了官方的承认与推崇,又在学者的传承与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其影响力不断增强,最终成为了易学界中的主流学说。
责任编辑:张克宾姜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