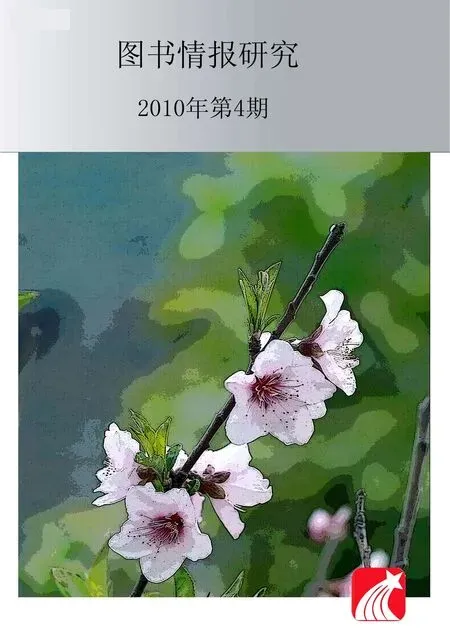洪亮吉的方志纂修思想
王 新 环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新乡 453007)
·史考纵横·
洪亮吉的方志纂修思想
王 新 环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新乡 453007)
洪亮吉生活的时代,正是方志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修志活动遍及全国。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的志书普遍存在着质量粗滥的现象。洪亮吉的修志思想与当时志书的质量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修志理论正是在纠弊中逐渐成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清代的方志名家,洪亮吉不但在方志理论上有所贡献,在修志态度上也为后世学者树立了榜样。
洪亮吉 志书状况 修志思想
洪亮吉(1746-1809),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字君直,又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等职。嘉庆四年,因直言上疏获罪,被遣戍伊犁,不久赦归。归里后,曾主讲于旌德洋川书院和扬州梅花书院。
作为乾嘉时期的修志名家,洪亮吉成绩斐然,备受学者赞誉。梁启超在谈到清代的方志学成就时,称“洪稚存之《泾县》《淳化》《长武》”为“最表表者”[1]。当代学者仓修良更称洪亮吉“是清代方志学界考据派的中坚人物”[2]。洪亮吉纂修的方志主要有:《登封县志》、《固始县志》、《澄城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延安府志》、《怀庆府志》、《乾隆府厅州县图志》、《泾县志》和《宁国府志》等。
洪亮吉生活的时代,正是方志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清王朝开国之初,为了掌握各地的山川形势、风俗物产、土地人口等资源,就开始了全国性的修志活动。特别是从康熙至嘉庆时期,清政府为了纂修和续修《大清一统志》,令天下广修志书,以备征采。各府、州、县的地方官员们奉檄而纂,修志活动如火如荼,燎原全国。
这一时期的志书虽然有不少体例精当、内容徵实的上乘之作,但也不乏应付差事、照抄前志的敷衍之文。此外,由于多为官修,主持人又往往是本地官长和士绅,难免矜夸乡里,虚誉人物。再加上修志时间仓促,讹舛极多,一些方志的质量大打折扣,失去了一方信史的功能。如康熙时期的学者施闰章在《安福县志序》中不但抱怨郡邑志乘中存在的“义爽笔削,颂长吏则谀,传先达则夸,纪名胜则附会,摭文词则浮芜,分星野、考沿革则淆混。书取速成,事多舛驳”的状况,还叹息作为一方信史的方志反“不如国史足信”[3]。康熙年间奉檄而修的《修武县志》,纂者李谟在《凡例》中也无奈地说:“是役也,迫于时日,又无群书以资考订征引,遗漏舛讹恐所不免。”[4]雍正时期,方志内容粗滥草率的现象引起了雍正帝的注意。他在诏令中说:“今若以一年为期,恐时日太促,或不免草率从事,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摭采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宽至二三年内,纂成具奏。”在这里,雍正帝把修志的时间放宽了,但对于应付了事的纂修,他则警告说:“傥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亦即从重处分。”[5]雍正帝的诏谕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志书修纂粗滥的普遍现象和政府对志书质量的焦虑。乾隆时期,这种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吴乔龄在《获嘉县志序》中说:“自京省以迄郡邑靡不有志……顾志虽多,而佳者鲜。觏其病有二,或但取计簿而其言不文,或徒炫博洽而其诚不著。”[6]150道出了当时志书的浮夸与俚鄙之风。嘉庆时期,著名学者纪昀在《安阳县志序》中说:“今之志书,……其相沿之通弊,则莫大于夸饰,莫滥于攀附。一夸饰而古迹、人物,辗转附会;一攀附而琐屑之事迹、庸沓之诗文,相连而登。”[6]189
总起来看,清代前中期的志书,其弊端主要集中在内容讹舛、文采俚鄙、人物及古迹夸饰等方面。志书质量的堪忧,使一些学者在批评方志的同时,在修志思想上更注重于利用文献、征引文献,用古证今,以此进行纠弊。同时,针对志书中出现的各种弊病,在体例和内容上进行修正。
洪亮吉正是这样一位病其弊、欲治其本的学者。在修志实践中,针对前期及当时的志书俚鄙和不实之风气,他以纂一方信史之精神,在志书修纂上求“典”求“信”。其所修志书,类目命名,一准昔贤;征引文献,不厌其详。正如毕沅在《登封县志叙》中所说:“稚存病夫近时府州县志皆俚而不典,信传闻而忽书传,故其命名皆取于秦汉以来至唐宋而止,又徵引历史及记传皆不厌其详,必无可徵,始采旧志及采访事实以补之。”[7]2洪亮吉求“典”求“信”的修志态度及采取的尊古与考证、采访与事实相结合的修志方法,使《登封县志》无论在体例安排上还是内容徵实上都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名志,备受学者之赞誉。时任河南府事的刘文徽称:“稚存好古渊博,于名胜古迹考证折衷,必无仍讹踵谬、挂一漏万之失,藏弆者将珍为珙璧。”[7]10金钟麟亦称此志为“名流之述作”[7]13。毕沅也说:“他日传是书者,当与宋敏求、孟元老同称,非近今方志所可同日而语也。”[7]3
因时代久远,求证困难,地理沿革之误,是当时志书讹舛的一大因素。在地理沿革的考证上,洪亮吉尤为重视。当看到新修的《庐州府志》称汉代的庐江郡“兼有江南”时,他致信庐州知府张祥云,称“一方之志,沿革最要”,并利用《汉书》《史记》《晋书》等文献考证汉代庐江郡的沿革源流,举五例来证明“汉庐江郡无江以南地”[8]。在考证的同时,洪亮吉还注重考古与证今相结合。他在纂修《淳化县志》时说:“凡志方隅,必推今昔,稽乎古图,准以今尺。”[9]作为考据派的代表人物,洪亮吉的这种“凡志方隅,必推今昔”的修志思想是极为难得的。因为,清代考据学家所纂修的志书多具有“厚古薄今”的学术特点,而洪亮吉在厚古的同时,也注意了与现实的结合。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还体现在他的《贵州水道考》中,洪亮吉在任贵州学政期间,看到贵州水道“一水则随地异名,有至十数名不止”,命名混乱,以至撰方志时,“询土俗者转转承讹,无一可据。”在此情况下,他就借督学之机,亲身考察,“轺车所至,类皆沿源溯流,证以昔闻,加之目验,即不信今,亦不泥古”,用两年时间撰成《贵州水道考》,希望“为方志者有所考镜”[10]。洪亮吉的心愿,在道光二十一年刊出的《遵义府志·水道考》中得以实现,纂修者郑珍借鉴了他的考察成果。
此外,针对当时志书滥收、夸饰的弊病,洪亮吉还提出了“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的修志主张。他认为:“苟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如明康海《武功志》,韩邦奇《朝邑志》等是也;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材于异地,侈景物于一方,以致讹以传讹,误中复误,如明以后迄今所修府州县志是也。”[11]1164-1165明确指出了明以后迄今所修的府州县志“借人材于异地,侈景物于一方”的滥收、夸饰弊病,致使志书内容“讹以传讹,误中复误”。在这种情况下,他指出,“撰方志之法,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只有这样,才能“博考旁稽,义归一是,……可继踵前修不诬来者。”[11]1165
在当时志书讹舛泛滥的情况下,洪亮吉提出的“一方之志,沿革最要”、“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以及“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的修志主张,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在纠弊的基础上逐渐成熟和发展起来的。除了在修志理论上创一方天地外,洪亮吉的修志实践也体现了一位方志学者不慕名利、治学谨严的可贵精神。
嘉庆十一年(1806),在纂修《泾县志》的间隙,洪亮吉还应宁国知府鲁铨的聘请纂修《宁国府志》,穿梭于两志期间,繁忙的修志生活,让他心情愉快。《泾川志馆口占》一诗充分反映了他此时的心情:“莫笑衰翁鬓雪盈,著书才了又吟成。平心不与时高下,举足仍为世重轻。调水符烦开士送,游山屐有野人迎。”[11]1569可是,不久之后,《宁国府志》部分刊出,当洪亮吉看到刊出的内容改窜极多、错误连连时,这对于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来说,实在不能容忍。他在给知府鲁铨的信中说:“不晤足下者,越一年矣。此回仆抵宣城,志事已刊至十分之四,闻底本皆自芜湖发来,改窜处极多,未知尽足下所定否?窃有未喻者数事,敢更质焉。”[12]1110洪亮吉在此信中提出了诸多“未喻”之事进行质疑,其主要内容如下:
志书重修问题:
祥异各志,营建诸门,于旧志皆照本抄誊,甚误者亦略无改正,何贵重修?是明为爱古而薄今,实则偷安而自便。[12]1112
事实搜访方面:
循吏中载宁国令范传真,是矣。然何以令宁国而得修南陵之堰?则唐宣城郡之地理与名宦传不可不合勘也。文苑中欲登唐诗人张乔,是矣。然何以家南陵而又附入池州之籍?则唐武德中之沿革及人物志不可不校也。此皆近在志传,而亦懒于搜稽。[12]1111
材料选择方面:
学校之金石,有登有不登;官廨之废兴,有载有不载。甚至宣城缺新建之祠,旌德削俞公之庙;泾则县丞廨宇亭脱见山,旌德则主薄衙斋堂删景吕;升降任心,去留随意。[12]1112
内容讹舛方面:
封建则挂七而漏三,大事则记一而忘两;流俗之传疑则信之,正史之明备则略之。[12]1112
在此信中,洪亮吉还着重指出志书讹舛的原因,多是人为造成的:
刊工虽集于宣城,而底本则来于榷署。局中总修分校诸人,皆若有不得预闻者,遂至一卷之内,前后迳庭;半部之中,各相矛盾。而奉行者又复过当,以为自芜湖来者,无一字之可更;自局中定者,无片言之足信。
虚设总修之号,翻为众怨所归。况足下既取独断而独行,又何须群策而群力?加以官事孔繁,高斋少暇,足下既假他人之手以代辛勤,他人亦既假足下之名以逞威福,以致物论沸腾,人情骇阻。[12]1112
洪亮吉毫不留情地在此信中提出了诸多问题进行质疑和反问。在重修问题上,针对一些门类不但照抄旧志,而且连明显错误也一无所改的,一针见血地指出:“明为爱古而薄今,实则偷安而自便。”如此作法,“何贵重修”?在材料的选择上,更是质疑有关人员“升降任心,去留随意”的毫无遵循的做法。特别是在对主持官员的专断行为上,洪亮吉的“既取独断而独行,又何须群策而群力”的尖锐质问,更让人心生敬意。在对诸多问题提出质疑之后,洪亮吉又说:“他日告竣之时,尚望于编纂内削去贱名,何敢于弁首中复加拙序?”看到志书被改窜得如此不堪,洪亮吉不但要求把自己纂修者的名字去掉,而且还拒绝自己的序文出现在书中,表现了一个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慕名利的可贵品格。
洪亮吉是乾嘉时期的学者,学术思想深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成为考据派的重要一员。但在方志纂修上,他的修志思想却是和当时志书的修纂现状紧密结合的,是在纠弊中逐渐成熟和发展起来的。洪亮吉的纂一方信史的重文献而忽传闻的徵实作风及“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的修志主张,以及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不容瑕疵、不慕名利的可贵精神,都值得后世学者借鉴、学习。
[1]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34.
[2] 仓修良. 方志学通论[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350.
[3] 江西省省志编辑室. 江西地方志序跋凡例选录[Z]. 南昌:江西省省志编辑室,1986:69.
[4] 刘永之,耿瑞玲. 河南地方志提要(上册) [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441.
[5] 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七十五[Z]. 北京:中华书局,1986:1122.
[6] 申 畅. 河南方志研究[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1991.
[7] 洪亮吉,陆继萼. 登封县志[Z]. 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76.
[8] 洪亮吉. 更生斋文甲集·卷三[M].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1019.
[9] 洪亮吉.卷施阁文乙集·卷一[M].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273.
[10]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四[M].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91.
[11] 洪亮吉. 更生斋文续集·卷二[M].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
[12] 洪亮吉. 更生斋文乙集·卷四[M].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
HongLiangji’sThoughtsonCompilationandRevisionofLocalChronicles
Wang Xinhuan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Hong Liangji lived at an age when local chronicles were in its heyday. Although local chronicles were compil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t that time, for various reasons most of them were of poor quality. Hong Liangji’s thoughts on compilation and revision of local records we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quality of the chronicles of his day and his theory gradually developed in rectifying the malpractice in the field. As a famous compiler of chronicles in Qing Dynasty, he made his contributions not only by establishing his chronicle-compiling theory but also by setting a good example for the later scholars.
Hong Liangji; quality of local chronicles; thought on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G237
王新环,女,1972年生,助教,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发表论文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