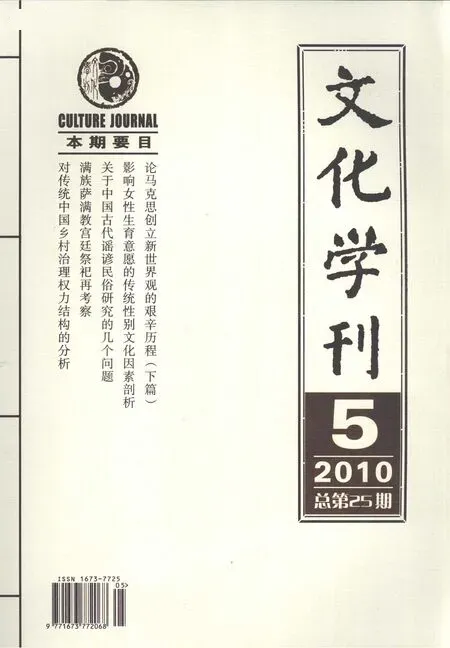辽海民间故事中的女性角色——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辽宁民间故事为例
赵东玉 何 欣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海历史与旅游文化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9)
“辽海”作为区域称谓,屡屡见诸史册,据学者考证,“‘辽海’一词出现的时间不应晚于东汉”。[1]而“辽海”的区域范围“就狭义而言,相当于今山海关以东至渤海、黄海间的空间范围,广义而言则涵盖渤海、黄海以北之整个东北地域”。[2]本文所采用的是广义的“辽海”概念,即古辽水①古辽水是古时东北地区的重要水系,有大辽水、小辽水之分。大辽水即今辽河、太子河下游地区;小辽水即今浑河流域。参见赵永复主编《水经注通检今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38页。周边广阔的边远地区。辽海地区的民间故事数量多,内容丰富多彩。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部分辽海地区民间故事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辽海地区民间故事,主要有古渔雁民间故事、喀左东蒙民间故事、谭振山民间故事、北票民间故事、满族民间故事。其中喀左东蒙民间故事的讲述与流传均采用当地的蒙古族语,而本文所讨论的民间故事主要是汉语故事,故不包括喀左东蒙民间故事。笔者试以这些民间故事为例,对辽海地区女性的角色结构及角色状况进行初步探讨。
一、女性角色结构论之外在形象
(一)美好生活的象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是指“共同居住、经济协助、有血缘关系的社会集团”,[3]它为多数成员提供物质和情感上的需要。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强,人们将家庭看做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常表现为对结婚成家的期待。女性在辽海地区的民间故事中被视为美好生活的象征,主要表现在娶妻与寻妻的故事情节中。
在辽海地区的民间故事中,娶妻情节大量存在。很多民间故事都以主人公娶了媳妇过上好日子为幸福美满的结局。如《穷打和尚》、《一文钱要媳妇》、《不识字的账房先生》等,其中的娶妻就意味着美好生活的实现。在“王恩石义”这组故事①《救皇姑》、《王恩石义》、《王恩与石义》、《王恩与施义》四则故事流传区域不同,但故事情节大体相同,故将其作为一组故事。中,娶妻是好人有好报的结果,故事中善良勇敢的人最终娶到了公主。娶妻还被当成生活中的重大喜事,《康大饼子接喜神》、《烧高香》就讲述了喜神帮助贫苦小伙子娶媳妇的故事,这里的娶妻是喜神降喜;而在《阿尔伦遇喜》中,打柴小伙阿尔伦所遇之喜就是娶玉竹姑娘为妻。娶妻在辽海地区民间故事中是好事、喜事,甚至有时娶妻即是获得幸福,人们对娶妻的肯定和重视,是女性象征美好生活的一种反映。
女性作为美好生活的象征,不但在娶妻情节中有所反映,也在寻妻情节中得以体现。辽海地区民间故事里的一部分女性是以神仙鬼怪的形象出现,这部分女性既有人的情感,又具备一定的法术本领,她们通常会嫁给普通男子,过常人的家庭生活,但其后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夫妻分离,接下来便出现了寻妻的情节。在《哥俩的故事》中,老弟在寻妻路上“直走得鞋烂衣裳破”;[4]《小梅》中寻妻的王祥“要翻过七七四十九座山九九八十一条河”;[5]《认媳妇》中的小伙要“朝一个方向走”,[6]遇海也不能改向;《寻妻》中的小伙子则要通过“牛毛沉底河”和“镜子山”的险境才能找到妻子;而《梅凤》中男主人公除了翻山越岭,还要面对妻子父亲的考验,更意外地去阎王殿走了一遭。寻妻之路如此漫长艰难、危险曲折,真心人却没有放弃寻妻,人们对寻妻的执著,恰恰反映了人们对女性所象征的美好生活的渴望。
在辽海地区的民间故事中,人们重视娶妻,强调寻妻的执著,都是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女性象征美好生活的表现。
(二)家庭的管理者
我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男性在家庭中多表现出“一家之主”的尊严和权威,负责领导和管理家庭,这点在民间故事中也有所反映。但辽海地区的部分民间故事中,拥有家庭大部分权威的长辈会让儿媳妇当家。在这类“儿媳妇当家”的故事里,女性呈现出了家庭管理者的形象。辽海地区的民间故事中讲述“儿媳妇当家”的典型故事有五则,分别是《考媳妇》、《黄土生金》、《媳妇当家》、《金马驹的故事》、《掌舵是肋骨肉换来的》。这五则故事流传区域不同,但就女性成为家庭管理者的故事情节显现出了一些共同特点。
首先,这些女性要通过家中长辈的考验,以确定其具有管理家庭的能力。如《考媳妇》中公公通过考试,相信儿媳妇能够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且对外办事妥善,故让她当了家。《掌舵是肋骨肉换来的》中的儿媳妇则割下自己的肋骨肉给婆婆做汤治病,婆婆才让这个忠于家庭的儿媳妇当家。
其次,要在祖宗、宗族和邻里面前宣布女性管理家庭。《金马驹的故事》中是公公请来东邻西舍,当着大伙的面把当家大事交给了儿媳妇;《黄土生金》中是公公把邻居请来,全家面对祖宗牌位,宣布让儿媳妇当家;而《考媳妇》中公公是当着祖宗和全族的面,定下了从今以后儿媳妇就是户主。
再次,管理家庭的女性具有一定权威和权力。在《媳妇当家》中,婆婆亲口承诺“谁当家,谁说了算”[7]后,儿媳妇接连发话组织一家人开展生产生活劳动;《金马驹的故事》和《黄土生金》中,当家的儿媳妇定下家庭成员共同劳动的内容,对于不遵守的大伯和丈夫进行惩罚,使家庭成员都能自觉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
此外,女性能够胜任家庭管理者的角色,获得人们的支持。在儿媳妇当家后,《媳妇当家》里是“没过3年,就排上新船治起大河田,日子慢慢富起来了”;[8]《金马驹的故事》、《黄土生金》里是全家人勤劳团结,最终使黄土中生出金马驹,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富裕,其中尽管带有幻想色彩,但还是说明女性可以成为合格的家庭管理者。而《金马驹的故事》中儿媳妇的不存私心、秉公办事,打消了妯娌分家的念头;《考媳妇》中公公宣布儿媳妇当家时“大伙儿就一齐叫好”,[9]从中不难看出人们对女性管理家庭的肯定与支持。
综上所述,在辽海地区“儿媳妇当家”的民间故事中,女性具有管理家庭的能力,能够对家庭进行有效管理,女性成为家庭管理者不是家庭内部的默许,而是向家庭外公开的事实,可以获得人们的接受和支持,这些都直接展现了女性作为家庭管理者的形象。但这类形象在辽海地区的民间故事中仅属特例,女性成为家庭管理者是由家中长辈决定的,其所管理的内容仅限于家庭日常事务,还不能就此认定这些女性家庭管理者就是家庭中的主人,但“儿媳妇当家”这类故事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与风采。
二、女性角色结构论之内在品德
(一)孝敬公婆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孝经》中就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10]的说法。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婚后一般要从夫居,孝敬父母对她们而言,主要是指孝敬公婆。辽海地区有些民间故事表达了人们对女性这一道德的期待和要求。
在辽海地区的民间故事中,有一些孝顺儿媳妇的典型代表,如《汤池的来历》里的李氏伺候瘫痪在床的公婆,不管怎样脏累,她都毫无怨言,甚至为了治好公婆的病,手捧着火炭到南山去烧水;又如《孝顺媳妇和小辣椒》中的儿媳妇在误以为自己要被雷劈死时仍挂念双目失明的婆婆,在收拾干净婆婆的被褥衣裳、为婆婆借来吃的后,又怕吓着婆婆而悄悄来到山沟里等死。这些孝顺儿媳妇在故事里最终都能实现心愿,得到好报。与此相反,辽海地区民间故事中的不孝儿媳妇往往会遭受惩罚,得到报应。《孝顺媳妇和小辣椒》中“对婆婆正经不咋地”[11]的“小辣椒”最终求财不成反丧命;《虾母子的来历》中背着丈夫不给婆婆一顿好饭的儿媳妇,被雷劈死后变成了虾母子;《西狼庙》中打骂公婆的儿媳妇,死后还要受到小鬼的抽打。辽海地区民间故事出现的孝顺儿媳妇有好报,不孝儿媳妇有恶报的情节设置,意在引导女性孝敬公婆,这点在《大车传后辈》也有所表现。《大车传后辈》里儿媳妇逼迫丈夫送走了年迈的婆婆,后经丈夫的教导,接回了婆婆并好好伺候的故事情节,无疑对女性具有教育作用。
辽海地区民间故事所塑造的孝顺儿媳妇形象,所具有的针对女性的教育作用,故事中孝顺儿媳妇与不孝儿媳妇的对比,其实都是人们对于女性作为儿媳妇应有孝敬公婆之道德的强调,孝敬公婆成了约束女性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与规范。
(二)机智勇敢
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观念影响下,人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且女子通常要扮演柔顺的弱者。但辽海地区的一些民间故事却显示了女性机智勇敢的一面,她们依靠自己的勇气,凭借聪明才智,解决了生活中的难题,化解了身边的危险。这些女性机智勇敢的表现较为多样。如《黑虎精》、《俊媳妇巧治蛇精》、《贫女智杀蟒蛇精》中的智杀妖精;《〈井台认母〉与〈拦桥记〉》、《增和桥》中的能言善辩;《害人如害己》、《聪明的丫环》中的临危不乱;《智追银子》、《绣花女》中的足智多谋,等等。可以说,辽海地区民间故事并不局限于刻画传统女性的弱者形象,其更多的是对民间女性机智勇敢的美好品质加以肯定和赞扬。
在辽海地区的民间故事中,对于女性所表现出的机智勇敢,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女性的智慧往往源于其生活经验。如《俊媳妇巧治蛇精》中的俊媳妇识破黑鱼精的身份,是因为她本是渔家女,“摊过险,经过风,懂海情,知鱼性”。[12]其次,女性的机智勇敢常表现在帮助家庭成员,或是处理家庭内部事务方面。如《没有的事儿》、《智追银子》中,丈夫束手无策的事情由妻子替其解决了;又如《三媳妇》、《呲牙瞪和五眼全》中,儿媳妇不怕老公公的刁难,勇于与其斗智,最终使老公公不敢再欺压自己。另外,女性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时,通常能冷静思考,随机应变。如《绣花女》中的绣花女见到大队人马前来逼婚,仍毫不慌张,能够从容脱身;《聪明的丫环》里的李英遇到一伙胡子抢劫时,主动出面交涉,最终使胡子被逮捕,这都说明女性有处理危险事件的能力。
在这些民间故事中,女性源于生活的智慧,可以帮助其他家庭成员,调节家庭关系,她们也可以镇静、正确地应付生活中的突发事件,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辽海地区女性机智勇敢的品质,在民间故事中得到了彰显与宣扬。
三、女性角色结构论之留守处境下的群体
(一)留守女性的形成
在辽海地区的民间故事中,有一些家庭的男性由于生活所迫或是职业需要而长期离家外出,他们的母亲、妻子或未婚妻则留在家中,这部分女性就成为了留守女性。
有关留守女性的故事中,男性离家多是去采参或打鱼。相传,在辽海地区有一种迁徙性的打鱼人,他们多数来自黄河中下游地区,每年或从水路或从陆路,像大雁一样春来秋去地到辽海地区从事渔业活动,这种打鱼人被称为“渔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古渔雁民间故事即是对这种传说的反映。
这种传说未见正史资料记载,难辨真伪,但是《奉天通志》说人参在“盛京吉林乌拉诸山中产焉”[13]且对采参的操作习俗有所记载,[14]又说“盖辽海四达天然渔产荟萃之地”[15]且“辽海渔业自魏晋时即已兴盛”。[16]可见辽海地区确实存在着丰富的采参、打鱼活动,民间故事中大量留守女性的出现当非杜撰,而是有着一定的现实基础的。
随着男性外出采参或打鱼,就出现了留守女性,辽海地区民间故事中的留守女性形象是对这部分真实存在的特殊女性群体的反映。
(二)家庭生活中的窘境
通常,留守女性的家庭负担沉重,生活十分艰苦。有些留守女性的出现源于生活贫困,如《蓝花宝参》中山西人亢小三去关外放山,《麻风女嫁渔郎》中生活在辽东湾的北根乘船南下,均是迫于生计。这些家庭本来就生活困难,在失去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后,留守女性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留守女性还要肩负本应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庭抚养和赡养责任,《汤池的来历》中丈夫在外扛活的李氏一人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婆;《绣楼会》中周云娟独自抚养儿子,直至儿子成婚那天才夫妻团圆。沉重的家庭负担也让一些留守女性的生活陷入绝境,在《两好凑一好》中,有人捎信给女人说她的丈夫死在去北方打鱼的路上,女人最终沦为了无家可归的逃荒者;《卖油郎救蛇》中卖油人的妻子因家中无柴无米、缺吃少喝而自寻短见。可见,沉重的压力,艰辛的生活,常常成为留守女性难以承受的负担。
面对巨大的生活困难,留守女性无疑希望男性回归家庭,但由于男性外出谋生所面临的风险与意外,这一愿望很难实现。《渔雁芦》中的晓华苦苦盼望北上打鱼的芦雁哥归来,却不知芦雁哥早已怀抱作为信物的竹梭,长眠于千里之外的黑龙江边。有时,男性回归了家庭,留守女性的生活状况也不一定会改善。《当“良心”》中出外做生意3年多的张掌柜,因在归家途中救助他人而一个钱没带回来,自己家中的媳妇和孩子仍无钱过年。尽管如此,许多留守的妻子仍旧难以得到尊重和理解,甚至容易受到归家的丈夫的怀疑。《谢石相字》里的小媳妇做好饭菜,满心欢喜地等待自己男人回家,她男人却因此怀疑小媳妇有外心,对她一顿暴打,差点逼得小媳妇上了吊;《三忍救妻女》中离家十多年的韩掌柜从南方回来后,看到妻子和女扮男装的女儿睡在一起,以为妻子给自己戴绿帽子,买了把菜刀要将“奸夫淫妇”砍死,险些酿成杀妻杀子的惨剧。留守女性的生活愿望难以实现,生活状况难有改善,而留守妻子在丈夫归家后还容易受到怀疑,这种生活处境使人同情和关心。
留守女性要承担家庭中绝大部分的生产生活劳动,肩负起各种家庭责任,但这种对家庭的付出与守护却很难改变留守女性的生活处境,她们甚至会受到不应有的对待。
四、江湖与风尘:女性角色的特定时空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一类特殊的女性,她们没有稳定的家庭和固定收入,只能依靠从事一些非正当的,甚至违反法律和道德的职业来维持生计。她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向来缺少人们的关注,就连民间故事中都极少出现她们的身影。从传说故事透露的蛛丝马迹中,可以窥探到其中既有江湖中人,又有风尘女子。
(一)江湖中人
这里的“江湖”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指旧时四方流浪,靠卖艺、卖药、占卜等谋生的生意人,也?指这种人所从事的行业。江湖中有“风”、“马”、“雁”、“雀”四大门,①亦作“蜂麻燕鹊”、“风马颜缺”、“风马燕缺”等。又有“金”、“皮”、“彩”、“挂”、“评”、“团”、“调”、“柳”等众小门,[17“]门”即江湖行当,没有严格划分“,即使是生意人自己也分不清楚”。[18]
辽海民间故事《撂大包》讲述的是一个女骗子设下层层圈套,先是雇佣小伙子为自己拉洋车服务,然后以身相许,将自己的财产解囊相赠,最后在丝绸店里将小伙子害死,借以向丝绸店讹诈巨额钱财。这与相声名家张寿臣先生讲述的单口相声《落榜艳遇》中“鹊”门的诈骗方法如出一辙。但是《撂大包》里的诈骗既不是团伙作案,又不靠买官缺的手段,女骗子在讹诈钱财时谎称“我爹就是总理”,[19]即捏造自己的政治后台,这又与“雁”门中的“独角雁尾”②一种“雁”门骗子。详见连阔如《江湖丛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382页。颇为相似。而《撂大包》这则故事的早期讲述者谭福臣本身就是辽宁省新民市一个“以走村串户为人家看阴阳宅为生”[20]的江湖人,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撂大包》这则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实为一例女性江湖人。文献中关于这类女性的记载少之又少,虽然近代以来的一些女性曲艺艺人的名字伴随着曲艺形式的发展、扩大得以保留和流传,如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便是辽海地区一位著名的西河大鼓演员,属于江湖行的“柳海轰”一门,“生来一副白面孔,人称‘白丫头’”,[21]但是也多局限在自己所处行业的一块狭小领域内,缺乏详细的资料。不过,在辽海地区曾活跃着各类江湖人,大连西岗的博爱市场,营口的洼坑甸,沈阳的北市场、西门脸、小河沿,当年都是江湖人云集之地,其中自然不乏女性,在民间故事《撂大包》中,出现了女性江湖人的形象,虽仅有一例,却也是对辽海地区女性江湖人这一群体的反映。
江湖人是“百工技艺一百二十行中地位最卑下的”,[22]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始终处于受人欺侮和歧视的地位,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改行》等即是对从前各地江湖人坎坷生活的写照。即使如那个女骗子,打扮入时,出手阔绰,也未必是真正的有钱人,因为那时的江湖中“有些人家无恒产,连个职业也没有,你别管他是坑蒙拐骗,到了什么时候,应时当令的穿什么,到了冬天亦能穿上细皮袄,水獭领子大氅,水獭皮帽,由头上到脚下真能值个一二百元。你要问他是干什么事的,人家是耍人儿的”,[23]何况她还要躲避法律的严惩,终究难以改变其社会地位的低下。而根据《江湖丛谈》等书的记载及一些老江湖艺人的回忆,江湖人之间也不是平等的,有着极严格的规矩。任何一行的江湖人都必须拜师,否则不许从事这一职业,拜师入门后还要为师傅义务效力一段时间,“徒弟将艺学成了,必须先谢师,然后才能挣工钱做活……学徒的学到了年份,不谢师不能挣钱,不谢师不能单独离开师傅单独做事的”。[24]有些江湖人在学艺的时候还要忍受师傅的鞭笞,称之为“鞭徒”,[25]而有些撂明地演出的艺人,甚至公然以“鞭徒”的方法博取观众的同情心赚钱。这些情况各地皆然,辽海地区的女性江湖人自然也难以摆脱这种厄运。
当然,《撂大包》中那个女骗子谋财害命,于理于法都是死有余辜,决不是人们肯定和同情的对象,只是在她所处的这一庞大社会群体中,确实有着很多生活窘迫、身不由己的女性。女性本身就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江湖人又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江湖中的女性自然是弱势中的弱势,其境遇之悲惨,是不言而喻的。
(二)风尘女子
然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尚不止江湖人一种,许多沦落风尘的娼妓,有着同样悲惨的遭遇。
在旧中国,娼妓并不罕见,溯其源流,“信而有征的娼妓史,当托始于殷朝”。[26]辽海地区曾有过许多烟花柳巷、秦楼楚馆,如从前沈阳“北市场、西北市场的平康里、永宜里、宜春里等地妓院林立,妓女多达千人”;[27]而民国初年的长春,“妓院集中在城内的四马路、五马路、宽城门、安达街一带,在七马路日本桥和头道沟一带还有不少日籍、俄籍、朝籍妓院以及一些本地中国人开设的妓馆”。[28]
辽海地区的娼妓又有“柜上孩子”及“自混”之分。“‘柜上孩子’是领班老板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小女孩,有的十几岁甚至七八岁,就强迫她们接客。‘自混’的妓女,与老板订立有限的年限契约。她们虽然出入自由,但也被老板派人监视”。[29]娼妓中既有单纯出卖色相为生的,也有兼而进行偷窃、诈骗等活动的,因此娼妓是否属于江湖人难以定论,但二者的社会地位之低下、生活状况之艰难,却是同病相怜的。如“有个妓女叫玉花,身患大疮,老鸨子用剪刀将其身上脓疮剪开,不管好肉坏肉一并剪下,最终被疼死”。[30]可见,妓院既是藏污纳垢之所,在女性而言,又是惨绝人寰的魔窟地狱,因此在民间故事中,人们既表达了对被迫为娼妓的女性的同情,又借娼妓表达了对为富不仁者的愤恨,同时还有对沉溺女色的嫖客的批评与规劝。
辽海民间故事中关于娼妓的描写虽然比江湖人相对多一些,但整体数量仍然较少。《当“良心”》中,张掌柜的仗义疏财,使被拐骗的姑娘从妓院脱身,回到了父母身边。而《想成龙的老财主》中“财主家女人落地,都当妓女去了”,[31]则成了最严厉的诅咒和惩罚。《观音治歪道》中的打鱼人不走正路,将辛苦挣来的钱送给野老婆挥霍,却回到家里找妻子的别扭,弄得一家不得安宁,多亏观音点化才改邪归正。在《女海神粘姑》中,为渔人服务的野妓粘姑则被塑造成了一位善良、勇敢的女神,她体贴娶不上媳妇的下海人,常常晚间钻进渔人的船舱,而面对贪色的渔霸,她又不肯屈从,拼死抗争,最终将渔霸变成了一种形似河泥鳅的小海鱼,被渔人世代唾骂。将娼妓描绘成女神或神女的现象,并不是民间故事特有的,早在先秦时期,宋玉的《高唐赋》中便塑造了一位巫山神女,“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32]从此“神女”便成了娼妓的美称,而巫山云雨、襄王楚梦更成了历代文人骚客笔下的美谈。民间故事的作者和传播者未必知道这样的典故,但是将粘姑描绘成女神,可见人们对于女性的尊重,渔霸想要霸占她,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行业女性所受的压迫和欺凌。粘姑虽然厕迹风尘,却不肯屈从渔霸的威胁,并与之拼死抗争,终于使渔霸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一义妓的形象,渗透了人们对于女性正直、坚韧品格的赞许,以及对于惩恶扬善的美好期望。
其实,不论是江湖人还是娼妓,都只是辽海地区特殊女性职业者的一个缩影,所揭示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五、结语
综上所述,辽海地区民间故事中的女性角色,其实是对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所担当的性别角色的反映。在这些故事里,女性主要承担与传统女性角色相关的妻子、母亲等角色,凸显了女性与家庭的紧密联系,无论是女性的外在形象和内在道德都与家庭紧密相连,完整的家庭是女性获得幸福生活的前提。与此相反,无论是留守女性,还是江湖人或者娼妓,一旦脱离家庭,她们在生活中往往举步维艰。
除此之外,辽海地区民间故事中的女性角色还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里多样性不但指女性在民间故事中所展现的外在形象、内在品德和群体种类较多,而且也是对女性自身所扮演的多种生活角色的强调。比如《汤池的来历》中的李氏,既是孝顺的儿媳妇,也是一名留守女性,而像李氏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总之,“每个人都可能具有两个或更多的角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两种或更多的身份”,[33]辽海地区的女性亦不例外,无论在故事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她们的性别角色都是由多个生活角色共同组合而成的。
辽海地区的女性在民间故事中扮演各种角色的同时,在故事外也肩负起民间故事传承者的角色。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文化水平通常较低,但是以养育孩子为主要职责的女性,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往往是从讲故事开始的。“东北三大怪,养活孩子吊起来”,一代又一代的辽海地区女性,无不是在“月儿明,风儿静,树叶挂窗棂”的夜晚守候在摇篮旁,一边轻轻地讲着故事,一边哄孩子入睡的,因此女性也无疑是民间故事的重要传承者。辽海地区民间故事的讲述者有些就是女性。如讲述《孤岗寺的传说》、《神牛的传说》、《刘关张的故事》的蒙古族妇女陈凤兰;讲述《玉杯的故事》、《三个瞎姑娘》的李马氏;而根据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的谭振山的回忆,其祖母孙氏对他成长为民间故事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孙氏这个不识字的乡间故事家,将谭振山引进了民间故事的艺术宝库”。[34]由此,我们可以说,辽海地区的女性,不论是对民间故事的流传和保护,还是对民间故事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继承人的培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田广林.辽海历史与中华文明[N].光明日报,2009-12-29.
[3]王宁.中国文化概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44.
[4][6][12]刘则亭.渔家的传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186.133.230.
[5]邵振棠.谭振山故事选[M].沈阳:新民县印刷厂,1988.152.
[7][8][31]刘则亭.辽东湾的传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62.63.67.
[9]乌丙安,等.满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434.442.
[10]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45.
[11]白景利.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北票资料本[M].建平:建平县印刷厂,1987.269.
[13][14][15][16]王树楠,吴亭燮,金毓黼,等.奉天通志[M].沈阳:沈阳古旧书店,1983.2444.2444.2723.2723.
[17][23][24][25]连阔如.江湖丛谈[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1.47.246.5.
[18][27][29][30]马魁.盛京杂巴地儿[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13.10.11.11.
[19][20][34]江帆.谭振山故事精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453.8.6.
[21]姜昆,倪锺之.中国曲艺通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04.
[22]宫钦科.古今评书选[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2.
[26]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10.
[28]单光鼐.中国娼妓——过去和现在[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128.
[32]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97.265.
[33][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