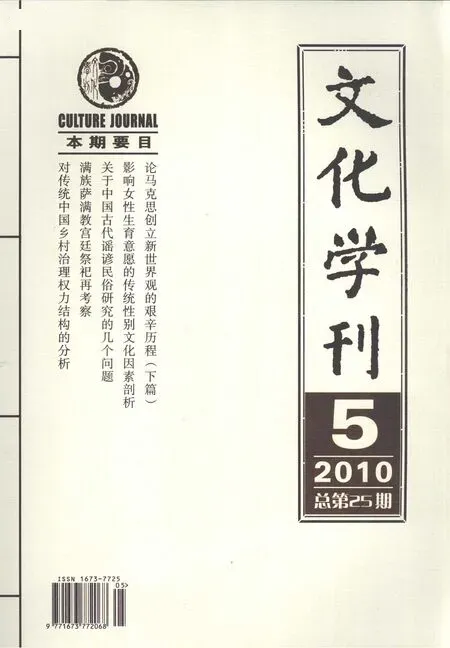近代西方法治思想的人文基础探究
刘晓善 洪晓楠
(辽东学院,辽宁 丹东 118001;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4)
法治思想内涵丰富,源远流长,众多学者从各种角度对法治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法治思想。一般认为,法治的典型社会实现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但其法治思想的萌芽却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历史的轨迹继续向前蔓延,从14世纪开端的,对整个人类影响空前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当之无愧地成为法治思想的发展和丰富阶段,历史和文明的积淀最终造就了启蒙时期法治思想的成熟。在近代西方法治形成、发展、成熟的历史脉络里,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人文主义精神。
一、中西人文思想历史溯源及要旨
在中国,“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周易·贲卦·彖辞》中记载“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根据后人所作的注释,认为上艮的刚和下离的柔交错在一起,这是天文。下离的文明遇着上艮的静止,这是人文。观看天文去察觉时代变化,观看人文去教化天下。[1]通俗地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天地万物阴阳有别,男刚女柔阴阳相济,这是自然规律。通过处理人际社会复杂关系而形成的道德规范、伦理制度和风俗习惯等原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标准,这是人伦准则。注意天道自然规律,能够通晓时令变化,妥善安排生产生活;注意社会人伦准则,能够修身明礼并感染他人,推而广之则教化天下大众。这是古人对人文的最初理解,将天文与人文对应,表达了天和人的客观存在及重要性的思想。随后,盛世鸿儒唐代孔颖达在其著述中写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2]同样也强调了人文具有强大的教化之功。另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中也充斥着丰富的人文思想:如《论语·卫灵公》载:“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管子·霸言》载:“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尚书·泰誓上》载:“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孟子·公孙丑下》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等。这些人文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国古老朴素的辩证哲学观,其要旨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有明显的不同。
在西方,“人文”一词被译为humanism,也被译为“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这个词实际上很晚才出现,它来自于拉丁文中的“humanitas”。“Humanitas”最早出现在古罗马作家西塞罗和格里乌斯的著作中,意思是“人性”、“人情”和“万物之灵”。1808年德国学者 F·J·尼特哈迈在一次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辩论中用德文杜撰了 humanismus(人文主义者)。[3]英文humanism是从德文humanismus转译而来的。后来由乔治·伏伊格特于1859年出版的著作《古代经典的复活》中首先使用,这部著作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此后布克哈特在1860年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大量运用“人文主义”一词。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主席爱德沃茨(Frdeerikc Edwords)在《什么是人文主义》一文中指出:“何谓人文主义?你得到的答案的类型取决于你所问的人文主义者的类型。‘人文主义’一词有多种含义,并且由于写作者和说话者弄不清楚他们所指的是哪种含义,因而试图对人文主义进行解释的人往往成为混乱的根源。”[4]即便如此,笔者仍然想尽力描述出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人文主义是立足于人性尊严的维护,倾向于人性本能的关怀,提倡自由、平等、公正与人权等价值要求,主张人的自我价值释放与实现的上升到哲学高度的思想。人文主义的核心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是对人的价值、尊严和生存意义的积极关注。以人为本、张扬理性、精神关怀共同构成了人文主义的价值追求。人文主义的核心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当人看,社会以及宇宙的中心是人类而不是上帝。其实人文主义就是作为中世纪神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在中世纪的西欧,附庸从属于封君,帮工依赖于行东,农奴受制于领主,整个社会都处于严密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之中。与此相应,天主教神学鼓吹蒙昧、禁欲主义的“神本”说教,要求人按照神意的安排与教会的训导绝对服从。这样一来,人们毫无独立性与自主性可言,丧失了个体的价值与尊严,也被剥夺了追求世俗生活的权利。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进行反神权、反封建的斗争,要求进行思想观念的更新。受新时代的感召,人文主义者在思想文化领域积极地除旧布新,提出了“个体本位”的人本思想,即一切以个人的意志、利益与欲求作为人自身观察、思考与判断万事万物的价值标准或是非尺度。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和文学力量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达到高潮。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也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初形式。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而作为历史概念的人文主义,则指在欧洲历史和哲学史中主要被用来描述14世纪到16世纪间较中世纪比较先进的思想。一般来说今天历史学家将这段时间里文化和社会上的变化称为文艺复兴,而将教育上的变化运动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提倡者相信人的本性有巨大的潜力,而不相信宗教的超验的价值。可以说,人文主义精神的宣扬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科技、文化、教育、艺术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变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轨迹,从而成就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明。
二、西方法治思想渊源及内容
虽然西方法治发端于近代,但众所周知,法治思想是由来已久的,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思想家都留下了经典的论述。在历史上,法治思想的明确提出和首次阐述是出自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的名著《政治学》中:“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5]这段话提出了法治的两个基本内容,即良法和守法,为后世研究法治思想提供了理论框架,因此这段话也被称为亚里士多德法治公式。同样也在这本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说明了法治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唯独神氏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氏和理智的体现。”[6]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包含三个推论:第一,良好的统治当免除情欲,即免除任意和不确定;第二,人的本性使任何人皆不能免除任意和不确定;第三,唯法律的统治即法治可免除任意和不确定。显然,此言既表述了诉诸法治的逻辑理由,亦透视出法治在宇宙秩序论、人性论等方面的哲学基础。法治内涵的形成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罗马人和诺曼人的法律传统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7]古希腊罗马法治思想在辉煌过后逐渐衰落,在中世纪黑暗蒙昧的神学压抑中几近消亡。整个中世纪史表现在政治法律上,即是一部教权和教会法与王权和世俗法之间互为消长的斗争史。[8]有学者认为,中世纪的法治理念和理论本身丝毫不具有革命的意义,它甚至只是提供一种虚幻的平等和法治的未来以作为对现实黑暗世界的一种慰藉,在中世纪,一切科学都沦为神学的婢女,而人性也被神性所取代,包括法治理念在内的一切人类进步思想都丧失了通往现实的途径。但我们同样要看到西方法治主义传统作为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种延续性的意识和信念在中世纪的存在与发展。[9]历史告诉我们,在中世纪精神强制的背后是人们对思想解放人性回归的强烈愿望,罗马法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使人们不断深入地接受灵魂的洗礼。文艺复兴运动所孕育的科学、理性、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法治精神得到空前的张扬,近代西方法治观就是在这一弘扬科学、理性、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的大舞台上得以确立的。[10]
近代西方法治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19世纪英国法学家戴雪(A.V.Dicey)的理论中。戴雪通常被视为近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奠基人,他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法治概念,他在《宪法性法律研究导言》里写道:构成宪法基本原则的所谓“法治”有三层含义:首先,法治意味着与专横权力的影响相对,正规的法律至高无上或居于主导,并且排除政府方面的专擅、特权乃至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其次,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者意味着所有的阶层平等地服从由普通的法院执掌的国土上的普通的法律;此意义上的“法治”排除这样的观念,即官员或另类人可以不承担管治其他公民的法律义务,或者说可以不受普通审判机构的管辖。……作为其他一些国家所谓的“行政法”之底蕴的观念,是涉及政府或其雇员的事务或讼争是超越民事法院管辖范围的,并且必须由特殊的和或多或少官方的机构来处理。这样的观念确实与我们的传统和习惯根本相忤。最后,法治可以用作一种表述事实的语式,事实是作为在外国自然地构成一部宪法典的规则,我们已有的宪法性法律不是个人权利的来源,而是其结果,并且由法院来界定和实施;要言之,通过法院和议会的行动,我们已有的私法原则得以延伸至决定王室及其官吏的地位;因此,宪法乃国内普通法律之结果。[11]概括地讲,这段被奉为经典的话大致有三层意思:第一,人人皆受法律统治而不受人性统治;第二,人人皆须平等地服从普通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无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第三,宪法源于裁定特定案件里的私人权利的司法判决,故宪法为法治之体现或反映,亦因此,个人权利乃是法律之来源而非法律之结果。[12]
三、近代西方法治思想的人文基础
(一)人性中的弱点预示了法治的必要性
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尽善尽美的,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不足,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也不能回避对自身弱点的揭露。西方的“人性恶”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性中不可忽视的弱点的存在。西方“人性恶”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法律篇》(The Laws)中指出:“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先考虑这些,然后才考虑到公正和善德。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他们本人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如果有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的行动,他们就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做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13]柏拉图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开始对那种依靠个人才智自由地、不受约束地治理国家的图式与统治者的自由裁量权受到法律限制的国家形式进行比较分析。虽然他仍然坚持“无法律”的国家(“non-law”state)是最高级且最完善的统治形式,但他也承认这种国家的有效运行需要具有最高才智的和不会作出错误判断的人士来掌控。由于这种人很难找到,所以他提出“法律国家”(lawstate)是人进行统治的次优选择。[14]柏拉图之后,其学生亚里士多德更加注重人和制度的缺陷及不完备性,他认为:“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15]将人性与法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西方先哲的专利,在中国同样也不乏这方面的论述,如荀况在《荀子·性恶》中提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又说:“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性情而导之也。”可见,荀子认为人性恶是法产生的重要前提。
中西“人性恶”理论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建立在对人性弱点的深刻剖析基础之上。正是出于对人性弱点的了解,西方法治的发展轨迹沿袭了相关的制度设计,近代西方法治所倡导的权力制衡、程序正义、人民主权等原则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与人性固有的弱点相关。因此,近代西方法治思想的人文基础之一,即法治是对人的关注下将其弱点进行规避的利弊选择。
(二)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奠定了法治的可能性
理性思维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是人们把握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能动活动,理性思维能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终标准。人类具有理性思维能力,这一认识在古希腊时期就得到了详细阐述,如柏拉图提出将人性分为理性、志气和欲望,其中理性处于最高层次,志气和欲望在理性的控制下能够发挥正面效用。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到人与其他动物相比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具有理性的生活。此外,托马斯·阿奎那将法律划分四种类型: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永恒法来自神的理性;自然法由人之物理的和心理的特性组成的,还包括一些指引人趋向于善的理性命令;神法是上帝通过《圣经》启示给人类的;人法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合乎理性的法令,它是由负责治理社会的人制定和颁布的。[16]可见,阿奎那也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把理性观念纳入了他的理论之中。经过中世纪神学压迫的洗礼后,理性精神重新回归到人们的视线中,成为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和启蒙运动的宣传要旨,总之,它是西方人文精神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积淀下来的珍贵成果。虽然人类具有理性思维能力,但并不表示人类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为理性状态,人类同样也具有很多非理性表现,如情感、直觉、本能等。这说明理性是一个相对的范畴,人类恰恰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结合体。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人的理性能力,但也不能忽视人的非理性状态,因为法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的非理性状态有着直接关系,人的犯罪行为、违法、违俗、违德行为都是在非理性的支配下发生的,为了预防和控制这些危害人类社会的行为,人们运用理性制定出具体的法律规则形成约束机制。
由上可知理性与法治存在着天然关系,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为法治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首先,理性是认识和理解法的前提。法是抽象的存在,单靠人类的非理性思维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即便是专业的法学家也不能轻松地领悟,对于普通的人民大众更是望尘莫及。因此,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人们识文断字,更重要的功用在于挖掘人潜在的理性思维能力,学会思考、推理和判断。人类的进步表现之一就是思维水平的不断提升,这对于深刻地理解抽象的法的原则和价值意义重大,并且对于复杂繁琐的法律技术的改进和创新也是不可或缺。其次,理性是人类主动并且被动地寻求法治的缘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和弱点,非理性的本能常常使自己或他人处于危险或尴尬的境地,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人类必须发挥自己的理性能力来克服非理性产生的弊端,这种理性主动驱使和非理性被动承受的途径就是法治,具体说来就是协调整合社会冲突的秩序规则。最后,理性是使法治成为现实的前提。法治不是简单的规则罗列,而是复杂的利益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要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理性思维能力根据人类自身的根本利益形成合理的规范社会秩序的冲突调整机制。在社会秩序走向法治的过程中,与法治密切相关的价值理想,如公平、正义、自由、人权等在人类理性的关注下得以树立和巩固,反过来愈加促进法治的进步和完善。总之,辩证全面地看待人类理性思维能力是充分理解近代西方法治思想得以确立的重要前提。
(三)人类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与法治的契合性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文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即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17]对人的关注是自古希腊以来人类思想的核心问题,古希腊哲学的命题是认识人自己。到中世纪,人成了上帝的附庸,成了上帝的创造物,从而被贬低了。这其实关系到如何看待人和宇宙的关系的问题。一般来说,西方思想有三种不同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超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本文化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18]很明显,中世纪属于第一种模式。到14世纪时人们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宣传人文精神。文艺复兴的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人,它的标志是与“神为中心”相抗衡的人本文化的形成。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文化特征有三:一是将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恢复人之尊严;二是复兴古典文学历史之研究;三是对人之才能的多方面表现,皆加以肯定。[19]这说明自文艺复兴开始,又重新发现了人,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这一重大转变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而有了今天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建构,有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模式和路径。
在关注人类的过程中,人类本能的价值追求逐渐清晰起来,对人性尊严保护的渴望,对自由、平等、正义、和平、安全等价值的追求与完善,日益成为人类思想家思辨的主题,这也充分反映了人类对这些价值追求的现实要求。如朱利叶斯·凯撒(Julius Caesar)所说,“任何人生来都渴求自由,痛恨奴役状况。”[20]卢梭痛苦地疾呼,“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21]康德宣称说,自由乃是“每个人据其人性所拥有的一项唯一的和原始的权利”。[22]埃德蒙·卡恩(Edmond Cahn)指出,“人们对非正义的感觉,就是对任何因专断行为而引起的不平等现象的憎恶”。[23]这些价值要求体现了理性人的本能追求,是对人生存意义的提升和高度精炼。在认真思索人类价值追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价值追求与西方法治一直倡导的精神不谋而合,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平等价值要求与西方法治的价值取向具有必然的契合性,法治的理想价值必须承认人的价值与尊严,保障每个人都是独立而平等地存在,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有权作出选择且这种选择获得应有的尊重。实现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始终应该是法治价值取向的重心所在。[24]这充分表明近代西方法治的传统是在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更确切地说,源于古希腊时期,兴盛于文艺复兴时期,成熟于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与近代西方法治传统倡导的价值要求具有高度契合性。
[1]宋祚胤.周易[M].长沙:岳麓书社,2000.111-112.
[2]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5.
[3][17][18][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5.转引自庄锡昌.西方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27-128.14.12-13.
[4]Frederick Ed words.What is Humanism[EB/OL].http://www.jcn.com/humanism.html.
[5][6][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9.168-169.9.
[7]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1999,(4):118.
[8][9]徐祖澜.论西方法治传统在中世纪的渊源[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62.63.
[10][12]刘明皓.近代西方法制观的生成与反思[J].法学与实践,2008,(1):18.123.
[11]转引自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1999,(4):122-123.
[13]柏拉图.法律篇[M].张智仁,何勤华,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14][1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9.29-30.
[19]胡伟希.传统与人文[M].北京:中华书局,1992.103.
[20][21][22][2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4]张革文.近代西方法治的人文基础[J].江西社会科学,2007,(3):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