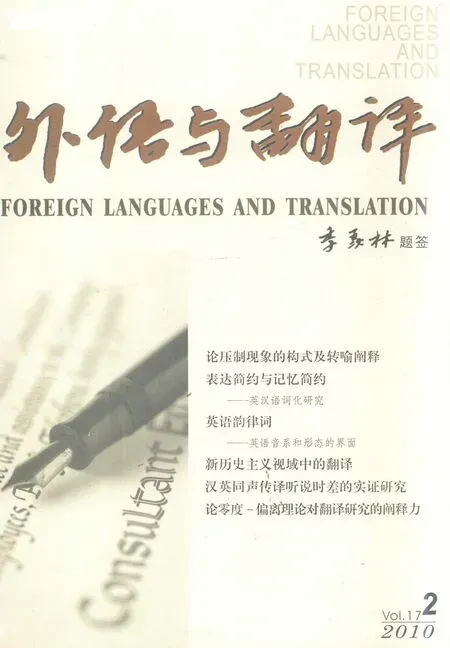自我的寻找与失落*
——《十九号房》浅析
尤 璐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安徽芜湖 241003)
自我的寻找与失落*
——《十九号房》浅析
尤 璐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安徽芜湖 241003)
《十九号房》是当代英国作家朵丽丝·莱辛的一部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位中产阶级女性在寻找自我的精神追求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误区以及最终的失败。本文简要介绍了故事的梗概,对其进行了分析,发现故事女主人公孜孜以求的正是她已经拥有的,她在自我的寻找中失落了真正的自我。
《十九号房》;自我;寻找;失落
朵丽丝·莱辛(DorisLessing,1919年10月22日—)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以及在非洲生活过的白人,女性和非洲给她的作品提供了素材和话题。她的小说大多围绕现代独立女性的困惑、追求和挣扎展开,或者讲述在非洲人民的生活以及在那里黑人遇到的不公正待遇。
一
《十九号房》是朵丽丝·莱辛的一部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位中产阶级女性怎样用理性和智慧安排她的婚姻、工作和家庭生活,力求让自己获得幸福和安宁,但是事与愿违,在精神的自我追寻中感到了空虚和绝望,最后以自杀了结自己的生命。女主人公苏珊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白领,近三十岁时和伦敦一家大报的副编辑马修结婚,婚后她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搬进了郊区的大房子,之后先后生下了两男两女。一家六口生活幸福愉快,应有尽有。然而在平静富足的生活中,她却感到一种心底的不满和诉求,一心要找到真实的“自我”,而不是那个为了工作、丈夫、孩子甚至是爱而活的“自我”,于是她努力为自己争取独处的时间和空间,先后在家中和家外的旅馆中找到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最后找到了“十九号房”——可以让她独处并安放灵魂的,有助她最大限度的发现自我、找到真正的安宁的房间。在寻求这种“真实的自我”的过程中,她经历了种种烦心的事件,到最后当她终于可以在“十九号房”里发现“自我”时,却发现工作和家人都抛弃了她,她感到怅然而有所失,觉得自己没有存在的意义,于是在那个象征自己独立灵魂和真实自我的“十九号房”里开煤气自杀,踏上了回归自我的终极之路。
二
在这篇小说里,苏珊孜孜以求的看似很虚无飘渺,甚至莫名其妙。在别人看来,她家庭幸福,生活富足,应该是无忧无虑、十分满足的了,可是作为一个有追求有思想的知识女性,她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还有精神层面的安定。她需要的是寻找自我,发现自我,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同于他人的、也不是他人可以给予的自己的幸福。自我即“真我”(True Self),即一种持续的自我意识,是对人生的本性、目的、意义等问题的终极追寻,并导致和个人的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行为。(“a persistent sense of self that addresses ultimate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purpose,and meaning of life,resulting in behaviors that are consonantwith the individual’s core values.”[1])苏珊所探求的也就是她个人人生的目的,即为什么而活,活着应该干什么。正如作者在文中借苏珊和马修之口的所问:“可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2]为了弄清楚“这个”是什么,苏珊努力地寻找着,寻找一个抽象而复杂的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她错误地以为“自我”即“自己”、即“独立”,而“独立”即意味着不以工作、丈夫和孩子为中心,而是为自己而活,追求自己的幸福。至于怎么追求自己的幸福,怎样才是真正为自己而活,她并没有想清楚,只是一味的要自己独处的时间和空间和自己独立的尊严和理性。当丈夫马修一天回来忏悔自己的出轨时,她为了显示自己不以丈夫为中心、不依赖丈夫、自己的情感不随丈夫的行为变化而变化,原谅和宽容了丈夫,而不表现自己的妒嫉和愤怒,不用夸张的字眼如“不忠”向丈夫发泄自己的不满,因为这样就显得她太重视她的丈夫和他的一举一动了,也就意味着她的情感是依附着他的,她的幸福是取决于他的,那么她的“自我”也就丧失了。可是,这样的理智和克制的结果却是“苏珊越来越感空虚(这种感受,通常是她单独一人在花园工作的时候,最为强烈……)”[2]。
三
等“双胞胎很快也要上学了”[2],苏珊“准备逐步恢复自主的女性生活”[2],因为“这些年来,苏珊老觉得灵魂不属于自己,似乎整个附在小孩身上”[2]。然而在两个月小孩上学苏珊可以“自由自在”的时光里,她却想尽办法不让自己闲下来,尽量做些琐琐碎碎的事,因为如果她去花园安静地独处,“她的敌人——气愤、不安、空虚之情,管它是什么,反正似乎特别逼近她。双手不停工作,倒使她觉得较为安全。是什么原因,她说不上来。”[2]苏珊认为问题在于她需要真正的独处,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不被别人打扰的房间。可是当她把楼上的空房安排为自己独处的房间后,她又感到“在里头所产生的封闭感,比在卧室里更强烈”[2]。不久,“那个房间变成另一间家人休息的地方。”[2]
楼顶的空房无法给苏珊以真正的独处时的安宁,她于是找到了一家安静的旅馆,呆了一整天,以体验真正的自由。看似在那里她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和自由,尽管家里的一切需要她、牵绊她。在她回家后,女佣白太太一大堆的怨言让她意识到无法根本切断和家庭生活的一切联系。于是她进一步安排自己的“自我”寻找之旅,她先是出门徒步旅行,但仍保持和家里的联系,这样还是不能摆脱心中的魔鬼,心中的疯狂而又压抑的情绪。为了切断和家庭的联系,把自己从家庭琐事中真正解放出来,自由地去追寻“真正的自我”,她说服丈夫找了一个家庭女教师苏菲,代替自己照顾孩子。自己放心地去寻找“自己的房间”。她在离家较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家小型旅馆,租了一个房间——十九号房。她在房子里什么都不做,独自享受一个人的愉快时光。她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失去已久的“自我”。在十九号房,她感到她终于剥去了过去种种外在的象征符号的自己,而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不是社会和他人承认的“自我”,是只属于自己的“自我”。当苏珊在外租房的行为引起了丈夫的注意和调查并找到了她的所在后,她感到她的那个独立的“自我”受到了侵犯:她“数度回到那房间,寻找自己,但发现的却是无名的不安”[2]。事实上,这是世界对她发出的最后一次邀请,邀请她回到原来的“自我”,回到一个和家庭社会自然融合的“自我”。但是她拒绝了这一邀请,执着地认为自己已经在十九号房找到了“自我”,只是总是被外在的事物干扰。然而令她自己没想到的是,当她勉强回到原来的生活中时,发现自己原来的身份已经完全被替代,她在家庭里已经没有自己的“房间”了,苏菲像一个真正的女主人那样照顾孩子们并被他们接受。在自己的家里,苏珊“自觉像个客人”。而当她为了掩饰去十九号房的真实目的对丈夫编了一个不存在的情人潘麦克时,丈夫的反应是很理智的接受并迅速承认他自己的婚外情还建议来个“四人行”。苏珊绝望地想“你要是理智的话,你要是讲理的话,你要是从来都不让自己有自私的念头、嫉妒的心理的话,那你自然会说:‘我们来个四人行吧。’”[2]她发觉马修对自己的爱是有保留的,感到他并不那么爱她、需要她。至此所有阻碍苏珊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的障碍似乎都已经消除,孩子和丈夫不再需要她,她可以摆脱他们的牵绊去寻找自己这么多年来想要的自由和真我。苏珊感觉到“恶魔不在房里,他走了,再也不会出现。她已向他购买了自由,已滑入黑暗的梦境”[2]。苏珊终于找到了她所追寻的那个“真实的自我”,代价是失去了她的家庭——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他们对她的爱。她在自己的“十九号房”打开了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永远“漂入黑暗的河流中”[2]。
四
小说里出现的四个房间——马修和苏珊的卧室、苏珊在家中独处时的空房,即“妈妈的房间”、离家不远的维多利亚区的一家旅馆的房间和离家较远的派丁敦的一家旅馆的房间,即“十九号房”,从空间上看,离苏珊的住房越来越远,象征着苏珊对家庭生活的一次次远离,从时间上看,属于她自己的独处时间越来越长,同样象征着苏珊对远离家庭生活的渴望,也是她自以为的对“真实自我”的寻找过程。她先是住在自己和马修的房间里,代表她的身份——男主人的妻子、一家七口人的持家人,然后找了一个顶楼的空房子,因为她需要暂时和家人隔离,以获得独处时的安宁,在这个尝试失败后,她在家外找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却仍然摆脱不了家庭的牵绊,于是她越走越远,独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以为脱离了家庭即找寻到了自我。但当她在“十九号房”里找到“自我”时,却发现家庭对她的需要和依赖不复存在,她成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她和世界的联系因为与家庭生活的隔离而被切断,她找到的“自我”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于是她了结自己的生命,寻找终极的自我——死亡。
苏珊所要的“自我”不过是把自己与家庭和社会隔离开,只不过是一个人独自呆着,不与他人交流沟通。她以为她的家庭生活是一种累赘,是她的丈夫、她的四个孩子、她的大房子、她的家庭主妇生活把她拖累成一个没有自我的人,实际上正是这些构成了她的自我。自我不过是外在种种客观环境的集合在个体上的投射。一个人的幸福就是在对丈夫的爱、对孩子的照顾、对家庭琐事的顾虑、和他人的相处甚至是和他人相处中情感的自然流露中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客观环境决定主观能动。人是社会动物,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只有在社会中通过和他人的相处实现自己的社会功能才能成为人。现代社会的人只有在一定社会联系中才能生存,这一点是“构成人的使命的东西”[3]。客观环境的种种影响塑造和决定了一个人的“自我”,这个“自我”其实也是个人在社会中不同的身份角色的总合,而不是脱离其他人独立存在的。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4]没有了在社会中的种种身份、角色和他人对这种种身份角色的认同,个人就无法生存下去或成为社会边缘人而游离于人类社会之外。人生的意义不仅在于个人“自身”的存在,更在于在和他人的互动中个人“自我”的实现。正是由于苏珊丈夫的不忠和她的默许隐忍、由于儿女的不再需要、由于家庭女教师的替代,使得苏珊原有“自我”的客观支持全部丧失,她成了一个没有人需要的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一个活着和死去没有两样的人,她已经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所以她选择了死亡,因为死亡能让她实现终极的自我,形体的消灭使她再也感受不了痛苦和沮丧,纯粹的“自我”于是就实现了。
五
英国作家王尔德曾说:“人生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其实苏珊的经历也是一种悲剧:她苦苦追寻一个自由真实的自我,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寻找的正是自己拥有的,而在寻找的过程中她失去了曾经的自我,最后以生命的结束来实现自我的终极回归。这是人生的一个悖论——我们苦苦寻找的是我们已经拥有的;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已有的。苏珊的悲剧是很多生活富足但精神上有更高追求的人的共同悲剧。我们放弃身边已有的幸福,去期盼那虚无缥缈不确定的满足,从而做出其他人无法理解的事。我们把别人不得以而忍受的境地看作自己追求的目标,得到后才发现自己原来的生活是多么的让人艳羡。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丧失了原有的一切,追悔莫及。
[1]Kiesling,Chris,et al.Identity and Spirituality:A Psychosocial Exploration of the Sense of Spiritual Self[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6,42(6).
[2]朵丽丝·莱辛.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2.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
2010-03-29
尤璐(1979-),女,安徽芜湖人,硕士研究生,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