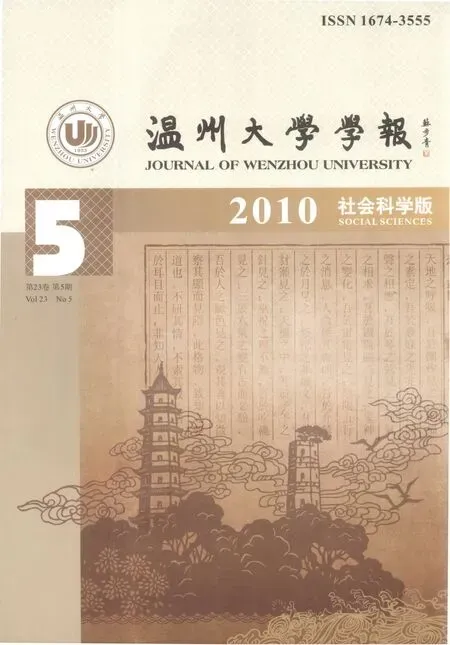时代强音遮覆下的顽强言说
—— 论茹志鹃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声音
吴其南,李智娟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时代强音遮覆下的顽强言说
—— 论茹志鹃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声音
吴其南,李智娟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十七年是一个意识形态高度一元的时代,女性声音这种按性别而非按阶级区分出来的意识很难“浮出历史的地表”,但茹志鹃小说或借日常叙事自身负载的信息而言说,或借宏大叙事将自己具有女性特点的意识权威化,或在无意识中化妆表演,虽然受到主流话语的压抑、扭曲、异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女性声音顽强地表现出来。
茹志鹃;女性声音;十七年小说
十七年是一个意识形态高度一元的时代。在十七年文学中,作家努力追求的是集体认同而非自我认同,一切创作都趋向革命的时代强音。在这样的语境里,女性声音这种按性别而非按阶级区分出来的意识很难“浮出历史的地表”,有表现也只能在时代强音的遮覆下,在话语的裂隙中隐蔽地进行,有时以潜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连作家自己都不一定意识到,由此形成十七年女性文学奇崛而又别具特色的风景。茹志鹃这一时期的小说,便是这一背景下最具阐释价值的文本。
一、借日常叙事的自我言说而言说
评论茹志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最先遇到的可能就是所谓“家务事,儿女情”的问题。据作者在文革后出版的《茹志鹃小说选》的“自序”中说,在干校时,造反派批判她,就说她的作品多写“家务事,儿女情”,是“腐蚀劳动人民的斗志”①参见: 茹志鹃.自序[C] // 茹志鹃.茹志鹃小说选.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下文所论作品均出自同一小说选, 不再一一注出.。按说,这些问题是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作者的各种讨论中已经提出并解决了的。茹志鹃小说不直接写战争和生产斗争的大场面,但以小见大,以“家务事”写时代风云,与时代精神不仅不矛盾还见出特色。可一些人为什么还是抓住不放,总觉得其中还有没有说出的藏匿呢?
不能说这些人的“敏感”全是无理取闹,按照那个时代的价值标准,这里确有一些和当时的主流话语不完全合拍的东西。在当时文学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价值取向里,一些理论家可以承认题材没有性质之分但同时认为不同题材在价值上是有差别的。沙粒中可以见出太阳,但肯定没有直接写太阳的辉煌;浪花中可以见出大海,但肯定没有正面写大海的气势,“作家完全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个性和特长选择写作对象并从不同角度加以描写,但作家有责任通过作品反映生活中的矛盾,特别是当前现实中的主要矛盾……为什么不大胆追求这些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形象,而刻意雕琢所谓‘小人物’呢?”[1]这已说得很清楚了。若举例,如《静静的产院》,写于全社会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时期,作者没有直接写三大革命的宏伟场面,而是选择了“产院”这样一个和女性、和个体生命紧紧联系的空间,选择了谭婶婶这样一个徘徊在进步与保守之间的女性人物,“产院”前面还加上“静静的”这样一个修饰语,一种安谧的、远离喧嚣的氛围便油然而生。按宏大叙事的标准,其意义自然不及写火热的革命斗争和英雄人物重大。可问题在于,即使在 20世纪 50年代那样的环境中,人们(包括作家自己)在内心深处、在潜意识里,是否完全认同这样的价值观呢?换一个角度,从生命价值的角度看,《静静的产院》的描写不也现出特别的意义?一些人批评茹志鹃,很大程度上就是感到那个和主流话语不完全相同的声音的存在。
其实,题材是可以自我言说的。一部作品选择特定的描写对象,就选择了这些对象所在的话语空间,选择了这些描写对象所负载的文化意义,在深层影响和决定着作品的质地。《静静的产院》如此,《妯娌》等作品更如此。《妯娌》是典型的“家务事”,从一个婆婆的角度写她对二媳妇进门、怕她与大媳妇相处不好导致分家的担忧。“二妈愁的是: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听说新媳妇在劳动方面是好手,进了门,和老二正好是一对,小夫妻俩干起活来,那还不是进账多、出账少?老大和大兰子要正经干,那也不差老二两口,可是他俩有两个孩子。大兰肚里又怀着孕,一天做十分工,还得给托儿所一分半。这一笔进出帐,不用打小算盘,一眼就能看个一清二楚。这在老二当然不会说什么;可是新媳妇呢,就算新媳妇再老实,再好说话,对这样一笔吃亏帐,也决不会没有意见。要是一个有了这种心,两个就不会和气;一不和气,按老规矩,就得分家。”这是从正常的日常生活的角度描写的,符合实际,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自然也符合一般读者的心理统觉。可故事没有朝着赵二妈担忧的方向发展,而是因为俩妯娌都是青年团员,都按青年团员的原则办事,不仅没有矛盾,还争着互相关心,争着为国家作贡献。比较俩妯娌,老人的想法倒显得有些多虑,有些跟不上年轻人,跟不上时代了。可作品始终没有提及赵二妈原来担忧的那些极具体的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回避不等于消失、不再存在,题材是能够自我言说的。在《妯娌》中,长期的社会生活带给“妯娌”、“婆媳”这些语汇的复杂内容被极度地简化和压抑了。“沉默”也是一种声音,无言中,人们仍可感受这些题材的声音,感受到它的顽强的言说。
由于题材自身负载信息,能够自我言说,所以,将宏大主题引入日常叙事,在个人生活空间表现时代强音,两者能互相融合也能互相扭曲,处理不好,会出现双方都显得怪诞、尴尬的局面。像《妯娌》这篇小说所反映的妯娌、婆媳这些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日常化、私人化的,它不但有自己负载着的传统文化的信息,而且有表现这些内容的方式,如叙事角度以及语调等。而“青年团员”却完全是另一叙事系统的语码,联系看一个和“妯娌”、“婆媳”、家庭等有巨大不同的语境。将“青年团员”这样完全政治化的语码引进“妯娌”、“婆媳”这些词汇构成的语义系统,虽然宣告着“青年团员”代表的语义系统的长驱直入,宣告公共话语对私人空间的占领,但这种占领也使“青年团员”代表的意识形态话语付出了代价:即在“妯娌”、“婆媳”这些语汇构成的语境的压力下变形,显得僵硬、霸道,甚至有点怪怪的。作品写新媳妇过门时,听别人向自己介绍婆家的家庭成员,“红英嘴里机械的跟着称呼,脑子里却想着昨天在青年团员小组会上同志们给自己做鉴定时,嘱咐的那些话……”;第二天一早,赵二妈听到两个儿媳为一件什么事在争执。大媳妇说她不同意,二媳妇反驳说:“你这是什么思想?还是青年团员呢!”把这些话和赵二妈细腻、真实的心理活动放在一起,不用多加比较,就立刻显出它们的僵硬、突兀、滑稽可笑。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如愿》、《春暖时节》等作品里。这显然是主流话语不愿意看到的。
在宏大叙事的遮覆下坚守叙事的日常性,尽管无法完全抵挡宏大叙事对日常空间的深入,但多少又形成对宏大叙事的一些悬搁,甚至某些局部的消解。这是茹志鹃十七年小说一再引起争议主要原因,也是一个在那个年代不肯完全放弃自己声音的女性作家所能固守的最后的空间。
二、在宏大叙事的遮护下言说
题材能够自我言说,但文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声音还主要来自背后组织这些题材的那个意识,在这一层次,十七年的作家是努力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这种一致对女性声音的表现并不全是负面的。中国主流文化的男性化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渗透到社会人生的一切方面,十七年主流意识形态虽然是高度政治化的,但在很多方面以反传统文化为旗帜,这就会在某些方面和传统文化中男性意识相冲突,这就给女性意识的出现提供了一些机会。一些女性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把握了这一机会,努力在赞颂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表现出对传统文化中男权意识的批判,使女性意识借主流意识形态权威化。茹志鹃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声音就是借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
比如《在果园里》,这是一个写童养媳生活的作品。故事的主人公小英“原是渔船上的,死了娘就给了姜大妈家。姜大妈也不是富裕的人家,只图多一双手干活,才收下了。”做了童养媳,自免不了挨打挨骂,这状况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土改工作组来到小英所在的村庄,小英主动要求离家去看果园,后来,果然在劳动中成为积极分子,并找到自己的爱情和幸福。通过小英解放前后生活的对比,歌颂了将受苦的妇女从苦海中解放出来的新社会。“怪来怪去,都怪旧社会旧思想不好”,女性意识的指向和主流话语的指向是一致的。但仔细体味,二者并非全无区别:主流意识形态更强调“旧社会”不好,女性意识更强调“旧思想”不好。小英第一次找到作为工作组成员的“我”,要求去果园时曾说:“我娘(指现在的婆婆)从前还骂我,现在也不大骂了,打更是不打了,可我看见家里的那两扇大门,头脑子就嗡嗡地响,这已经习惯了,想改也改不掉。我想我要能看个果园,离了家,自己挣工分自己吃,这不就是妇女解放,独立了吗?”这是在已经解放了的情况下说的。小英极力想摆脱那个给她许多不幸记忆的家,但造成这些不幸记忆的姜大妈并不是旧社会统治阶级的人,她只是有些旧思想。作者作为女性作家对童养媳陋习的理解要比将其单纯地归罪于旧的社会制度的理解要宽阔得多、深刻得多。但在当时,人们并不特别在意这种主要仍属“大同小异”的区别。所以女性声音是借主流话语表现出来并获得权威化的。
还有一种,如《如愿》、《春暖时节》这样的作品。《如愿》中的何大妈,解放前,为了照顾儿子放弃了去外面作工的机会。解放后,快 50岁了,硬是不顾儿子的反对,去街道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儿子反对说现在家里并不缺钱,母亲老了,应在家里享福。这是说出来的理由,没有说出来的理由是母亲出去工作没人帮他烧饭带孩子。而何大妈要出去工作的原因也恰在此:她清楚地感到,在家里烧饭带孩子和在厂里干活是不一样的。作者写她第一次拿到工资时的感觉:“她活了 50年,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自己做好做坏,和大家,甚至和国家都有了关系。”将这句话反过来,意思自然就是:何大妈活了50年,从没感到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自己做好做坏,和大家、和国家都没有关系。不管何大妈这样想时是否感到辛酸,旧时的男性文化其实就是这样看待女性和女性的家务劳动的。但这种将女性圈在家庭里的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当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再把妇女圈在家里,是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的。何大妈也正是获得主流话语的支持,所以才在行动上挺直腰杆,说话也显得理直气壮。很显然,这一价值取向也是这篇作品中隐含的作家的观点。作者、女性人物、主流意识形态在这儿达到一致,代表传统男性话语的何大妈的儿子只能节节败退了。作为革命战士的茹志鹃和作为女作家的茹志鹃持的是相同的看法。
但是,女性意识和主流意识形态不是在什么时候都是一致的。当这二者不一致时,依傍主流话语的言说方式便会现出矛盾和尴尬。这在《在果园里》尚不明显,在《如愿》、《春暖时节》便表现出来了。在《春暖时节》里,作者写静兰受丈夫冷落时的心理活动:“她不比朱大姐起得迟,也不比朱大姐睡得早,朱大姐忙碌辛苦,她也没有闲着,明发更不比朱大姐的丈夫差,为什么他们是那样和谐而自己却是这样?为什么?”对于人物的疑问,作者的回答是她只满足于做一个家庭妇女,而朱大姐有自己的事业,静兰能从心底认同这样的回答么?由于作者采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角,一个很有女性意识特色的声音被忽视了。直到十年动乱之后,作者才在《家务事》、《儿女情》等作品中听懂这种声音。这或许可视为女性意识借主流话语表现时付出的一种代价。
三、在潜意识的化妆表演中言说
在十七年一元化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女性叙事不具有合法性,所以,一些有特色的女性意识,不待社会批判的出现,作家自己人格结构中的“超我”便自行将其压抑、转到潜意识中去了。但压抑中的潜意识不甘自行消失,总是找机会浮现出来,化妆表演便成为常见的表现方式。茹志鹃作品中的一些女性声音便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是《百合花》。
《百合花》是一篇给作者带来声誉也带来争议的作品。据作者回忆,稿子第一次寄给一家杂志,没被接受,编辑部意见觉得“感情阴暗”[2]13。后来作品在《延河》发表了,又得到茅盾先生的肯定,但争议并未平息,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有人说它歌颂了党领导下的军民关系,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鱼水情[3];有人说它表现了青年男女“某种朦胧的身体吸引”[4];作者自己在文革后说它表现的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2]45。段崇轩则认为,“表现了一个稚嫩而蓬勃的生命在严酷的战争中的悄然消失和毁灭,作者谱写了一曲纯真、浑然的青春与生命的挽歌。”[5]总体上,我们更倾向段崇轩的说法,但认为,上述其他说法也非全无道理。我们理解这个作品的主题是分层次的。在深层,确实包含了更复杂的、或许连作者自己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含义。
这可以从作者对构思作品过程的回忆中看出来。1946年八月中秋,总攻海岸战斗打响,作者在前线作战勤工作。战争开始,就有伤员送下来,“有时担架刚抬到,伤员就不行了。担架摆在院子里,皓月当灯,我给他们拭去满脸的硝烟尘土,让他们干干净净的去。我不敢揭开他们身上的被子。光从脸上看,一个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就着天上大个儿的圆月,翻看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心里不可遏止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有秘密,未了的心事。”[2]40中秋,本是团圆的日子;月光,最容易使人产生清寒、孤寂的感觉。在一个远离家乡的陌生的地方,这些可爱的还未完全长大的年轻战士就这样去了,永远永远地去了。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年轻人,从小到大曾寄托父母多少期望;自己心中曾有多少梦想,可这一切,在瞬间都戛然而止了。此情此景,在一个天然地对生命有着更多敏感的女性的感觉里,不能不有些黯然和神伤。这,应该是孕育这篇作品的最初的种子。
但这仅是一个朦胧的感觉,光靠这个感觉是无法成为作品的。要将这感觉变成故事,还要结合作家的其他生活经验进行联想。作家并不缺少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在莱芜战斗中,一个小通讯员曾冒着危险送她去前线;一次参加战士讨论会,见过一个一说话脸就红但打仗却非常勇敢的小战士,等等。将这些活着的战士和那些死去的战士联系在一起,就出现了后来《百合花》中通讯员的形象。“在确定小通讯员性格、特点的同时,就出现了一个女性的‘我’,来串起整个故事。……带着一个女性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2]4但是,用这样的人物、故事表现什么?仍表现当初面对战争的残酷性而产生的有些黯然的感觉吗?显然不行。作者真正动手写这篇作品是在1958年。在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里,对革命战争任何的、哪怕是最微小的疑问都会被视为对革命战争的不敬。将这种感情放在一个青年女战士身上更是不合适的。作者说自己写《百合花》时,正是反右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2]39从自己战时认识的、给过自己帮助的小战士上升到战争时期美好的同志关系,有迹可寻,但仅此,和当时的主流话语显然还是有距离的。于是,作者虚构了新媳妇这一人物形象,以小通讯员舍身掩护抬担架民工的举动表现军爱民,以小媳妇献上新被子表现民拥军,军民鱼水情,既实现自己表现战时美好的人际关系的愿望,又和主流话语完全地接轨了。
说作者“虚构了新媳妇这一人物形象”,是因为作者生活体验里有女战士的原型,有小通讯员的原型,却没有新媳妇的原型。虚构一个新媳妇的形象在这个故事中有着三重的作用,这三重作用正好对应作品三个层次的主题。一是作为“民”,回应小战士的“军爱民”,表现“民拥军”,合成“军民鱼水情”的显层主题。二是和小战士、“我”合在一起,表现战争期间美好的同志关系,暗中成为写作这篇作品时正在进行的反右斗争的反衬。新媳妇的存在其实还有一层意义,即作为作者当初的情感的转移和延伸,将“我”在包扎所感受到但又不便通过女战士表现的情感放在她身上表现出来。新媳妇刚结婚,正处在幸福中。从一个正处于幸福中的女性的眼睛看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年龄的人,如果不是战争,他也会和自己一样,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享受人生的全部快乐和幸福。但顷刻间,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想到此,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震颤和悲悯。这一层含义,在作者那儿,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但绝非无迹可寻。
但作品的这几层含义间是不怎么连贯和统一的,甚至是有矛盾的。反映在新媳妇这个人物形象身上,由于负载的内容太多,且不统一,便形成其性格上的模糊和矛盾,特别是一条印有百合花的带有爱情隐喻的新被子的设计,使情感变得有些暧昧,把读者带入迷雾之中,出现许多没有多大必要的想象和阐释。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新媳妇是一个并不怎么成功的人物形象,但从转移和掩盖作者关于战争的残酷性的思考的角度看,这个设计却成功了。一些人敏锐地感觉到它心有别鹜,说它“情绪阴暗”,并非全是空穴来风。若无这层转移和掩盖,后果如何就很难预料了。
四、时代强音认同下女性言说的有限性
在宏大叙事的遮覆下进行带女性意识的言说使茹志鹃小说在十七年宏大叙事的一统天下里找到一些小小的裂隙,使自己某些具有女性意识的声音潜行于历史的地表之下,偶尔还挣破重重阻压顽强地浮现出来,在一个总体话语趋于僵硬的环境里获得较多的质感和弹性,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女性意识的文本,但其缺憾也隐含在这种叙述中。
由于是在追求社会认同的前提下隐含自己的女性意识,并借主流话语使自己的女性意识得以表现和权威化,这种叙事能获得的女性话语的空间一开始就极其有限。即使一些很有个性很有深度的女性意识,也由于其和主流话语不合,受到主流话语在自己意识层面的投射而形成的“超我”的压抑,很快地沉潜和转移了。更多的遗憾和缺陷还表现在,因为追求与集体话语的认同,借用主流话语的视角观照生活,很容易遮蔽自己对生活的新鲜感受,出现认识上的盲区、误区。如《如愿》、《春暖时节》一类作品,母亲一辈子烧饭带孩子,儿子明明享受着母亲的恩惠却对母亲的“家庭妇女”身份大加漠视;妻子为家庭终年操劳,丈夫明明享受着妻子的照顾却还因此而对她冷漠,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不仅在个别人那里,就是在社会、群体文化的层次,人们长时间以来不也这样看待女性的家务劳动吗?何大妈第一次拿到工资时说“自己活了 50岁,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自己做好做坏,和大家,甚至和国家都有了关系”,此话后面,不也包含着女性的家务劳动得不到社会承认的辛酸?静兰在受到丈夫冷落时发出的疑问,其实不也是对社会不承认女性家务劳动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的抗议?可惜,当时的人们都没有听懂这种声音。由于认同主流话语(或许还有自己也不一定认识到的精英视角的原因),作者也多少陷入误区,没有听出何大妈、静兰发出的包含了许多辛酸、委屈、不满甚至抗议的声音,使一个极有探讨价值的女性文学话题被浅化,至少从今天的观点看,《如愿》、《春暖时节》等算不得很成功的作品。
到十年动乱后的《家务事》、《儿女情》等作品,作者终于将这一课补上了。同样是写女性的家务操劳、儿女牵挂,但不是将它们放在“革命”、“国家大事”的陪衬、甚至相反的位置上,而是让它们走到了话语的中心。《家务事》的故事背景在十年动乱中,金凤刚送走大女儿去上山下乡,小女儿又生了病,还被催逼着去干校,相比之下,“家务事”显得正当、重大而“革命”却显得不近人情;《儿女情》故事背景在十年动乱后,革命干部田井不满儿子的生活方式,一再声称要把自己的积蓄作为党费交给组织,但在死亡真正到来时,还是选择把钱留给儿子,完成了“母性”对“党性”的僭越。这儿变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细节,而是看问题的切入点,评判的价值标准。人、生活、生命成了出发点和归宿。从这样的角度看世界,家务琐事、儿女情长,自然不再是“可有可无”、不再是与社会、国家都没有关系。公然以“家务事”、“儿女情”作为小说的题目,表现了作家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这一角度对作家所作的批评的回应,也是对写作这些作品时依然存在的男性话语对此类话题的压抑的挑战。作者在十七年小说中一直隐含着的女性声音终于响亮地表现出来了。这是作家创作的飞跃,也是历史本身的进步。
[1] 欧阳文彬.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C] // 孙露西, 王凤伯.茹志鹃研究专集.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118.
[2] 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C] // 孙露西, 王凤伯.茹志鹃研究专集.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3] 汤铭.美丽的花朵 纯朴的诗篇[C] // 孙露西, 王凤伯.茹志鹃研究专集.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263.
[4] 戴锦华.涉渡之舟[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1.
[5] 段崇轩.青春与生命的挽歌[J].名作欣赏, 1989, (1): 96-99.
Unyielding Speech under Ictus of Time—— Study on Female Voice in Ru Zhijuan’s Fictions during Period of 17-years before Cultural Revolution
WU Qinan, LI Zhij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eriod of 17-years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49–1966) was an era of highly unified ideology.In the period, female voice, distinguished by gender instead of class, could hardly be recognized.Fortunately, in Ru Zhijuan’s fictions, female voice, which might be oppressed, distorted or mutated by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was unyieldingly expressed to some extent.In the narration, she took advantage of the internal information in the daily narration to broadcast the voice, the grand description to authorize the sense of feminization, or makeup and performance to unconsciously demonstrate the voice.
Ru Zhijuan; Female Voice; 17-years Fiction
I206.7
A
1674-3555(2010)05-0045-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5.006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10-02-28
吴其南(1945- ),男,浙江安吉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