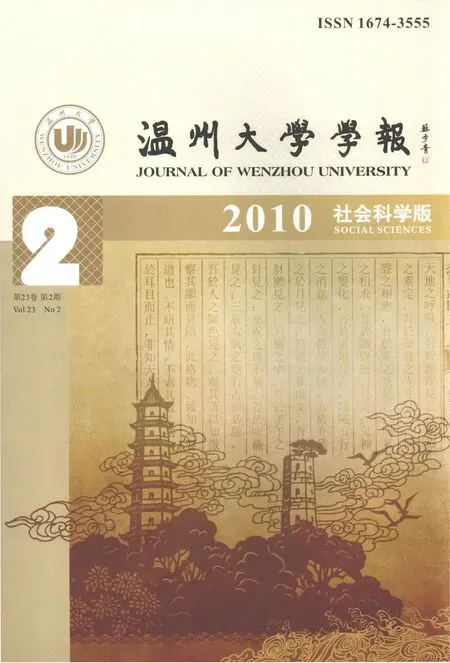论新诗中的旷野意象
钱韧韧
(华侨大学文学院,福建泉州 362021)
论新诗中的旷野意象
钱韧韧
(华侨大学文学院,福建泉州 362021)
新诗中的旷野意象包括自然旷野、社会旷野和精神旷野等。在实际诗歌创作中,旷野意象的内涵有时更为复杂,不同形态的旷野意象也可相互交织存在。
新诗;意象;自然旷野;社会旷野;精神旷野
旷野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意象。古诗中的旷野意象与地域性紧密相关,是古人生存状态的写照。中国古诗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旷野意象呈现的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或经世致用的社会环境,较少个体精神的体验。五四以后,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冲击,新诗中旷野意象的内涵比古诗中的更为复杂了。首先,受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新诗突出了旷野的地域性特征,并表现了对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其次,新诗书写了旷野上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及民族情感;再者,在特殊的国土环境中,新诗作者也开始了精神探索的新历程。当然,新诗旷野意象的三重特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往往是相互交织存在的。新诗中的旷野意象从地域性和精神性生发开来,具有丰富的审美特征。学界有关新诗旷野意象的研究极少,即使有也仅仅局限于个别诗人、个别诗歌流派的研究①参见: 杨琼. 旷野上的追寻者: 略论七月派的诗歌创作[J]. 文教资料, 2007, (7): 115-117. 咸立强. 踯躅旷野的灵魂: 胡也频诗歌创作的几个问题[J]. 运城学院学报, 2003, 21(4): 41-46.。笔者试图从整体上对新诗旷野意象的多重特征进行归纳,以此丰富人们对新诗旷野意象的感知。
一、新诗中的自然旷野
从对自然旷野的敬畏之情,到物我融合的审美体验,再到对生存环境的征服,人类主体地位的提升,使得旷野与人类的关系日趋紧张。旷野意象不仅具有地域性特征,而且也表现了诗人对生存环境的生命体验,即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
由于作家出生或常年生活在某一地域,对该地域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信仰习惯、价值观念和心理结构特别熟悉。所以其作品常具有某种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内涵[1]。因此,旷野意象的地域风貌在西部诗人笔下表现得较为明显。
曾经在青海生活过的昌耀,其诗歌明显带有西北地区的印记。如《旷原之野》:“我们于是向着旷原之野走去。/走向十二肖兽恪守的古原。”“人们去玉河掘取羊脂玉。/ 神祗半狮半鹰,眼膜半垂,示以阴柔之美态。”①参见: 昌耀. 旷原之野[C] // 昌耀. 昌耀抒情诗集.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6: 144. 下文所引众多诗人之作品, 只在正文中标明作者和篇名, 不再一一作注.诗人既写出旷野的环境特征,又化用十二肖兽、羊脂玉和神祗等意象,高歌这片土地上的人类文明。《慈航》:“摘掉荆冠 / 他从荒原踏来,/ 重新领有自己的命运。/ 眺望旷野里 / 气象哨 / 雪白的柱顶 / 卧着一支安详的剑镞……”诗人用原始人类形象和旷野意象隐喻生存主体与命运之力的角逐,这里的旷野意象有深邃的历史感。相似的还有在新疆生活过的周涛,他的诗歌有着对旷野之力的敬畏,如《站在天空旷野之间》:“如今我正站在天空旷野之间/ 这广阔而高远的世界/此刻只有我,只有我 / 是太阳灼热的目光所注视的焦点”,诗人在辽阔的旷野上张扬着野性的生命力,诗歌境界因此而显得气势磅礴。
在特殊的地域环境中,西部诗人有着对自然旷野的敬畏之情,同时又张扬了自身粗犷苍凉的血性生命力。描写东部旷野的诗歌则缺少这种力的表现,诗人与旷野也多呈观望或契合的关系。桑克的《夜景》:“我坐在边座上。/ 我的热贴着玻璃的冷脸。/ 我望着移动的旷野。/ 我望着移动的旷野中的雪。……”诗人在“橙色列车”上望着北方旷野上的雪、树、乡村、星光和大地,感叹道:“我深解它的冷,一如深解它的穷。”所以“这大地一动不动,让我欢喜。”诗人对土地怀有特别的情愫,无论是贫瘠或者富足,土地都是可以“退而独善其身,进而兼济天下”的场所。因此,生活在北方旷野的诗人早已锻炼出了坚实、旷达、从容的胸怀。而南方诗人的旷野意象则十分柔美。如席慕容的《流浪者之歌》:“在异乡的旷野 / 我是一滴悔恨的溶雪 / 投入山涧再投入溪河 / 流过平原再流入大湖”席慕容实际上是将内蒙古这片土地作为她的故乡,所以异乡的旷野没有草原旷野的那种粗犷之美。“异乡的旷野”是与溶雪、山涧、溪河和大湖等意象相连,表现出南方旷野的隽永之美。总体说来,旷野意象在不同国土环境中呈现的地域性特征也不尽相同。
旷野意象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同时包含了中国哲学思想固有的自然审美意识。罗门的《旷野》:“把柔静给云 / 把跃动给剧奔的蹄声 / 你随天空阔过去 / 带遥远入宁静……”这种向往旷野上优美自然环境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什么时候诗人从旷野的实际体验变成想象性体验了呢?这与工业文明的进程休戚相关。“人所以追求自然是因为他已经感到他和自然分开了。”[2]当自然旷野蜕化为令人震惊的荒野时,人们就不得不在想象中去怀恋家园了。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旷野的侵袭。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诗人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
刘德吾的组诗《旷野》是反思工业文明的文本。他似乎就是“那只从城市逃回的蟋蟀 / 呻吟是疼痛的肌肉依附于骨头。用骨头遥望星空”;他对要进屠宰场的牛感到无奈痛苦“昨天它还在耕田,朝远方叫唤”;他想要“赤脚踩进油菜花地”,“仰望星空”,“让荒草退出内心”,但“再次想到渡船时,我已经见不得河水”。诗人对城市文明的抵触心理在《城市事件》中达到极致:“水泥和钢铁的城市大惊失色 / 细看,确实是鸟的头颅 / 一颗颗击碎在广告牌上”,众鸟像“焦急的箭”奔向城市,却最终酿成死亡“血淋淋的声音”,因为“广告牌上画的是一棵树 / 树枝树叶背后,隐约有巢 / 已经被鸟血染红”。旷野之地被剥夺导致自然生命的死亡,而城市文明又无法产生真正的家园,死亡因此带有悲剧的色彩。诗人刘德吾笔下的旷野已经变为荒野,他不断地诉说荒野的生存现实“不要告诉我”,“亲爱的你对,你说得很对 / 才令我寒气爬上了脊骨!”诗人对工业文明心怀警惕,他没有去自然旷野寻求逃避,他的诗歌呈现了人与旷野的尴尬关系,他将人的反思写得力透纸背。
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旷野的地域景观如何,只要人的心灵没有荒芜,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得到改善。鲁枢元曾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潜伏着一片自己的心灵旷野。如果你能够暂时躲开喧嚣的市声,排解掉日常的焦虑,以宁静、恬淡的心态回顾一下自己的生命、追忆一下自己的童年、怀恋一下自己的故乡、重温一下飘逝的梦幻,你也许就会回到那片蓊郁浩茫的精神旷野,那无疑就是一次心灵的返乡。”[3]事实上,返回旷野确实可以缓解物质文明带来的压抑之感。例如王明韵的《我在旷野里轻轻呼唤爱人的名字》,诗人置身于长满庄稼和阳光的田埂上,实现了灵魂和肉体的双重返乡。总之,旷野意象的自然性最终视人与旷野的关系而定。
二、新诗中的社会旷野
面临 20世纪剧烈的社会变革与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诗人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时代环境之外,旷野意象因此带有社会性的色彩。活跃于1947 – 1948年间的上海诗人发表声明:“我们现在站在旷野上感受风云的变化,我们必须以血肉似的情感抒说我们思想的探索……”①参见: 叶维廉. 中国诗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284.也就是说,诗人十分关注社会旷野上的风云变幻。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旷野之上的国土境况也不同。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期间,新诗中的旷野意象十分凄冷恐怖。如杜运燮的《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我害怕旷野,/ 只有风和草的旷野,/ 野兽四处觅食:/ 它们都不怕血,/ 都笑得蹊跷,/ 尤其要是喝了血;”狗、黑鸟和野兽在旷野上四处觅食,象征敌人在我们的国土上疯狂搜刮。当然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诗人并非总是在低吟苦难,七月派诗人饱含旷野生命力的战斗诗篇,曾激起了众多被压迫者的斗志。战争胜利时的旷野意象则充满蓬勃向上的激情。诗人刘流尽情地欢唱《祖先的战场》:“百里无障的旷野,/ 铺着猩红的土壤 / 烟雾茫茫 / 静听指南车的轮响。/ 啊!这是祖先的战场,/ 胜利的地方!”猩红色的土壤覆盖着的旷野,是胜利者豪迈之情的印照。新中国成立后,旷野意象就着重突出了新旧对比的社会面貌。梁上泉在《盆地巡回》中歌吟道:“当年干的冒烟的旷野,/ 修起的水渠似银带;/ 当年寸草不生的戈壁,/ 拓出的绿洲百花开”这里的旷野是人民新生活的见证。
但是,部分宣传鼓动的诗,旷野意象的生命力显得单薄,这些诗歌也就缺乏生命力。真正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是七月派,他们以激昂的旷野生命对抗黑暗社会,完成了自我价值的确认。
纵观七月派的诗歌创作,扑面而来的是那血与火交织的时代气息:国土沦丧的忧愤,人民流离失所的苦难,人民浴火重生的自信,对光明自由的渴求,对罪恶腐朽的控诉……[4]艾青诗中的旷野意象也始终跳动着庄严朴素的忧郁诗魂。他在《旷野》中反复低吟:“薄雾在迷蒙着旷野啊”,“你悲哀而旷达,/ 辛苦而又贫困的旷野啊”,然而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什么声音,/ 一切都好像被窒息了;/ 只有那边 / 看不清的灌木丛里,/ 传出了一片 / 威慑于严寒的 / 抖索着毛羽的 /鸟雀的聒噪”,在此,旷野意象笼罩着阴沉悲凉的氛围,是中国社会艰难险恶的真实写照。但诗人并非一直忧心忡忡,他也曾说过“我始终是旷野的儿子”,并且“看着旷野的边际”,“把我的火一样的思想与情感 / 溶解在它的波动着的 / 岩石,阳光与雾的远方……”,蕴含着不息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的旷野意象,在艾青诗中充满了生命的律动,是诗人在战争风暴中的栖息地。
作为七月派的重要诗人,“绿原走过了从天真抒情到与现实肉搏的过程。”[5]在《童话》时期,绿原沉寂在文学幻想中,以生机勃勃的旷野梦境补偿都市化生活所带来的孤独之感。当走进现实的社会环境时,诗人开始审视这个荆棘丛生的世界,在《无题》中写道,“它是那样严厉 / 就像旷野里的一个巨人 / 折断自己的肋骨在磨剑……”,旷野的力量开始严峻起来。绿原在《读“最后一课”》中想象着“那宽阔得使你融化的旷野,/ 那深而且密的闪泽的丛林,”在《春雷》中提及“一个士兵梦着白茫茫的旷野无聊的休战”,在《复仇的哲学》中,诗人描述:“家住在青面獠牙的旷野;/ 在荒凉的高峰 / 同暴雷答话的 / 吃死人的鹫鸟 / 是我们的伙伴。”绿原写作的年代跨度较大,旷野意象是诗人生存环境和坎坷命运的象征。作为充满“荒野力量”的歌手,绿原用强烈的复仇意识与社会搏斗,诗歌风格坚实而粗犷。
胡也频是一位在旷野中孤独抗争的漂泊者,他的诗歌氛围阴沉压抑,相关意象奇绝诡异,如《旷野》:“我寻找未僵硬之尸骸迷了归路,/ 踯躅于黑夜荒漠之旷野。/ 凛凛的阴风飏动这大原的沉寂,/ 有如全宇宙在战栗、叹息。”充满着死亡气息的旷野意象,不仅是现实环境的写照,也是精神焦灼的象征,诗人踯躅于旷野的痛苦悲郁之情呼之欲出。从表现的精神实质来说,只有旷野意象与诗人漂泊孤寂的灵魂最融洽[6]。也就是说,胡也频的旷野意象承载了诗人的生命体验,使他的诗歌风格沉郁冷涩。相对而言,石民诗中的旷野意象更为明朗,如《良夜》:“良夜为我收拾了这旷野,/ 天宇高高地覆盖在我上面,/ 我展开而且检视这闭塞的胸臆,/ 借明月之慧光与列星之炯眼。”这里明月列星的旷野带有诗人灵魂内省的主观色彩,不同于胡也频的那种阴冷的旷野。但两位诗人都是以时代场景来充实个体精神,以旷野意象寄寓着对历史民族的理解。
七月派的旷野与历史环境相关,展现着诗人激昂的战斗精神和献身精神。他们在与阴暗现实的搏斗中无所畏惧,以“在风暴里歌唱”的姿态来报效祖国。随着时局的转变,七月派诗人的旷野意象也逐渐从荒凉走向明朗。冀汸在《旷野》中歌唱奔腾的生命力是如此恢宏阔大:“旷野 / 亲爱的旷野,/ 在这里 / 这样的奔驰 / 是这样的自由自在呀!”诗人在旷野上高歌他的昂扬斗志,即使诗中偶尔流露出不能奔驰到旷野边缘的意思,也很快被一种浪漫主义精神所消解。鲁藜诗中的旷野也给人一种健康向上的感觉,在《风雪的晚上》,诗人写道:“啊,我好像闻到花香 / 从我的门边阵阵沁来 / 我感觉舒服,我感觉沉醉 / 这是冰冷的雪香,/ 这是全山谷,全旷野喷出的芳香 / 这是我爱的北方土地的香气”,只有在积极抗争之后,才能体验到旷野上最辽阔的自由。
总之,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和不屈不饶的民族精神在旷野意象上有着充分的体现。如何书写作为历史见证的旷野意象,是衡量诗歌审美价值的一个重要依据。七月派诗人将社会内容融入旷野之中,同时以主观战斗精神完成了对历史民族的理解,因此诗歌呈现出坚实的穿透力。
三、新诗中的精神旷野
旷野不仅是自然环境的象征,而且也是社会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诗人在自然和社会两重世界奔波之后,自然会产生对精神旷野的内在诉求。杜光霞、周伦佑在评论百年新诗经典《旷野》时指出,诗集《旷野》的编选尺度,着重于诗歌作品的精神向度及对存在的反观[7]。显然,此处的旷野也是诗歌精神的比拟。
中国新诗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对峙碰撞中发展的。事实上,对西方的知识、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沉醉,往往压倒了对中国文化原质根性异化生变的思索[8]。基督教文化对现代中国曾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圣经》中,旷野是考验和净化之地,也是避难和沉思之地,更是立约的福地[9]。杨剑龙阐述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①参见: 杨剑龙. 旷野的呼声: 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虽然中国现代作家不一定是完全意义上的基督徒,但他们对宗教文化总有些了解。因此,他们笔下的旷野意象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精神拯救的特征。
在多元异质文化共生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受探索新的精神之路的煎熬。这时,他们会去旷野敞开自我、寻求真理。比如穆旦,姑且不论他是否为基督徒,但受到西方现代派特别是艾略特的荒原意识影响,基督已“匿名”地存在于他的诗中,“上帝”、“神”、“主”等词语经常在他的诗中出现。穆旦《在旷野上》高唱:“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 为了窥见我美丽的真理。”旷野意象是真理降临的地方,这与旷野的呼声有着某种共通之处。《听说我老了》中的旷野同样是心灵意象的象征:“人们对我说:你老了,你老了,/ 但谁也没有看见赤裸的我,/ 只有在我深心的旷野中 / 才高唱出真正的自我之歌。”这里的旷野是和现实世界相对的。站在现存的社会成规之外,反观现存社会成规之中自我的生存状况,是穆旦晚年“真正的自我之歌”的一个主要内容[10]。只有对自我和社会进行反思,才能在心灵深处真正地歌唱,旷野意象因此具有鲜明的形而上的特征。
在精神旷野上,常有着抒情主体的身影。如杨子的《行走在黑暗的旷野里》,诗人独自走在夜幕中的旷野却不感觉孤单,因为“没有星光,/ 但一切都很明亮,/ 一切都映照在我的心上,”大地、石头和小鸟这些原本无法在黑暗中窥见的事物,都在诗人的主观世界中得以显明。接着“在死亡中青草沙沙作响”,“惟有那些不会进入历史的/才值得我去关注”。也就是说,诗人关注的不仅是旷野上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更是那些渺小的易被忽略的事物。这里的精神旷野也与生命旷野相连,见证了诗人内心执着而坚定的信念。在杨子笔下,只要有心灵的澄明就可以进行精神的求索。而一般说来,心灵旷野更需要精神之光的照耀,表现在诗歌中就是火、灯、星光等意象。西渡在《火》中写道:“她用袖子点燃一朵火焰 / 远远地把它携入风中,携入 / 一片黑暗的旷野,然后 / 它突然变大,充满整个舞台”,郑愁予《野店》:“是谁传下诗人这行业 / 黄昏里挂起一盏灯……是谁挂起这盏灯啊 / 旷野上,一个朦胧的家 / 微笑着……”在这里,火在旷野中变大,灯照亮诗人回归的家园,它们都承担着启蒙的功能,原本黑暗的精神旷野因此而明亮。
如果说上述诗歌侧重主体的精神体验,那么另一类诗歌中主体形象则隐而不显。诗人借助于旷野的相关意象来寄寓心志。纪弦在《狼之独步》中写道:“我乃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只狼,/ 不是先知,没有半个字的叹息 / 而恒以数声凄厉已极之长嗥 / 摇撼彼空无一物之天地 / 使天地战栗如同发了痢疾”,狼作为独行旷野之上的意象,是勇于向既定秩序挑战的生命个体。还有树的形象也是这种独立精神的象征,如王太文的《看见旷野唯一的树》:“孤零的一株树,兀立旷野 / 世界宁静的中轴 / 大地绕着它匀速地旋转”蕴含着诗人主体意志的树,在旷野的姿态亦柔亦刚,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都能坚定地生存:“它舒展鲜艳的花朵,是世界的花冠 / 它光秃在雪野里,世界在思想。”同样,诗人也可借助物象来反省自身,如王家新的《风景》:“一到夜里 / 满地的石头都将活动起来 / 比那树下的人 / 更具生命”在诗人的主观情思中,现实的自然旷野与精神旷野相汇合,石头在夕阳燃烧后的夜晚比人更具有生命力,是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反讽。值得一提的是,精神旷野也与时空意识相关,是人类审美性地体验自我价值的居所。诗人在旷野上的姿态也不尽相同,他们不断寻求主体的多种生命感知方式,以实现精神世界的富足。
四、结 语
总而言之,新诗中的旷野意象包括自然旷野、社会旷野和精神旷野等。在实际诗歌创作中,旷野意象的内涵有时更为复杂,不同形态的旷野意象也可以相互交织存在。新诗中的旷野意象有许多新鲜的要素。诗人有时用存在主义哲学来书写旷野,有时用后现代的手法来消解旷野,有时甚至在旷野上书写死亡、梦魇、灵魂、乐园等主题。旷野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意象,是新诗研究中值得深入挖掘的课题。
[1] 陈剑晖. 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M].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4: 134.
[2] 鲍桑葵. 美学史[M]. 张今,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116.
[3] 鲁枢元. 心中的旷野[J]. 绿叶, 2006, (12): 75.
[4] 杨琼. 旷野上的追寻者: 略论七月派的诗歌创作[J]. 文教资料, 2007, (7): 115-117.
[5] 王庆福. 生命力来自旷野的张力: 对七月派文学的一个宏观考察[J]. 江苏社会科学, 1994, (2): 124-127.
[6] 咸立强. 踯躅旷野的灵魂: 胡也频诗歌创作的几个问题[J]. 运城学院学报, 2003, 21(4): 41-46.
[7] 杜光霞, 周伦佑. 精神还乡的诗性之旅: 评《旷野》的百年新诗经典遴选尺度[J]. 西南大学学报, 2008, (5): 39.
[8] 叶维廉. 中国诗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260.
[9] 胡家峦. 篱墙花园与旷野: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园林诗歌研究[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4, 20(6): 3-9.
[10] 段从学. 在冬天的旷野唱出自我之歌: 论穆旦晚年的诗歌创作[J].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5, 21(2): 14-20.
Study on the Images of Wilderness in Chinese Modern Poetry
QIAN Renren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qiao University, Qianzhou, China 362021)
Images of wilderness in Chinese modern poetry included images of wilderness in nature, in society, in spirit and so on. In practice of poetry creation, the connotation of images of wilderness sometimes is more complex and different forms of images of wilderness can be intermingled with each other.
Chinese Modern Poetry; Image; Wilderness in Nature; Wilderness in Society; Wilderness in Spirit
I206
A
1674-3555(2010)02-0073-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2.01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09-11-19
钱韧韧(1986- ),女,安徽蚌埠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和诗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