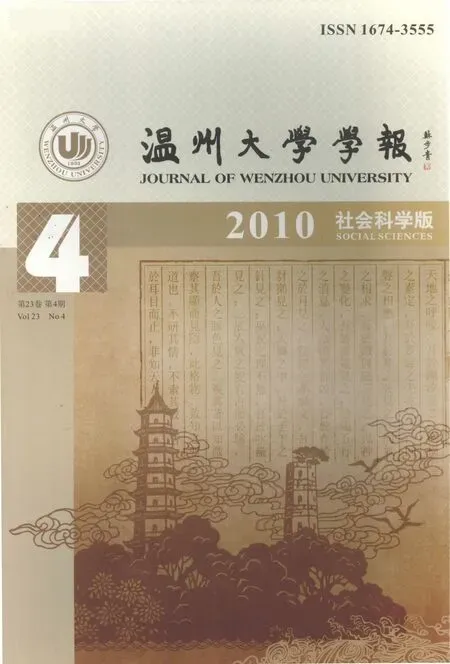山水审美:启蒙与终极关怀的主题变奏
吴海庆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山水审美:启蒙与终极关怀的主题变奏
吴海庆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中国古人浓厚的自然本位思想和中国优良的山水环境使中国山水审美文化在古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贯穿其发展过程的是终极关怀与审美启蒙两大主题的交融与变奏。
山水审美;启蒙;终极关怀;主题变奏
山水诗和山水画构成了中国古代艺术的主体,这在世界审美文化中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造成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很多人认为是由中国古人浓厚的自然本位思想决定的,老子、庄子、孔子以及他们的后学大都认为人应当效法自然,《周易》更是持完全的自然教化态度,这无疑对整个中国审美文化偏重于自然审美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还有一个更为基本却容易为美学家们忽视的原因,就是我国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山水形貌千姿百态,这为山水艺术的生成提供了最优良的物质条件。从中国山水审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上述两个方面恰恰支持了它的两大主题,前者使中国古代山水艺术多以关注和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在自然山水之上寄托人的终极关怀①本文所谓“终极关怀”取神学家蒂利希的说法, 即“凡是从一个人的人格中心紧紧掌握住这个人的东西, 凡是一个人情愿为其受苦甚至牺牲性命的东西, 就是这个人的终极关怀, 就是他的宗教.” 参见: [英]宾克莱.理想的冲突: 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M].马元德,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297.,后者又使许多优秀山水艺术作品以发现自然山水的独特魅力为己任。这样,中国山水艺术便在山水审美启蒙与对人的终极关怀这样两大主题的交融与变奏中一路向前,光辉灿烂。
一
山水审美早在魏晋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如《周易》中指涉美的贲卦即与山相联系。贲卦的象是“山下有火”,意为火光映照着山上的草木,变幻出各种颜色,造成一种鲜艳美丽的景象。《周易》认为,自然美先于人而存在,人类经过大自然的启蒙,对自身有所感悟才认识到人自身的美。在魏晋以前,由于人类生存能力十分有限,所以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消耗在生存斗争中,尚无充分的剩余精力去发现和欣赏大自然的美,因此人与自然山水之间的审美关系十分微弱,而且多是不自觉地掺杂在错综复杂的巫觋、伦理和功利关系当中。其大体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山水审美意识在图腾崇拜中的悄然萌芽。在许多民族的原始文化中都有山水造人的传说,中华民族自谓是龙的传人,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说法,“龙,水物也。”也就是说,古人认为中华民族的根在于水。《左传·昭公元年》说:“山川之神,则水旱厉疫之害,于是乎崇之。”由于自然山水对人的命运的巨大影响乃至决定作用,使古人逐渐形成了山水崇拜心理,秦汉时期各代帝王隆重祭祀五岳就是我们民族山水崇拜心理的最重要的官方表达方式之一。古人的山水审美意识在这种根性思考与命运忧患中开始萌芽,想象出了龙的形象,刻画了洛神、湘君等众多的人格化自然神,发明了复杂的祭神仪式,这些东西在后来经常会作为一种文化原型对国人的山水审美活动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二,比德——山水审美道德化的源初形式。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伦理体系,对于这个伦理体系的合法性,《周易》将其推定为“以神道设教”,就是说所有的社会伦理原则都是以自然规则为依据的,大自然是人类伦理实践的启蒙者和导师。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古人常常用山水比德的方法来进行道德启蒙和自我反省。如对于孔子的“仁者乐山”之说,《韩诗外传》作了这样的阐释:“山者,万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殖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四方益取与焉。出云道风从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于山也。”[1]古人比德并不是仅仅把山水自然看作是道德的象征,而是认为自然本身就有德性,且这种德性是人类道德的源泉,因此人类应该依据自然来规范和省察自身。这是自然人化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而尚不充分时所形成的道德体悟与自我认识方式,这种体悟与认识方式在农业社会里发展成为一种基本的教化方式,并且促成了一种稳固的道德化审美思维形式。第三,风水学——功利主义山水审美意识的摇篮。如何免除自然灾难,让自然环境更好地为人造福是古人一直在努力探索的问题,中国古代风水学是人们进行这种探索的重要成果。在《周易》、《山海经》、《河图》、《洛书》和《汉名臣奏》等早期文献中都已经显现出了古人浓厚的风水观。风水学以人与山水环境的和谐为目标,以人文与自然的互补为操作原则,它的基本内容是世俗的和功利的,但是它却在无形中深刻地影响了人对自然的评价方式和审美态度。第四,渗透在艺术中的潜在的山水审美意识。早期人类在心理上和大自然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隔阂,在实践中还有极多的不和谐处,但是,越是这样,人们在特定的条件下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境况就更加为人称道和受到珍重。《吕氏春秋·本味》和《列子·汤问》中都讲到了伯牙与钟子期于“高山流水”中成为知音的故事,对这个故事的解读,人们往往侧重于理解伯牙与钟子期心心相通的知音关系,而忽视高山流水自身的意义。其实,这个故事同样告诉我们,人类一直在努力消除自身与大自然的隔阂,在大自然中倾听人类实践的回声,“高山流水”的故事正是一种极致和典型。在《庄子》中山水审美意识已经隐约可见,让井蛙自得其乐的一洼浅水、让河伯陶醉的滔滔黄河以及北海若与东海之鳖向人们展示的苍茫大海等,尽管庄子对它们并非全是赞美,但都让人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了自然的魅力。庄子对自然的描写和想象,仍然激荡着一种神话式的广大、幽邃和浩渺,《逍遥游》中的北溟与邈姑射之山,《秋水》中的江河与尾间,都不是专门的审美对象,而只是表现庄子自由精神的素材与媒介,所以在庄子那里只具有一种“潜在的山水精神”[2]。《诗经》中人与山水的审美关系相对清楚了一些,虽然其关注的重点仍然是人的行动,但是山水自然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的构成性意义更加显著,而不再是一种可以任意置换的因素。《诗经·唐风·扬之水》云:“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诗经·陈风·泽陂》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诗经·秦风·蒹葭》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中的爱情故事多发生在水边,不管这种写作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水与亲情、爱情和生命之间的那种难以分割的天然联系和涌动在简洁而生动的语言中的清亮完美的意境。在《楚辞》中,自然山水成为更为直接的审美与抒情对象,许多情况下山水被拟人化,成为一种人格或精神的象征。《楚辞·湘夫人》云:“沅有茝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楚辞·山鬼》云:“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楚辞》中的自然抒情对象是以潇湘山水为中心的,潇湘山水后来成为文人墨客反复歌咏描绘的对象,成为构建中国审美文化的重要平台,这固然是由其本身的自然特性决定的,但是也不能忽视《楚辞》的首倡之功。
总的来看,在魏晋以前自然山水已经与人形成多方位和多层次的复杂关系,从图腾崇拜到伦理信仰,从对自由的追求到爱情的表达都或隐或显地联系于自然山水形象。不过,那时人们对自然山水关注的重点还不在审美方面,除了《诗经》和《楚辞》等少数艺术作品外,人对自然的神性崇拜和对自然的功利关系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对自然美的发现,遮蔽了自然美的光芒。
二
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在构建中国审美文化中发挥作用,是以江南山水之美的发现为开端的。东晋王朝南渡使江南山水以异质的风韵呈现在北来的文士面前,以陌生化的效果对其形成强烈的审美冲击。《会稽郡记》曰:“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栢,擢干疏条,潭壑镜彻,清流泻注。王之敬见之曰:‘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3]133东晋画家顾恺之到浙江绍兴一带云游,回来后向人们描述会稽山川的形貌时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3]132这种诗文化的描述并非完全依赖语言天赋,会稽山水本身引人入胜的品性才是使北方南迁文士发出观止之叹的根本原因。北方南迁文士对江南山水由衷的爱恋情绪又反过来感染着土生土长的江南文士,启发他们以审美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家园。较早从纯审美的角度大写特写江南山水的既有江南本土文士“三谢”,也有从山东南下的文士鲍照,他们以大量歌咏江南山水的诗篇唤醒了沉睡的“江南”。其中,作为中国山水诗鼻祖的谢灵运在这方面的贡献最大,他那精美的诗句把江南写得宏阔而又细润,似乎能让人听到江南山水妙流不息的节拍,如“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①参见: 谢灵运.游南亭[C]//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 第14册.长沙: 岳麓书社, 1996: 733.以下所引谢灵运的诗均出自《船山全书》第14册, 不再一一作注.等,王夫之在谈到这些诗句时,称赞其“条理清密,如微风振箫,自非夔旷,莫知其宫徵迭生之妙。翕如、纯如、皦如、绎如,于斯备。”[4]这种对永嘉山水之美登峰造极的描绘,让后来试图在山水诗创作上有所建树的诗人们多有目倦心灰之感。
与先秦艺术中将山水作为人类活动的背景不同,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人反过来成了山水整体中的一个要素或衬托,如“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和“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难匹”,纯洁高尚的人增加了山水的韵致,而且似乎只有这样高尚的人才能够与那迷人的山水相配。《登池上楼》以一个离群索居并久卧病榻的孤寂老人的眼光,来审视山峦叠翠、杨柳婆娑和莺歌燕舞的江南春色。那种从阴暗的房间走出来突然面对明媚阳光和清爽自然的心态,使诗人能够把春天的江南写得广远而微至。不过,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也时常表露出一种留恋山水与向往世俗幸福的矛盾心理,“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这与前人明朗的价值取舍相比是一种新现象,它表明谢灵运发现永嘉山水之美以后,过去所持守的功名富贵观念发生了动摇,这种动摇正是我们民族审美意识更加丰富、全面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谢灵运之后,被后人称为“小谢”的谢朓又为唤醒“江南”发挥了重要作用。小谢笔下的江南突破了大谢的地域范围,扩展到了建康、皖南宣城一带。其笔下的山水形象与谢灵运所写仍保持着近似的美学特征,而且他的不少诗句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①参见: 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C]//杜晓勒.谢朓庚信诗选.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50.以下两句均出自《谢朓庚信诗选》.、“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以及“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等,和谢灵运的诗句一样成为展现江南山水之美的源始性文本,对后人吟咏江南山水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李白的“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②参见: 李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C]//瞿蜕国, 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520.以下所引李白的诗均出自《李白集校注》, 不再一一作注.、王安石的“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5]以及清代王士祯的“余霞散绮澄江练,满眼青山小谢诗”[6]等诗句都是小谢的诗的余韵。
就魏晋时期那些才华横溢的文士会心林水的整体行为而言,并不仅仅是在追求一种另类的生活,实际上,那也是他们探索人生价值和人的归宿等问题的方式,因而其山水审美行为中的终极关怀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正如玄学家孙绰所表白的那样:“然图像之兴,岂虚也哉?非夫遗世玩道,绝粒茹芝者,乌能轻举而宅之?”[7]286这里的“图像”指的是山水画,在孙绰看来,逍遥于自然山水和山水艺术都是为了“玩道”。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文士们以践行山水、与山水同体为荣,并在理论上极力把山水审美与圣人、神明和大道向一处说:“嗟台岳之所奇挺,实神明之所扶持。”[7]286“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萁、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者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乐乎?”[7]391
既然圣人必有大山之游,那么以圣贤为榜样的文人当然也要尽力效仿,于山水之游中去妙悟宇宙大道和人生哲理。魏晋时期山水审美启蒙的发动,从表面上看是当时士人兴趣和爱好的转移,实际上却带有很多形而上的色彩。当时不少文人看清了功名的虚伪性、权势的腐败性、修身齐家的庸俗性和治国平天下的残酷性,发现了个体自由的真实性、心灵安逸的纯洁性和恬淡快乐的高尚性,“人生贵得适意尔”成为当时文士的普遍心理。人生观的转变使他们将注意力由世俗生活转向了山水自然。晋人张翰说:“我辈本山林间人!”这简单的言语反映了晋人把山水价值与人生价值对等,而最终又使人生价值归属于山水审美价值的倾向。这比谢灵运对待自然山水的态度更为鲜明,因此,魏晋时期的山水审美启蒙是建立在当时文士终极关怀移位的基础上的。
三
经过魏晋山水审美启蒙的洗礼,唐宋文人开始更加自觉地关注和探索自然山水之美。如唐代山水画的奠基人王维在论及山水画的创作时指出,“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8]在王维看来,大自然中蕴藏着无限的美等着人们去发现,大自然既是美的创造者,又是人类审美实践的引导者,它向人类显现艺术创造的规则和方法,并指明艺术创造的方向。对于江南山水,唐宋文人带着一种朝圣般的心情,不怕千里万里的辛劳,以求一睹其风采。“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③参见: 孟浩然.济江问同舟人[C]//赵桂藩.孟浩然集注.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1: 265.以下两句均出自《孟浩然集注》.“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孟浩然进入越中之前对越中山水向往之至,来到越中以后,这里的景致也没有让他失望,这才有了“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样的经典之作。对于唐宋文人来说,发现和展现自然山水之美仍然是一个神圣而崇高的使命。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与提高,这种发展与提高对自然环境的反作用是巨大的,最明显的表现是山水自然的人化程度空前提高,在人的心理上获得了一种“准主体”地位。从山水审美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的人们在探寻自然本身之美时,还倾向于与山水自然的对话与交流。如李白笔下的敬亭山就像诗人的一位老朋友一样,在蓝天、白云和飞鸟的陪伴下与诗人娓娓交谈。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中小丘“清泠之状与目谋,漕漕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9],人与山水实现了全方位的交流与沟通。唐传奇《柳毅传》中,钱塘江和洞庭湖分别被人格化为钱塘君和洞庭君,他们是兄弟,有老婆孩子和人间的是非恩怨,甚至他们的女儿还与落第书生柳毅有了一段爱情姻缘。自然山水不仅被赋予灵魂和情感,而且成为人类须臾不愿分离的亲密朋友。宋代诗人陆游一生写了大量的山水诗,其中写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家乡越中山水。陆游笔下的越中山水无论是跃然目前还是浑然梦中,无论是风清月明还是细雨霏霏,都给人亲切而温暖的感觉,如“菱歌嫋嫋遥相答,烟树昏昏淡欲无”①参见: 陆游.小雨泛镜湖[C]//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366.以下所引陆游的诗均出自《剑南诗稿校注》, 不再一一作注.和“最是扁舟暮归处,一川风月远相迎”等诗句。诗人对越中山水的细腻体味通过这些诗句从心坎中涓涓流出,句句婉丽多情。在晚年回到故乡以后,陆游更是以大量的山水诗来歌咏与这个老伙伴共同的生活历程,“射的山前云几片,一秋不散伴鱼翁”,这使得诗人感到那生活的恬淡与宁静仿佛全是越中山水的赠与,因此与家乡山水长相伴守或许才是最可靠的幸福,“吾生清绝烦君看,不枉人间梦一回。”在一生的记忆中,诗人感到最亮丽的瞬间便是在那世外桃源般的环境里,自己的身心与山水瞑合之际,“一首清诗记今昔,细云新月耿黄昏。”在陆游的山水诗中,越中山水不是一个对象,而是自己的家园,是从玩童时代起就结下浓厚友谊的亲密的伴侣和知音。总的来看,山水审美在唐宋时代所形成的这种历史性转折,正如邵宁宁所说的那样“人长高了,山变矮了,天地的辽阔中也渗入了更多的人间趣味。”[10]
山水的宜人程度仍然决定着人们的审美感受和态度,这可以从文人描绘江南与塞北时的情绪色彩中明显地反映出来。当写到江南山水时,诗人们多表现出一种幸福与满足,如李白的诗句“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和“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李白笔下的江南如同现实中的江南一样让人感到温暖、自在和自由,而当他写到塞北风光时,则多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式的苦寒气。江南山水给人的也并不全是幸福与满足,它也引人伤感和忧愁,但那多是温柔和甜蜜中的忧愁,是那种在南朝民歌中无处不在的因美而生的忧思。一般情况下,人们生存压力很大时多用心于眼前生计,很难再有精力去关注普遍价值和终极归宿等问题;而人们在生活安定幸福的时侯,往往自然地产生那种对个体生命和利益之外的问题的兴趣。正因为如此,很多诗人,一到江南,便会在对普遍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思考中产生一种“幸福之痛”。李白的《采莲曲》、《子夜吴歌•夏》等作品,多是在叙写欢快、明朗和自由的过程中把人带入一种温柔的忧郁与隐痛之中。将人类的“幸福之痛”写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张若虚,在他的《春江花月夜》中,春、江、花、月、夜,这些人世间最生动的美景,带给诗人的不是无忧无虑,而是这样一种感受:“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11]人的“幸福之痛”是由人的思维的形而上的本质决定的,越是在这种“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和“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的仙境中,人的思维越是可能深入到诸如自然的目的、宇宙的本源和人生的价值等永恒的问题之中。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唐代开始,山水审美与人的生活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联系,艺术家们往往在展现山水与人的生活世界的审美关系的基础上,展开形而上的存在之思,终极关怀与审美启蒙在唐宋诗人那里实现了水乳交融般的结合。
四
明定以后,知识分子对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非常珍惜,它们渴望能在有生之年充分享受一下自由与宁静的生活。于是,一场摹仿谢灵运放浪山水、探逐幽胜的新的山水审美启蒙拉开了序幕。“去从千叶隐,归爱一花迎。吴歌并子夜,谁似櫂歌声?”[12]以及“荷叶高低笼水碧,叶下花红沾露湿”[13]都是在明代和平时期文人士子们以宁静的心灵、欣赏的眼光和享乐的态度与江南山水神交的成果,诗中透露的意趣和传达的神韵是魏晋以来山水诗中最稳定、最基本的美学要素,不管是藉山水吊古还是进行政治评说,均表现出这样的美学特征。如刘基的《晚泊海宁州舟中作》、《过苏州九首》等诗,以本色素朴的语言把对历史兴亡的感慨和对人心不定、人事变幻的讽喻与山水的自然特征相结合,使自然山水给人富于时代特色和历史沧桑的美感。
山水审美启蒙往往和个性解放互为表里,明万历以后的情况更证实了这一点。由于朝廷失去号召力,万历以后的文人开始更热烈地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到江湖山水中去寻求生活的乐趣。袁宏道说:“宁作西湖奴,不作吴宫主。死亦当埋兹,粉香渍丘土。”①参见: 袁宏道.湖上别[C]//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409.以下所引袁宏道的作品均出自《袁宏道集笺校》, 不再一一作注.虽然在庄子的时代就喊出了到山林中去的口号,但是像袁宏道这样如此尖锐地把朝廷与江湖对立,认为江湖远远好于朝廷,而且他的这一看法在众多文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赋予山水江湖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不是诗人们一时的兴起,而是文人们经过长期反思人生和社会政治以后的一次集体性彻悟。袁宏道说:“十载青山约,今番始赴期。如云投旧岭,似鸟念高枝。”罗孚尹云:“对大江而饭,胃气达目,眼山川则腹溪谷,饭比常加倍。古人以乐侑食,能有此江光、石韵、松声、竹响耶!”[14]袁中道说:“生平有山水癖,梦魂常在吴越间。”[15]江南山水成为晚明文人最钟情的地方,一些文人甚至耽游成癖,以山水为家,如“东南之久客如家,吴越之一游忘返。”[16]可以说,明中后期的这次“青山之约”既是明代知识分子的一次伟大践约行动,也是我们民族山水情怀的一次集体性表达。
晚明文人在广泛的山水审美实践基础上,概括出了一些山水审美的经验性标准,如袁宏道认为,“凡山深僻者多荒凉,峭削者鲜迂曲,貌古则鲜妍不足,骨大则玲珑绝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关于西湖的美,袁宏道提出:“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认为西湖春天的朝烟、夕岚最具风情。这是对江南山水审美实践的一次重要总结,但是这种总结也存在着把江南山水之美类型化进而损害其自然魅力的危险。总的来看,通过明中后期的山水审美启蒙,一个山水审美大众化的时代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悄然到来。
宋明两代晚期,都经历了一次由国力衰微而带来的严峻的民族危机,在这样的时刻,山河大地成为民族生命的象征,人们对于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和思考往往表现为一种山水关怀。一部分消极文人带着绝望的情绪浪迹江湖,纵情山水,但他们又不像魏晋时代的人那样把隐居山林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而是把一片松阴、一棹春水看得和人生一样虚幻,和民族命运那样飘摇不定。在江南的风花雪月与歌舞美色间销魂,成为一群身和心都无家可归的游子的选择。也有不少文士在民族危亡之际持积极的态度,纷起结社,评说政治,鞭挞丑类,砥砺气节,于山水中寻求民族的血气和力量,如王夫之在谈到荆楚山水时称其“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鲞嵌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拚抑。”[17]山是骨,水是血,江湖山水乃自己的命脉所系,朝廷腐败,但他们相信灵秀的江南山水一定能给予他们胜利的信心并孕育出挽救民族危亡的圣贤豪杰。明末抗清英雄陈子龙云:“禹陵风雨思王会,越国山川出霸才。依旧谢公携妓处,红泉碧树待人来。”[18]清初节烈诗人吕留良亦云:“缥缈金鳌春信远,凄凉白马午潮迴。半死心火疑消歇,到此方知心不灰。”[19]朝代更替的血雨腥风使人们在江南的空濛山色、潋滟水光、温软花香和轻盈鸟语中看到了钱塘大潮的力量以及它所承载的民族希望。
晚清是整个封建时代最黑暗的时期,清朝的灭亡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王朝更替,而是意味着整个封建时代的结束,这黎明前的黑暗最容易让人心灵迷茫,信心消歇,但也最能激发起人们改革的激情,这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人们何去何从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自然环境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在江南度过自己童年时代的龚自珍,改革的困难与失败使他产生了归隐太湖的念头,但是当他面对太湖时,却热血沸腾,作出了以下诗句:“湖山旷劫三吴地,何日重生此霸才……江天如墨我飞还,折梅不畏蛟龙夺。”[20]可以看出,他的改革的信心反而更坚定了,意志更坚强了。与此同时,面对“大浪如山拥月至”[21]的浩瀚太湖,魏源也生出了“我辈未必非仙才”[22]的自信。这些最具未来眼光和改革精神的时代精英们,在祖国山河之美的感召下,摆脱了沉沦,选择了奋起。在晚清的山水诗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明末民族主义精神的复苏,诗人们在希望与失望、救世与还山这种矛盾、犹豫、痛苦和彷徨中铸就了山水审美的新诗篇。
五
如果说中国古代山水审美文化形成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那么在当代山水审美文化中却让人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丝丝紧张。在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人的主体性过度张扬,甚至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相信人将是这场对立冲突中的最后胜利者,这种精神在山水审美方面也体现了出来。比如在毛泽东的山水诗中,祖国山河的美丽与壮阔就成为一种显示人之伟大的媒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①参见: 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诗词集.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95.以下两句均出自《毛泽东诗词集》.、“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以及“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等,在这些诗句中,充满了人主宰自然、操纵自然的信心与豪迈,就其作为表现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并激发人民进取心的方式来说,其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这里完全抛弃了古人的“折腰”或“齐物”精神,自然山水因人心大振而显得渺小起来,其审美启蒙价值似乎已经微不足道。
如今的生态环境恶化却是全国乃至全球性的,而且因为现在的污染多是工业化污染和化学污染,具有不可恢复性,所以其危害性与过去时代的生态危害相比,不仅规模上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于是,在审美批判上,艺术家们就以传统山水审美的异化形态,展现他们对生存的极度忧患和对环境改善的绝望。一位诗人写到:“沙枣花的香气和蜜糖 / 已被雨水冲到远方 / 混合着羊粪牛屎和卡车司机的野尿 / 它们将形成下一个绿洲和未来世纪 / 经典的养料。”[23]另一位诗人写到:“他听到空中催促的声响。他看见出血的秋山在死去。事物的马蹄已踏弯了灵魂,而黄昏的斜坡上站满了骨头。”[24]在这类诗中,传统山水诗所具有的美感荡然无存。从表面上看,诗人似乎是有意在挑战传统的诗歌写作,要革除优雅与意境,实际上他们是试图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环境恶化的强烈不满和对人类前途的极度担忧。在绘画方面,一些当代山水画家把浅淡的山水背景与各种物像相组合,以制造“野、怪、乱、黑”①这本是“文革”前批判画家石鲁时给他戴的帽子, 但后来石鲁承认这也正是他自觉的艺术追求.参见: 陈孝信.20世纪水墨艺术问题[C]//周宪.人文艺术.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 142.的感觉效果刺激人的神经,引人深思,并引导人们去追问宇宙间生命与物质的内在关联。以刘子键为代表的“实验性水墨”和以胡又笨为代表的“抽象山水”等,几乎完全是以异化型的终极关怀主题取代了审美启蒙,或者说终极关怀与审美启蒙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不少人对这类山水审美艺术的精神价值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总的特征就是“失魂落魄”,工业化人文环境取代山水自然环境以及多元化价值观取代一元化“和谐”,已经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山水审美远离了当代主流审美文化,或者说在当代审美文化中,山水审美文化已经被严重边缘化,“衰弊”是整个当代山水审美文化发展的趋势。就当今山水审美文化存在的状况而言,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不仅那部分放弃追求传统美感的艺术家让人忧虑,而且那部分试图以当代人的生活视野、胸襟、气度、观察山水的条件和更为先进的绘画技法来托起传统山水审美文化这座琼楼玉宇的艺术家也让人担心。这是因为,由于过度开发和严重污染,山水艺术创造的根基遭到了严重破坏,这可能使他们的创作成为无根之木。翻开中国当代一部部新诗史,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山水诗的位置,这可能和新诗史学家们藐视当代山水诗的心态有关,但是,主要原因应该正如一位年青诗人所写的那样,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即“有一汪清泉,荡净心际尘埃,云朵滑过脸颊,纷繁的思绪在海天飞翔”[25],已经很不容易。
总的来说,优质的山水环境是中国山水审美文化发达的根本。在古代社会,由于完美的山水环境的存在,山水审美文化便得以在审美启蒙与终极关怀两大主题的交融与变奏中推宕展开,富丽堂皇;但是,当今天这个根本受到动摇和极大破坏的时候,山水审美文化的衰落就成为一种必然,其审美启蒙与终极关怀的意义在喧嚣的现代生活面前渐行渐远,我们梦寐以求的艺术化的生存理想也似乎变得遥不可及。
[1]韩婴.韩诗外传: 卷三[C]//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11.
[2]李文初.中国山水文化[M].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133.
[3]刘义庆.世说新语: 言语[C]//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4]王夫之.古诗评选: 卷五[C]//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 第14册.长沙: 岳麓书社, 1996: 733.[5]王安石.桂枝香[C]//王兆鹏, 黄崇浩.王安石集.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6: 141.
[6]王士祯.江上看晚霞[C]//钱仲联.清诗纪事.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522.
[7]孙绰.游天台山赋[C]//叶朗.中国历代美学文库: 魏晋南北朝卷.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8]王维.山水篇[C]//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9.
[9]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C]//柳宗元.柳宗元集: 第29卷.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766.
[10]邵宁宁.山水审美的历史转折[J].文学评论, 2003, (6): 22-28 .
[11]萧涤非.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55.
[12]高启.櫂歌行[C]//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 第14册.长沙: 岳麓书社, 1996: 1160.
[13]胡俨.采莲曲[C]//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 第14册.长沙: 岳麓书社, 1996: 1168.
[14]罗孚尹.箨壁稿[C]//周亮工, 张静庐.结邻集尺牍新钞三集.上海: 上海杂志公司, 1936: 67.
[15]袁中道.游青溪记[C]//袁中道.珂雪斋近集.上海: 上海书店, 1982: 97.
[16]谭友夏.退谷先生墓志铭[C]//田秉锷.谭友夏小品.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6: 195.
[17]王夫之.楚辞通释[C]//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 第14册.长沙: 岳麓书社, 1996: 208.
[18]陈子龙.钱塘东望有感[C]//时志明.山魂水魄.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6: 14.
[19]吕留良.自老砦山步至黄沙坞观潮[C]//时志明.山魂水魄.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6: 170.
[20]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C]//叶朗.中国历代美学文库: 清代卷.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17.
[21]魏源.太湖夜月吟[C]//魏源.魏源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714.
[22]魏源.西洞庭石公山吟[C]//魏源.魏源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716.
[23]北野.天山北麓的一场大雨[C]//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2005年中国诗歌精选.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53.
[24]陈东东.秋歌十五[C]//洪子诚, 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58.
[25]尚琳.我想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地方[C]//谢冕.2002年中国年度最佳大学生作品.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3: 290.
Landscape Aesthetics: Thematic Variation of Enlightenment and Ultimate Concern
WU Hai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China 321004)
The strong nature-based thought of ancient Chinese and excellent landscape environment in China enabled Chinese aesthetic culture of landscape to be fully developed in ancient times, and its process of development had been permeated with blend and variation of the two major themes – ultimate concern and aesthetic enlightenment.
Landscape Aesthetics; Enlightenment; Ultimate Concern; Thematic Variation
I206
A
1674-3555(2010)04-0054-09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4.00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付昌玲)
2010-03-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ZW008)
吴海庆(1965- ),男,河南安阳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