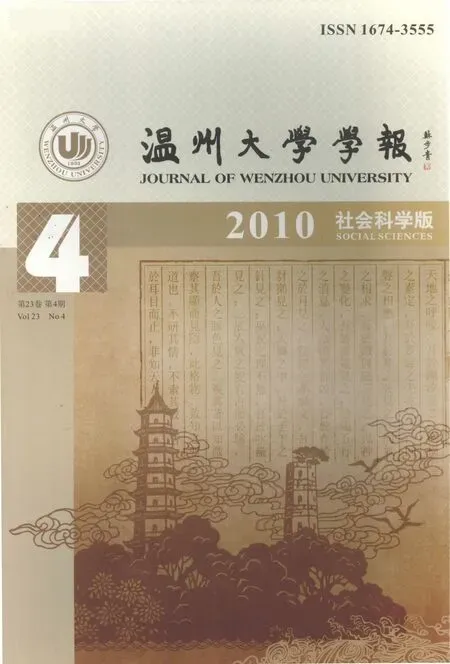主体性阅读与文学想象力及形象创造机制
李咏吟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主体性阅读与文学想象力及形象创造机制
李咏吟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创作者的主体性阅读是自觉自由的生命活动,它是审美想象力激活的重要方式,也是形象创造的前提条件。在阅读过程中,不仅要强调文学经典的主体性阅读,而且要强调思想经典的主体性阅读。只有通过形象与思想的自由综合,文学想象与形象创造才会实现真正的自由。
主体性阅读;想象;形象创造
一、主体性阅读与文学想象力的激活
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刘勰指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这是中国古代美学家对想象力活动所做的精妙描绘,触及了想象力的实质。同样,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也谈到,“因此,在美的艺术中,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理解力、才智和趣味是必不可少的。”[1]康德把想象力置于审美创造能力的首要位置,就是对想象力的高度重视。事实上,《判断力批判》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考察想象力与知性的关系以及想象力与理性的关系,为优美与崇高进行思想立法。应该承认,在诗学史或美学史上,想象力问题得到了充分而深入的讨论。不过,想象力与文学性和思想性阅读的关系,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如果说,想象力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审美主体的审美经验累积的结果,那么,就离不开审美主体的生命体验和思想经验,因此,文学性与思想性阅读就成了丰富和强化想象力的重要途径[2]。
首先,文学性阅读与思想性阅读决定了想象力的广度与深度。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保存了丰富的文学经典,每部经典皆具有个体创造性,自由的文学性阅读就提供了想象力无限自由的想象空间。只有通过文学性阅读,创作主体才能充分吸收人类优秀的艺术传统,特别是民族艺术的优秀文化成果,当然,仅有文学性阅读是不够的。如果说,文学性阅读提供了艺术家想象生活的广度,那么,思想性阅读则深化了艺术家想象生活的深度。思想性阅读有助于生存的深度理解,它不仅具有广阔的思想空间,而且具有确定的价值指向。思想性阅读难免带有主体性价值取向,但丰富的思想性阅读可以克服主体性思想的狭隘性。思想性阅读决定了主体想象力的审美自由指向。艺术形象毕竟具有生活的示范性,这说明很多人其实不理解生活的意义或生活的真谛,其实,我们自己又何尝真正理解了生活的真理,我们总在异化的生活中挣扎,却并没有真正地警醒与自觉。有多少人获得了真正的心灵自由?所以,每个人,皆需要通过文学形象学习生活或通过形象领悟生命存在,这就给艺术创造生命形象提供了无限自由的价值基础[3]。时代的悲剧与存在的悲剧已经使我们惨不忍睹,我们需要新的生命想象方式,美丽的生命想象与自由的生命想象,这些皆出自主体的内心需要,并不是服务于某个特定的政治现实,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展望生活的美好,甚至,我们希望古典英雄主义的复活。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要特别强调思想性阅读的重要性,特别是宗教性与哲学性阅读的重要性,强调形而上之思的重要性,或者说,要把精神哲学的自由探索看作是我们时代的作家最重要的思想任务与思想功课。这无疑是为了强调审美价值反思之重要性,强调生命存在的精神反思的重要性。没有哲学,即没有真正的作家,但是,作家的哲学不同于哲学家的哲学,他们只是在问题上相通,而解决方式完全不一样。想象不只是情节想象、形象想象与生活想象,更重要的是,精神想象与生命自由可能之想象,这是与思想相关的,而与纯粹的感性形象无关,好像许多中国作家并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许多作家很少或从不进行宗教或哲学阅读,这是应该加以更正的现象。
其次,文学性阅读与思想性阅读决定了主体想象力的审美建构或审丑建构冲动。如果说想象力包含审美与审丑双重因素,那么从审美想象意义上说,审丑想象与审美想象同样必要。我们不应在夸大审丑能力时忘记甚至忽视了文学的天赋使命,即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审美想象。人类生活需要更美好的想象,伟大的经典主要靠审美的力量获得自己的生命。生命美丽的想象需要文学性与思想性阅读,当然,生命丑恶的想象也需要文学性与思想性阅读。相对而言,生命丑恶的现实体验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它有时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实记忆,生命美丽的自由想象则不然,它不是生活中自由存在的,它需要想象性与审美性发现。就文学创作而言,面对想象力问题,我们需要改变固有的想法,即现代作家的想象力不应只是体现在对现代性灾难与苦难的想象之上,还应体现在对自由美丽生活的想象与展望上。想象力从不是单一的,我们需要面对黑暗与苦难的想象力,也需要面对自由与光明的想象力。诗人与作家必须是“存在的思想者”,我们必须面对自己的现实存在与历史存在,必须面对他者的历史存在与现实存在。如果充满想象力,我们对这个世界,对生活的幸福,可能有更多的崭新认识,这就给想象力提出了挑战。想象力应该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指向,应该防止极端化,极端现实或极端虚幻皆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多样性,包括丑恶的多样性与美丽的多样性,这样人类的想象力就不会单调,更不会出现审美想象力与思想想象力的匮乏。在我看来,人类的心灵已经日渐残忍无情,人们在面对现实苦难或现实悲剧时已经超级冷静,也就是说,已经具有从容应对苦难与悲剧的能力,甚至默认了苦难与悲剧的合法性,也选择了痛苦而悲壮的承受,但是,我们不能对美好事物失去想象力,想象美好生活应该成为诗人和作家的重要任务。我们皆有历史与现实记忆的能力,我们已经记忆了无穷的苦难,不需要过多地重漫恶梦与苦难,而更需要自由地呼吸,因此,我们需要想象自由与美好,想象优美与崇高,这应该成为越来越多的诗人和作家的生命共识。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乌托邦研究,旨在说明一个问题:人类不能失去希望;特尼森(Michael Theunissen)在品达的抒情诗中发现了什么?那就是“希望、自由与信仰”;残酷与苦难,已经让我们不敢对美丽存有希望,但是,在希腊神话中,潘多拉释放苦难与灾难的瓶子中惟一保留的就是“希望”,这个古老的希腊神话可能就是深刻的时代隐喻,可能就是人类命运的最深刻象征。所以,为了生活与生命的自由,我们还得想象美丽,重温希望。作家的人民性并不意味着“作家能够拯救人民”,作家与诗人做不了这一点,或者说作家与诗人永远成不了人民的救助者,他们只能代替人民歌唱或呼喊,发出人民心中的情感声音。不过,诗人与作家是时代生活或历史生活的敏锐感应者,能够很好地记录现实历史生活并反思历史文化生活。作家的现实主义倾向使得我们的文学具有强烈的历史性记忆,特别是苦难性记忆,但是,许多作家往往迷恋于苦难记忆,而忘记了提醒人民:“苦难的生活,到底是谁之罪”,是谁造成了阿Q的悲剧生活?是谁造成了祥林嫂的悲剧生活?这是我们必须追问的问题。“这是谁之罪?”既然历史有着这样的罪恶,这罪恶是否可以避免,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这样的罪恶?如何从罪恶中救赎?难道罪恶是永远必然的强大力量,永远不可改变?这是诗人与艺术家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4]。为此,就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艺术家不仅要进行自由的文学性阅读而且需要自由地进行思想性阅读。作为审美主体的艺术家并不能直接改变人民的生活,但是,诗人与作家可能通过艺术创造,引导人民思考,引导人民追求,这是诗人与作家的审美想象性任务。我们必须明确诗人与作家所应承担的特殊的历史文化分工,他们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不要把不属于诗人或作家的任务,强加到他们身上。我们的文学幻想,就在于把许多不该文学承担的任务强加给诗人与作家,结果,诗人与作家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而真正的政治家与法学家仿佛失去了自己的应有的责任,这是历史的错置。因此,创作者的自由尊严和天赋,只有在分工明确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想象力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第三,文学性阅读与思想性阅读决定了审美主体想象力的生存探索性。“诗人何为?作家何为?”在我看来,诗人与作家就是探索人类生命存在与生命情感的人。诗人与作家最重大的任务,应该是教导人们如何生活,不只是教导人们如何认识生活,更应是教导人们如何自由、正义和平等地生活,这是艺术的重要使命。许多人以为自己能够自由地生活,不需要人教导,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真正自由的生活或真正美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心灵的启发。是的,现实生活本身是最好的导师,生活本身就教会了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但是,生活所教会我们的更多的是如何现实、世故或无耻地生活,并没有教导我们如何自由、美丽和安宁地生活。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真正的生活,诗人与作家也不一定知道,但是,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去探索,他们在探索中寻找自由与美丽的生活,这种探索就可能给予读者以启示。认识历史现实生活,认识生活的无限性与人性的无限性,认识人类生活方式与生活价值原则的无限性,认识生活悲剧与喜剧的无限性,这是诗人与作家的重要任务;同时,想象生活的自由可能性,想象生活的美丽的可能性,想象生活的爱情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想象一切可能的美丽的自由生活,应该是诗人与作家最重要的任务。当许多电影成为全球观众争相目睹的对象时,我常常想,是什么让人们有如此大的兴趣?从根本上说,还是对陌生生活的好奇,也是对自由美丽生活的展望,或者说,是对美好生活或罪恶生活的窥视兴趣。自由美丽的生活想象毕竟最能持久;丑恶或罪恶的生活,我们很快就会厌倦。因此,强调想象力的同时,我们在阅读文学的时候,应该特别强调想象美丽生活的能力。从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来看,我们想象丑恶生活的能力或者说还原苦难生活的能力实在是超级强大,诚然,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人们不能生活在幻想或欺骗之中。但是,我们同样需要想象美丽生活的能力;如果我们失去了想象美丽生活的能力,那么,我们只会感到压抑与痛苦。什么时候,我们的诗人与作家才能自由地歌唱?在重新理解文学想象力中,我特别强调想象美丽生活的能力的复活,只有如此,人类才有生活下去的希望。我们的生活已经被不美丽的生活所控制,如此喧哗的车市,如此恐怖的大都市,如此忙碌紧张的人群,难道这就是生活的真理?不仅是我们,世界也需要想象美丽的生活。汽车正在毁灭整个世界,但是,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我们可能更多地想象汽车给我们带来的享受与自由,然而,空气污染,能源危机,世界战争,皆与之相关,这就需要诗人与作家想象:“美丽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乌托邦,这是幻想,那么,我们的回答是:艺术本来就应该有幻想,谁说艺术只能表现丑恶的现实?布洛赫在讨论乌托邦时,还特别建立了自己的“希望哲学”,这也是想象力,思想性想象力,是对人们美好生活的展望,也是为了建立自由生活的信念[5]。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正因为缺乏自由的想象力,我们才过分迷信现实法则的强大力量,才屈从于现实生活法则并异化地生活,以现实生活法则作为幸福原则与生命惟一性原则,缺少生命的超越性精神信念。
二、经典重读与想象力自由的价值确证
作为创作者的审美主体,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文学性阅读或思想性阅读,那么,为何还要再三强调呢?在我看来,阅读不可能是完全独立的,在习惯性思想指导下,对文学传统的文学性阅读和思想性阅读,可能无助于想象力的自由发挥。相反,在新思想意念下,在开放的思想意念下,面对文学传统的文学性与思想性阅读,将会极大地激活想象力。单一地从时间和空间上认识想象,我们会把想象力看作是事物形象的记忆与回想,这样,可能就把想象力看作是纯粹图像的,其实,想象力本身就是对生活本身的无限可能性之理解,生活的深刻性就在于生活的复杂性与精神的复杂性;许多作家出于惯性,还是过于偏爱文学形象的想象,却不重视思想或精神生活可能性的想象。但是,回顾我们的文学,应该看到,中国文学从来不缺乏形象想象力,而且具有极为丰富的形象想象力传统,但是,我们的文学在思想创造力上显得非常薄弱,也就是说,我们对精神生活世界的复杂性的想象与理解的大门,还没有真正打开,或者说,那样伟大的中国文学精神想象传统,一直处于遮蔽状态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世界性或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中国文学的想象力绝对是伟大的,特别是在形象与情感想象方面。《诗经》中对神圣的想象是伟大的,例如,对谷神后稷的想象;《周易》对宇宙生命世界与人类生活世界的想象,乃旷古奇观;《道德经》这部伟大的哲学诗,对谷神与阴柔的想象,对圣人的想象以及对道的想象,达到了神妙的高度;屈原对日神的想象,陶渊明对栖居的想象,张若虚对春江花月夜的想象,李白对梦游天姥的想象,苏东坡对明月相思的想象,吴承恩对孙悟空的想象,曹雪芹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凄美想象,鲁迅对绝望的想象,等等,皆达到了形象与精神相统一的高度。中国文学从来就不缺乏第一流的文学想象力,但是,现代作家并没有把中国文学的伟大想象传统当回事,这就是对思想的轻忽。中国文学的伟大想象传统,绝对是深刻的思想与形象创造传统,而不只是文学的时间与空间处理问题,更不是情节的处理问题,与这种思想性想象传统相关的,那就是对空间与生命传奇的想象,在这方面,中国有惊世骇俗的传统。另外,现代主义文学的新变,使我们在中国人的苦难与悲剧想象上,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那真正是恐怖的生命酷刑,绝对的非人道。那么,现代以来的许多文学作品,为何显示出“思想的贫弱”,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我们的作家把形象想象与思想想象分离开来,把生活想象与生命自由想象分离开来。想象不是在自己那可怜的生活经验上的神经反映式呻吟,想象更应是对自由生命存在的复杂性的伟大展望。生命想象,或者说,伟大的生命想象,是大作家的标志;弱小的生命,如果仅仅显示同情与悲悯的意义,是无法引起深刻的思想与形象震撼的。伟大的生命形象,不是身躯的高大,而是灵魂与意志的伟大。
中国文学具有自己的伟大想象传统,但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这就需要作家与艺术家“重视民族文学的经典阅读”。诗人与作家,其实,就是最好的文学接受者或文学批评者,他们以其文学的天赋敏锐可以直接领悟到民族艺术的真正伟大。诗人与作家的文学经典阅读,必须是发现性的,也就是说,无论人们对经典已经进行了怎样的解读,你必须读出自己的理解,这非常关键。我们的文学阅读往往有自己的选择:一是时尚性选择,有影响力的作家以其自己的阅读行为影响了别的作家或时代的青年读者。例如,阅读米兰·昆德拉的作品,阅读《大师与玛格丽特》,阅读《日瓦戈医生》,虽然并不是每个人真正能够读懂,但是,经典作家所引导的时代文学阅读潮流,决定了你的阅读选择,你不阅读这些作品,你就落后在时代的后面。我们害怕落伍,所以,必然会“迷信式跟读”。但是,真正具有独立思想意志的作家是不应受此影响的,他必须在广泛的阅读中作出自己的选择,那些自称从不阅读文学经典作品的作家,甚至当人们指正其作品可能借鉴了某一经典作品时,有些作家那种坦然的回答,“我从没有读过《老人与海》之类”,在我看来,这是极其愚蠢的宣言,事实上,这也可能是极具通俗影响力的作家对自己的偶然成功的“故意炫耀”。当批评家指出某位作家的作品相似于某个经典作品时,有的作家可能会说,“我根本没有阅读那个作品”,其实,这并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作家自身的浅薄无知。在我们的时代,作家不可能赤身裸体地创造,或者像原始人一样单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而不在乎历史与时代。这不是那个蛮荒时代,诗人或作家也必须学习,必须通过阅读文学经典,与作家或诗人进行主体间性的思想交流,通过交流获得自己的创作独创性,那种闭门造车式的独创只能是时代的笑话。当然,这并不是说诗人或艺术家必须读完全部的经典艺术作品,不是的,我们只是说,诗人或作家必须以自己的文学敏锐或文学发现力,从文学史上找到真正的知音作家的作品,与他们的作品一道沉思遐想,反省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想象,找到自己的思想与艺术独创性。
诗人与作家,皆需要有自己的“选择性阅读”,文学青年只会跟随在作家之后寻找道路,真正的文学作家必须自己选择与寻找道路。文学想象力,自然与文学阅读有关,只有在文学的阅读中,我们的创作才会感觉到与文学的真正亲近,许多作家正是在文学阅读中发现了自己的“敌人”,找到了自己的“战友”或“导师”。诗人和作家,在文学阅读中,可以从自己的审美体验出发为自己喜欢的作家或作品正名,当然,这直接涉及如何看待经典作家作品的问题。时代的文学接受,可能误认或错认天才的作家,例如,洛阳纸贵的作品,许多其实是伪劣作品。我们的时代曾经喧嚣一时的作品,今天,已经无从寻觅其踪迹。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诞生的作品,人们的眼光或判断力往往容易受到蒙蔽,不过,经验总是有效地帮助人们,我们不能只欣赏这样的作品,所以,人们很快就会觉醒,厌恶地从这样的作品身边转身。当余秋雨的散文不可一世时,即使是鲁迅也只能哀叹;在易中天和于丹如日中天时,熊十力只能委曲退缩到边缘。这不会长久,虽然永远是通俗的东西操纵大众,但是,也必须承认,永远是美好的经典引导大众。从长时段来说,还是经典作家作品具有永远的诱惑,一个时代能够留下的作品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时代的文学就有属于它的时代读者。真正的诗人与作家,应该超越这种简单的虚名与实利,诗人与作家不是为了创造财富而诞生的;经典作家与经典诗人所获得的一切,已经足够他们自由生活了,不能期待太多。文学阅读的发现性眼光极其重要。我们只能不断地领略美并沉浸在美丽之中,诗人与作家皆应是自由奔放的“世界公民”,心中要有世界,当然,诗人与作家也有自己的民族,他们还必须对民族充满无限热爱,所以,我们要阅读世界一切优秀的经典,也要阅读民族文学的经典。相对而言,如果不懂得文学所属的母语,我们对外国文学的翻译接受会受到许多限制,我们的想象可能是变异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从翻译文学真正理解外国文学,而是说与外国文学毕竟隔了一层。但是,阅读翻译文学极其重要,它能扩充我们的文学想象力,在民族想象力的陷阱中能够突围。不过,我们未必能够真正理解民族文学经典,许多经典已经被文学史的标签破坏了,我们需要重新恢复民族文学经典本来的样子,这就需要直接进入作品。《诗经》与《楚辞》,我们完全可以有不同于文学史的阅读,事实上,在纯粹的《楚辞笔记》中,张炜已经有了自己的发现,当然,它还不能直接转化成想象力,同样,残雪的经典阅读笔记,例如,关于但丁、莎士比亚和卡夫卡的阅读,皆是在自己的成名作完成之后所做的功课,这说明,文学经典阅读是许多作家自我突围寻找新的道路的必要准备工作。不过,张炜和残雪,在大量的文学经典阅读之后,却再也没有创造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一现象也极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作家与诗人,在文学经典阅读中可能倒下,觉得自己既然创造不出许多优秀的作品,不如就此停住,以阅读经典为乐,这是消极的阅读;积极的阅读,在承认经典的优越地位的同时,也激活了自己“不屈的创造力”。那种敢于与经典较量的勇气,可能成就最重要的作家,不过,轻视文学经典或蔑视文学经典,并不会有好的结果,狂妄的经典阅读并不合适,但真正超越文学经典确实十分必要。被动的读者,在经典面前倒下,像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总是匍伏在文学经典面前;诗人与作家,作为主动的阅读者,应该永远勇敢地站立在经典面前,优雅地与经典对话,形成自己的文学超越。人的想象力之所以需要刺激,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与我们的想象往往是蛰伏的,它隐藏在幽深的角落,如果没有光亮,它们可能永远不能发现;文学的经典阅读,经常能够带来经验的强光或生命想象的火种,我们的心灵记忆与想象空间突然被照亮,世界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出现,想象力就必然地被激活了。在我看来,屈原的作品,一定值得重新激活,当然,我们首先要从僵硬的楚辞研究中跳出,因为这些专家大多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什么是屈原真正的价值。在真正的诗人屈原的世界里,我们会领悟艺术的魅力,“谁说屈原是个官迷?”难道不做官,他真的就会寻死觅活,永远悲凄,无以为生?我从来不相信文学史家的这个“前定想象”。作为天才的诗人,难道他真的如此留恋那个佞人充斥的朝廷?诗人就没有在楚国灿烂民间文化面前或伟大的楚国普通百姓面前受到震撼?那些衣衫褴缕的楚国人民,可能就是伟大生命奇迹或伟大生命歌声的创造者!我以为,屈原从朝廷走向民间,才真正找到了他的生命价值所在!屈原投江,难道就没有深刻地同情人民的因素,难道没有对邪恶的宫廷世界的绝望?这一切,皆值得重新理解,历史的人物与历史经典,谁敢有这样的强权:“只能选择惟一的理解”;经典的解释,为何不能向诗人与作家无限开放?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重新理解屈原,重构屈原,我们完全可以重新想象这个伟大诗人的作品,重视想象这个伟大诗人所具有的伟大而神秘的生命精神,这正是我们后来的文学特别缺乏的,或者说,后来的文学过于功利了,失去了对生命最神秘美好的事物的想象[6]。我们更应该重视他的《九歌》与《九章》,而不是那个哀伤的《离骚》。你在《九歌》与《九章》中,难道只看到和听到了哀怨?那是众神降临的时代,生活应该有了别样美丽的想象,像屈原这样重视神话与诗歌的联系,本来就是优美的中国诗歌传统,只可惜,后人被他那古怪的文字吓倒了,或者可以说,我们在“诗言志”的简单宣泄中迷失了方向。我们的新诗人总是远离这样的诗篇,或者,可能出于厌恶文学史的惟一性解释。既然我们不满意,那就自由地创造新的解释,这种新的解释,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我们的想象。中国文学中许多美好的东西,皆被文学史的解释或所谓权威的解释压迫住了,《四书》和《五经》,本可以自由解释,但是,一部朱熹的注疏,压迫了多少自由解释的可能性!诗人与作家是天生的叛逆者,就是不迷从权威的解释,“诗人要创造自己的世代”。鲁迅的小说史解释,受到了外国文学史的启发,他的解读基本上是发现性的,如果没有这种发现性,他的文学想象力就不能够发散出那么多思想的光芒。
作为诗人与作家,我们必须不断地寻找“自己的意中人”,不断地寻找新的文学经典作品,可以进行颠覆性阅读,也可以进行更深刻的生命阅读,就是不要屈从于权威的或古典的解释,这样,我们的文学阅读就会永远有想象力,也永远有发现性。阅读不是惟一的,事实上,许多天才的作家就给人以不读书的印象。拜伦读书吗?好像看不出;惠特曼读书吗?好像不多;顾城读书吗?好像也极少。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总是一直在探索生活,一直在追问生命,这也是积极的文学阅读。显然,喜欢读书的天才作家与诗人好像更多,雪莱对希腊的阅读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荷尔德林对品达的阅读达到极细致的程度,尼采读过的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因为尼采的个人图书馆目录就是一本厚书。天才的诗人作家,有天才的创造力,也有天才的阅读力与天才的文学想象力,其实,只要看看天才作家的早年作品,你就可以发现,他们并不是生来就是天才的,原来,他们也曾经像我们一样青涩与笨拙,但是,天才的作家会有惊人的突破或化蝶之举,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不过,我要指出的是,文学性阅读仅有文学理解本身是不够的,真正的文学性阅读是通过“思想性阅读”而获得巨大突破的,这可能也属于“功夫在诗外”。必须承认,纯文学阅读是我们的误区,许多作家看到哲学或宗教经典就头疼,这说明他们的理解力与心智思考力相当薄弱,因为在一切经典的背后,皆是对活生生的生命的理解与重新理解,文字与语言的障碍根本阻挡不了人们对生命最自由的理解。诗人与作家对思想经典或文学经典的理解应该比哲学家更具穿透力,因为哲学家只是通过语言和逻辑在那里玩弄深邃;失去了概念和逻辑,哲学家会与诗人作家一样,更喜欢赤身祼体。诗人或作家喜欢赤身祼体地走向上帝,上帝欣赏这样的姿态,人更能在这种姿态面前获得生命的激情。不过,我们不能迷恋激情,也需要崇拜理性,因为人类生活从来就不是情感与意志单独可以解决的,它需要理性,理性同时也需要反思与批判,因而,在关注文学性阅读时我更想特别强调,“发现性的文学性阅读需要思想性阅读的支持”,否则,我们的文学阅读就会陷入情节或技术之中,那样的话,“我们的文学阅读就会永远处于迷航状态”。
三、思想性阅读与文学想象力的深度精神建构
思想性阅读,阅读什么,自然要读“经典”,读人类思想史上大量的思想经典。试想,顾城如果不是读过《道德经》和《圣经》等思想经典的话,他后期的诗歌与小说创作就不可能具有那种弥漫的深邃性,这就是思想性阅读的结果。思想性阅读,是否就是借鉴和抄袭思想?不是的,我以为,作家必须进行创造性阅读,不能以“学者性经典阅读”要求作家,那样的话,作家的创造性感悟力就会受到极大伤害。思想性阅读就是回到经典,回到问题本身,回到关注问题的新方式,回到生命根本意义的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哲学史就是反复批判和反复重建形而上学的历史,同时,它也是不断地探索意识活动与存在可能性的历史,还是不断探索理性与意志以及情感与理性之命运的历史。面对思想经典,思索经典的存在论问题或生命意识问题,这就叫思想性阅读,是回到人本身,回到生命本身的阅读。当然,我们也不反对作家或诗人需要故事性阅读与技术性阅读,技术性阅读对于“学徒作家”非常重要。对于成熟的作家来说,惟有思想性阅读才具有意义,如果还是停留在技术性阅读上,作家就失去了思索的方向。思想性想象力,在思想性阅读中可以自由展开,这可以是问题,也可以是命运。为什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只是关于《约伯记》的注解”,果真如此?《约伯记》到底在思考什么?信还是不信?坚信还是功利地信?为得到好处而信还是无条件地信?其实,思想本身或生命存在本身,并没有完全标准的答案,但思想想象本身就能深化人生的理解,这就是思想性想象力的艺术力量与生命能量[7]。可能有的作家会说,我思索人的存在,就是在思索思想性问题,应该承认,天才作家无师自通地可以达到深度思考的精神境地,但是,即使是天才,也无疑受到了宗教或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在青少年时期的实践经验中就奠定了。如果仅从文学的方式思索,就可以触及问题本身,并且提供无限弥漫的思想空间,那就是文学思想的深邃之境。当然,文学性话语经常缺乏内在的思想重量,例如,在纯粹思想探索方面,歌德的论述往往不如席勒系统深刻,这是由于席勒接受了哲学的训练,在哲学想象中锻炼了自己的思想想象力。当然,歌德对形象的思考,特别是对“浮士德”这一形象的思考,是任何伟大哲学家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他的浮士德创作是否受到哲学或宗教的思想性影响?据神学研究者的研究,歌德的神学思想,在德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家要进行思想性阅读,但不是机械被动的阅读,也不是无条件地向思想家或哲学家投降的阅读,而是向哲学家或神学家提出思想挑战的阅读,这才是真正的思想性阅读所需要的精神。思想性阅读,不可能直接转化成文学的创造力,因为思想与形象的融合是艺术创造的重要工作,没有艺术形象的自由创造能力,思想在艺术中的嵌入就会显得极其生硬,这样,就不是文学创作了,可能变成了学术研究。也就是说,从思想性阅读转向艺术形象的创造是复杂而神秘的过程,是内在的思想与情感体验过程,这需要艺术家的伟大体验与创造。
那么,到底什么是想象力?想象力具有怎样的使命与任务?简单地说,想象力是形象的感知力与创造力,也是对生动而复杂的人类生活世界的建构能力,更是对美好的生活世界与美好的人性生活的创造性的解释能力。从诗学意义上说,想象力是艺术情节虚构与艺术意象建构的能力;从哲学意义上说,想象力是人性与思想的理解与创造能力,是对人类生命的深度发现能力,它不仅要看清人类的历史与现实,还要看到人类的命运与人类的未来。想象力必须是全面的思想与艺术创造能力,既要能想象光明美好的生活,又要能想象黑暗苦难的生活,也要能想象神秘未知的生活世界。作为主体性的思想艺术创造能力,肯定有其个体的传奇性,我们所要关注的,就是如何培育想象力,并且使艺术想象力真正能够承载艺术审美创造的伟大而光荣的思想任务。
那么,对于诗人和作家来说,思想性阅读是否一定只能通过艺术创造来体现?那倒不见得。诗人与作家,可以将思想性阅读的成果转化成艺术创造的内在精神力量,也可以直接以思想的方式写作,也就是说,“谁也不能阻止诗人或作家成为思想家”,或者说,“作家有权以比思想家更具思想原创性的方式写作”。事实上,不少诗人和作家的思想性作品也相当有价值,有时,它可能与经典艺术作品一同给予人们以思想启示。我们当然应该重视艺术家的直接的思想性写作,罗丹、歌德、席勒、雪莱、但丁、海涅、加缪、萨特等人,皆有思想性写作;现代中国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闻一多、郭沫若、茅盾等,他们的思想性写作,也极具影响力。在我看来,诗人或作家最好运用两套笔墨写作,既可以进行思想性写作,也可以进行艺术性创作,这样的话,中国艺术的思想性的深度建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问题在于,许多作家不能或不善于进行思想性写作,甚至以为思想性写作是有悖艺术创作精神的,这是极大的思想误区。在真正的艺术层面上,或者说,在真正的艺术创作完成之后,艺术家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技术,而是在乎技术是否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当艺术与思想天然统一时,艺术家更在乎他的思想的深刻性与形象的完整性或深邃性。当艺术作品获得了无限可以阐释的思想空间时,艺术家就获得了最大成功!思想,惟有思想,才能赋予艺术形象以高贵的灵魂,思想也只有通过艺术才能走入人们的心间,才能获得更为持久的力量。海德格尔有关荷尔德林的思想性解读,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思想经验,当然,他不只是在阅读荷尔德林,也在阅读尼采、里尔克和赫伯斯,或者说,他的一生,皆是在阅读希腊经典以及德国思想经典和诗歌经典中度过的;离开了思想性阅读,就不可能有海德格尔,他那已经出版的一百多卷作品,有许多皆是经典哲学与诗歌阅读的思想记录。在经典阅读中,海德格尔绝对是艺术与思想大师,例如,在《语言与故乡》一文中,他详尽地展示了自己阅读赫伯斯《夏夜》(Der Sommerabend)的心得,细致入微,堪称典范。他由语言与故乡这一问题发端,最后,形成了关于语言和故乡之关系的深刻说明,他说,“语言是诗思的本质力量,由于隐秘,因此,在宽泛意义上说,是源自故乡的恳切赠予,基于此,我所得到的题目‘语言与故乡’就是恰当的、明确的。听起来是家乡的口音,就一定能说家乡的语言,所以,不应泛泛地说:‘语言与故乡’,而应该说:‘语言作为故乡’。”[8]这无疑是极富启发的思想性阅读。
艺术家不是从思想原则出发而创作,但是,艺术家的形象创造确实在于,通过形象提供了无穷可思的艺术空间。“哈姆雷特”到底有什么魔力,让我们可以持久地谈论?这就在于哈姆雷特的形象所包含的复杂而含混的思想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既有性格因素,又有历史因素;既有道德因素,又有自我因素;既有神秘因素,又有现实因素。在生活中,人们所要面对的境遇经常是如此的复杂,这就是艺术的思想力量。当艺术引发不了思想力量时,它可以成为快乐的消费品,但无法成为永恒谈论的艺术经典或思想经典,经典意识或思想深度正是文学批评必须给予维护的。其实,有了思想性阅读,或者有了思想性支撑,艺术家思考人生问题时可能更加敏锐深刻。艺术家本来就是具有思想力的人,但是,有时可能找不到思想的兴奋点,而思想性阅读就可以触发我们的思想兴奋点,调动我们的创作激情,艺术的自由变得具有可能。思想性阅读,必须把我们自己摆进去,我们不能置身于思想的事件之外,人类思想的庄严就在于:我们认真严肃地对待思想性问题本身,我们老在叩问:有没有上帝?需不需要这样的神灵?我们为什么孤独无援?我们在什么地方彷徨?如何找到回家的自由之路?生活的幸福与生命的真理是什么?生命的易消逝性与生命的脆弱如何才能拯救?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意志?理性总想限制我们的意志,情感又总想放纵我们的意志?意志的自由给我们快乐,意志的不自由给我们带来痛苦?如何才能实现意志的自由?这一切问题,需要新的回答。艺术需要情感的自由表达,需要形象的自由建构,也需要思想性阅读作为文学的内在价值支撑,当创造力获得了自己的自由权利,当想象力在文学性阅读与思想性阅读中得到了滋养,此时,我们再回到生命自身,回到存在自身,叩问自由与美丽,叩问丑陋与邪恶,我们肯定能在人生需要光明的地方找到光明,也肯定能在黑暗的前夜对黎明时的日出充满期待,如此,诗人与作家就拥有自己的自由,我们在诗人与作家的自由中就能读到属于生命与未来的启示。我的简单结论是:没有文学性阅读,想象力没有广度,没有思想性阅读,想象力没有深度,一切皆是为了突破个人经验的界限;文学性阅读与思想性阅读,对于作家而言,可能是自我突破或腾越的契机,可能是生命灿烂的自我激活方式,它如同生命的双翼,可以让作家和艺术家自由飞翔,并在思想与想象的深处获得自由!
[1] Kant I.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M].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6: 210.
[2] 默里斯. 海德格尔诗学[M]. 冯尚,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08.
[3] 李咏吟. 审美与道德的本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36.
[4] 李咏吟. 形象叙述学[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15-16.
[5] Bloch E. Das PrinzipHoffnung [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4: 21.
[6] 张炜. 楚辞笔记[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67.
[7] 舍斯托夫. 在约伯的天平上[M]. 董友, 徐荣庆, 刘继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71.
[8] Heidegger M. 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 [M].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 1983: 180.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Reading,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Mechanism of Image Creation
LI Yongyi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310028)
Creator’s subjective reading is a kind of conscious and free life activity.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way of activating aesthetic imagination, but also a prerequisite for image cre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not only should subjective reading of literary classics but also subjective reading of thoughtful classics be emphasized. Only through the free integration of images and thoughts, can true freedom be realized in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image creation.
Subjective Reading; Imagination; Image Creation
I206
A
1674-3555(2010)04-0045-09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4.006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付昌玲)
2010-03-03
李咏吟(1963- ),男,湖北黄冈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