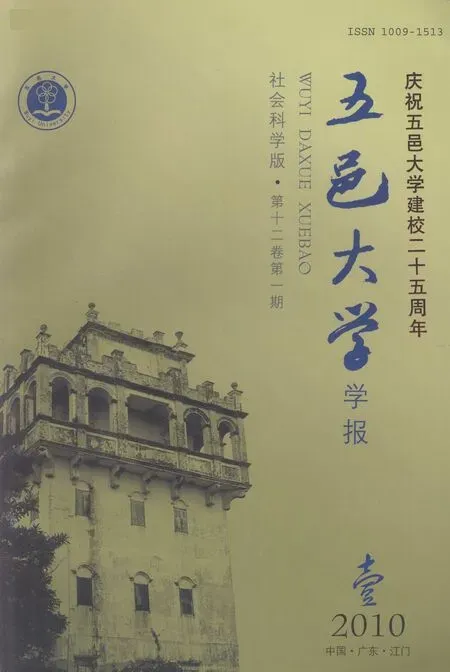“诗比历史更富有哲理”
——论普希金历史文学的“真实”问题
宋德发,刘朝君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诗比历史更富有哲理”
——论普希金历史文学的“真实”问题
宋德发,刘朝君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普希金的历史文学追求“历史的真实”:刻画真实的历史人物,讲述真实的历史事件,追求真实的历史细节,力争对历史现象作出符合历史全局的评判。同时,他的历史文学又遵循文学的逻辑和规律,追求“艺术的真实”,运用必要的虚构来传达一定的历史观。
普希金;历史文学;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
1830年,在《论瓦尔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一文中,普希金指出:“在长篇历史小说里,使我们入迷的便是我们在其中所看到的历史的真实。”[1]181-182“历史的真实”既是普希金的审美理念,也贯穿于他的历史文学创作中。普希金不仅深知“何谓历史的真实”,更懂得怎样传达“历史的真实”。同时作为一个热爱俄国的人,为了给俄国历史正名,反驳恰达耶夫的“俄国无历史”的思想,唤醒民众的历史认同感和自豪感,他更需要在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中再现“历史的真实”。
一、“只对时代和历史人物作广泛的描绘”
1827年,普希金在《致<莫斯科通报>出版人的信》中谈到《鲍里斯·戈都诺夫》时说:“我自愿放弃了为经验所证实、为习惯所确认的艺术体系向我提供的许多好处,力求用对人物和时代的忠实描绘,用历史性格和事件的发展来弥补这个明显的缺点。”[1]161-1651829年,他又说:“我效法莎士比亚,只对时代和历史人物作广泛的描绘,而不追求舞台效果、浪漫主义激情等等……”[1]211-227正因有这样的美学观念,所以当他在1830年11月收到波果津的历史悲剧《玛尔法女市长》后,立即复信表示肯定,称赞该剧做到了“完全真实地再现过去的时代”,对约翰的描绘“符合历史,几乎贯穿始终。在这种描绘中,悲剧家并不比自己的对象逊色。他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展示在我们面前时没有作戏剧性的夸张,没有违情悖理,没有冒充内行”[1]24245。称赞“真实”的历史文学,意味着对“不真实”的历史文学的批评。普希金在读了雷列耶夫的长诗《沃伊纳洛夫斯基》后,指出该诗“用虚构的恐怖去加重历史人物的负担,这种做法既不困难,也不宽厚”[1]211-227。
纵观古今中外被称为历史文学的作品,浪漫主义的也好,现实主义的也罢;尊古写作也好,“失事求似”也罢,其实都在遵循一个底线,即所写的主要人物和时代是真实可靠的。普希金的历史文学也不例外,它们的主角及其活动的年代都有据可考。例如奥列格、伊凡四世、鲍里斯·戈都诺夫、彼得大帝、保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还有农民起义领袖斯杰潘·拉辛和普加乔夫等。至于人物的生活年代,由于史书上都有明确记载,所以,普希金也不可能随意捏造。
普希金喜欢并且善于讲述英雄和帝王的故事,因此,在他的历史文学里,“战争”、“权力”、“国家建设”之类的“宏大叙事”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普希金不只是偏爱英雄帝王的故事,他的诸多“宏大叙事”中,交织着一个“日常生活叙事”。如《上尉的女儿》将家庭纪事、个人遭遇和历史大事融合在一起,通过贵族青年安德烈从军、恋爱和被捕等非常琐细的生活细节来塑造英雄普加乔夫的形象,以至于读者无法确定小说的主题到底是爱情还是国家。小说还通过民女马利亚为丈夫鸣冤的情节来歌颂叶卡捷琳娜二世,其宏大叙事几乎是隐藏不露的。再如《波尔塔瓦》,既是关于国家命运的,也是关于普通女人马利亚个人的爱情和幸福的,从中我们读到了个人是如何意外和无辜地成了巨大而可怕的历史权力游戏的牺牲品。相似的情况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中再次出现。再如在《铜骑士》中,彼得大帝的丰功伟绩和小人物叶甫盖尼微不足道的生活纠缠在一起;在《彼得大帝的黑人》中,彼得大帝的宽厚仁爱也借助于黑人上尉伊勃拉基姆的日常生活来展示。因此,在普希金的历史文学中,历史是由帝王英雄和布衣草民、达官显贵和平头百姓共同谱就的,是由许多声音和许多力量共同组成的。
对于历史文学家来说,当他们面向历史的时候,有时不是想不想写英雄帝王的问题,而是只能写英雄帝王的问题。因为历史文学的取材主要来自史料,史料尽管依据的是事实,但绝不等于事实,它不过是一系列被接受的判断而已。因此很容易知道,“人民群众”虽然参与了历史的创造,甚至被认为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可是在文字的历史中,向来只有英雄帝王的事迹,几乎没有“人民群众”的名字。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卡拉姆津的《俄国史》单写英雄帝王,张扬英雄创造了俄国历史的英雄史观了。
作为《俄国史》最忠实的读者,普希金对英雄帝王的偏爱并不难解释。不过,作为一名伟大的文学家,他在自己的历史文学中,创造了很多史料上没有的“历史小人物”。之所以说是“创造”,是因为普希金又如何知道彼得大帝时代有个叶甫盖尼?普加乔夫时代有个安德烈?叶卡捷琳娜时代有个马利亚?他不知道的可能性远大于知道的可能性,所以,严格意义上说,这些和英雄帝王们直接发生关联的小人物们,尽管有名有姓,有故事有生活,但其实都是虚构的。而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帝王的国家事务之间发生的联系,也是作家通过文学手段“制造”出来的历史故事。不过,我们应该感谢普希金的这些“创造”,一方面,他们的存在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可能和人物自身性格发展的逻辑,也具有“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他们的存在有助于“再现”当时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从这个角度来看,诗不仅比历史更真实,诗也比历史更丰富。可是,既然他们是被“创造”出来的历史人物,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在历史文学中,“历史的真实”其实就是“艺术的真实”,就连彼得大帝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当他们和虚构的小人物们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其形象同样是“艺术的真实”的生动体现。
二、“放下琐屑的和令人可疑的奇闻逸事”
在历史小说《戈留欣诺村史》中,普希金借主人公之口说:“放下琐屑的和令人可疑的奇闻逸事,去描述真实而伟大的事件。这个打算早就激荡着我的想象。做一个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评判者、观察者和预言家,我认为是作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2]如果将《戈留欣诺村史》看作历史文学的话,那倒是一部很独特的历史文学。因为,无论对普希金来说,还是其他历史文学家而言,让帝王英雄完全缺席,以一个真实的普通小村庄的历史作为题材都是难能可贵的。通常的史学著作也没有用专门的篇幅来记述一个村庄的变迁和普通村民的喜怒哀乐。
《戈留欣诺村史》中“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历史文献中是无法寻觅的,但他们同样有历史的依据,这些依据便是普希金自己通过调查后所发现的“一个村庄的历史”。“一个村庄的历史”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的一部分,只不过,人们往往只看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因此,普希金对这段小历史的书写,从一个侧面暗合了新历史主义者的呼吁:恢复历史的丰富性和民间性,让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 ries)取代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此外,《戈留欣诺村史》在叙事上还颇有新历史主义风范,因为传统历史小说的叙述主体总是隐藏于幕后,让历史自行上演,以告诉世人,历史是历史,“我是我”,两者不可混淆。在这部历史小说中,尤其是前半部分,“我”不仅从幕后走向台前,而且作为公开的叙述者和积极的对话者,堂而皇之地穿行于历史档案之中,与之展开交流对话,将“我”与“历史”、“现实”和“过去”融会贯通起来,从而让历史小说散发出生活纪实散文的气息。
普希金的历史文学主要还是取材于“大历史”,因此,其中的历史事件也更为世人所熟知,判断其历史真实性也更加容易、简单。《波尔塔瓦》以1709年俄国和瑞典在波尔塔瓦进行的战争为背景;《上尉的女儿》以1773~1775年的普加乔夫起义为背景;《铜骑士》以1824年的彼得堡洪灾为背景,它在《前言》中还特别声明“这篇故事所描写的事件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洪水泛滥的详情引自当时的报刊。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B·H·别尔赫撰写的报道”[3]。《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情节基本遵循《俄国史》第九章和第十章对“混乱时期”皇位更替的记述,因此,普希金也在题词中写到:“谨以虔诚和感激将本剧献给俄罗斯人所珍贵纪念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本剧系受其天才鼓舞而作。”[4]
为了再现真实的历史事件,历史文学必须追求“典型历史细节”的真实。在谈到欧洲那些瓦尔特·司各特的模仿者们时,普希金揶揄道:“他们自己背着家庭习气、偏见和日常印象的沉重包袱,走进他们想把读者带入其中的那个时代。在插着羽毛的圆形软帽下,您可以认出你们的理发师梳理过的脑袋;从ála HenriⅣ(亨利四世型)的花边褶纹高领里露出了现代dandy(花花公子)的浆得挺硬的领带。哥特式的女主人公受到M adame Campan (康庞夫人)的教育,而16世纪的国家要人却在阅读Tim es(《泰晤士报》)和Journal des débats(《论坛报》)。有多少不合情理的东西、不必要的细节和严重的疏忽!有多少矫揉造作的成分!”[1]32-34在给雷列耶夫的信中,普希金也指出了《奥列格》犯了历史常识错误:“古代的国徽、圣乔治十字章,不可能出现在多神教徒奥列格的盾牌上;崭新的双头鹰是拜占庭的徽章,我们是伊凡三世时期采用的,不是在此前。”[5]显然,普希金对于历史文学中明显的张冠李戴、胡言乱语现象难以忍受。
历史文学所蕴含的“历史的真实”不仅涵括了上述的“写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时代”、“写真实的历史事件”和“追求典型历史细节的真实”,还应该包含着对历史现象作出符合历史的全面评判。普希金对历史人物的态度虽然褒贬不一、抑扬交织,但都基本符合历史大势,很少因为个人偏好而随意评判。如他用“英明”来评价奥列格,这和奥列格在俄罗斯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相对称的:奥列格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基辅大公,他征服基辅的882年通常被认为是基辅罗斯(基辅大公国)的建国之年。再如他对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整体上的赞赏态度,也是与他们在俄罗斯历史上所做的贡献相匹配的:彼得大帝为俄罗斯打开了朝向欧洲的窗户,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俄罗斯打开了通向欧洲的大门。再如他对保罗一世的不屑也对得起保罗一世在历史上拙劣的行为。另外,他对亚历山大一世、鲍里斯·戈都诺夫的爱恨交加与他们在历史上毁誉参半的表现也是相匹配的。
三、“人民的历史是属于诗人的”
1825年2月23日,普希金给诗人尼·伊·格涅吉奇的信中说:“人民的历史是属于诗人的。”[6]这句话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诗人需要承担起书写俄国历史的重担;二是诗人需要用诗人的方式来写历史。诗人的方式便是历史文学。对于史学著作来说,历史就是“前景”,“历史的真实”是它终极的追求。对历史文学来说,历史只是背景,“历史的真实”是它的追求之一,但不是唯一的追求,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追求。历史文学更应该追求“艺术的真实”,从历史文学是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才是它终极的追求。
“历史文学”和“文学”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不是原则性的,而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历史文学归根结底属于文学,它遵循的是文学的逻辑。“历史文学”和“历史”是有联系的,但这种联系远小于两者之间的区别。“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它和“历史”的差异,古人早已经有了精准的论述:“两者的真正差别在于一个叙述了已经发生的事,另一个谈论了可能会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有哲理、更富有严肃性,因为诗意在描述普遍性的事情,而历史则意在记录个别事实。”[7]
这就告诫我们无法苛求历史文学能像历史著作那样,无一事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否则,历史文学就有等同于历史著作的危险,从而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历史文学要遵循艺术真实的逻辑,运用自己的心灵、智慧去提炼和组织混沌、散漫、荒芜的历史素材,从认识、审美角度出发,多层次地对这些历史素材进行加工,然后讲述可能发生的、具有普遍性的事。
比如《鲍里斯·戈都诺夫》,它虽然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但作为文学作品,为了主题表达的需要,它不免要做一些主观上的艺术加工。在历史学中,一直存有两个悬而未决的疑案,一是真皇子季米特里究竟是如何死的?是在做“插刀入地”游戏时偶然丧命的,还是鲍里斯·戈都诺夫派人所杀?二是伪皇子季米特里究竟是何许人?对于前一个问题,卡拉姆津的《俄国史》给出了这样的答案:真皇子死于戈都诺夫之手,可这个答案只是根据民间传说而来,并没有得到证实,实际上也无法去证实了。对于后一个问题,更是无人可以知晓。《鲍里斯·戈都诺夫》根据传说,“安排”真皇子死于鲍里斯·戈都诺夫之手,突出了鲍里斯·戈都诺夫的野心,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从而让善与恶、目的与手段、光明与黑暗、外在的强悍和心灵的脆弱融于一体,增强了人物性格的张力,让悲剧从单纯的道德剧提升为复杂的权欲悲剧。戏剧还将历史学家没有定论的伪皇子确定为在逃的小僧格里果里,并让他借助外力推翻了鲍里斯·戈都诺夫的统治,也旨在传达两点:第一,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凡夫俗子,权欲存于每一个人心中,只等待适合的时机爆发;第二,民众的力量可以左右权力的更替,格里果里能推翻戈都诺夫,靠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外族的势力,更不是死去的真皇子的威望,而是广大的民众。
如果用“历史的真实”原则机械地评判一些属于“艺术的真实”的问题,不免违背了文学的创作逻辑,贻笑大方。如《波尔塔瓦》的批评者们就犯了这种错位评判的错误。在最初评论《波尔塔瓦》的20篇文章中,有一半指责长诗不符合历史,是反历史主义的。在诗中,马里亚克服宗教障碍、双亲诅咒、社会耻笑和年龄差距而爱上马塞帕,批评者们认为这简直不可思议,他们讽刺普希金“任何人从未见过一个女人爱上一个老头,因而马里亚对老盖特曼的爱情是不可能存在的”。对此,普希金在《驳<波尔塔瓦>的批评者们》一文作了正面回答:“我对这种解释是不能满意的:爱情是一种最任性的情欲。且不说每天都有人认为丑陋和愚蠢比青春、智慧和美要好得多。请回忆一下一些神话传说、奥维德的《变形记》、勒达、菲利拉、巴齐法雅、皮格玛利翁吧——请相信,所有这些虚构的故事和诗歌并不是格格不入的。而奥瑟罗,那个用自己的历险和战斗故事来俘虏苔丝狄蒙娜的老黑人呢?还有促使一位意大利诗人写出一部优秀悲剧的密拉呢……”[1]45-48
普希金遵循的是爱情逻辑,而爱情的逻辑就是没有逻辑。年轻的马里亚爱上一个老人和苔斯狄蒙娜爱上黑人奥瑟罗一样,固然难以相信,却又是可以相信的。亚里士多德说:“一件尽管不可能,然而使人可以相信的事,总是优于一件尽管可能,然而使人无法相信的事。”[7]从生活的角度来看,马里亚应该爱上一个年轻人,一个和自己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一个家族可以接纳的人,只有这样才是可能的;但在普希金看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爱情悲剧中,那反倒使人无法相信了。纵观爱情悲剧史,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爱情悲剧中都是可以相信的。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生活中人们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在爱情悲剧中作家们却偏爱于写劳燕分飞。
不管是“历史的真实”,还是“艺术的真实”,作为历史文学中不可分割、也无法分割的两种因素,它们的存在都是为了艺术的整体服务,即传达一定的历史观,以及对现实、未来的态度。①
注释:
①关于普希金历史文学的时代向度问题,可参阅拙文《“请在各方面像祖先那样”——论普希金历史文学的时代向度》。载于《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普希金.论瓦尔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M]//普希金.普希金文集:第7卷.张铁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2]普希金.戈留欣诺村史[C]//普希金.普希金文集:第6卷.迎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68.
[3]普希金.铜骑士[C]//普希金.普希金文集:第3卷.冯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473.
[4]普希金.鲍里斯·戈都诺夫:题词[M]//普希金:普希金文集:第4卷.林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08.
[5]普希金.关于《沉思》[M]//俄罗斯的夜莺:普希金书信选.张铁夫,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92-93.
[6]А.С.Пушкин.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вдесятитомах,том девятый[M]..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ЛИТЕРАТУРЫ,1962:136-138.
[7]亚里士多德.论诗[M]//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崔延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654.
“Poetry Is More Philosophical than History”——On the“Reality”Question in Pushkin’s Histo rical Literature
SONG De-f a&L IU Chao-ju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Pushkin pursued“historical reality”in his historical literature by po rtraying real histo rical figures,narrating real historical events and unveiling authentic histo rical details,and strived to make a judgment of histo rical phenomena in line w ith the overall histo rical picture.A t the same time,he followed the logic and law of literature and pursued the“artistic truth”,using the necessary fiction to exp ress his special histo ry view-points.
Pushkin;histo rical literature;historical reality;artistic reality
I109.4
A
1009-1513(2010)01-0047-04
[责任编辑文 俊]
2009-09-23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因素”(04 YB057)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关于历史题材创作与改编中的重大问题”(04JZD 0035)的阶段性成果。
宋德发(1979-),男,安徽庐江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