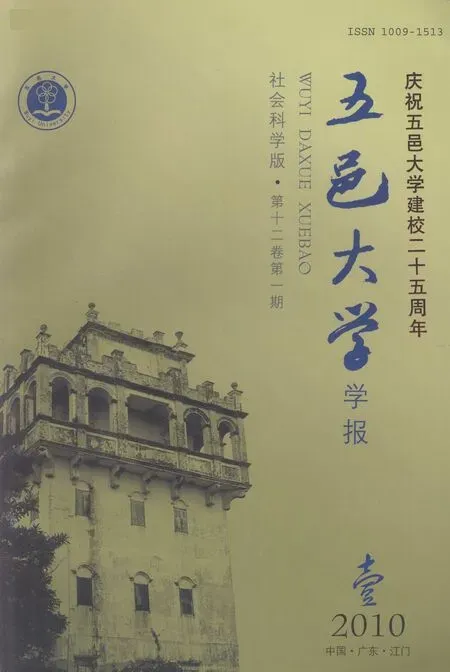“世界去魅”三步曲
闵长虹,周月英
(1.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上海200433;2.海军兵种指挥学院军队政工系,广东广州510430)
“世界去魅”三步曲
闵长虹1,周月英2
(1.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上海200433;2.海军兵种指挥学院军队政工系,广东广州510430)
“世界去魅”是指运用理性把世界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人本取代神本。然而,宗教的退场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以工具理性为尺度的现代“拜物教”继续遮蔽人性的尊严。为“世界去魅”的人类使命远未完成,需要在对工具理性的深度反思中借助实践解放人性。
世界去魅;消除神性;反思理性;解放人性
韦伯将世界理性化的过程称为“世界的祛魅”(Die Entzauberungder Welt),他说:“宗教发展中的这种伟大历史过程——把魔力(magic)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在这里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1]“世界去魅”完成人性对神性的取代,相伴而来的却是工具理性对人性的污染,因此,“去魅”应该沿着消除神性-反思理性-解放人性的历史逻辑展开。
一、“世界去魅”的自然欲望:消除神性
宗教是古代的科学,以全知、全能、全善的彼岸上帝禁锢此岸的人性。经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西方开始了为“世界去魅”的世俗回归运动。“世界去魅”的目标是“消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想象”[2],于是,便有了培根的“四幻象”说、伽利略的“对自然的数学化”[3]、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莱布尼兹的把逻辑“当作形而上学的基础”[4]和康德的“大胆地运用你自己的悟性”[5]。总之,这是“一个无神的、没有预言者的时代。”[6]
在人本主义潮流的推动下,费尔巴哈通过理性地分析人性揭示人之异化的思想根源,阐明上帝的本质就是人自身,呼吁用人本的爱改造人的劣根性。对于人的劣根性,费尔巴哈这样评价:“如果他竟把他自己的局限当作整个类的局限,这就是由于他把自己跟类混同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是跟个体对安逸的爱好、怠惰、虚荣和利己心有着最密切的联系的。”[7]36因此,“人怎样思维、怎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怎样思维和主张;人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上帝就也有这么大的价值,决不会再多一些。”[7]42“上帝正是人自己的、嫉妒其他一切的那种自私心理之自我满足,是利己主义之自我享乐。”[7]60-61尽管人性中潜藏超越的本能,可是“如果我心地不正,理智败坏,那我怎么能够感知神圣的东西,感知善的东西呢?如果我的灵魂在审美方面低劣不堪,那我怎么能够欣赏一张绝美的绘画呢?”[7]61
能拯救自我的只有自我,费尔巴哈把上帝还原为世俗的人本的爱。他说:“神圣的东西,是对我的罪恶的谴责;在这里面,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在其中谴责我自己,我认识到什么是我现在还不是的、但应当是的、从而按照我的规定说本来能够是的。”[7]61“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7]30-31“你的本质达到多远,你的无限的自感也就达到多远,你也就成了这样远的范围内的上帝。”[7]37
与费尔巴哈通过分析“常人”异化的思想根源否定宗教不同,尼采以“超人”的诗性方式宣告“上帝死了”。“啊,我的弟兄们,我以前创造的这个神,乃是人的制造物,人的幻想,像所有的神祈一样。这个神是人,只不过是人和我的可怜的一端。”[8]27“那个希伯来人耶稣……他死得太早;如果他活到我的年纪,他自己可能会收回他的教导!他是太高贵了,要他收回是困难的。可是他还没有成熟。这个青年没有成熟,就去爱,也没有成熟,就去仇恨人和大地。他的心情和精神的翅膀还被捆紧,还很沉重。”[8]79
费尔巴哈阐明上帝的本质是“常人”,呼吁用“常人”的爱相互改造“常人”的劣根性。尼采阐明上帝的本质是“超人”,呼吁用“超人”的权力意志改造“常人”的薄弱意志和由此导致的人性堕落。如果说费尔巴哈“爱的王国”是对理想人性的呼唤,那么尼采崇拜的“超人”之权力意志实质上是对消灭人性自私、软弱、悲观、报复、堕落的精神渴望,是对剔除人的劣根性后的人类完满性、上升性的真诚呼唤。“我爱那样一种人,他肯定未来的人们,拯救过去的人们:因为他甘愿因现在的人们而灭亡。”[8]11
二、“世界去魅”的自由意志:反思理性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彼岸的神性还原为此岸的人性,上帝的统治让位人的世俗主宰。可是人刚从上帝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又陷入计量、算计、可通约的物性桎梏之中,自私自利通行于市民社会,良心、贞洁、德性、爱情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如果说古代的上帝是彼岸的权威(精神之通约),那么现代的上帝则是此岸的权威(物性之通约),前者用“单向度”的绝对精神藐视自由的人性,后者用“单向度”的工具理性蔑视丰富的人性。
西美尔认为,人类意志创造力的表现,即多种客观文化本应丰富人类自身,但实际上却日益脱离了人类自主创造力的控制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异已的外在力量。这就是西美尔所谓的“文化悲剧”[9],即人类已经丧失了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而沦为一种物,成为一种工具而非目的。启蒙并没有错,错误在于把从古代上帝那里解放出来的人性进行物性的处理,让自私自利遮蔽原本丰富的人性;在于追求人本的启蒙理性,不仅没有沿着人性自由的维度发展,反而萎缩为狭隘的“工具理性”,让“单向度的人”沉溺于“可通约”的物质功利算计。
作为理性形而上学的代表,康德认为意志的本质特征是自由,而“自由”是以意志无条件地服从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为前提。叔本华反驳康德:“既然意志是自由的又要为意志立法,说意志应该按法则而欲求:‘应该欲求呀!’这就等于木头的铁!可是根据我们整个的看法,意志不但是自由的,而且甚至是万能的。”[10]373叔本华坚信意志的本质特征是自由,而自由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制约,他讥讽康德:“很可能是以最有理性的方式,就是说,根据科学地推导的结论,斤斤计较掂量;可是却遵循最自私、不公正和甚而邪恶的格律。……‘有理性的’与‘邪恶的’这两个词搭配的很好;确实,重大的,影响极坏的罪行,没有两者的联合,根本不可能。”[11]叔本华对理性形而上学作了彻底批判:“从我全部的基本观点看来,这一切说法都是把实际的关系弄颠倒了。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10]401-402
叔本华以意志(或欲望)形而上学颠覆了理性形而上学的传统,他把生命意志理解为世界的本质,认为生命意志所蕴含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满足这些欲望的环境和资源是有限的,由此引出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尼采批判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生命就是权力意志。”[12]182“‘权力意志’,即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示权力……”[12]154尼采认为,权力意志引导人生奋发向上,因而人生不是悲观的、消极的、被动的,而是乐观的、积极的、自由的。
无论是理性形而上学还是意志形而上学,在谈论理性或意志的自由时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仅仅满足于精神观念的自由,在思想的范围内兜圈子。自由的真谛在于克服现实障碍的社会实践,在于立足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使“社会关系的总和”逐步符合人性的愿望。无疑,马克思达到了这一维度,从而开启了在历史的辩证发展中扬弃不合理现实、颠倒异化的实践视域。
三、“世界去魅”的实践愿望:解放人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意志并不是无条件地自由,而是受制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关系。他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3]31因此不能像康德、叔本华、尼采那样脱离社会历史条件、脱离物质利益和物质生产关系抽象地谈论意志自由,而应该看到现实的人不得不首先把自己的意志投入并消耗在具有生存意义的生产劳动中。
马克思洞察出这一事实:“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深究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13]213意志必须由物质生产关系决定,说明意志并不像康德所想象的那样是完全自由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不得不受制于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结成的物质生产关系。
这种具有谋生意向的劳动不仅不是自觉自愿的,反而具有异化的命运,这一命运在资本社会的雇佣劳动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界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界限。”[14]在劳动必然异化的资本社会,工人的“意志自由”仅仅是为谋生而拼命劳动,资本家的“意志自由”则是无限制地追逐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如果说尼采通过透视个人的心理特征洞察出资本社会的人性堕落,那么马克思则通过剖析资本的诞生史愤怒于人性尊严的全面异化。
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悲观地把资本的趋利意志理解为个体意志的永恒归宿,“正如人类劳动力并非天然是资本一样,生产资料也并非天然是资本。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生产资料才取得这种独特的社会性质……”[15]马克思坚信有尊严的人应该有意志的自由,但意志的自由程度不能不取决于个体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处于“物的依赖性”阶段的一切权力根基于资本的“经济权力”,资本越是积聚和集中,它所拥有的“客观权力”也就越大;到最后,资本的权力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权力,而是渗透到国家的所有领域;它也不再是单纯的地区性权力,而扩张为世界性的权力,呈现出全球化的图景。
无孔不入的资本权力导致劳动的异化,使应然的理想而幸福的生产劳动在此岸难以实现,个人才绝望地、麻木地在各式各样的思想观念中寻求自由,甚至躲进已死去的“上帝”怀抱进行精神上的自慰。如果说,为“世界去魅”的自然欲望揭穿了神话的欺骗,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让理性取代神性、人本取代神本,为“世界去魅”的自由意志开启反思工具理性的闸门,揭露资本社会自私自利、物性泛滥的人性实然,那么,要创造人性的应然,就必须通过人类解放铲除发酵物性的资本土壤,依靠实践改造资本原则主导下惟利是图的工具理性,让生命意志的自由在人类解放中得以实现。
[1]M.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79.
[2]M.霍克海默,T.W.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
[3]E.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7.
[4]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6:119.
[5]康德.什么是启蒙?[J].哲学译丛,1991(4):3.
[6]M.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9.
[7]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8]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9]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72.
[10]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M].任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72.
[12]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M].张念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294-295.
[15]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45.
Trilogy of“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M IN Chang-hong1&ZHOU Yue-ying2
(1.Fudan Univ.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433,China;
2.Political Work Department of the Navy A rm s Command Academy,Guangzhou 510430,China)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means eliminating divinity from the world by means of reason and rep lacing gods w ith humans.However,the w ithdrawalof religion has not resulted in the real liberation of humans;modern fetishism based 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cts as modern religion,blotting out human dignity and supp ressing human freedom.“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being far from being comp leted,we need to liberate humanity bemeansof p ractice in the in-depth reflec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 rld;elimination of divinity;rational reflection;liberation of humanity
K02
A
1009-1513(2010)01-0023-03
[责任编辑朱 涛]
2009-09-23
闵长虹(1972-),男,安徽霍邱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