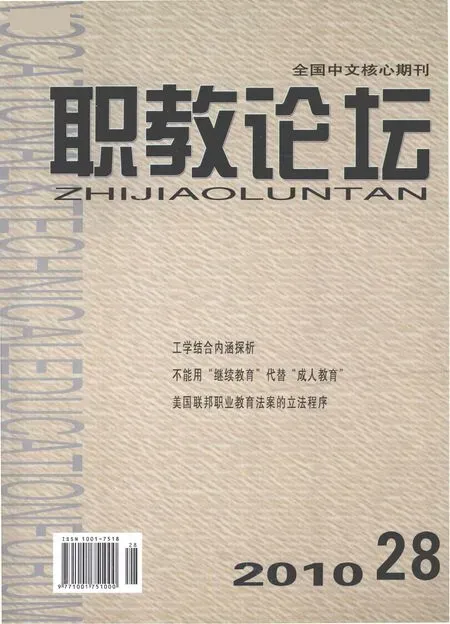简论民国时期劳工教育的经验与问题
李 忠
劳工是以出卖体力和技术获得工钱谋生的人,劳工问题是通过提高劳工的生产技能水平、增加企业的生产效能进而改善劳工受雇佣情形的问题。民国时期,中国劳工问题渐成一社会重大问题,“中国劳工问题之解决,在目前已不容忽视”。[1]解决劳工问题有诸多方案,如改良工作条件、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实施科学管理法等等。但是,劳工教育被当作解决劳工问题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手段。“我们要工人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要切实实行劳工教育,尤其是劳工保险、合作等事业的设施,实有赖于劳工教育为之先驱。于是劳工教育遂成为劳工事业之中心,因之劳工教育的声浪日高,劳工教育的潮流日盛,渐成为重大的问题。”[2]劳工教育在民国时期受到高度重视,不仅出台了系列的劳工教育法律、法令,而且组建了劳工教育管理部门,劳工教育在全国普遍展开,并获得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劳工教育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最终导致劳工教育走向反面而陷于失败。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积淀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为今日农民工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然而,有关劳工教育的研究成果在目前尚属空白,本文抛砖引玉,并期望能对今日的农民工教育与企业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些许助益。
一、时人对劳工教育的认识与提倡
民国时期的学者认为,劳工教育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首先,教育是人从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的基本途径,接受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有教无类”是对这种权利的体认。然而,由于社会等级和贫富悬殊,致使一部分人的教育权被剥夺,劳工就是教育权被剥夺的一个社会阶层。所以,劳工教育问题首先就是对教育权利的追问。骆传华指出:“教育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占有和独享,而是大多数人民的权利,不能以少数人的趋向为去就,应以全民众的需要为依归。今后的教育方针,是应当采用平民化、生活化和职业化,把以前只务虚名不重实际的观念,不顾多数民众的利益,只求少数特权阶级的便利的思想打破,然后中国的教育庶几有望。”[3]劳工教育问题就是要打破这种特权,使劳工获得受教育权利的问题。
劳工教育还是经济问题。作为经济问题,劳工教育的作用体现在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依赖上。生产经营活动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教育是传授科学技术知识的主要方式,“举凡各种事业之发达与进步,莫不与工人之知识有关。故增加工人之知识,实为使产业原料之不至浪费,工作时间的节省,生产能力藉以锐进等等之最大原因之一。由此观之,在我国现今推广职工教育,实为刻不容缓之内容。”[2]劳工教育成为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改善劳动者素质结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劳工教育也是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输入,致使延续两千多年到以手工业、小商业为基础的产业组织逐渐崩溃,新的生产方式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资本家期望企业发达与利益增加,祈盼劳动者能量发挥到极大而付给薪水最低;劳动者方面,则期望生活充裕、家族安全,对于雇主的待遇,莫不要求较好之改善、较高之改进。劳资双方所处地位不同、目的不同、拥有资源和享有权力也不同,出现劳资矛盾。资方以解雇、开除、减工、减薪等作为手段,劳方则以怠工、罢工、破坏生产等作为应对措施,由此酿成工潮。所以,劳工问题的存在,足以妨碍国民经济的进展,增加国家社会的不安定。解决劳工问题的办法很多,如改良工作条件,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倡科学管理法等。但是,“最彻底的办法,还是在实施劳工教育。”时论指出,劳工教育缘起于三大端:(一)工人知识薄弱,生产效率低;(二)工人每为资本家所轻视,苦乐悬殊,若欲提高其地位,非先由教育入手为功;(三)以人类平等为原则,故工人应享教育均等之机会。[3]所以,劳工教育不仅是劳工教育权力的获得,而且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与和谐不可或缺的内容。
劳工教育旨在对劳工实施一定程度和性质的教育,提升其能力、价值与人格尊严,提高工厂企业的效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改善劳工的被雇佣情形。劳工教育就是以教育为手段、以经济发展为中介、以个人幸福与社会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教育。劳工教育的目标不仅在于糊口,还在于为谋享受比糊口更有意义的生活。时论指出:“提高民族意识,须有健全的国民,发展生产事业,须有健全的生产劳工,中国劳工教育应以此为中心,中国整个教育精神亦在于此。”[4]所以,劳工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将劳工培养成为人,具备共和国国民基本素质,成为健全的国民。时任交通次长的郑洪年指出:“劳工问题应宜从根本上主张教育主义,其意图不仅在铁路职工应以相当之教育,即对于全国劳工亦冀以教育之方法加以陶冶,使成为健全之国民,并希望世界劳动程度幼稚之各国,咸以劳工教育为培植劳工生活之基础。”[5]劳工教育的目的还在于使劳工具备承担国民义务的素质,即具有熟练的技术、有建设能力;养成劳工领袖人才,能够代表劳工为劳工谋求利益,实现工人的解放。“工人教育的目的还在于养成劳工领袖人才、修养劳工高尚人格,造成健全的革命工人以期实现世界劳动化。”[6]时人对劳工教育的认识与提倡,使得劳工教育思潮得以形成。
二、劳工教育的普遍展开
民国时期劳工教育的实践经历了从自发到强制实施两个阶段。自发阶段的劳工教育出于劳工的教育需求和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包括学徒教育期和劳工教育孕育期;强制阶段则体现出政府对劳工教育的安排,包括劳工教育试验期和推广期。早在1915年,铁路交通部门为谋工人知识技术的提高,即在各路段设有工人补习学校十七所,招收学生3700余人;1921年成立“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积极开展铁路系统的劳工教育,并编辑出版《铁路职工教育旬刊》,以示研究、宣传和提倡。南京国民政府建成后,劳工教育受到高度关注,劳工教育开始向法制化方向转化,在政府的参与下,劳工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首先,劳工教育受到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劳工教育走向法制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台了系列的劳工教育法律、法令,并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工教育管理部门。以1927年8月7日公布的《国民政府劳工局组织法》为开端,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出台了包括 《工人教育计划纲要》、《工厂法》、《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等在内的数十个相关法律、法令,地方政府出台了具体的实施细则,由此形成劳工教育法律体系。同时,依据相关法律组建了包括劳工局、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劳工教育实施委员会在内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工教育管理机构,不仅为劳工教育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为劳工教育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次,企业被指定为劳工教育实施主体,实施劳工教育成为企业的法定责任。《工厂法》规定:工厂须使劳工受补习教育,违者处以百元以下罚金。《修正工厂法》对此作出进一步规定:工厂对于童工及学徒应使受补习教育,并负担起费用之全部;其补习教育之时间,每星期至少须有十小时;对于其他失学工人,亦当酌量补助其教育;工厂所招学徒人数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的三分之一;当工厂所收学徒过度,对于学徒之传授无充分之机会时,主管官署得令其减少学徒之一部,并限定其以后招收学徒之最高额;工厂对于学徒在其学习期内,须使职业传授人尽力传授学徒企业所定职业上之技术。[7]《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规定:劳工教育分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三种,各地方应于最短时间内按工人教育程度分别实施;由各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当地农工商及其他各业之厂、场、公司、商店负责完成之;各厂、场、公司、商店等雇佣工人在五十人以上二百人以下者,应设立一个学校或劳工班,工人每增加二百人应即递增一班,其不满五十人者得与附近之厂、场、公司、商店联合办理之,每班学生额数以三十人至五十人为准。
最后,在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参与下,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得到广泛推行。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先在上海、天津、武汉等部分工业发达城市的企业中展开试验,随后推广到全国的企业。因此,从地域看,劳工教育先从部分工业城市展开,随后推行到全国;从主办单位看,此次劳工教育是在政府部门主持下,以为数众多的工商企业作为主办单位的教育活动。“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之费用,由原设立机关负担;其联合办理者,应共同负担之。”劳工教育在工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各个行业所属的各个实体内展开,成为全国范围内以工商企业为主办单位的教育活动。从教育对象的年龄上来看,劳工教育不限于学徒,还包括已经出师的学徒。地方政府出台相应的措施加以管理:青岛市规定,“各工厂工人均须一律入校补习,不得藉故规避”;浙江杭县规定,“各校招收学生在十四岁以上”;重庆市规定,“十二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工徒均得入校修业”;上海市则规定,“本市区域内(四十五岁以下)不识字之工人一律受识字教育,……如至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以后仍未受识字教育者,应即日勒令停止工作”,铁路部门则规定,“凡全路职工人数不满一千人者设立识字学校一所,二千人左右者设两所,以此类推;沿路各站有职工五百人左右者设立识字学校一所,两百左右者设立识字班一所,六十人左右者设立识字处一所。”并要求,“不满四十五岁之职工一律毕业于职工识字学校,不满四十岁之职工,应一律毕业于职工公民学校”。企业也开始制定劳工教育实施细则,如湖南第一纺纱厂指出:“本厂设有工余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凡在厂工作之童工、学徒、失学工人及其子弟,得入校补习。”荣氏企业中接受劳工教育的人数一度达3000余人,大大提高了企业职工素质结构,对荣氏企业文化的形成与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也不无裨益。
在劳工教育思想的推动与政府、企业的积极参与下,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获得比较迅速的发展。指出:“各省市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农、工、商之厂场、公司、商店,比前尤力,厂场、公司、商店办理劳工教育不得不为之职责。各厂场、公司、商店所设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亦比此前普遍且完善。”[8]
三、劳工教育的成绩及问题
劳工教育的需求不仅体现在劳工希望通过教育提高谋生技能,而且还在于通过教育获得做人的尊严,过有意义的生活;企业主实施劳工教育,旨在提高生产效能,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政府介入劳工教育,希望通过劳工教育缓解劳资冲突、消弭劳资纠纷。民国时期劳工教育一定程度上达成了这一目的,并取得可喜的成绩。然而,由于政府介入劳工教育主要考虑的是政治意图与政府利益,使得劳工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严重问题。这种问题由于劳工教育内容的意识形态化与劳工的被动参与,使得劳工教育被异化而最终陷于失败。
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形成劳工教育思潮,为劳工教育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劳工教育思想的传播,引起了时人对劳工教育的广泛关注,辅之以新文化运动中教育民主化与实用化思想的传播,不仅劳工、企业开始重视劳工教育,而且引起社会团体、立法机构与政府部门的重视。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劳工教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教育思潮,也构成教育民主化思潮的重要内容。劳工教育思潮对劳工教育性质的分析、对劳工教育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对劳工教育目的、内容等的观点,为劳工教育实践活动的展开创造了舆论氛围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其二,出台了系列劳工教育法律、法令,并组建了劳工教育职能部门,使劳工教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劳工教育法律的颁行,标志着政府和立法机构对劳工及劳工教育的重视;劳工教育职能部门的组建,标志着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劳工教育,就此而言,今日中国也没有做到,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进步。
其三,劳工获得受教育权利,接受教育成为劳工的福利,大批劳工因此而受益。民国时期劳工教育法律不仅规定劳工须受教育,而且是免费的,大批劳工由此获得受教育权利与机会。据1936年5月《国际劳工通讯》对上海从1935年8月到1936年2月的统计,上海“约有400多个劳工学校,分742班,学生人数35116人”。若考虑其他未做统计的地区,接受教育的劳工人数当远远超过以上数字。对铁路系统的劳工教育作出以下评述:“铁道部于1932年春开办铁路职工学校,实施职工教育,两年以来,实施之效果,虽未能全部达到吾人所希望之圆满成绩,然各路文盲之减少,以及职工知识与技能之逐渐提高,亦即中国劳工教育史上之最大收获。”[9]所以,民国时期劳工教育是教育民主化的重要体现。
其四,形成有特色的劳工教育形式,出现教育型企业。企业是劳工教育实施的主体,由于劳工教育的展开,民国时期出现诸如民生公司、荣氏企业、各路段铁路公司、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等等弥漫着浓厚教育气息的企业,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企业文化的形成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培养产生了积极影响。以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为例,该厂于1922年创建时,即设立教育设施,“训练学生培养技师是为本厂发轫之始。”到1932年,康元制罐厂已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校化之工厂”和“工厂化之学校”。所谓“学校化之工厂”,意指将工厂当作学校来经营,在工厂设立教育设施并对全厂职工进行德、智、体、技等方面的教育,使工厂具有学校的性质,即“一面训练熟练技能,一面灌输丰富学识,一面培养服务道德,一面锻炼强健体格,使本厂成为学校化之工厂,教育空气弥漫各处”;所谓“工厂化之学校”,意指克服以往企业中学徒教育重技能轻学识和学校教育重学识轻实践的弊端,将学理与经验结合起来,兼顾学校与工厂的优势,使人人成为具有建设能力的公民,“实施生产教育,一面革除一般工厂惟物主义之流弊,一面革除一般学校惟心主义之流弊。”[10]
民国时期劳工教育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问题。
第一,政府参与劳工教育主要出于政党意图和政府利益而非劳工意愿的考虑,使得劳工教育开始被异化;而劳工教育内容的意识形态化,使得劳工教育背离了最初的意图,成为实施控制和巩固统治的一种政治手段。为了贯彻“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纲,国民政府将党化教育扩展到劳工教育,用“三民主义”灌输工人。在思想上,要“将三民主义融化于一切科学,使全体学员有深切之认识与信仰,并明瞭中国国民党之政纲政策及历次有关工运之决议”,“使学员认识国内一切反革命派及帝国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重要敌人”,“使学员明瞭共产主义之荒谬及违反三民主义之各种理论的错误。”劳工教育成为消弭劳资纠纷,让劳工接受劳工资本家的剥削而非提升劳工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的措施,劳工教育被异化。
第二,劳工成为劳工教育的被动参与者,使劳工教育效果受到影响。“劳工教育的实施要以真正的民主政治作为实施前提;政治不民主,一切还是靠强迫、命令、独裁来维持,劳工教育问题仍不免落于空谈。”[11]从民国时期劳工教育法律的制定,劳工教育制度的出台以及劳工教育内容、方式方法的选择等方面看,劳工都是劳工教育的被动参与者;加之,劳工教育内容的意识形态化以及劳工繁重体力劳动的现状,使得劳工开始消极对待劳工教育。正如杜威所言:“我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基本方法,……但是,所有的改革,如果只依靠法律的作用,或仅以某种惩罚威胁,或只借助机构和外部安排上的变动,都只能是昙花一现,是无效的。”[12]这样,以“增进工人之知识技能及其工作效率并谋工人生活之改进起见”而实施的劳工教育不断被异化而走向反面,最终陷于失败。民国时期的劳工问题,不是通过劳工教育实现劳工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得以解决,而是通过劳工的暴力革命实现了社会性质的变化,这成为民国时期劳工教育中的最大问题。
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也遭遇到严重问题,正是这种问题使其最终失败,成为一次悲壮的教育尝试。然而,民国时期劳工教育的失败不等于今日劳工教育没有成功的可能:民国时期出现的有特色的劳工教育形式,为劳工教育的成功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发达国家的劳工教育经验,为劳工教育的成功提供了范例。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劳工教育问题被关注的程度也较高。英、德、法、美、日等国家,不仅有比较完备的劳工教育法律、政策和制度,设有劳工教育主管部门、实施单位,有劳工教育设施及辅助设施,而且有具体的劳工教育目标、内容、方式与考评机制等。由此出现产业化程度高,重视劳工教育,劳工教育发达而推动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并发展演变成为今日的企业教育,出现了企业大学。克雷明在《美国教育史》中指出:这种“发生在企业内的教育体制的发展与体系化,是20世纪美国最为突出的教育发展成就。”日本学者细谷俊夫在系统考察英、美、德、前苏联和日本等国技术教育的基础上,将企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并列,称之为“第三教育场所”。并言:“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站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立场上看技术教育的最基本的问题就在于此。”[13]目前,企业教育已构成发达国家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方式。
与发达国家“高技能、高薪水、全就业”的劳工教育方针相比,中国的农民工教育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何通过教育,将农民工、企业、政府三方利益结合起来,实现农民工、企业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中国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以使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成为摆在当前中国人面前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民国劳工教育中积淀的思想资源和域外劳工教育的成功经验,为今日中国劳工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需要对其加以重视。
[1]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M].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3:1、288、241.
[2]中华民国大学院.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乙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415.
[3]唐钺,朱经农,高觉敷.教育大辞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1146-1147.
[4]中国劳工教育研究社.发刊词[J].劳工教育,1934,(1):2.
[5]交通部.中国政府关于交通四政劳工事务设施之状况[M].北京:祁世宝印书局,1925:3.
[6]顾炳元.中国劳工法令汇编[M].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7:107.
[7]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M].第五编.实业部,1932.
[8]陈振鹭.劳工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7-8.
[9]王天觉.铁路职工教育之过去与现在[J].劳工教育创刊号,1934,(1):12.
[10]沈刚中.康元印刷制罐厂十周年纪念刊[M].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1934:1、65.
[11]杜播.关于劳工教育的一点意见[N].新华日报1945-2-7.
[12](美)劳伦斯·A·克雷明.美国教育史: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3](日)细谷俊夫.技术教育概论[M].江丽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1983: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