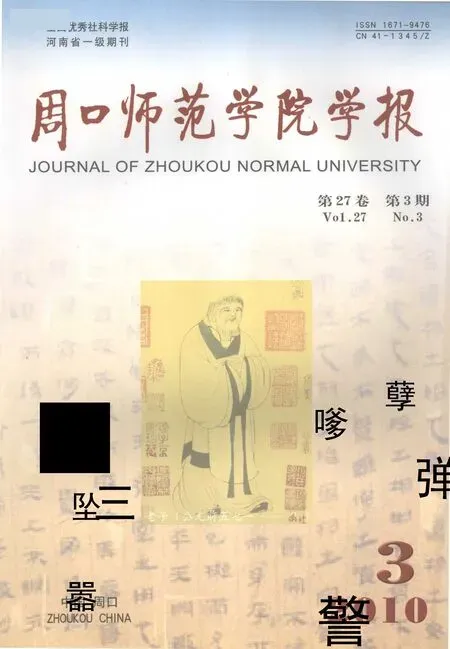农村纠纷成因及解决偏好分析
郑 昊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青海西宁810007)
社会环境不同,纠纷的表现形式也不相同,社会主体之间均衡关系的破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秩序和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风俗不一,农民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国家法律无法事无巨细地实现正义保护,重新审视和反思农村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农村社会的纠纷成因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各种纠纷日益多元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秩序的重要因素。农村社会的特点及其生产方式决定了其纠纷大多数是与其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矛盾。涉及征地补偿以及干群关系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新型纠纷,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一)家庭矛盾引发的纠纷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百善孝为先”“万事和为贵”,但近些年来,“一切向钱看”“利益论”成为某些人的追求目标,从而导致人生失去方向,心理扭曲,亲情缺失,以一己之利而丧失天良,道德沦丧。家庭矛盾主要包括婚姻关系的解除、家庭成员之间因赡养所引起的纠纷等。前者除了一些传统因素的影响,如夫妻草率结婚、互相猜疑以及婆媳关系不合等原因之外,社会“打工经济”的发展,使得许多原本以土地为生的人外出务工,在看到了外面世界精彩的同时也与家里的“留守人员”在思想上产生了碰撞,这也是农村家庭婚姻矛盾频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后者则是由于部分人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淡薄,认为老人吃穿用住、疾病治疗都需要经济上的花费,因而把老人当作家庭负担,漠视赡养老人的法律义务。
(二)邻里矛盾引发的纠纷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逐渐富裕起来,然而贫富差距的现象也日益加剧,心里不平衡导致邻里之间的偏见和误会增多,原有的“远亲不如近邻”的思想观念淡化,“从本质上来说,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是一切邻里纠纷的根源”[1]。部分农民思想狭隘,争强好胜心强,常因宅基地、通行、排水、采光或田间地埂等事发生纠纷。由于诸方面的原因,斗殴现象时有发生,双方的亲朋好友多倾巢相助,不计后果。发生该类事件,容易造成人员伤害,致使医疗费用高,一旦处理不当,容易激化矛盾。而对于“面子”的争夺,也是诱发邻里纠纷的因素之一。“面子竞争行为贯穿于农民的一生。……它的外延非常大,涉及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2]在遇到问题时,他们往往首先考虑的是对方给不给自己“面子”,是否在挑战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三)建设开发引发的纠纷
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在农村工程建设中,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征地补偿等问题日趋严重。而当某些人的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阻挠施工、上访,甚至引起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在较大村落,此类现象更为突出,在“法不责众”思想的影响下,纠结煽动同族或相关利益人以种种理由起哄闹事,妨碍施工,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破坏。
(四)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引发的纠纷
个别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较差,官本位思想严重,摆不正自己的“公仆”位置,只索取,不服务,被称为“三要干部”:要钱、要人(殡葬改革)、要命(计划生育)。在工作中消极涣散,热衷于讲排场、摆阔气,成天忙于吃喝玩乐。在处理村务上优亲厚友,甚至假公济私。结果给农民造成很大经济损失,致使群众产生逆反心里,导致与基层干部“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在情况比较严重的地区,甚至出现“对着干”的现象,严重影响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纠纷解决机制选择的偏好分析
(一)“熟人社会”——一种内心的价值判断
我国著名学者和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他的著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写道:“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农村社会关系由于生产方式的原因,导致他们有着不同于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他们往往通过“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遇到纠纷冲突时,更讲究的是一个“面子”。美国法社会学家布莱克将社会的横向关系和分工、亲密度、团结性等人员分布的状态普遍变量称为关系距离(relation distance),他认为关系距离与法的变化之间存在着曲线相关:在关系较亲密的社会群体中,诉诸法律显然是被尽量避免的;随着关系的疏远,法的作用也相应增大;但是当关系距离增大到人们完全相互隔绝的状态时,法律又开始减少[3]。在农村地区,邻里之间发生矛盾,人们首先选择的是忍让;接着就是以家族和乡邻为基础的人情、礼俗进行和解;如果还不能解决,就会找村干部或者族内有声望的人进行调解。一般为了以后关系的维持,很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1.忍让。忍让是纠纷发生后,当事人主动放弃争执,使纠纷归于消灭的一种方式。忍让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是人们在发生纠纷时最常见的解决方式。牺牲一定的利益,来换取另一部分利益的实现。这种方式的成本最为低廉,但得到权利救济的可能性也最小。忍让有一定限度,村民对其他村民的占强行为能保持忍让的最大临界点,一旦占强行为超过利益模糊区间的底线,村民的不满也会达到极限,这时他们就会放弃忍让,极力反抗。付少平认为:“在中国农村,回避、忍让也是常见的现象,文化影响也好,社会结构的限制也好,忍让仍是一个重要的解决纠纷的方式,不过,是否忍让最终取决于纠纷的性质、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和不忍让可能带来的后果。”[4]
2.熟人调解。调解作为一种由第三方介入的解决机制,在解决我国农村地区的纠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调解的种类很多。因调解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内部调解、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以及律师调解等。本文所讲的调解是指内部调解,即村庄内部的“熟人调解”。“熟人调解”的概念,可以从“熟人”这个修饰词中得到解读:出面解决纠纷的人大多数是熟人。调解人一般是宗族内有威望的人或者村里的“熟人”,他们调解的依据除法律以外,主要是依据乡村社会沿袭已久的“情理”,并以高超的协调手段使双方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其目的并不是主持普遍正义,而是使原有的秩序得到尽快的恢复。在纠纷发生之后,是否使用调解方式完全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在调解过程中,如果不同意调解,可以随时退出;当事人只需向调解人支付很少的调解费用或者不支付。调解人或以情、或以法来说服当事人,但更多当事人是看在调解人的“面子”上接受调解方案,使事情尽快得到解决。另一方面,由于村庄信息特点导致了村民对于国家大事并不关心,而对身边的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十分关注,这些往往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话题,所以一旦当事人有了纠纷,势必影响其在村庄中的声誉。而调解往往不会涉及隐私曝光的问题,只是在调解人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极大程度地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社会关系和个人隐私。
所以,笔者认为,熟人调解并非主持普遍正义,而是纠纷发生后原有秩序得以恢复的一种方式。熟人之间有着长远的预期,并非寻求当下的分毫利益得失,而且,只有互让、施赠人情,才能让相互之间的情感得以延续下去,才会产生今天你给我个“面子”明天我给你个“面子”的这样一种情感弥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越深厚,他们之间的预期合作也就越长,就更加不会计较当下利益的得失。
(二)诉讼成本分析
美国著名学者埃里克森在研究美国夏塔斯塔县牧民处理牲畜越界纠纷时发现,大多数民区居民信奉着“邻人之间要合作”的主导型规范,信奉着“自己活别人也要活”的生活哲学,认为这种规范和哲学则是乡村生活的现实状况[5]。理论上,当权益受到侵害就可以主张赔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不愿意这样去做,“有仇必报”必然会影响到日后的相处与合作,每个人都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来解决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一切困难和问题。当纠纷发生之后,当事人除了考虑对方的身份和可能出现的后果,考虑更多的还是成本的问题。这里的成本是指纠纷处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所消耗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原有的社会关系、社会声誉等损失。
国家法严格的程序在理论上更利于保障一般的公平正义,但同时也带来了高成本、诉讼时间以及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当事人不但要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还需支付其他费用,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精神损失更是无法估量。即使胜诉,但因实践中存在“执行难”的问题,而出现“赢了也是赔”的现象。另外,个别法官素质低下,对当事人“吃拿卡要”、办“关系案”等司法腐败现象也时有发生,造成部分村民对诉讼失去信心,往往出现“人家有人,告了也赢不了”“也没人家有钱,告了有啥用”的说法。在农村地区纠纷标的额小的情况下,选择“熟人调解”的方式也是情理之中。
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变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其社会机制也趋于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亦是如此,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人们在解决纠纷时趋向于选择寻求法律诉讼。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人们往往选择私下或者通过熟人解决。诉讼对于实现社会正义有着无可替代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但同时人们往往也对诉讼不同程度地持否定态度,中国传统文化中力行“德治”“息讼”“无讼”的态度,在西方传统中诉讼同样也被视为一种“负价值”。原美国总统林肯曾对律师说过:“劝阻诉讼吧,尽可能说服你的邻居达成和解,向他们指出,那些名义上的胜诉者实际上往往是真正的输家……损失了诉讼费、浪费了时间,律师作为和平的缔造者,将拥有更多的机会做个好人。”[6]
大部分村民在权利受到侵害时,一般不是选择寻求国家法的诉讼,而是通过熟人调解。虽然国家已经对涉农诉讼采取减免费用的措施,可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诉讼费用仍然是一种不能承受之重。当然,在村民意识里,把事情交给司法机关处理,就等于“撕破脸”,对以后邻里之间的交往很不利。梁治平认为农村对法律的规避或违反并不能简单归咎于农民的愚昧,他指出:“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因此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7]选择诉讼纵然有着终裁的效果,使得纠纷在表面得以消弭,但是农村社会世代传承的血亲和友谊也随之割裂。这样就造成了“虽然作出了判决,关系也崩裂了”的结果,甚至原来的互赖互利的关系也荡然无存。若一方或双方对判决不服,有时会出现“民转刑”的现象。
三、国家法在纠纷解决中的困境
纵观目前各类农村法治的研究,大多都是关于国家法在纠纷处理中遭遇“地方性知识”或者“法律不及时”等现象的研究,学者们试图借助于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和新制度的建立来解决国家法在乡土社会所遇到的阻力。近些年来,国家一直倡导如何使“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创立权威并使之得以实现”,而一般来说,司法官员介入乡村个案,其身份只是一个外来者,他们熟悉的是国家法律,在村民眼里,国家法律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他们日常生活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是一种根植于血液里的“地方性知识”。国家法并非对所有事情都有事无巨细的规定,社会的纠纷层出不穷,而法律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能及时对这些新情况进行规范。在农村地区的具体个案中,国家法的统一平等性往往与之出现矛盾,即使案件通过诉讼途径得到解决,往往因为“执行难”的问题,而达不到相应的救济目的。
民间纠纷的多元化决定了解决机制不能拘泥于固定模式,不同的解决机制在纠纷解决中的效果也不同,我们不能奢望一个固定模式可以解决一切纠纷,要在国家法的框架内因时因地、合情合理地解决农村社会中出现的纠纷。
[1]曲天立.当前农村邻里纠纷增加的社会原因[J].理论界, 1995(8):43-44.
[2]汪永涛.农民日常生活中的面子竞争[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9(6):26-29.
[3]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2-30.
[4]付少平.对当前农村社会冲突与农村社会稳定的调查与思考[J].理论导刊,2002(1):37-39.
[5]罗伯特.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10.
[6]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张文显,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36-37.
[7]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权威[M]//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