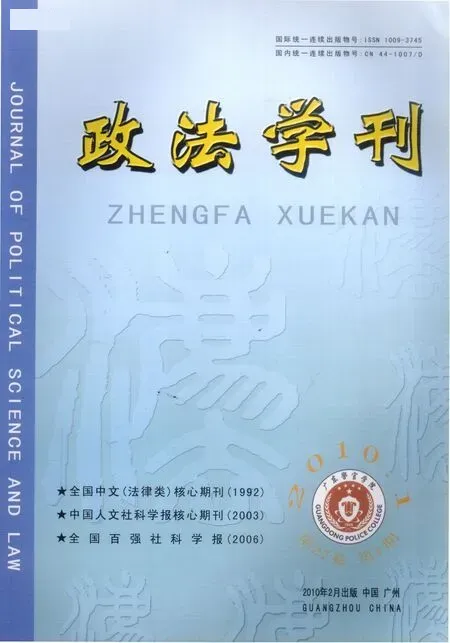两要件双层次犯罪成立要件模式论纲
刘 剑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两要件双层次犯罪成立要件模式论纲
刘 剑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先事实判断、后价值评价是认识事物和决定取舍的普遍方法。我国犯罪成立要件模式具有静态性和整体性。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同时的、一次性的完成,不仅混同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而且颠倒了先事实判断、后价值评价的顺序,带来了诸多弊端。构建由典型事实到刑事违法性的两要件双层次犯罪成立模式,能克服现存犯罪成立要件模式之弊,对确保刑法功能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判断;价值评价;典型事实要件;刑事违法性要件
一、二元论和犯罪成立要件模式
自从休谟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区分以来,这种二元的范式得以发展,休谟认为,“是”与 “不是”是一种事实判断,而 “应该”与 “不应该”是一种价值判断,由此区分事物的规律和道德的规律:前者是实然律,后者是应然律。[1]509-510在休谟看来,道德上的善恶性质表明的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属性,而是事物满足人的需要的肯定或否定的意义,是评价主体根据人类的一定利益的需要对行为和品质的一种价值认知,并在这种价值态势的支配下流露出的一种情感。休谟关于事实和价值的二元论在伦理学上曾产生重大影响。在刑事法领域,犯罪是一种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背道而驰的行为。对犯罪进行认定和处理是国家政权的一项长期使命,但对犯罪的认定和处理必须遵循一定的规格和标准。这个规格和标准就是国家司法机关据以确立犯罪的标准,即犯罪成立要件①“犯罪成立要件”、“犯罪构成”、“犯罪构成要件”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是一个层次的概念,学者们大都不对其明确区分而互换使用。笔者认为,作为“判断犯罪成立唯一标准的主客观要件的总和”的内容而言,以 “犯罪成立要件”表述更为恰当,不仅揭示了犯罪行为本身静态的内部构造,还强调了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动态的判断过程;而“犯罪构成”和“犯罪构成要件”从语言表述上看,更多的是对犯罪行为本身内部构造的静态分析。。理论上大致有以下三类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模式:第一类包括前苏联及我国在内的静态反映犯罪规格的平面整合结构式;第二类是美国刑法的体现控辩双方对抗活动,蕴含刑法的维护秩序和人权保障两大功能,表明 “定罪过程”的公正性价值取向的犯罪构成双层模式;第三类是大陆法系责任范围逐步收缩,反映 “定罪过程”的三元犯罪结构式。[2]对犯罪与否的判断,首先是事实的判断,即对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范明确列举的构成要件作判断。这里的事实包括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事实和情况,只有危害行为而没有犯罪心理,或只有犯罪心理而没有危害行为就谈不上构成事实存在。对事实的判断仅仅揭示行为人在何种心理事实支配下从事了何种行为,造成了何种结果,并未明示法对该事实的态度,因此在事实判断之后,往往要对给该客观事实进行价值评价,这种价值评价正是法对该确证事实的态度,或肯定、或否定,前者合法,而后者则可能构成犯罪。价值评价的对象包括客观事实和主观事实两个方面。在大陆法系三元犯罪结构式中,前者表现为违法性的评价,这里的违法性是指客观的行为事实本身,这和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奉行的“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相关。这种评价,就是在构成要件符合性基础上,从法律规范的整体价值观上进行评价,将法律精神所能容忍和许可的行为排除出去,即存在阻却违法事由而否定行为的违法性,后者则是从行为的主观面,针对行为人的心理事实进行的刑法价值评价,对没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人免除其责任,从而最终确定犯罪是否成立。在英美法系国家,犯罪成立要件是双层次结构:犯罪本体要件和责任充足要件。犯罪本体要件包含了犯罪行为和犯罪心理,它们是构成犯罪事实的基本方面,具备这两个条件就可以认定犯罪事实存在,就可以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除非行为人有合法辩护的理由,所以事实判断涉及行为事实及心理状态。这一层次的判断属于构成事实判断范畴。而价值评价则主要与行为的违法性评价有关。行为符合辩护条件的,则排除了行为的犯罪性[3]。所以说,英美法系刑法中对犯罪成立与否的判断也是遵循先事实判断,后价值评价顺序进行的。
二、我国通说犯罪成立要件模式的特点
我国犯罪成立要件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同时和一次性的完成,犯罪构成四要件是闭合式构造,基本特征是经验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更多的是一种经验生活上的感受和一种平面的思考。从宏观上看,我国刑法的犯罪成立模式具有非常明显的特征,即静态性和整体性。
静态性主要表现我国刑法中传统犯罪成立模式 (犯罪构成要件)重视对犯罪行为内在结构及特征的静态分析。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以及犯罪主观方面是刑法理论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对犯罪行为进行的剖析,用来揭示犯罪行为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客观害和主观恶。这是一种对已经被认定为 “犯罪”的行为的事实特征和价值归属的描述。在这个理论体系里,并没有提供如何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具有客观害和主观恶,从而决定这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方法和路径。在此理论框架内,定罪过程被有意无意的忽略,变得可有可无。而定罪结果则被彰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模式在理论上具有极强的功利主义倾向;在实践中对于实务工作者也具有极强的暗示作用:只要结果正确,过程无足轻重。司法实践中极易导致先对行为定罪,再论证其构成犯罪的不正常现象,这和刑事诉讼领域所谓的“有罪推定”是一脉相承的 。殊不知,定罪结果的准确性正是建立在定罪过程的合理性之上的。
整体性是指犯罪构成四要件之间相互勾连,彼此支撑,各个要件之间并非一种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并存关系。一有俱有,一无俱无。对一个构成要件有无的判断,往往要从其他构成要件里找答案。比如,判断一个行为是否侵害了社会关系 (是否具有犯罪客体),就必须到犯罪客观要件里看危害行为所侵害的是怎样的犯罪对象;而在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 “危害行为”时,又不得不先去犯罪主体要件以及犯罪主观要件中,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该行为是否“有意识支配”下的危害行为。理论上虽然将犯罪成立要件界分成四个方面,但从各要件之间的关系来看,构建者根本就没有把这个理论当作判断犯罪成立的标准来构建,相反,它是对犯罪行为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解释和说明。因此,犯罪构成四要件之间当然就是一种彼此勾连和渗透的关系,各要件在彼此的关照中共同将犯罪行为的事实特征和价值归属交代清楚。这样的 “犯罪成立”模式在实践中不能给认定犯罪提供可资借鉴的认定方法和路径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具有静态性和整体性特征的我国犯罪成立模式并非没有对行为事实和价值的描述,而是混淆或颠倒了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的顺序。使判断犯罪是否成立的“过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呈现一种混沌状态。按照通说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很难对这种判断的过程进行描述。在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体系之下,犯罪成立的判断过程被名正言顺的个体化了。不同认识能力、不同价值取向的判断者在认定犯罪是否成立时,可能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路径和方法——有的可能先就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开始;有的可能先就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罪过开始;也有的就可能先假定行为构成犯罪,然后再用构成要件去证明,而这种先进行有罪推定、后进行论证的定罪方法是极其危险的。
通说的犯罪成立要件模式中的价值评价存在两个特征:一是价值评价过于前置。犯罪构成理论中,客体是犯罪成立的首要条件,而所谓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就是实质的价值评价,此评价一旦完成,行为即被定性。这是一种过分强调国家权力的做法,它可能会导致一些危险:1)一旦发生使人心冲动的案件,感情上便会产生处罚的强烈要求;2)一旦行为人主观恶劣,便不充分调查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何种后果就进行处罚;3)一旦危害结果重大,就不问行为人的主观状况就进行处罚。[4]95由此看来,价值评价过于前置不利于保障人权和实现法制。二是价值评价无层次性,违反法律推理的一般原则,与大陆法系犯罪成立模式认定犯罪的由一般到特殊、从形式到实质的评价顺序不同,我国刑法中无此层次性,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笼统地一次性完成,形式评价和实质评价没有理顺。而事实说明,如果一次司法判断过程承担过多的使命,裁判结论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同时进行,或者以事实判断代替价值评价的做法,会带来诸多弊端:
(1)不利于刑法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无论刑法理论还是实践都已昭示,犯罪成立模式如果只反映定罪结果而不反映定罪过程,则只能突出刑法的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的功能,而保障人权的功能不免弱化。在大陆法系犯罪成立三元模式之下,定罪过程就是国家刑罚权不断被限制,刑罚打击范围逐步缩小的过程。在刑罚权发动之初,该权力即受到构成要件符合性的限制,刑罚权的发动被限定于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范围之内,对分则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国家刑罚权不能对其加以处罚;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对刑罚权的行使作了最初的限制。而对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过程就是对行为进行事实判断的过程,就是对行为事实进行中性无色的判断,得出 “有无”结论的过程。也正是因为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是事实判断,不掺杂价值评价的因素,因此不必担心判断者可能因为自身的原因出现误判。
经过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的行为进入违法性判断阶段。违法性判断属于价值评价的范畴,其实质就是评判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对法秩序所具有的意义。由于构成要件是违法行为的类型,所以,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在通常情况下就具有违法性,因此违法性判断只须判断有无正当化事由即可,如果存在正当化事由,则行为无违法性,当然不构成犯罪;如果不存在正当化事由,则行为具有违法性,从而进入有责性的判断。由此可见,违法性的判断通过正当化事由的过滤机制,将一部分符合某一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排除于违法性之外,使其不可能构成犯罪。可能成立犯罪的行为范围进一步缩小,国家刑罚权受到进一步限制。最后,再经过有责性的判断,将已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的一部分行为排除于犯罪之外。从而再一次限制、缩小国家刑罚权的发动。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犯罪成立的判断的静态性和整体性,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综合平面一次性地完成,这样既不利于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也不利于有效的指导立法和实现刑法个别公正。因为“如果要处罚一个行为,社会危害性说可以在任何时候提供超越法律规范的根据……”[5]8。
(2)造成刑法理论的不协调和内在矛盾。首先,把刑事违法性等同于犯罪性,由于刑法规定的阻却事由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备无遗,则对于法律明文加以规定的但实质上不具有犯罪性的行为,如何在理论上得到合理解释,则不无疑惑。例如,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据此规定以及刑法学说的解释,重婚罪的犯罪构成是:客体要件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客观要件是必须具有重婚的行为;主体要件是已经有配偶的人,或本人虽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者;主观要件是故意。按照通说的观点,只要符合这四个要件就应当成立重婚罪;否则,不成立重婚罪。然而,司法实践中对于重婚罪的认定却将下列情况排除在外:a.因自然灾害流亡而重婚的,或因婚后受虐待外逃再婚的;或被拐骗贩卖再婚的。b.对主动解除或经劝说、批评教育而解除非法婚姻关系的。c.因配偶长期外出下落不明,造成家庭困难,又于他人结婚的[6]500。这些被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完全符合重婚罪的犯罪构成。显然,司法实践裁判是否成立重婚罪并不只是考虑重婚罪的犯罪构成,而且还考虑了行为人所处环境等的具体情况。通说的犯罪成立要件理论无法对此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理论上的尴尬境地,理由之一就是:通说的犯罪成立要件理论即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本来就只能解释犯罪是何种行为,而不能用来判断何种行为构成犯罪。这是由犯罪构成四要件模式没有遵循先事实判断、后价值评价的动态定罪过程决定的。其次,强调犯罪构成是判断犯罪成立的唯一根据,另一方面,犯罪阻却事由理论又被置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之外论述,在体系上难免不协调[7]。在二者的关系上,则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如果犯罪阻却事由符合犯罪构成,依据“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判断该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唯一标准”,则犯罪阻却事由成立犯罪;反过来,如果犯罪阻却事由不符合犯罪构成,又不能很好地解释刑法为什么要专门对这类行为做出规定。
因此,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出现的一些不易解释的悖论或矛盾就是混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取消先事实后价值的评判顺序所造成的。
三、两要件双层次犯罪成立要件模式
由我国犯罪成立要件通说理论之弊,循着由事实到价值的认识进路。笔者设想可构建两要件双层次犯罪成立要件模式,所谓两要件是指典型事实要件和刑事违法性①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形式特征,是第二性的,是由犯罪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决定的。在本文中,刑事违法性概念包括形式的刑事违法性和实质的刑事违法性两个层面,前者大致相当于通说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形式特征;而后者则是指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是犯罪的实质特征。将犯罪的特征理解为刑事违法性有利于避免理论纷争;有利于明确犯罪概念的层次性;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公正的实现。要件,所谓双层次是指在刑事违法性要件里分为形式的刑事违法性评价和实质的刑事违法性评价两个层次。在此犯罪成立要件模式下,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判断遵循典型事实判断——形式的刑事违法性评价——实质的刑事违法性评价的顺序进行。最终达至既合乎法律推理的一般原则,又能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实现刑法公正的目标。该模式由典型事实和刑事违法性两大要件构成,次序上,遵循先典型事实判断后刑事违法性评价的顺序,以和先事实判断后价值评价的逻辑顺序相吻合;内容上,典型事实和刑事违法性都是主客观要素的统一。在刑事违法性要件内部,按其评价的次序,又可分为形式的刑事违法性评价和实质的刑事违法性评价两个层次,前者评价行为是否违反实定法,是形式的评价、积极的评价和一般的评价;后者评价行为是否从根本上侵害法益,是实质的评价、消极的评价和具体的评价。
1.典型事实要件
(1)典型事实的概念和特征。所谓典型事实是犯罪规范中对现实中发生的某种事实的描述。现实中发生的具体事实符合刑法规范规定的典型事实,是认定犯罪的首要步骤。由于成文法本身的抽象性和一般性,也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以及人类社会行为的多样性,刑法规范不可能将所有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都囊括于刑法规范中加以规定,而只能借助类型化的方法将无数个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行为加以抽象和概括,然后以刑法条文的形式公布在成文法典中,留待司法者在认定犯罪时结合具体事实进行套用,从而判断其是否与典型事实相符合。因此,对行为进行典型事实的判断,是决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最初的标准。准确的描述具有刑法意义的命令或禁止的内容是典型事实最基本的要求。
典型事实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客观要素与主观要素的统一。犯罪的核心概念是行为,任何刑法意义上的行为类型——即典型事实——都是主客观的统一。所谓客观要素,是指典型事实表现在外的物质因素,如行为的样态、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这些都是可以用感觉加以认识的物质实存,而主观要素则是内在支配行为人行为的心理因素,它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还包括动机、目的等其他主观内容。
第二,描述性因素与规范性因素的统一。描述性因素和规范性因素是从对典型事实要素的性质的界定上所说的。描述性因素是指典型事实中那些简单的以人们的经验为基础来判断的因素,如故意杀人中的“人”的概念就是指这种情况,因为一提到人,人们立即就想到应该指有生命的人。而所谓规范性因素则是指需根据某个特定的标准进行判断的因素,如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中,对“公私财物”的判断,仅仅依靠一般的生活经验为标准,是不足以得出正确结论的,而必须以民法规范中有关所有权的规定来做出判断。根据人们所援引来进行判断的规范的性质,规范性又可分为法律的规范性因素与非法律的规范性因素。
(2)典型事实的机能。[8]73-74首先,自由保障的机能。由于典型事实将各种犯罪行为以类型化的方法规定于刑法各分则条文之中,也就是对犯罪进行了定型化,这样就明确地划定了当罚行为与不当罚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只要不实施符合典型事实的行为,就不会受刑事的追究,也不会受国家刑罚的干预。正是在此意义上,典型事实保障公民的自由。另一方面,不仅刑罚的动用以行为符合典型事实为前提,而且,刑罚轻重的量定也要以典型事实的规定为限。在此意义上,典型事实又保障犯罪人不受不恰当的处罚。
其次,犯罪个别化机能。由于典型事实是犯罪的类型或定型,这就使得各种犯罪具有自身的特点,使之与其他犯罪相区别。杀人罪的典型事实,就不同于盗窃罪、放火罪的典型事实。不同犯罪之间的区别,要在典型事实中寻找,也就是说,典型事实使各种犯罪相区别成为可能。
最后,刑事违法性推定机能。由于典型事实是立法者根据对无数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特征的总结、概括、抽象规定的行为类型,因此,这类行为一旦发生,就可以立刻与“法益受到侵害”联系起来,这也是法律推理上的 “三段论”:大前提——具有某一类特征的行为侵害法益 (具有刑事违法性);小前提——某一具体行为是具备某一类特征的行为;结论——某一具体行为也侵害法益 (具有刑事违法性)。所以,只要行为符合典型事实,通常都能得出行为刑事违法的结论,除非在例外的情况下 (具有阻却刑事违法事由),才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由典型事实对刑事违法性所具有的推定机能并不能得出典型事实即刑事违法性的结论。因为,典型事实仅针对行为发生与否而言;而刑事违法性则是对符合典型事实的行为在刑法上意义的价值评价而言。二者性质是不同的。
(3)典型事实的要素。第一,客观要素。客观要素主要包括:一是行为人的要素,包括行为人的年龄、行为人的精神状况,以及行为人的特殊身份等。二是行为的要素,包括行为的时、地、方法、手段、强度、以及行为的对象、行为的结果。三是行为和结果间的因果关系。
第二,主观要素。主观要素主要包括支配行为人进行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包括故意、过失以及行为的动机、目的等。
需要注意的是,典型事实符合性的判断由于是司法者对造成一定法益侵害结果的行为所进行的事实判断过程,因此,典型事实的构成要素也应排除任何价值评价的色彩而成为纯粹的、中立无色的物理过程。客观构成要素的行为是有一系列身体动静的物理过程,主观构成要素的心理态度则应理解为一系列心理学意义上的因素,如故意就应理解为认识到结果的可能发生而希望或放任其发生的心理事实,而不包含对其进行价值评价的因素。①我国现行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中,主观方面的故意、过失是作为 “罪过”的下位概念存在的,其本身就已经包含着刑法否定的价值评价。而典型事实中的故意、过失,拟或目的、动机则仅仅指行为人在选择具体行为时的一种心理事实,不包含对这种心理事实的刑法价值评价。
2.刑事违法性要件
刑事违法性评价是司法者对符合典型事实判断的行为,就其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所作出的刑法的价值评价。在刑事违法评价中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形式的刑事违法评价和实质的刑事违法性评价。
(1)形式的刑事违法性评价。形式的刑事违法性评价是从外观上、表象上对符合典型事实的行为所作的初步的刑法的评价,即凡符合典型事实的行为就具有形式的刑事违法性,这也是典型事实所具有的违法性推定机能的体现,立法者所以将一些类型化的行为抽象地规定于刑法规范中,是因为大量的事实证明,具备一定条件的行为人,在一定的心理状态下实施的一定行为,造成一定的结果往往侵害了法益,这些行为才被立法所禁止。典型事实蕴含着价值评价的因素。之所以强调要在价值评价之前进行典型事实的判断,一方面是为广大民众提供一个可资效法的行为规范,另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为司法者进行刑法的价值评价提供明确的标准。既然行为符合典型事实,可以推定行为具有形式的刑事违法性,那么为何不将二者合而为一,将两要件——典型事实和刑事违法性直接表述为形式的刑事违法性和实质的刑事违法性?这是因为典型事实判断相对价值评价具有明确性和直观的特点。典型事实判断由于给司法者提供了一套完全客观化的标准,对于某一特定行为是否符合典型事实,司法者可以很容易的进行判断,不必在进行事实判断时还要考量这些事实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意义。典型事实作为刑法上犯罪行为的载体,作为一个前定性的标准已经确定,司法者只需判断其有或无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推导出这种行为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评价的结果。
由于典型事实是刑事违法类型,所以典型事实的要素原则上也是刑事违法要素。只是刑事违法性评价和典型事实符合性的判断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价值评价,而后者是事实判断。与典型事实的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相对应,刑事违法要素也包括客观的刑事违法要素和主观的刑事违法要素。具体包括:第一,客观的刑事违法要素。包括刑事违法主体,即是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实施一定的刑事违法行为,并造成一定刑事违法结果的行为人 (其中不包括对特殊身份的规定),刑事违法行为主要是指危害行为的时、地、行为的方法、手段以及行为的强度、行为的对象、行为的结果等。第二,主观的刑事违法要素。包括刑事违法的故意和刑事违法的过失以及动机、目的等。①刑事违法要素和典型事实要素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包含价值评价的因素,而后者没有。例如:刑事违法要素中的故意,可以理解为罪过,而典型事实要素中的故意就仅仅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故意”;刑事违法要素中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为是“危害行为”,而典型事实要素中的行为仅仅是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身体动静等。
(2)实质的刑事违法性评价。因为典型事实具有标识犯罪的功能,司法者如果对符合典型事实判断的行为作出其具有形式的刑事违法性的评价,就可以原则上推定其具有实质的刑事违法性。而且通常情况下,形式的刑事违法性和实质的刑事违法性往往是统一的,具有形式的刑事违法性行为也具有实质的刑事违法性。形式的刑事违法性和实质的刑事违法性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冲突,和不一致的情形,法定的阻却违法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即属此类。这一类行为虽然符合典型事实的判断,但就其实质来看,并未造成法益侵害的后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对法益的一种保护,同时,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和成文法所具有的内在缺陷而不能将所有符合典型事实判断,但在实质上并未侵害法益的行为全部包含在内的缘故,还有一些行为也有必要排除其于刑事违法性之外。为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实现刑法的公正,笔者认为,在形式的刑事违法性评价之后,有必要再对行为的实质的刑事违法性作进一步评价,从而将上述这些行为排除于刑事违法性之外。
和形式的刑事违法性的评价以积极的评价方式进行不同,实质的刑事违法性评价是以消极的方式进行的,对于具有形式的刑事违法性的行为,只需判断其是否具有一些特殊的情形。如果具有此类情形,就可以排除其法益侵害性,从而阻却其刑事违法性,行为也就不能构成犯罪。具体而言,进行实质的刑事违法性评价主要考虑以下阻却刑事违法的事由:
首先是法定的阻却刑事违法事由,包括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其次是超法规的阻却刑事违法事由,包括第一,正当业务行为。第二,被害人的承诺。其他如自救行为和自损行为等。
除此之外,司法实践中还有其它超法规的阻却刑事违法性事由。主要有以下两种:首先,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表面上看,这一类行为虽然在刑法中有明文规定,似乎是法定的阻却刑事违法事由,但刑法终归没有对其设立具体的行为类型标准。在具体判断时,还要司法者根据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而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的指导原则,对各种具体的行为进行判断。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其作为超法规的阻却刑事违法性事由看待。其次,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阻却刑事违法性的行为,所谓缺乏期待可能性的行为,在大陆法系是作为责任要件的消极因素,在行为具有违法性的前提下,通过阻却行为人的责任而阻却犯罪成立的,由于本文将刑事违法性界定为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概念,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又由于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对期待可能性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出现了以之为阻却犯罪的因素的实际情况,笔者倾向于将其纳入实质的刑事违法性评价中来讨论。
由于提出超法规的阻却刑事违法事由,有人担心会不会和罪刑法定原则发生冲突——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超法规阻却刑事违法事由的提出有其合理性,首先,因为成文法本身的缺陷,立法者不可能将所有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尽数规定于刑法条文中,有些行为虽然符合了典型事实,形式上也具有刑事违法性,但究其实质,并未和保护法益的刑法目标发生冲突,这也从侧面证明形式的刑事违法性和实质的刑事违法性也存在冲突和不一致的地方,所以才强调要在形式的刑事违法性评价之后对其实质的刑事违法性进行评价,以实现刑法公正。其次,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在于保障人权,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也正是为了防止司法官擅断和任意入罪而提出的,而超法规阻却刑事违法事由是犯罪成立的限定因素,换句话说,只会出罪,不可能入罪。其实质上是对国家刑罚权的一种限制,超法规阻却刑事违法事由不仅不和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相反,它和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1]休谟.人性论 [M].吴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储槐植.美国刑法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周光权.事实与价值之间 [A].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二○○二年年会论文汇集 [C].西安: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学院,2002.
[4]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5]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 [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6]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7]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8]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林 衍
A bstract:First fact judgment and then value evaluation is a common way for people to know something.The mode of cr ime elements in Chin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tic nature and integrity.The simultaneous conduction of fact judgment and value evaluation will bringmany drawbacks.Constructing a mode of two elements and dual layer can overcome the drawbacks and ensure the functional realization of criminal law.
Key w ords:fact judgment;value evaluation;typical fact element;criminal illegality element
On Two Elements and DualLayer Crine ElementsM ode
L iu Jian
(Hena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w,Zhengzhou 450002,China)
DF611
A
1009-3745(2010)01-0028-07
2009-12-23
刘剑 (1972-),男,河南固始人,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讲师,从事中国刑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