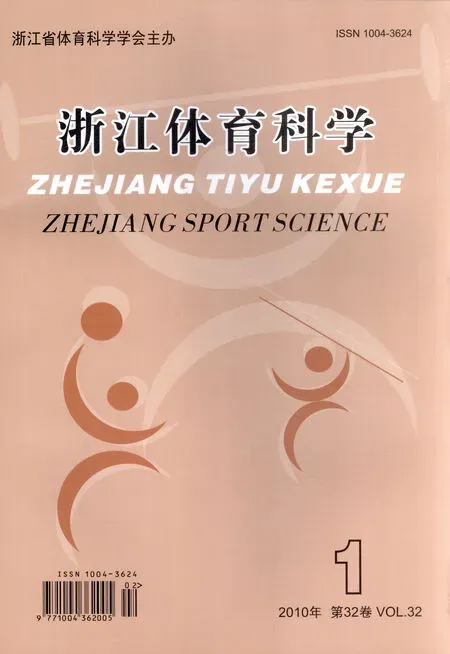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战争隐喻对现代竞技体育的影响
赵旻燕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0028)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战争隐喻对现代竞技体育的影响
赵旻燕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0028)
认知语言学认为言语交际与思维、行事是基于同一概念系统的。体育比赛言谈中存在着的大量战争隐喻,对人们如何看待体育比赛,如何进行体育比赛,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隐喻是一把双刃剑,在凸显事物某一特性的同时,遮蔽其它特性;在通过为人们熟悉的、较为容易把握的始源域来体验为人们不熟悉的、较难把握的目标域的同时,将始源域的某些因素强加于目标域。文章希望对体育比赛中战争隐喻工作机制的剖析,能够使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反思现代竞技体育。
概念隐喻;“体育比赛即战争”;映射
战争对体育比赛有着深远的影响,大多数研究都是从体育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的[1]。体育比赛话语中,无论是人们的日常言谈也好,媒体报道也好,充斥着大量的战争隐喻。概念隐喻“体育比赛即战争”如何影响竞技体育?文章的目的就是要从分析隐喻的工作机制入手,为战争隐喻的过分使用如何对现代竞技体育造成负面影响找到语言学上的证据。
1 概念隐喻“体育比赛即战争”
在开始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关于体育比赛的话语。
①鲁京战前瞻:鲁能期待雪耻国安难复制“屠杀”。
②面对韩鹏和李金羽组成的豪华锋线,他们能否抵挡是个疑问。
③刘翔“因伤”小组赛就宣布退赛,逃兵行径遭全国鄙视。
④全场比赛只看到科比凭借一己之力对抗火箭众将。
⑤阿布的异军突起让湖人内外线手忙脚乱。
上述这些话中黑体部分都是隐喻。在传统语言学中隐喻被看成是一种修辞手段,但是近年来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其研究已经从语言层面步入了认知领域。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手段,更是深层的认知机制。它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日常推理、想象、创造等诸多活动中,其认知性在于它能够组织人们的思想,是人们思维、行为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的方式。语言中纷繁复杂的隐喻来自于人们概念体系中的隐喻。像上面这些看似杂乱无序的隐喻句子,其实背后是同一个概念体系,这里体现着“体育比赛即战争”这样一个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
隐喻的本质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它是我们探索、描绘、理解和解释事物的有力工具[2]。隐喻中的两类事物涉及两个概念领域,“始源域”(source domain)和“目标域”(target domain)。始源域中一些为人们所熟悉的、有形的概念被用来构建目标域中较为抽象的概念,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目标域的隐喻概念体系。在“体育比赛即战争”这个概念隐喻中,“战争”为始源域,“体育比赛”为目标域。像③这个句子中,始源域“战争”中的“逃兵”被用来描述目标域“体育比赛”中的“退赛运动员”。这一隐喻过程完成了从始源域“战争”到目标域“体育比赛”的映射。
概念隐喻对人们认知目标域概念起着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体育比赛这个概念体系与战争概念体系之间的隐喻关系使得我们能够用认识战争的方式去认识体育比赛。实际上,我们不但用战争术语来谈论体育,我们还通过战争来理解体育,当我们进行体育比赛时,也会将体育比赛当成战争看待:比赛双方互为敌手;教练员为帅,运动员为将;打败对手称斩杀;比赛失利添仇恨等等。总之,概念隐喻“体育比赛即战争”帮助我们谈论、理解和构建体育比赛这一概念。
有关体育比赛的隐喻中,始源域除了上面介绍的“战争”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如:“搜狐启动奥运版奉上奥运饕餮盛宴”这个句子的始源域是“食物”;F1中国站六年来首遇寒流”的始源域是“天气”。有人收集了各种体育比赛隐喻语料,并参考eignan对始源域的分类,列出了各种“始源域”(包括人体、动物、天气、战争等)到目标域“体育比赛”的隐喻[3]。这些隐喻都是将一个较为具体、内在结构清晰的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体育比赛上,帮助我们把握“体育比赛”这一概念。所有这些关于体育比赛的概念隐喻共同构成一个和谐一致的网络体系,使得我们对体育比赛有一个系统完整的了解。然而这些概念隐喻比例并不均衡。有人做过统计,“体育比赛即战争”在所有的体育比赛隐喻中很明显地占有最大比重[3]。我们知道,隐喻在本质上是认知性的,语言层面上的隐喻表达是我们了解人类认知的重要线索。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体育比赛即战争”这一概念隐喻在人们的概念体系中最为凸显,也就是说人们在想到体育比赛时,往往会将它同战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其它的什么。
2 过分使用战争隐喻的弊端
用描写战争的语言来描写体育比赛,固然能够丰富体育比赛语言,增添紧张气氛,调动人们的情绪,使比赛更加惊心动魄。但是如果我们对隐喻的工作机制作进一步地深入探讨的话,战争隐喻对人们关于体育比赛的思维和行动造成的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与反思。因为隐喻意义的产生要在凸显始源域和目标域相似性基础上,完成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而这一过程在实现了隐喻最基本的认知功能——通过始源域的经验来理解目标域——的同时,无可避免地会对目标域造成某种反作用。
2.1 任何隐喻都是跛足的——体育比赛并非只是战争
“任何隐喻都是跛足的”,这是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隐喻只能在一个特定方面作些说明,不可能面面俱到。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隐喻的工作机制就是通过凸显始源域和目标域事物的相似性,来揭示目标域事物特征。目标域事物的某一特征,只有得到认知凸显,和始源域事物某一特征建立了相似联系,才能进入人们的视线,隐喻也才能得以形成。但是,正如束定芳[4]曾指出,所谓相似,其实只是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点的部分相似。而所谓凸显,则是指对语言所传达信息的取舍和安排[5]。由此可见,目标域事物的某一个特征通过隐喻得到凸显,成为注意的焦点的同时,意味着其他特征就会被舍弃,受到抑制[6]。因此,在选择事物某特征作为相似性时,必然会舍弃其它特征。正如束定芳[7]所说“隐喻是一种日食”,而“日食”的主要特征是“部分区域明亮,部分区域黑暗”,这形象地揭示出隐喻在凸显目标域和始源域的相似性必然会以遮蔽其它特性为代价。
我们知道每一个事物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都有着丰富的特性,这些要通过不同的角度表现出来。就拿“体育比赛”来说,从战争角度看,具有激烈的对抗性和竞争性;从人文的角度看,体育比赛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和生命的维护、追求和关切;从体育比赛结果的偶然性来看,体育比赛如同天气,充满了许多风云变幻的未知因素……换言之,“体育比赛”具有不同的侧面。有关体育比赛的不同的隐喻就起到了对其不同侧面的凸显作用。当某一侧面被某一隐喻激活,得到凸显时,其他侧面则处于被抑制或休眠状态。通过“体育比赛即战争”这一隐喻,我们固然能够借助对战争的认知,来更好地认识体育比赛激烈的对抗和竞争。但是,当体育比赛的这一个侧面获得凸显,成为注意的焦点后,其他侧面便会从我们视野中淡出。不同隐喻带有不同的倾向性,传递出不同的信息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战争隐喻在体育比赛言语中占有如此大的比重,引导我们看到更多的,无疑是体育比赛和战争之间的相似性——激烈的对抗性和竞争性,以及只能有一个赢者的排他性。我们有理由担心过分地强调体育比赛和战争之间的相似性会影响到我们对体育比赛其它方面的认识。而实际上,战争隐喻在体育比赛中占据如此大的比重,加深了我们的这种担心。“体育比赛即战争”这一概念隐喻只是帮助我们把握体育比赛这一十分丰富的概念的一部分内容,要全面完整地理解“体育比赛”,不能忽视其它的方面,例如体育比赛的人文精神等。体育比赛绝不仅仅是争夺输赢,它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方面。如果光看到它和战争的相似性,而看不到其它方面,那么体育比赛将变得越来越狭隘,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早晚会迷失方向。
2.2 隐喻映射的强加性——体育比赛不能承受之重
隐喻通过跨域映射,为我们提供看待事物的新视角,赋予日常活动以新的意义,但同时,不可避免地把一些原本属于甲事物的特征强加到乙事物上面,并且,这种强加的特征因为隐喻的反复使用而成为约定俗成的东西,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事实。
那么,人们所了解的体育比赛究竟有多少是它本来面目,又有多少是战争隐喻强加的呢?我们希望通过深入分析隐喻的映射机制,来说明人们所认识的体育比赛,有些不过是战争隐喻创造出来强加给体育比赛的,要想还体育比赛以本真面目,不能忽略战争隐喻对它的改造。
Lakoff指出,隐喻是一种概念映射(conceptual mapping),它不存在于词,也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仅存在于人们的思维当中,而隐喻的意义肯定与思维相关,它是人的思维将一种新的意义强加于目标域[8]。隐喻的跨域映射包括始源域图式中的空位(slot)、关系、特征及知识被映射到目标域上。这意味着,隐喻映射使得我们能够为一个原来不存在的概念结构提供结构[7]。通过借助始源域的结构,目标域的结构能为人们所认知。而我们对某一领域的知识使得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推理。此外,我们还可以借用对始源域事物评价的方法来评价目标域的事物。最后,隐喻渗透进我们的意识形态,当人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隐喻就成为现实了。
我们通过刘翔退赛事件来看看,战争隐喻是如何将战争领域的东西强加给体育比赛,并且成为人们接受的现实。首先,在隐喻中,有些情况下,目标域中的某些空位是原本就存在,不依赖于隐喻映射的。例如,与战争领域的“帅”相对应,体育比赛领域存在着“教练”这一空位。而有些空位是通过隐喻的映射过程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目标域中原本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例如将战争领域中的“逃兵”映射到体育比赛领域,意味着我们必须把临时退出比赛的运动员理解为逃兵,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在体育比赛这一领域创造出“赛场上的逃兵”这一空位。战争中逃兵背叛国家,这种关系映射到目标域体育比赛上,赛场上的逃兵也是有负于其背后的国家或支持者;而逃兵的特征贪生怕死映射到目标域,临时退出比赛的运动员也是胆小懦弱的。
当某一领域作为隐喻映射的始源域时,该领域的推理模式也被映射到目标域。也就是说,隐喻可以使我们借用始源域的推理模式在目标域进行推理。因为是战争,就有了一个敌人,威胁国家安全,因此需要确定目标,号召作出牺牲。而战争中不愿作出牺牲,临阵退缩的人就是不顾国家安全,是逃兵,是可耻的,应该受到谴责惩罚。如果在战争和体育比赛两者之间建立了映射关系,那么始源域战争中的逃兵被映射到目标域体育比赛上,体育比赛中退出比赛的运动员就是背叛国家利益的逃兵,也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按照战争领域的逻辑,刘翔退出比赛就对不起国家,就是逃兵。我们在谷歌输入“刘翔”和“逃兵”,居然搜查42 800条结果,隐喻创造出来的真实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战争中的逃兵是可耻的,应该遭到鄙弃。我们如果将战争领域中的这套评价方式应用到体育比赛,那么网上那么多人对刘翔退出奥运比赛所反应出来的谴责和叫嚣声一片,就不足为奇了。刘翔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谴责,就是因为人们把体育比赛看成了战争。
最后,隐喻会渗透进我们的意识形态,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指导我们看待和了解世界的方式,但是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因为一个隐喻在最初产生时能给人强烈的新鲜感,其字面义和隐喻义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若通过无数次的反复使用和联想,这些隐喻已经固定下来成为“死隐喻”(dead metaphor)或者说“常规隐喻”(conventional metaphor),人们在使用这样的隐喻时,往往意识不到其始源域的意义。像“进攻”“防守”这样表达方式早已是习惯成自然的常规用法了,谁还会想到体育比赛中的这些词汇本来应该是用来描写战争的。以一个概念隐喻为基础,可以构造出一件真实的东西,并且被大众想当然地理解和接受。正如lakoff声称“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真实和个人经验中的很大一部分真实都是通过规约性的概念隐喻被构造和理解的[9]。”可以这么说,人们所认为的现实可以是隐喻实现的。对于上一代人而言是某个隐喻制造出来的新的对应关系,在下一代人那里很可能被当作该隐喻的经验基础而被接受了[9]。由于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对它们毫无戒心,根本意识不到其隐喻性。这样,隐喻更具杀伤力。因为一旦隐喻渗透进我们的意识形态,就会成为 Fairclough所说的“常情假定”(commonsense assumption)[10],潜在地塑造和支配着人们的言语交际习俗。对这样的隐喻人们一般总是会照单全收,而不会对它进行反思,无法意识到其中的抵牾。
战争隐喻在体育比赛言谈中泛滥,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个概念隐喻一旦建立起来,为语言使用者广泛接受,那么它就会通过在生活经验中制造新的对应关系,将自身的结构强加于现实生活,从而得以实现[11]。当战争隐喻成为体育比赛表达中的死隐喻时,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体育就成为战争了。这样,体育比赛会被注入更多战争的元素:战争的功利性,使得现代竞技体育为了输赢,可以不顾一切——运动员沦为工具,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高强度的训练,轻伤不下火线,甚至服用兴奋剂,作弊等以取得形式上的成功;浸润在战争意识形态中,体育比赛因缺乏世界视野的人文关怀,无法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陷入暴力、仇恨的泥潭。当体育比赛失掉对竞技本身的关注,承载起了太多本应由战争承载的东西时,体育就成为了我们不能承受之重。如此看来,战争隐喻对体育比赛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成为危害竞技体育健康、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3 余论——人文精神吹散战争硝烟
那么,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方向在哪里?把体育比赛看作战争,输赢高于一切,只会使竞技体育逐渐被异化,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偏离其产生时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宗旨。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回归体育比赛最初对人文的追求。我们认为,只有在人文精神的指引下,体育比赛才不至于迷失方向,才会变得更“纯粹”。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文章对此进行探讨。
[1] 刘嘉丽.体育与战争关系浅析——体育人类学的视角[J].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2005(4):31-33.
[2] Lakoff,G&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0:10.
[3] 程浩.汉英体育语言中隐喻认知的对比研究[J].外语研究,2005(6):29-34.
[4] 束定芳.隐喻和换喻的差别与联系[J].外国语,2004(3):26-34.
[5] Ungerer,F.&H.J.Schmid.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1996:F38.
[6] Deane,P.D.Grammar in Mind and Brain: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Syntax[M].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92:183.
[7]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33,138.
[8] Lakoff,G.Cognitive Linguistics:What It Means and Where It Is Going[J].外国语,2005(2):8-9.
[9] Lakoff,G.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In A.Ortony(ed.),metaphor and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244,241.
[10] Norman,Fairclough.Language and Power[M].London and NewYork:Longman,1989.
[11] 蓝纯.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120.
Reflection on Mordern Competitive Sports from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ZHAO Min-y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Cognition,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China)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language comunication is based on the same conceptual system as mind and act.In view of this,war metaphors in sports game discourse has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in ways of thinking and behaving in sports games.Yet,like a double-edged sword,metaphors,while profiling one property,hide others.Although they make it possibl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target domain,which is unfamiliar and intangible,in terms of the source domain,which is familiar to us and easy to handle,they impose some elements of the source domain on the target domain.We hope that through probing working mechanism of the war metaphor,we may reflect on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 in a new approach.
conceptual metaphor;Sports Games Are Wars;mapping
G80-05
A
1004-3624(2010)01-0004-03
2009-09-23
赵旻燕(1979-),女,江苏张家港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