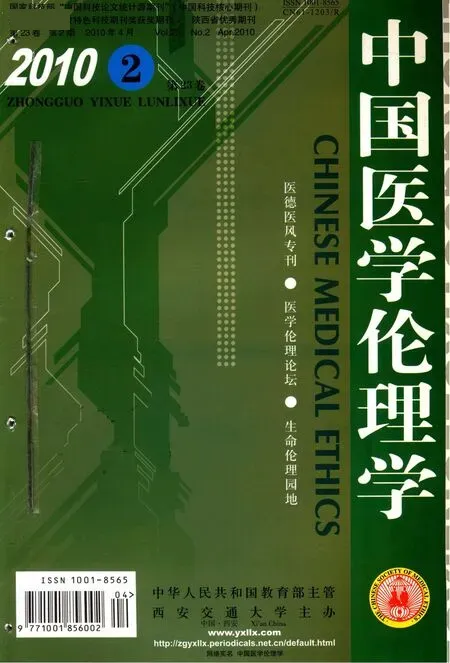军医伦理学视域下生命伦理问题研究
常运立,杨 放,杜 萍,杨 威
(第二军医大学人文社科部,上海 200433)
1 军医伦理学的兴起与发展
1.1 军医伦理学的源起
军医伦理学的研究源于对二战中日军和德军军医道德扭曲的伦理反思,[1]《日内瓦公约》和《纽伦堡法典》奠定了军医伦理学发展的基石。20世纪 70年代以 Danies和 Howe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开始关注军医这一特殊群体的职业道德与普通医生职业道德的区别,军医双重身份的伦理困惑被首次提出。[2-3]冷战后,非传统战争的发展向战场医学的“中立”原则提出了严重挑战。特别是“9◦11”之后,新的反恐战争引发的关塔那摩监狱和阿布格莱布监狱军医参与的虐囚事件,激起了国际社会和医学界的强烈反响,掀起了对军医伦理讨论的热潮。此后,军医伦理学在西方骤然成为显学,并正经历着激烈的争论。为应对现实需求,2003年美军卫生部办公室、沃尔特里德军事医学中心的波尔登协会、国防科大联合出版了《军事医学伦理学》(Military Medical Ethics),[4]此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军军医伦理学无论在理论体系的探索上还是在现实问题的解析上都日臻成熟。
国内对军医伦理学的研究兴起于 20世纪 80年代,1988年郭照江教授率先提出“军医伦理学”的概念。[5]不同于生命伦理学源于国外,军医伦理学在我国具有本土生成性。这种本土生成性也充分体现了异质文化下的伦理差异,如国内军医伦理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注重对军医的道德塑造,而疏于对伦理困境的道德剖析;注重道德原则的规范,而疏于不同境遇的伦理抉择。由此也不难发现,国内第一部军医伦理学著作缘何称之为《军队医德学》(1996年)。书中首次表述了我军医德的基本原则:“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军民健康服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6]在发展军医伦理学的同时,军内学者对生命伦理学也进行了深入研究,2008年 9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生命伦理学》一书,是军内学者对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第一部系统著作。[7]
1.2 军医伦理学的结构
军医伦理学自产生之时,就存在“是否需要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之争。[8]有一种观点认为,军医伦理学只是医学伦理学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医学伦理学为军医伦理学提供了理论依托,军医只需依据现有的医学伦理原则对自己的道德行为作出判断与选择,因此军医伦理学研究也只需关注现实问题和热点追踪。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医学伦理学还是军事伦理学,都不能为军医提供明确和充分的价值判定,军医伦理学应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基础,应依据道德哲学建构军医伦理学的理论体系。[9]我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军医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必不可少,无论其理论直接建构于道德哲学之上还是来源于医学伦理学,军医伦理学要想关注现实就必须发展理论,缺乏理论的现实研究是空洞、匮乏的,不断地进行本体的追问和哲学的反思才是军医伦理学赖以生成之根本。依此,笔者认为军医伦理学的研究可以区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2.1 军医伦理学的理论研究
探求军医伦理学的本源,要厘清其与医学伦理学和军事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明晰其道德哲学基础、学术思想渊源、发展史;要建构军医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包括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范畴;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军医伦理的普适性,不同文化背景下传统、宗教、民族、风俗、社会影响对军医伦理造成的差异性;要研究军医个体的道德角色、道德情感、道德责任和道德冲突,研究伤病员个体的生命质量和生命意义。
1.2.2 战争行动中的军医伦理
这方面研究战地伤员救治伦理,实现战斗力的优化与再生;战地类选的可适性和理论依据;医疗资源严重匮乏情况下战俘的医疗保障;参与战俘审讯时军医的道德良知和职业操守;战场伤亡中器官来源与器官移植;不可逆死亡征兆时战地安乐死的实施;现代战争中平民伤亡与平民救治;生化恐怖、生化威胁日益加重的情况下防生化疫苗的合理化使用;战场恐慌引起的非正常应激相关伦理问题;对与康复医学相关的脑外伤综合征患者的道德责任;战争造成的生态失衡对生命健康的危害和生态伦理。
1.2.3 非战争行动中的军医伦理
这方面包括灾害医学救治中军医的道德责任和道德要求,军医所应遵守的伦理原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军医与病人的权利之争,病人的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国际医疗援助中军医行动的公正性与公平性,医学活动的政治无涉与军事行动的利益驱动;反恐行动中军医的道德角色,恐怖分子的医疗权利;军事医学科研中军医的道德规诫和道德监督,实验时的伦理审查和受试者的知情同意。
2 生命伦理在军事领域中的生成性分析
2.1 实践基础:生物技术在军事领域内的应用
生物技术和生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可分为医学领域和非医学领域两大方面。医学方面主要包括药物、疫苗、快速诊断方法、野战急救技术等,对挽救战场生命、提高战场生存能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非医学领域中的应用则主要用于武器装备的开发与研制。生物技术与其他科学技术一样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惨痛的灾难。高技术不断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及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克隆技术研究的迅猛发展,促使一些国家在生物武器的基础上,提出发展杀伤力更强的基因武器的计划。随着生化武器和基因武器的出现,防生化污染疫苗的研制与使用成为各国刻不容缓的课题,然而疫苗使用并非简单之事。如对“海湾战争综合症”的研究表明,可能涉及疫苗使用不当问题,这无疑向我们敲响了疫苗使用的警钟。由此可见,缺乏伦理规训的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可怕的,生命科学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有效的伦理保障,生命科学家在作出事实判断的同时必须明析相应的道德判断。
2.2 理论探询:生命本体追问和医学人道反思
军事行动中的道德思索无疑是发人深省的,也是更为复杂的,这一思索过程充满着对医者的道德追问和伦理反思。首先,在军事活动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存。战场中,极易出现工具理性的凸显和价值理性的缺失,这是因为军队是国家机器,战斗员只是这个机器的有机构成要素,为了战斗目的的达成,必要时战斗员必须放弃其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所应享有的多种权利,如最基本的生存权、医疗权和自主权,而作为作战系统的一分子服从整体需求。战场中,工具理性的存在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然而,人毕竟是目的性的,人的目的性的存在才使人生而为人,人的价值理性的存在要求我们要尊重他人。其次,在军事医学行动中医学人道与国家利益并存。以关心、同情、救治病人为中心的医学道德的基本信条是医学人道,它是人类最基本的愿望也是医学的基本任务,是人类在几千年医疗实践中形成的珍贵的医德瑰宝。而军事行动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和捍卫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军事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牺牲个人利益获取国家利益是军事活动本身所固有的属性。然而国家利益并不等同于国家公正,如将国家利益置于国家公正之上,以人道为宗旨的医学事业势必成为罪恶行径的帮凶。另外,国家利益的获取也并不可以无原则、无限制地牺牲个人利益,在战场医学活动中,以国家利益为由而任意违背作战人员的医疗权利有违人道之根本。
3 军医伦理学对生命伦理的关注域
3.1 战地安乐死
面对死亡,战地安乐死成为军医伦理学的重要话题。探求战地安乐死是直面死亡时的理性回顾,这是因为战地安乐死是战争境遇中无法回避,也不容回避的问题。战争造就了大量不能迅速死亡但也毫无生还希望的伤病员,为摆脱痛苦和可能的潜在威胁,伤病员和指挥员心中就萌生了加速死亡的想法,这就是战地安乐死的最初雏形。对战地安乐死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战场上有限的医疗资源必须发挥其最大效能,以服从和服务于军事需求,与其将紧缺的医疗资源用于延长不可逆死亡者的死亡过程,不如将其用于救治轻伤员,以实现战斗力的再生。再者,战场的紧急态势也不可能给予伤病员平时所能享有的临终关怀,无谓地延长其生命,只能增加死亡的痛苦。反对者则认为,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生命的尊重推动了医学人道主义的发展,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珍视生命、为挽救生命而尽心尽力是每名医生行医的基本准则。另外,即使实施战地安乐死,在战场上也很难做到知情同意,而安乐死的实施需要规范的程序做保障,战争境遇使其很难得到有效的执行,且一旦作出决策其影响将是长远的,如将战地安乐死作为一项军事政策推广实施,很可能出现严重的“道德滑坡”。
3.2 战场器官移植
战场上器官移植对于恢复健全肢体、挽救战士生命具有重要的作用,日益成熟的器官移植技术,也使得生命的继承与延续充满无限希望。然而,战场上基于人的善良意志的器官移植活动,要朝合理化的方向发展却并不简单,围绕器官的获取、分配与使用的诸多伦理之争,需要战地医生保持清醒的道德良知和道德头脑。从刚刚死亡者身上摘取某一器官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方式,其作法是理智的,也已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同,并不会引起大的伦理争议,争论点多在于对脑死亡标准的确认与推定的同意上。而从死亡不可逆者身上采摘器官,虽然是获取活体器官的最佳方式,但是却最容易出现道德混乱和道德失衡。如何判定死亡之不可逆?能否做到和如何实现知情同意?何时可以采摘器官?以何种方式采摘器官等等,诸多问题无不需要军医慎思、笃行。对于战俘,强烈的敌视情节很容易使其成为潜在的器官来源,此时,如没有坚定的职业操守,为了己方伤者的利益,很容易冲破道德底线,侵犯甚至剥夺战俘的生命权。另外,对于器官的分配与使用:谁可以优先得到器官,是将军还是战士?由谁做出决定,是战场指挥员还是医生?依何标准判定,是医学标准还是社会标准?对此,无不需要作出认真的思考与审视。
3.3 军事医学科研
战后,对德军法西斯医生罪行的无情揭露促生了《纽伦堡法典》,奠定了人体实验的道德基石——人类自由的伦理学价值和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此后诞生的《赫尔辛基宣言》进一步规范了人体实验的伦理原则。将人视作非人,任意践踏和蹂躏,严重地背离了为医救人之初衷和“医乃仁术”之根本。另外,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思想也是引发人类灾难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维护伦理道德,医学应时常对民族主义和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名所作的各种主张加以审视。这个教训本身一点也不新,问题是人类是否会真正吸取这个教训。”[10]法西斯分子所进行的人体实验产生的震痛是长久的,对其反思也应该是深刻的。然而,时至今日,肆意剥夺受试者的基本权利,利用战士和平民开展的军事医学人体实验仍然受到一些国家的普遍推崇。如上世纪 90年代,美军沃尔特里德军事医学中心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开展的 E型肝炎实验,虽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但却受到军方的大力支持。[11]
3.4 疫苗使用
继 9◦11恐怖袭击后,2001年 10月,美国的 “炭疽邮件”事件再次掀起了生物恐怖的轩然大波。如何对核生化武器的杀伤进行有效的防护,与此相关的伦理问题时刻困扰着军医的选择,其中最难以处置的就是如何解决疫苗使用中的知情同意问题。首先,疫苗使用的真实效果难以知晓。任何药物研制最终都要通过人体实验后进入临床应用,但核生化疫苗却难以借助人体实验验证,这是因为将健康人员暴露于核生化武器威胁之下,以此检验防核生化药物或疫苗的实际效果很可能会造成大量的伤害与死亡,也严重违背了医学的初衷。第二,战场疫情并不明了,直接影响疫苗使用的选择性。战场情况是复杂多变的,敌方会使用何种生化武器难以预测,并且众多生化武器的致病机理并不十分确定。未来战争中,一旦 DNA重组技术应用于生物武器,造成何种疫情危害更是难以知晓。第三,战士对强行注射疫苗极为反感。以“个体防护”和“保存与储备战斗力”为由强行注射防生化疫苗,将严重地违背战士的自主权和同意权。第四,谁来为疫苗使用者的长期健康负责。由于缺乏临床记录,疫苗的功效也很难确定,从短期看也许具有很好的免疫能力,但从长期看是否对身体具有潜在的伤害难以知晓。
3.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就医者而言,军医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环境危险、条件艰苦、情况多变、处置困难,军医必须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必要时甚至要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就患者而言,公共卫生事件所涉及的不是单个生命的自身遭遇,不是如何处置生命个体的伦理困境或极端情况下的伦理抉择,而是涉及群体的生命。在面临公共健康威胁的情况下,生命群体与生命个体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各自应当遵循什么道德规范,这些规范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无疑应是军医伦理学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之一。
3.6 生态伦理
战争可以从基因到生态系统的各个层次上威胁生命的存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使用导致了不可估量的生态灾难。1961年至 1975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为消灭“丛林战士”,大量使用“落叶剂”毁灭森林,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战后几十年,“落叶剂”的影响还在延续,该地区的居民遗传疾病和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持续攀升。[12]关注生命就必须关注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关注生态的破坏对人类生命带来的危害。伦理学在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积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这是我们所应该积极倡导的生态伦理和生态观念。这种生态视角,代表着一种时代性的观念转折:从征服自然到敬畏生命,人们开始去认识大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人类的自然观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深刻转变。[13]以此反观现代战争,不管是用战争手段维护正义,还是用战争的手段夺人城池,都会产生一个非正义的结果,那就是对地球、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河流、湖泊、空气等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毁坏。生态伦理向人们提供了一种生存哲学和生存智慧,面对冲突,它将使我们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冲动;多一份包容,少一份厮杀;多一份关切,少一份战争。
[1]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militarymedical ethics[E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itary_medical_ethics.
[2] Danies A K.In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the psychiatristas double agent[J].Hastings Center Reports,1978,(supp1):3-6.
[3] Howe E G.Medical ethics:are they different for the military physician?[J].Military Medicine,1981,(146):837-841.
[4] Thomas E.Beam,MD.Military Meddical Ethics[M].Office of The Surgeon General Department of the Army,United Statesof America,2003.
[5] 郭照江.关于军医伦理学的若干问题[J].中国医学伦理学,1988,1(1):23.
[6] 陆增祺.军队医德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37.
[7] 杨放,张晨,仲向平.生命伦理学[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
[8] George J.Annas.Military Medical Ethics-Physician First,Last,Always[J].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08,11:1087-1090.
[9] Physicians Toward a Framework for Military Health Ethics[M].Springer Netherlands,2008:75-88.
[10]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Declear on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adopted by the 42nd World Medical Assembly Rancho Mirage,Calif: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1990.
[11] 聂精保,土屋贵志,李伦.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及其对当代医学伦理的挑战[J].医学与哲学,2005(6):37.
[12] Jason Andrews.U.S.Military Sponsored Vaccine Trials and La Resistance in Nepal[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2005,5(3):W1.
[13] 王亚洲.战争与生态破坏[J].现代军事,1998,(3):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