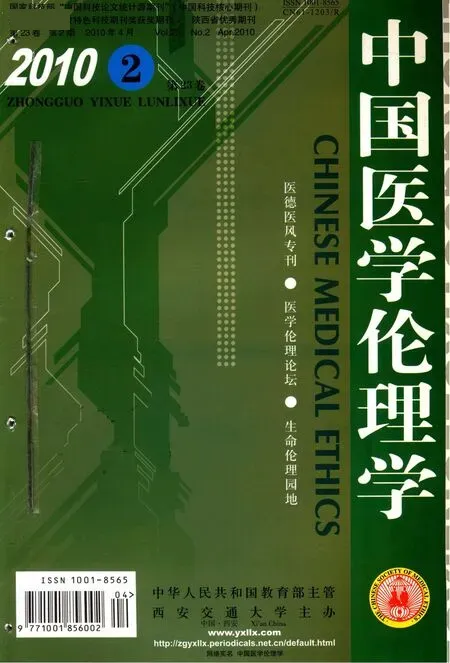患者知情同意落实难问题之原因分析*
张奥会,董玉整
(广州医学院,广东 广州 510182)
知情同意原则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存在流于形式的现象,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并未得到实质意义上的维护。因患者知情同意问题而引发的医疗纠纷层出不穷。
1 医疗父权主义影响
父权主义(Paternalism)来自拉丁语 pater,意思是指像父亲对孩子那样对待他人。[1]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医乃仁术”、“医者父母心”等医学伦理思想与父权主义亦是高度吻合的。当涉及一些特殊病种,如癌症等疾病时,医务人员和病人家属往往会“串通”起来对患者隐瞒或轻描淡写病情。[2]与此同时,无论是在法学界还是伦理学界对医务人员拥有医疗特权的高认可度是一贯的。[3]
除了深受医生父权式职业习惯的影响,患者知情同意权利意识低下还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是我国多年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一切经济行为甚至是就业、婚配都是“被”计划,听安排。其二,是中国人含蓄的性格特征因素。不愿标新立异,含蓄、内敛的性格特征,使得国人普遍倾向于对医生的安排言听计从,并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医生的尊敬。其三,是患者缺乏知情同意的权利意识,甚至会误将法律程序的知情同意书看作是医方推卸责任的“生死契约”。患者自身知情同意权利意识如此薄弱。[4]这种患者不充分知情的同意是非理性的、是出于对医生的依赖,甚至是慑于权威的同意,是不为患者所真正理解的,这为日后医疗事故演变为医疗纠纷埋下了隐患。
医疗父权主义同时也影响了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推广。目前,我国医学院校教育普遍存在重专业理论轻人文社科的现状,[5]导致部分医生伦理意识淡漠,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素养,对患者缺乏应有的同情心,漠视患者的疾苦、无视患者的正当权益。
医务人员的过度自我保护行为,使得患者感受不到医生发自内心的尊重。一旦发生医疗事故或是治疗效果没有达到病人的预期,甚至是医疗费用过“高”,不知情不理解的患者很可能会将之视作医生的“猫腻”行为所致,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医方。如果此时医生不能主动和患者沟通并作出充分的解释说明,患者便会由“变脸”发展到跟医生“翻脸”。这样不但有损医患关系的和谐,对医生信誉度影响也很大。
2 “家文化”的影响
“家文化”是指注重家庭关系协调,强调人与人之间血缘联系的文化。[6]“家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邃的文化内涵。“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国之本在家”足以看出“家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中国式的医学伦理学必定会被打上深重的“家文化”烙印。患者知情同意错位于为家属知情同意,自然就不难理解了。曾经就有因家属有意躲避手术签字,医生不理会孕妇的剖宫产请求,造成一尸两命的悲剧事件报道。[7]以“保大人还是保小孩”的知情同意条款为例,孕妇的丈夫掌握了对妻子生杀予夺的权利,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是对孕妇生命权的无情剥夺。如此种种家属知情同意优先于甚至是完全取代患者本人知情同意的现象,无疑是“家文化”的产物。
患者家属对知情同意拥有部分权利是合情合理的。首先,是出于患者自身的需要。当患者处在疾病状态,身心状况有可能对其判断力、理解力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没有家属的适当参与,很可能做出缺乏理性的选择;患者因为疾病原因没有知情同意的意愿,或是不希望知悉病情而影响心情,明确表示让其充分信任的家属代理知情同意,医务人员应该遵从患者意愿;患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患者家属作为患者的法定代理人,全程包办知情同意自是合理、合情、合法的。[8]其次,是从家属的利益诉求出发。不同费用的治疗方案或手术器材,家属和患者间,或家属与家属间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种情况需要患者和家属共同商议后知情选择。这是对家庭成员个人合法财产支配权的尊重,也是对家庭成员话语权的尊重,亦是家庭民主的体现。此外,涉及一些特殊的医疗行为,如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前提是患者配偶的知情同意;否则配偶一方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但是,将家属知情同意代替患者本人知情同意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因为毕竟患者本人才是其生命健康的权利人,家属只能算作是关系人。
3 卫生体制不健全的影响
3.1 医院的收入分配制度畸形
受市场经济论的影响,部分医务人员在自身经济利益和业务指标的双重压力下,极易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诱导患者,做出开大处方、重复检查或乱收费等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而真实、全面的信息告知会使得他们的这些有违医学伦理的行为暴露,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医务人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自身利益驱使下“选择性”做出损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行为并不难理解。[9]曾经就有医院医生为了锁定药品销售提成收入,处方单所用的药名居然是只有医院自家药房才能解密识别的代码。这种严重损害患者知情权的行为,迫使患者只能舍“平价药”买“高价药”。
3.2 卫生资源配置畸重畸轻
卫生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致使百姓对小地方小医院缺乏信任感,哪怕是患个普通感冒也会“花钱买放心”,这样就出现了“大医院门庭若市,小医院门可罗雀”、某专家号被爆炒至上千元、某专家预约已排到一年之后等怪现象。医生工作量超负荷,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对患者充分告知。身心俱疲的医生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实施知情同意,效果可想而知。
3.3 医疗卫生保障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医疗费用往往成为百姓生活的不能承受之重。城乡差距使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大病扛、小病拖”等现象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更是普遍。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致使多数人的养老和医疗都必须依赖家庭互助甚至是家族互助来实现。患者知情同意权必定要受制于其他家庭成员甚至是家族成员。
4 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4.1 法律制度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 26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家属介绍病情,但应当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师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属同意。”该法条中的“或”字为知情同意错位开了口子,有将患者知情同意等同为家属知情同意之嫌。容易导致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被别有用心的家属或是害怕发生医疗事故后患者家属闹事的医务人员剥夺。目前,实施的孕妇难产时由丈夫签署“保大人还是保小孩”知情同意书的制度就是对孕妇本人知情同意权的无情剥夺。此外,该法案对告知内容—— “病情”的规定太过笼统、模糊,缺乏实际的指导价值,在实践操作中不容易把握,[10]甚至容易被医方钻空子。且对违反告知义务的行为也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条例,医方违规的道德成本几乎为零。甚至出现了法规条例相矛盾的现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 31条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第 33条规定,医方在采取紧急治疗措施前也应把病人的情况告知患者或其亲属,必要时还要适当解释以帮助患方尽快做出决定。并要求医方施行手术前必须取得家属签字同意。[11]但是在很多临床紧急情况下医生是来不及取得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的。而相关的法律法规却并未明确指出特殊情况下,医务人员的紧急救治权优先于患者知情同意权,这也是类似肖志军悲剧之所以会发生的关键所在。
4.2 评价机制缺失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都明确规定了患者拥有知情同意权,但是对患者知情同意原则落实的真实情况及实际效果,却缺乏有效的评价机制。告知是否只是程序性、形式上的,是否存在“被”同意现象,这些都只能等到出了医疗事故被患者投诉或诉讼后,才能收到滞后的信息反馈。
4.3 监督机制缺位
目前,医院中高层管理职务多由技术骨干担任,其中鲜有伦理学专业背景的人员,在医院规章制度建立及日常管理过程中难免会缺乏伦理学视阈。同时,医院伦理委员会并没有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知情同意的落实只能寄希望于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良知。而一纸知情同意书与其说是知情同意原则的落实凭证,某种程度上还不如说是医方自我保护的免责凭证,这种知情同意不能反映法律所赋予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的真正内涵,甚至违背了立法的初衷。
[1] 陈麟,徐新娟.医事法学课程中对父权主义理论的批判与继承[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7,(12):69.
[2] 姚晚侠,李义,姚明.维护癌症患者知情同意权中伦理问题的质性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22(5):115.
[3] 张雪,孙福川.生命权、知情同意权和特殊干预权的冲突及衡平[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22(2):34.
[4] 朱卫中,吕伟超,吴小妹.实践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理原则的难题与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22(1):152.
[5] 孟宪志,王冰,刘连新.医学生的新挑战:医师职业精神与医患沟通[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22(1):81.
[6] 张英涛,孙福川.论知情同意的中国本土化[J].医学与哲学,2004,25(9):13.
[7] 方红丽,张桂青.“知情同意”实施难原因研究综述[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19(2):55.
[8] 丁春艳.由谁来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患者还是家属?[J].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14(1):33-34.
[9] 赵西巨.从美国 Moore案看对人体组织提供者的法律保护[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2(1):33.
[10] 殷冀锋.我国病患知情同意权利的立法审视[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21(5):140.
[11] 任丽明,刘俊荣.试论患者紧急救治权与知情同意权的冲突与化解[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21(5):58-59.